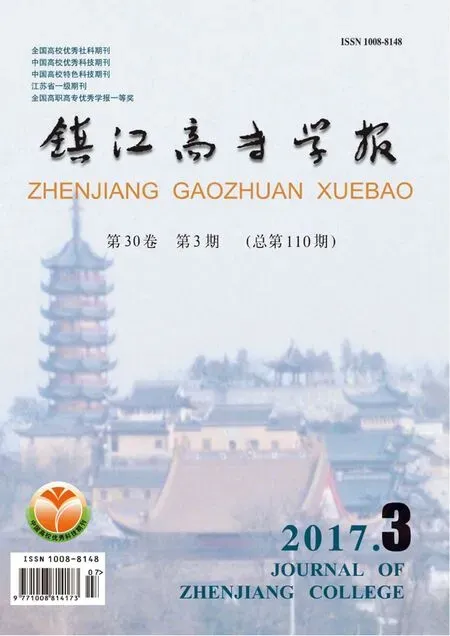“互联网+”背景下法学教育中隐性知识的挑战及其回应
牛玉兵
(江苏大学 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互联网+”背景下法学教育中隐性知识的挑战及其回应
牛玉兵
(江苏大学 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鉴于隐性知识对于法学教育的重要作用,互联网时代的法学教育需直面隐性知识的挑战。重申法学教育的目的、把握知识转移的一般规律、创新隐性知识传承的具体方法、选择适合于隐性知识特性的网络教学技术,是“互联网+法学教育”时代认真对待隐性知识的可能路径。
互联网+;法学教育;隐性知识;显性知识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包括法学在内的教育活动带来了深刻变革。远程教育(remote education)、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数字学习(e-learning)等学习模式以及微课(micro-course)、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网络公开课等课程形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正在逐渐打破传统法学教育在时间与空间、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然而,在互联网所带来的一场场光彩炫目的知识盛宴中,本应成为法学教育重要内容的“隐性知识”,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此种现象引发我们对“互联网+法学教育”进行反思,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隐性知识之于法学教育的作用,探讨互联网时代法学隐性知识面临的挑战,寻求适应于网络时代法学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传承的可能路径。这对于正确认识“互联网+”时代的法学教育变革,厘清互联网在法学教育中的效用边界,促使技术创新充分助益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这一国家法律教育目标的实现,无疑具有显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 隐性知识之于法学教育的作用
隐性知识,又称默会知识、缄默知识、内隐知识,是知识学对知识类型的重要分类。按照波兰尼的观点,隐性知识不同于那种可以用书面文字、符号、图表、公式等加以表述的显性知识,它隐藏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通常也不能用文字符号等形式完全编码并予以规范化的、系统化的表述[1]。日常生活中那些“日用而不知”“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的典型表现。由于“我们所认识的远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2],人类所拥有的隐性知识的丰富程度也就远超那些可言说的显性知识。
如在学术研究中,在法学教育领域隐性知识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确定问题、如何展开论证,往往和研究者个人所具有的隐性知识密不可分。坊间流传的《法学论文写作》等书籍或类似“秘籍”,其中就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作者学术思考与写作的内隐性心得。在法律实践中,隐性知识同样丰富。如在侦查讯问中,讯问人员如何配合、讯问策略如何选择、相关证据何时出示等知识就是依赖于侦查人员侦讯经验的内隐性知识。在现代诉讼制度下,以自由心证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在凸显裁判者认知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为与个体认知密切相关的隐性知识提供了可能的存在空间”[3]。案件裁判固然要受到明文法律规则的制约,但除此以外,“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所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4]。霍布斯由此得出的“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论断,假若经由隐性知识角度予以透视,或许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隐性知识在法学教育中存在的事实,这也向法学教育提出了要求。第一,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不可分割,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时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对学生而言,不仅应该学习和掌握那些记载于教科书或法律文本中的显性知识,而且应该学习体会与领悟那些法律信念、价值观、心智模式、阅读写作思维、实践操作技巧等隐性知识,如此形成的知识结构才足够完整。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由于任何显性知识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5],学生知识结构中隐性知识或许应占据更为基本的地位。整合、传承隐性知识,当然也就成为教师的职责所在。第二,法学教育中的知识创新离不开隐性知识。在法学教育中,教学过程参与者,尤其是教师个体隐性知识的外化、联结、组合、转换、传递,无疑就是法学知识从个体扩展到组织、从分散聚合为整体、从陈旧过渡到更新的发展过程。隐性知识之于法学知识创造的作用不容忽视。第三,隐性知识制约法学学生的综合能力。法学是技术性、实践性非常明显的学科。“法律学拥有着‘秘授不外传’的技术特征。为此,当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精通了这类技术后,就会有一种类似于习得了祖传密技的感觉。”[6]这种“密技”般的经验知识是构成学生综合能力的基础所在。那些在学校学业成绩优异但在工作岗位上却暂时未有出色绩效的学生,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其对法律制度等显性知识掌握得不好,而可能是因为他对于如何技术性地进行法律认知与实践操作的隐性知识储备不足。
正是由于隐性知识对于法学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在法学教育中努力实现隐性知识的整合、传承与创新,就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命题。在传统法律教育中,师徒制的教育模式是隐性知识传承的重要方式。黑德勒姆在《律师会所》中谈到,学徒们频繁地参加案例讲解、聚会、案例讨论、模拟审判和其他学习训练,在与教师和同伴的交流之中,获得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的各种知识[7]。隐性知识的获取无疑就隐藏在这种个体化的、面对面的教育中。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师徒制教育模式虽然已经为工厂式、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所取代,但隐性知识仍在师生之间得到传递。今天在我国法学院系中采用的本科学业导师、研究生导师制度为师生之间隐性知识的传承创造了条件。但不可忽视的是,相较于此前那种师徒式的“密技”知识传授所创造的亲密关系,现代教育中师生间的疏离感已经增加。那么,当互联网时代来临,教室有形的围墙被打破之后,法学教育中的隐性知识又会遭遇何种境遇呢?
2 “互联网+法学教育”中的隐性知识挑战
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技术向教育活动的蔓延同样引发人们对“互联网+法学教育”的乐观畅想。“‘互联网+’时代为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准备了丰富的资源。法律法规随时可以通过“度娘”寻找。法学教育课程也为适应这个时代而开发了大量的各个层次的网络精品视频课程。学生不但能看到自己的任课教师上传的视频,也能通过点击分享国内各高校优质的教学资源。电子期刊的建设和电子书库的存在,能让每个学生轻而易举地获得目不暇接的理论资源。案例检索平台的开启,不但能让学生获得大量的以往的案例,也能通过最新的裁判文书网获得最权威的和最新的案例。”[8]除此之外,师生交流的场所和方式也更为多样和便捷。“网络化的教室改变了授课的时空与资料的规模。法律课程的声音与文字资料(甚至图像)已经存在服务器中 ,服务器24小时开通,学生们在教室里或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上网学习。同时,他们同教师的‘提问与回答问题的对话’‘案例的讨论’也可以通过电子信箱或‘BBS’随时进行。”[9]这些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的法学教育场景,确实会让我们叹服于网络对法学教育的改造,也不禁为互联网时代法学知识传承的高效快捷而欢欣鼓舞。
然而,当我们以知识学的视角理性地看待互联网中的法学教育场景时,却不得不讶异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电脑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是以传播显性知识为主要特征的”[10]。那些能够进入网络之中被我们所学习和传承的法律条文、电子期刊、案例数据等,基本上是已经被编码的、较为系统的显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对应的那些更为鲜活的、丰富的隐性知识,在网络世界中基本上是默不作声的。
当然,在法学教育中以教学视频、录音等形式开展的网络课程,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教育者的隐性知识成分。但不应忽视的是,当隐性知识脱离了它所依附的知识主体而呈现为视频、录音等时,它们就已经获得了外化的载体,成为“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进而和依附于主体的隐性知识产生了距离,而且,隐性知识本身可以区分为“无意识的知识”“能够意识到但不能通过言语表达的知识”和“能够意识到且能够通过言语表达的知识”等不同层次[11]。当隐性知识尚处于未编码、未格式化状态时,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观察与体悟就成为隐性知识获取的重要方式。这样来看,那些法学网络教学中的视频和声音等知识载体,即使包含着隐性知识,也不可能是知识传授者隐性知识的全部内容,那些“无意识的知识”,或者“能够意识到但不能通过言语表达的知识”,在采用视频和声音加以固定并借助于网络流传的过程中仍然无法得到转移和传承。由于“言不尽意”表意局限的影响,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也就总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隐性知识的筛选与删减。因而,套用波兰尼的话,互联网中的法学隐性知识“被表述的远远少于实际存在的”。
至于那些采用了多重技术而实现师生同时在线交流的法学课程,它们在隐性知识传承方面无疑要较单独的视频或音频效果更好一些,这种方式虽打破了法学教学的空间阻碍,但师生之间仍可进行实时交流。这是互联网对于法学教育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虚拟场景中,我们所面对的仅仅是呈现于电脑屏幕上的人像,由此进行的交流毕竟与现实交流有所不同。在完全虚拟化的交往场景中,由于意义表达的时空距离基本消失,教育活动原本应该具有的社会情境限制也就被冲淡到几乎消失的地步。然而,隐性知识却是需要这种体验性情境的。“隐性知识总是与特定的情境紧密相联系的,它总是依托于特定情境而存在,是对特定的任务和情境的整体把握。”[12]当虚拟化的交流消除了隐性知识所需要的社会情境时,即使这样的交流中包含了隐性知识的传承,其效果也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无疑已经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悄无声息地来临了。其表现:第一,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法学教育中隐性知识传承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网络时代的法学教育又如何可以回避隐性知识这一命题?第二,从互联网时代法学教育实践看,显性知识越是容易获得,隐性知识传承的任务和压力反而越重。吴志攀教授在论及网络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时曾指出,“网络化教室发展后,教师不是以讲授法律知识为主,而是要将分析的经验教给学生”[9]。这里“分析的经验”,指向的正是法学教师的隐性知识。在法学教学实践中,那种教师刚论及某一法律制度,学生马上利用网络终端搜索到相关历史背景、法律规范、案例数据等的情景也并不少见。于是,传统教育中原本横亘于师生间的显性知识鸿沟,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消弭,而隐性知识的重要性则在这样的情境中与日俱增。第三,互联网时代知识高速传播所引发的个体法学知识分散化、碎片化趋势需要借助于隐性知识加以矫正。互联网时代,知识的供给已经呈现几何式增长,而快捷高效的数字化阅读则日渐占据了人们的零碎时间。然而,知识的数量爆炸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知识的体系化增生,快捷的数字化阅读带来的也许恰恰是知识的碎片化效果,这一点并非推测而是现实。今天,数字化阅读的流行已经使人们“对合理的文本长度的期待缩水了。短小文本格式(比如消息、短信、推特、手机的新闻APP,甚至手机小说等)的激增,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无闲暇时间用于较长时段的阅读。”*根据美国语言学者贝伦等人的研究,数字化的电子阅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由数字装备便捷功能而导致的分心以及专注性的丧失。南京大学周宪教授也谈到,在数字化阅读中,大学教师也越来越倾向于布置短小的在线读物(某些章节或文章),而不是整本书的阅读。“而有关文献引用的国外研究也证实,即使是学术阅读,也缺少持续聚焦的沉浸式阅读。读者往往只阅读一个文献的前三页,不再有耐心和需要通读全文。这项研究的统计学结果令人震惊:46%的引用只限于文献的第一页,23%的引用限于文献的第二页,77%的引用来自于文献的前三页。”参见周宪.喧嚣的数字时代,人类仍离不开孤独的深度阅读[EB/OL].[2017-03-02].http://www.1xuezhe.com/academic/detail?nid=283969&tabtype=2.这种现象既导致了网络学习专注性的削弱,也使得原本就已经碎片化的知识更为分散。法学隐性知识传承中所培养的专注、沉浸与忍耐的学习精神,隐性知识对于显性知识体系的整合作用,在这样的情境下无疑更显其珍贵。第四,互联网时代法律职业发展更依赖于隐性知识的供给。职业“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般的‘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有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13]。相对于其他职业,法律职业更是隐含着丰富的技巧与经验。柯克所谓“法律是一门艺术”的名言正是对法律职业技术性、实践性、经验性的写照。对于那些从事法律职业的人而言,隐性知识的获得正是他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此而言,正视互联网时代法学隐性知识的挑战,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及时更新隐性知识,也就成为网络时代法律人在职业发展上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
3 对“互联网+法学教育”隐性知识挑战的回应
当今时代的法学教育已经不可避免地嵌入互联网技术。然而,技术发展既可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导致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社会中技术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的哲学分析提醒我们,在“互联网+教育”大行其道的今天,法学教育对互联网的应用同样应避免被技术绑架和异化的命运。假如我们不能对此警醒,互联网时代的法学教育就真的可能自满于那些由显性知识构筑起来的无限超文本链接所造成的“知识繁荣”表象,沉迷于虚拟网络空间创造的师生交流的迅捷快感之中。在这样情境下开展的法学教育,也许就会沦落为一场场“热闹的假面舞会”,师生间的疏离则必然与知识的分裂相伴而生。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重申法学教育的目的。“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因为法律是社会组织的纤维,所以法律的事业,是公益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14]法律人才由此也就不仅要有认识法律、运用法律以及知晓法律是如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法律学问,而且也要有法律的道德与社会的常识。相对于这样的法律人才培养目的,法律隐性知识与法律显性知识无疑就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传授这种方法和技巧应该成为职业化或其他类型的法律教育的目的之一”[15]。这一点即使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也不应改变。因为,互联网固然提供了法律教育的新技术,但在“互联网+法学”的教育活动中,“技术根本不是一种预先确定的事物,而是一种环境,是一个教师必须栖居于其中并使其活跃动起来的空洞的空间。教师与技术有一种职业关系,而不是与一种发展战略有职业关系。教师们努力去感受技术,领会到如何激活技术,将他们的‘声音’在技术上表现出来。教师们在这样做时,他们就实施了一种古老的教育传统,即将教育定位在人类关系中而不是设施上”[16]162。这样的“人类关系”才能打破技术的遮蔽,呈现网络时代法学教育目的的本真,而法学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也才能在这样的目的重申过程中得以展现,为人体认。
第二,把握知识转移的规律。按照野中郁次郎等提出的知识转移的SECI模型,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作用、互相转化的模式主要有四种: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内部化[17]。社会化是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即成员间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实现知识共享与沟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隐性知识转移。外部化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即利用语言、文字等形式使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组合化是指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它强调的是对显性知识的采集、组织、分析、提炼与传播。内部化是指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是个体吸收、消化显性知识并使之转化成为自己的内隐性知识的过程。上述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构成了知识转移的一般性规律。依照上述知识转移的一般规律,可以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电脑和网络的知识转移主要指向的是法学知识的“组合化”阶段,实现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移。这一点在各种法律数据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由于知识的“组合化”本质上只是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部分阶段,法学知识传授的“社会化”“外部化”和“内部化”等阶段也就必须要被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阶段恰恰又是隐性知识得以整合与传承的关键环节。只有把这些环节也纳入法学知识转移过程中,法学知识传授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法学教育的目的才能实现。
第三,革新知识整合与传承的方法。因应互联网之于法学隐性知识的效用边界,网络时代的隐性知识传授方法也同样面临“变”与“不变”的选择。一方面,“变化”是需要的。在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前,知识传授方法的选择并非全部由个人决定。即使是那些对技术抱有戒心的人,在面对技术的侵蚀时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抵制教育的自动化趋势不是简单地沉溺于怀旧的契普斯先生的伤感中”,人们必须面对“在不同制度基础上的不同文明规划的问题”[16]163。法学教育同样无法逃脱这一情境。另一方面,也应意识到互联网技术革新实际并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的核心。那些在教育活动中以“师承链”形式被代代相传的东西,可能并不只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类似于“思维风格”那样的隐性知识。以这样的立场出发,针对互联网时代法学隐性知识挑战的方法革新可能需要关注以下内容:首先,重估师徒制价值,完善导师制教学方法。师徒制是较为适合隐性知识传承的教学方法,这一点在英美法律早期教育中已经得到证明。正是通过师徒间的亲密接触,法学个体知识才在潜移默化中实现顺利转移。当然,学徒制本身有强人身依附性以及知识传授的随机性等缺点,但即使如此,师徒制中蕴含的“言传身教”的传统教育观念仍应被尊重和保存。其次,强化对于法学实践性的认知,注重亲历性方法的应用。法学是强实践性学科,法学的强实践性指向的不应仅仅是法律规范的实践性操作,还应包含法学理论的操作性实践[18]。就此而言,法学教育中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实践性”这一层面是相通的。法学既然是强实践性的,那么亲历性的教学方法,如参与式教学、对话式教学等,在互联网背景下更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再次,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强法学隐性知识的整合与传播。互联网背景下法学隐性知识的整合需注意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对于隐性知识的整合与传播是极为重要的。在组织层面,可考虑创建以针对法学特定问题或特定领域的实践性社团,以学习型组织的形式,对法学相关领域的隐性知识进行整理。这不仅意味着要继续丰富传统的线下的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而且也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线上虚拟空间,推进隐性知识的整合、交流与共享。最后,选择合适的网络教学技术。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不同的网络技术对不同类型知识的传承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别。总体而言,受隐性知识本身难以表述、个体性、情境性、文化性等特征以及法学本身实践属性的限制,那些能够使师生更好地进行交流的互动空间和情境,有利于法学隐性知识传承的网络技术,在互联网法学教育中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在这方面,医学、建筑、汽车驾驶等领域已经开始采用的虚拟实在技术,可以给我们丰富的启示。今天,利用虚拟实在技术,医学院学生可在网络中完成十分逼真的解剖课程;利用电脑模拟驾驶培训系统,驾校学员就可在电脑上迅速掌握必要的驾驶技能。这样的虚拟实在技术创造了职业技能演练的仿真空间,对技能型隐性知识的学习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类似的虚拟实在技术在法学隐性知识传承方面,也有着加以利用的可能。只不过以复杂易变的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知识的传承,毕竟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医学对生物性人体、驾驶员对无生命机器的操作与控制。虚拟实在技术运用中有从“仿真”到“失真”的可能,这最终也可能使我们面对的只是徒具感性外表的符号世界,这和真实的现实世界无疑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所有这些意味着,认真对待隐性知识,我们尚需在确认互联网技术积极作用的同时,对类型纷繁多样的网络技术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保持足够的谨慎,并从法学隐性知识的特性出发,作出具有针对性的选择。
4 结束语
隐性知识是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隐性知识作为一种内在的、个体性的知识体系,在法学教育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它是提取和创造显性知识的最为丰富的素材库,也是建构受教育者知识结构体系,构筑法律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面对互联网时代技术发展的挑战,如何在法学教育中实现隐性知识的整合、传承与创新,进而推动互联网时代法学教育中理性与经验、逻辑与悟性的融合,实现个体知识与公共知识在法学教育与法律治理实践中的共生,无疑仍有待法学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与回应。这也意味着,“认真对待隐性知识”仍是互联网时代法学教育中有待展开的命题,相关的讨论因而也就远未完成。
[1] MICHAEL P.Study of ma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press,1958:12.
[2] MICHAEL P. The tacit dimens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4.
[3] 胡学军,涂书田.司法裁判中的隐性知识论纲[J].现代法学,2010(5):93-103.
[4] 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5] EDWARDS S, HAMMER M. Laura’s story: using problem based learning i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teacher education[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06(22):465-477.
[6] 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申政武,王志安,渠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37.
[7] 黑德勒姆.律师会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13-16.
[8] 曹伟.互联网+时代的互动式法学教育[N].光明日报,2015-10-13(14).
[9] 吴志攀.大学法学教育与网络的互动性[J].法学家,2000(5):106-112.
[10] 方明.缄默知识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95.
[11] CLEMENT J. Use of physical intuition and imagistic simulation in expert problem solving[M]//TIROSH D.impli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an educational approach. Norwood and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4:204-244.
[12] 黄荣怀,郑兰琴.隐性知识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4.
[13] 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4.
[14] 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1.
[15] 马海发·梅隆.诊所式法律教育[M].彭锡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
[16]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 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的螺旋:知识管理理论与案例研究[M].李萌,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52-60.
[18] 刘星.法学知识如何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19.
〔责任编辑: 张 敏〕
Onthechallengeoftacitknowledgeoflaweducationandresponseinthebackgroundof“internet+”
NIU Yubing
(Law School,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education of law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knowledge spread. With knowledge pedigree observation, what is suitable on Internet is explicit knowledge of law, rather than tacit knowledge. 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legal educa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tacit knowledge, we still need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acit knowledge, and take tacit knowledge seriously. Reiterating the purpose of the law education, grasping the general rule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novating methods to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hoosing suitable teaching technology are possible paths for tacit knowledge in Internet age.
Internet+; law education; tacit knowledge; explicit knowledge
2017-04-0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FX008);江苏大学高教研究重点课题(2015JGZD024)
牛玉兵(1975—),男,河南鹤壁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理学教学与研究。
D90
: A
:1008-8148(2017)03-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