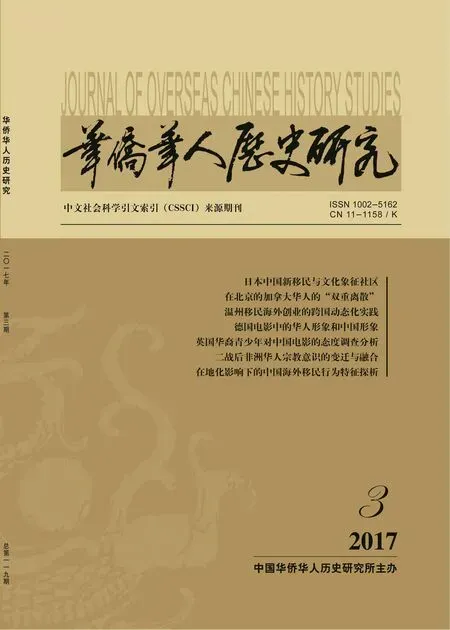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
李海蓉
(清华大学 华商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史海探源
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
李海蓉
(清华大学 华商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澳洲;戊戌变法;保皇会;康有为;梁启超;《东华新报》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海外期间继续其变革中国的政治活动,保皇会为二人所依托的庞大跨国组织。然而对于保皇会如何于世界各地之成立及其运行的细节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晚清史学者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论文根据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澳洲保皇会档案及其他澳大利亚所藏原始文献,分析探讨了澳洲保皇会成立的动因、过程、初期活动,尤其着重展示《东华新报》作为保皇会机关报的沟通宣传职能以及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会的互动情况。论文以澳洲为切入点,以点带面,构建全局视野与想象,为深入理解海外华人如何参与进晚清大变局提供新的门径。
保皇会系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所领导的庞大跨国政治组织。目前,海内外研究者关于保皇会分会总数的说法不一,但各类有关康梁及辛亥革命的研究显示,保皇会曾遍布海外华人世界。①美国独立学者谭精意(Jane Leung Larson)发起的保皇会研究论坛(Baohuanghui Scholarship)所提供的各分会地点加起来不少于150个,http://baohuanghui .blogspot.co.nz/(2014年1月22日检索)。谭精意系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谭良后人,其私家所藏保皇会资料自1990年公开以来一直被视为保皇会研究的重要原始文献,见方志钦、蔡惠尧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桑兵转引各处史料显示,保皇会总数在140至160个之间,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第506页。流亡中的康有为何以赢来数量庞大的海外追随者?遍布世界各地的保皇会成员为哪些人?保皇会作为跨国政治组织如何运行?已有研究对康梁二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并未提供圆满解说。②康梁研究的总体状况综述,可参见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出版) 2005年8月号;马洪林:《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08年12期。
大量的辛亥革命研究明显倾向于将保皇会简化为革命派的对立面,主要基于两方原始史料:一是国民党的官方叙述,最具代表性的为冯自由作为孙中山机要秘书的回忆录。[1]桑兵已指出其中的不实之处,[2]陈蕴茜另揭示,随着国民党政权确立,孙中山崇拜乃至辛亥革命意识形态化深刻贯穿渗透整个国家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3]如此,极可能导致保皇会曾动员海外华人参与晚清大变局的真实历史被歪曲乃至湮没。二是康梁年谱及二人文集。然而,加拿大学者陈忠平近期利用北美所存档案、碑文等资料撰文指出,关于保皇会最初创立于加拿大,“康氏的说法并不完全可靠,其中最不可信之处,是将叶恩及其他温哥华的华侨领袖摒弃于保皇会创始人之外。”[4]可见,更多挖掘海外第三方史料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入揭开历史真相。
本文主要依赖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澳洲保皇会档案及其他澳大利亚所藏原始文献为核心史料撰写。笔者已发表过专题文章讨论《东华新报》作为澳洲保皇会机关报的发行与内容,[5]本文将更多呈现该报所记录的澳洲保皇会公开活动及保皇会公启等组织文件。澳洲保皇会档案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诺尔·布特林档案中心(Noel Butlin Archives Centre)所藏新南威尔士保皇会会议纪要(Chinese Empire Reform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 Minute book)。这些一手资料的保存及信息发布者均为当时澳洲及各国广为尊崇的精英华商兼侨领,其可靠性应远远高于国民党的官方叙述,尤其应被视为已出版康梁年谱及各类文集的重要补充。本文主体涵盖以下内容:一是澳洲保皇会成立动因;二是澳洲保皇会成立过程;三是澳洲保皇会初期的主要活动。笔者旨在以澳洲为契机,从微观进入宏观,进一步还原保皇会的历史。③目前,唯一已出版专题考察保皇会的著作,为高伟浓利用美国原始资料而撰写的《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学苑出版社,2009年。然而,高著并未详解保皇会运动如何在美国展开。
一、澳洲保皇会成立动因
澳洲保皇会的存在曾屡见于各类康梁及辛亥革命研究中。杨进发(Yong Ching Fatt)、刘渭平、黄乐嫣(Gloria Davies)、费约翰(John Fizgerald)、郭美芬(Meif-fen Kuo)、杨永安等学者虽曾论及澳洲保皇会,并征引过《东华新报》与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但均未就澳洲保皇会如何成立给予说明。④Yong Ching Fatt,The New 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1921, Richmond,S.A.:Raphael Arts,1977.中译本,杨进发著,姚楠、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Gloria Davies,“Liang Qichao in Australia:a Sojourn of No Significance?”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27(September 2011),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27_liang.inc&issue=027;John Fitzgerald,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2007;刘渭平:《梁启超的澳洲之行(一)》,《传记文学》1981年第1期;刘渭平:《梁启超的澳洲之行(二)》,《传记文学》1981年第4期;刘渭平:《清末保皇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1991年第6期;Meifen Kuo,Making Chinese Australia:Urban Elites,Newspap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1892—1912,Clayton,Victoria: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2013;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刘渭平曾提及康有为和加拿大保皇会头面人物叶恩向澳洲侨领致信,但刘文对如此重要的原始文件几乎未做任何分析评价。
笔者曾讨论过保皇会利用《东华新报》在澳洲华人移民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动员功能。《东华新报》由海外华商报摇身一变服务保皇会,其部分文章的政治立论及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视为保皇会的政治宣传,①例如,《东华新报》曾转引《清议报》所刊登的《戊戌政变记》,实系康梁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但其追踪报道康梁及其追随者的公开活动,尤其展现保皇会在加拿大的成立及其在香港、澳门、横滨、新加坡、槟城、暹罗、檀香山以及旧金山等地的扩展情况,在当时则是新闻,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是有价值的史料。
置身澳洲的保皇会同情者或支持者可谓经过一番精心舆论造势后,1899年10月11日,《东华新报》刊登出康有为及加拿大保皇会负责人叶恩分别致澳洲头面华商及侨领梅光达的两封信。两信抵达日期不具,但我们注意到,同日,《东华新报》以大幅醒目版面登载加拿大维多利亚及温哥华两埠创立保皇会的公启。1899年7月,保皇会于加拿大率先成立,[6]而《东华新报》登载公启的日期明显滞后。显然,《东华新报》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其公开。康有为来信全文如下:
“光达仁兄足下,闻盛名义久矣。自新金山归者莫不言仁兄豪杰义侠,是以夙夜侧慕无已也。中国守旧垂亡,吾同胞五万万人种将绝,弟诚哀之,故屡次上书变法以救之。皇上圣明,过蒙大用,言听计行。去年大变新法,天下拭目,而西后及荣禄守旧见妒,圣主幽废,新党咸戮,弟幸为英国所救而免。然今日月割中国将亡矣,海外同胞国人五百万,岂无忠君爱国之杰,天应留之以救中国?仁兄□其人也,若联络各埠,互相通识,合大会以救中国尤尚可为。若能合大会收银行轮船之权,上以保皇上,下以保商民,中国种尚有望也。□豪杰留意新金山,闻极多忠义之人及通达西学之才,渴望无已,皆望代问。敬大安。弟康有为再拜”②《信函照录》,《东华新报》1899年10月11日,第2~3页。此信为笔者自缩微胶卷转抄,有两处字迹无法辨认,故以□符号替代。以下另有多处使用□符号,原因同。
梅光达,1850年生于广东新宁(民国后改称台山),19世纪末新南威尔士华洋社会共知的华商巨贾,其社交圈甚至囊括新南威尔士总督、悉尼市长等各路精英,为华洋各界公认不具名而实际的中国领事。1903年,澳大利亚联邦第一任首相埃德蒙顿·巴顿(Edmund Barton)及驻悉尼二十国领事曾联名恳请清政府委任其为驻澳洲领事。③梅光达的传记最早为其妻玛格丽特(Margaret Tart)撰写,The Life of Quong Tart or,How A Foreigner Succeeded in A British Community. Sydney:W. M. Maclardy,“Ben Franklin” Printing Works,1911。这部著作成为后来澳洲学者重新撰写梅光达生平的蓝本,见Robert Travers,Australian Mandarin:the Life and Times of Quong Tart,Dural,N.S.W.:Rosenberg Pub Pty Limited,2004。了解梅氏其人,有助于我们理解保皇会于加拿大成立后向海外拓展初期,康有为为何向其致信。
从康信内容看,他对梅光达其人的了解来自“新金山归者”。④“新金山”指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因两地晚于北美发现金矿,因此华人习惯称其为“新金山”以区别于北美。梅氏在澳洲华人中无人媲及的社会影响力想必已为返回新宁侨乡的华侨口口相传,因此,其声名已远扬加拿大华人社会。于是,康有为寄希望梅氏联络各方人氏,加入保皇会,以救中国,上保皇上,下保商民。此信中,康有为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特殊身份,蒙受皇上重用,皇上对其“言听计行”,为拯救将绝的五万万人之中国,才开始大变新法。《东华新报》此前曾报道,康有为在加拿大被千百“乡人”簇拥,为其创会演说而“垂泣多呜呜欲绝”。[7]以皇上重用之亲信的身份向澳洲首屈一指的侨领介绍自己,期望其影响澳洲华人,这显然是康有为的政治策略。
此时的康有为已在香港、日本、加拿大、英国积累了一定的海外生活经历,比较去国前主要通过阅读书报获取见识,当在海外亲身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之后,他应更坚信变革中国急需熟悉西方世界的精英人才。抵达不列颠哥伦比亚之时,康有为曾被维多利亚市长接见,并在该省财长陪同下参观了议会、立法院、教育部等办公场所。他深表震撼,告诉加拿大官员,中国也将修建相似的宏伟建筑。[8]致信时,他应已了解在同为英国殖民地澳洲生活的广东乡人中亦多通英语、明达西学之才。因此,信中重申自己对“通达西学之才”的渴望。“请其代为问候”,即希望梅氏帮助引荐,将此类人才吸纳进保皇会中。此外,康有为提到保皇会有意“收银行轮船之权”,表明该组织即将开启的商业活动,此要点令我们更明确精英华商加入保皇会的重要性,对此,笔者已论述过。总之,这封信意图清晰,直截表达了康有为的意愿—力争梅光达入会、吸收人才,助力保皇会于澳洲的拓展。
《东华新报》同时刊发的另一封信来自叶恩,同样致梅光达。众多涉及保皇会与辛亥革命的文章及著作对叶恩的描述通常十分简略,称其为北美华商、侨领,曾深得康有为信任,在保皇会的商业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叶恩与康有为后来龃龉不断,振华公司招股及刘世骥被刺杀案则导致二人最终决裂,①有关叶恩参与保皇会商业活动的研究,可参见贺跃夫:《刘士骥被刺案与康有为保皇会的衰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张荣华:《振华公司内讧与康、梁分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 2002年第3期。因此,叶恩消失于康有为春秋笔法下的原因可想而知。
叶恩,亦写作叶惠伯,系温哥华著名华商叶春田的侄子。叶春田,1845年生于广东新宁,曾代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华工招募,并经营华工补给进口业务。据称,他曾参与将超过7,000名华工引入加拿大铁路工地。叶氏的永生公司还代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汽船航线往返中国的船票,并经营侨汇“金信”业务。他还是温哥华中华会馆及华贸董事会的创立人之一,中华会馆被视为温哥华华人社团的代言人。②叶春田的生平介绍,参见网站:https://ccncourstories.wordpress.com/our-stories-features/yip-sang/(2015年6月8日检索),以及Timothy J. Stanley,“Yip Sang”,in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Vol. 15,University of Toronto/Université Laval,2005,http://www.biographi.ca/en/bio/yip_sang_15E.html(2017年2月23日检索)。由此可以推断叶春田在当时加拿大华人社会的重要影响力。1901年加拿大人口统计记录显示,叶春田当时56岁,然而他的11个子女均年幼,最年长的儿子仅16岁。③叶春田家庭状况,可参见加拿大人口统计历史数据资料,http://automatedgenealogy.com/census/View. jsp?id=60022&highlight=34&desc=1901+Census+of+Canada+page +containing+Sang+Yip(2015年6月8日检索)。因此,当时担任海关翻译的叶恩自然在叶春田的商业活动中担当重任,而叶春田可能赋予叶恩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应顺理成章。康有为在《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一文中曾详细记录两次保皇会集会,称“主持温哥华者叶恩”。[9]叶恩的名字再次醒目出现在其稍后撰写的《美洲祝圣寿记》中,“湾高花(按:温哥华)将举庆典,天大雨,新宁叶恩曰‘我圣主若终不复位,雨终夕;若天不亡中国,圣主将复位者,雨当晴。’已而果晴,众人大喜,醵资益多,欢祝益乐。又数埠华人生计,皆以渔红鱼,去岁不来,多亏败者,是时鱼亦忧少。叶恩祝曰:‘若圣主终不复位,鱼不来;若天不亡中国,圣主将复位,鱼可大来。’祝寿毕,已而鱼即大来。”[10]
这段文字中康有为为保皇会所营造的神秘主义色彩尤其醒目,而对叶恩神话式言语的着意描述似乎暗示两人彼时关系密切。1899年仲冬,温哥华保皇会成员的一张集体照片显示,较年长的叶春田担任“核数”,应是负责财务,而正值壮年的叶恩则为“加拿大属总理”。④参见美国金山西北角华裔研究中心(the Chinese in Northwest America Research Committee)网页,http:// www.cinarc.org/Associations.html(2015年6月13日检索)。以上背景说明或可解释保皇会于加拿大成立后何以由叶恩致信梅光达,其全文如下:
“光达仁兄乡台阁下,远隔重洋久闻大名高义矣。今中国危亡日割,广东尤朝不及夕。去岁圣主舍身变法,竟为荣禄奸贼幽废。吾乡康工部以经天纬地之才,屡上万言书,哀中国而救之,乃被奇祸,几于全家被戮。于是旧政全复,国亡更迫矣。而吾海外五百万兄弟,恨不能联络,齐心发愤以救中国而保黄种。今欲救中国非能救圣主不可,欲救圣主非去奸贼不可。今敝处各埠与日本埠创建保皇会及保工商以救之,众人同心,已有数万份。素稔阁下豪侠,望倡率贵埠,共成大会,互相联通,想有同心也。康大人遍游地球,亦素闻贵埠高义,素知阁下豪侠,如足下欲见之,与贵埠鼓舞,必更有益,如足下欲之,可与贵埠议定有信或电来,康大人必欣然也。敬请大安弟叶恩拜”
与康有为来信相比较,叶恩的来信更注重渲染乡谊。首先,他以“乡台”称呼梅光达,以同是新宁人拉近关系,而新宁华人的跨国网络足可令两人已彼此了解,即使远隔重洋。加拿大官方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885至1903年间,进入加拿大的华人45%来自台山(按:新宁)。[11]以侨乡为切入点,叶恩随即将乡谊扩展至整个广东。在中国举国危亡下,广东形势尤令海外华侨焦虑。如叶恩所言,那里“朝不及夕”,侨乡家人尚需生存,倘国不存,家何在?其后,叶恩以“吾乡康工部”的“几于全家被戮”的个人境遇打动梅光达。如此一位挽救中国危亡的皇上亲信却遭遇奇祸,身为“豪侠”又久负“大名高义”的侨领梅氏岂能无动于衷?叶信强调以“同心”为基础的跨国乡谊,可视为康信的有力补充。叶恩同时暗示,在乡情联谊鼓动下,加拿大与日本保皇会的创建已有可喜进展,因此力促梅光达率澳洲华人之众投身这场集合海外兄弟以保皇、保国、保工商、保家的“大会”中。末了,他特别暗示,康有为有意访澳,希望梅氏协助。
梅光达的回信已无从找到,但笔者查阅到新南威尔士财长弗朗希思·科克派特里克(Francis Kirkpatrick)于1900年3月23日写给梅光达的回信,该信则提供了清晰线索,表明梅氏曾力促康梁到来,并设法使其免交入境人头税。科克派特里克提及梅氏为此于12日的致信,并附四份电报,分别来自维多利亚、南澳、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四省首相,唯塔省首相表示人头税照收。①原件现存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特藏部,“梅光达及家人—文件(Quong Tart and fmaily -papers)”MLMSS 5094。另,梁启超抵澳后曾致信康有为写道,“雪埠初时以为梅党可抚,乃竭全力以图之”。[12]此处“雪埠”指悉尼,旧称雪梨,而“梅党”应指梅光达所集合的政商势力。其后,梅光达在一场法庭诉讼中自称,“保皇会之事是吾先创,因后保皇会人做事不公,故吾脱身于该会”。[13]而澳洲保皇会成员也佐证了梅氏的参与,称“既成会后,光达等始入斯会,然推原保皇会之先设,乃由英属加拿大埠”。[14]然而,下文将提到,《东华新报》所公布的澳洲保皇会最初名单中并不见梅光达。对此,笔者认为,保皇会为当时清廷追捕的政治要犯康有为所领导,而梅光达曾接受清廷四品封赏,戴蓝翎,又实为不具名的中国驻澳洲领事,其特殊身份令其不愿公开承认参与保皇会,情有可原。
以上,笔者以讨论《东华新报》公布保皇会致信澳洲侨领梅光达及梅氏实际参与保皇会为重心,意在以澳洲案例深层揭示康有为如何在海外华人中实施其政治策略,即依托虚拟皇权、感召集结各国侨领,以实现其依赖侨领拓展保皇会的目的。
二、澳洲保皇会之成立
自公开保皇会致信梅光达后,《东华新报》几乎每期均登载康有为及保皇会在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相关报道与评论。1899年10月28日,该报全文刊登了《保救大清皇帝会例》、②见《东华新报》(附页),1899年10月28日。此会例以数字序号排列,至二十三款,与中华书局1981年版本略有差异。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415~420页。康有为自称所持光绪皇帝“密诏”内容、加拿大属保皇会公启。公启宣布康有为奉诏为海外保救大清皇帝会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另附雪梨阖埠华民公启宣称:“……海外各国华人并兴义举,本洲华人自应同力度德,和衷共济,盖保皇救国名正言顺……”1900年1月17日,该报正式宣告保皇会于澳洲成立,其细节笔者节录如下:
“康君有为游历海外倡设保皇会,盖欲救光绪大皇帝复登大宝,变法自强……本埠梓友早经集议,曾将其之叙文规例刊派供览.....兹接保皇总会谕,并接美国保皇会信函章程等件催促开办,故本埠华人商民即于本月十四晚在东华新报馆楼上集议,赴会者约一百人,当时乐做保皇会者已过二千余份,每份收司令银四元,①此处的“司令银”,指先令,20先令折合币值1镑。由一份至千份均可,随人鼎力,先有做五百二百份,数十份者,不一而足……”[15]
从档案看,这个分会最初全称为“澳洲鸟修威②鸟修威,即新南威尔士。省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雪梨正埠总理多名,包括刘汝兴、李益徽等共9人;协理包括《东华新报》主笔郑禄等22人;值理包括《东华新报》主笔伍萼楼等28人。尽管总理人数众多,但刘汝兴与李益徽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人,因该会起初数次议事纪录最后均由二人签名,二人参与管银事宜,刘汝兴还掌管保皇会图章,公议决定凡保皇会给发银凭票及付信函均以此图章为依据,经书记人缮写后,即交刘汝兴过目妥当,印信底才得寄出,如果有要信,需交李益徽看过方可。此外,各埠付到澳洲保皇会的书函由东华新报代收,但须交刘汝兴与李益徽亲手开拆,东华报则可先开电报。③见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之“公议”纪录,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晚,此日保存李益徽参与保皇会集议的最后记录。
刘汝兴,为增城邑老字号安昌商行店东,系《东华新报》大股东。④《东华新报》作为有限公司的政府注册文件显示,其预期集资股本为1000镑,分作5000股,每股4先令,最初股东仅8人,共集850股,刘汝兴持300股,合60镑,为最大股东。见新南威尔士州档案,SANSW:NRS 12951,1723。李益徽为香山邑安益利店东,二人均为新南维尔士华商联合组织联益堂的重要成员。⑤李益徽曾参与澳洲保皇会初期活动的事实无可争议,但其后与《东华新报》发生诉讼官司,导致该报破产,复刊改称《东华报》,诉讼情况可参见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相关内容。联益堂代表四邑、香山、东莞、增城、高要的八家老牌商行(广茂安、安昌、广兴昌、安益利、新兴栈、合利号、均利号、义益号)于1891年成立于悉尼,⑥八家商行名称由笔者综合《东华新报》所刊联益堂众多广告整理而成。这些商行主要批发零售澳洲华人所需的各类进口中国杂货,兼营“金信”侨汇,并代理三家大型航运公司,出售旅澳华人船票并承接澳洲华商货运,其性质与上文提到的叶春田的永生公司相似。联益堂的三大宗旨为:慈善救济,为旅澳华人公益服务;促进商人间联系;调解华社内部争端。⑦关于联益堂的更多情况,见杨进发著,姚楠、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24~126页;李承基:《李益徽与联益堂》,《中山文史》(第51辑)2002年,第91~93页。可见,身兼华商及侨领集团的联益堂把持着新南威尔士州华人的生命线。
一个月后,《东华新报》公布的认做保皇会份名单显示,任捐者已达两百四五十之多,还包括少数华商铺户。[16]加拿大保皇会的致信则透露出澳洲保皇会与联益堂的关系,笔者抄录关键字句如下:
“贵属联益堂列位乡先生大人……南海康先生有为奉皇上衣带密诏后往海外友邦求救,辱临鄙埠,迨事与愿违,乃大呼同志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澳门知新报为总会所,总理其事者乃何君穗田,忠义殷实,富有数十万,故重推举其收贮会款银元,香港何君晓生富拥百万,均为此会总理。凡各埠保皇会捐款无论多寡,皆承康先生命汇交澳门知新报馆,彼当给回收条,以昭核实……现美属英属合众华人概为鼎气力捐会份,付至总会,以应救挽君国,今日之危,毋分论何样堂行头及三四邑之旧泥也,顺为一及耳……”[17]
信中再次点明,保皇会之创立以康有为所携密诏为动因,以保皇、保国、保家为宗旨,而保皇会形成及拓展的基础则是以三邑、四邑宗亲乡谊所维系的广东华侨跨国网络。因此,港澳作为连接海外华人与中国的门户,于保皇会至关重要。保皇会以其澳洲喉舌《东华新报》公开何穗田及何晓生①何穗田,即何连旺,晚清澳门赌王之子,兼营鸦片及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华资工厂,为葡澳政府倚赖的华界精英,其生平见林广志:《澳门晚清华商》,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第33~41页。何晓生,即何东,以买办起家,1898年始任象征香港华商及买办集团领袖的东华医院主席,其生平见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香港三联书店,2007年。入会的意图明确,即以港澳最知名华人的参与对更多人进行感召,一方面凸显保皇会民心所向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暗示保皇会名下所集结的华人跨国政商网络。而联益堂系澳洲保皇会核心的事实为不久后《东华新报》公布梁启超旅澳经费来源的新闻明证,“……保皇会同志大集商家联益堂人等在东华新报馆会所集议,为请梁孝廉启超来游演说保皇保国事宜,联益堂各总理准将存款若干拨作经费。”[18]
以上详细讨论保皇会如何动员澳洲华人精英,尤其以细节展现华商组织联益堂及其关键人物的参与。剖析跨宗族、跨地域、具有广泛领导意义的联益堂参与,有助于加深理解澳洲保皇会的生成及其性质,即澳洲华人已有的跨国社会网络又新添了跨国政治组织职能。
三、澳洲保皇会的初期活动
保皇会于悉尼成立后,其最先活动即由《东华新报》刊发广告,组织公众集会,澳洲保皇会的第一次公开演说集会在悉尼一所戏院内进行,其情形如下:
“本埠华□开办保皇会……昨礼拜晚在□丹的戏院演说□会源流,梓友聚听者约四百余□。李君益徽为主席,先将保皇会义举提纲挈领慨乎□之,与闻者罔不□掌称善,他如刘君汝兴,吴君济川……等相继与□……在座诸□□掌者甚众,极欲赞劝是会也。也尚有数□仍欲续谈,但已深夜,余候□机,姑俟下次筹劝讲云。”[19]
1900年2月7日,《东华新报》宣布,经保皇会总会批准,该报正式成为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作为保皇会喉舌,《东华新报》积极履行其宣传职能,继续传播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主张,同时,通过新闻报道向公众展示保皇会于海外及澳洲本土的活动,包括募集捐款,召开公众集会,进行政治演说等。此外,该报还公布其承担保皇会内部通讯与信息传递职能。[20]
从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及《东华新报》新闻看,保皇会于悉尼成立后的其他主要活动包括四方面:一是拒立己亥新君;二是为庚子勤王汇款;三是为光绪皇帝及孔子庆圣诞;四是安排梁启超来访。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主谋,欲废光绪另立“大阿哥”,立储上谕一经电报局沪局总办经元善公开,天下哗然。②有关事件经过,详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71页。1月27日晚,澳洲保皇会集议新加坡《天南新报》来电,“上谕□嗣以继同治,似有新君即位。邀集南洋澳洲各华民合□□电返京以拒朝廷之所为?又云,望众百姓齐□助光绪君复位,业已即□发电信上京照陈矣。”当晚,集议又决定,再付电往布里斯本、墨尔本、新西兰、阿德雷德等埠。2月7日,《东华新报》公开报道,本埠华民电达清廷,“合力抗拒,毋使皇上被人强迫退位”,并称“东华新报代举华民禀”。笔者认为,此处所还原的澳洲保皇会致电总属之决策及行动过程,可视为当时保皇会发动暹罗、新加坡、海防、菲律宾、美国金山等海外四十六埠华人联合电争、阻止立储[23]的缩影。
为配合海内外全面铺开的勤王计划,档案显示,澳洲保皇会亦加紧筹款汇款行动,各总理、协理、值理曾为此多次集议。1900年2月14日,澳洲保皇会劝捐行为指向各华商铺户;[24]3月21日晚,参加集议的各总理、协理、值理又加捐五百余份;[25]5月30日晚,确认已经汇丰银行付交总会总理何穗田,汇款金额为1000英镑;①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五月初三晚。另见南澳英文报纸新闻报道,位于悉尼的保皇会已向澳门保皇会总会电汇1000镑,“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South Australian Register,4 July, 1900.7月3日,回应康有为自新加坡催款应急来电,集议每人加捐四百便士,明日汇澳门总会;[26]12月10日晚,已置身悉尼的梁启超申明大义“面谕再行加捐”,于是“同志”再加捐至1800余份;[27]12月18日晚,公议,又批准电汇1000英镑交新加坡邱菽园收;[28]1901年3月1日晚,集议决定,次日由电汇新加坡,交邱菽园收300英镑,并再筹寄,另汇银日本,交冯紫珊;[29]4月14日,集议电汇香港渣打银行,交何穗田收200英镑,包括墨尔本的150英镑,悉尼的50英镑。[30]《东华新报》报道,光绪廿七年二月初二(1902年3月21日),刘汝兴等四□前往鸟卡□埠(Newcastle,今译纽卡斯尔)演说中声称,保皇会已于悉尼捐银三千镑左右。[31]
综合上述史料,兼对照梁启超致信康有为有关澳洲筹款的报告,[32]我们可理清澳洲保皇会前期筹款及汇款的基本情况—募款总数应超过3000英镑,主要部分汇往海外,资助庚子勤王。余款用于其它,例如,响应总会号召,资助美国的南海籍保皇会成员罗赞新家属。[33]罗妻于侨乡被缉拿,后在保皇会救助下获释。[34]救助事件应与《东华新报》所刊《保皇会会员被难救恤章程》对照解读,《章程》内容包括保皇会员及家属被捕后为营救甚至求助港澳总督、上海各国领事,以及报仇、死难后抚恤等。[35]保皇会筹款救助罗妻事件亦在梁启超旅澳期间致康有为书信中记录。[36]
此外,澳洲保皇会组织还举办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庆典聚会。其一,该会集议“六月廿八乃圣皇万寿,务邀齐各同胞梓里聚集□□庆闹以表一片忠义之心”。[37]1900年7月24日,为光绪皇帝祝寿,此次活动于悉尼租用西人戏院举行,以茶点奉中西宾客“不下千二三百”。[38]其二,1900年9月20日,为祝孔子圣诞,保皇会于东华新报馆设圣位,摆祭品,并再次租用同一西人戏院,以茶点奉中西宾客。[39]两次活动中,刘汝兴等人均进行了时政演说。澳洲保皇会创立之初的另一重要活动为安排梁启超来访。档案显示,保皇会多次集议均与此有关。梁氏澳洲之旅已广为学界所知,此处不赘述。
以上笔者以具体史实钩沉保皇会于澳洲创建初期的活动,尤其着重展示《东华新报》作为保皇会机关报的沟通宣传职能,以及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会的互动情况。这些鲜活的史实为我们理解保皇会作为曾经运行过的晚清华人跨国政治组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四、结语
本文对澳洲保皇会的成立及初期活动进行了基本还原。笔者意在从澳洲之一斑窥全豹,揭示保皇会系康有为领导下由19世纪末已有的海外华人社会网络更新而成的庞大跨国政治组织,而海外精英华商兼侨领的积极参与则是保皇会得以铺开运行的关键。戊戌政变后,流亡中的康有为继续鼓吹变革中国、自强御侮。尽管就“衣带诏”真伪问题,学界一直有所争论,②引人较多关注的相关研究,如,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737页;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马勇:《康有为“衣带诏”缘起及演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但笔者认为,我们还应思考“衣带诏”产生的实际效应,即“衣带诏”化身为光绪皇帝的象征,既然为康有为“所携”,便是光绪皇帝一直“授权”康有为于海外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的“明证”。因此,康有为“携带衣带诏”行走天下,不仅仅为一己之“护身”,而是其依靠虚拟皇权在海外华人中进行政治总动员的策略实施。换言之,保皇会运动实际是戊戌变法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延续。现有康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考察二人引领海外华人参与晚清大变局的活动与客观评价。本文以澳洲保皇会为案例分析,深入保皇会历史,或可为学界多角度审视辛亥革命提供新的门径。
[注释]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
[2]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44、246页。
[3]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5] 李海蓉:《保皇会在澳洲的兴起—基于《东华新报》的媒体传播理论与量化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 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 《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东华新报》1899年7月15日,第2页。
[8] Chen Zhongping,“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9,No. 1(2014):3.
[9] 《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东华新报》1899年7月15日,第2页。
[10] 《美洲祝圣寿记》,《东华新报》1899年10月25日,第2页。
[11] 李胜生:《加拿大华人与华人和会》,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第19页。
[1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13] 《殴案详审》,《东华新报》1901年11月13日,第3页。
[14] 《三续殴案详审》,《东华新报》1901年11月23日,第3页。
[15] 《同倡义举》,《东华新报》1900年1月17日,第3页。
[16] 《雪梨各埠义士认做保皇会份芳名》,《东华新报》(附页)1900年2月21日。
[17] 《保皇雁帛》,《东华新报》1900年1月20日,第2页。
[18] 《名士行踪》,《东华新报》1900年3月28日,第3页。
[19] 《会谈义举》,《东华新报》1900年1月24日,第3页。
[20] 《义举翕从》,《东华新报》1900年2月7日,第2页。
[21]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七晚。
[22] 《电函译登》,《东华新报》1900年2月7日,第5页。
[23] 汤志钧编:《致濮兰德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
[24]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元月十五日晚。
[25]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二月廿一晚。
[26]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六月初七晚。
[27]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拾月十九日晚。
[28]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拾月廿七晚。
[29]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七年)正月十一晚。
[30]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七年)二月廿六晚。
[31] 《义捐益愤》,《东华新报》1900年3月28日,第3页。
[3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第261页。
[33]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三月廿四晚,五月廿九晚。
[34] 《义眷释放》,《东华新报》1900年5月16日,第3页。
[35] 《保皇会会员被难救恤章程》,《东华新报》1900年5月5日,附页。
[3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8~229页。
[37] 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五月十八晚。
[38] 《祝嘏庆会》,《东华新报》1900年7月28日,第2页。
[39] 《东华新报》之《恭祝孔子寿诞定章》,1900年9月15日,第3页;《祈圣改章》,1900年9月19日,第3页;《圣诞余谈》,1900年9月26日,第3页;《圣诞清单》,1900年10月10日,第3页。
[责任编辑:张焕萍]
In Search of the Origin of the Australian Chapter of the Baohuanghui: Re-visiting the Tung Wah News and the Baohuanghui Archives in Australia
LI Hai-rong
(Center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ustralia; Wuxu Reform; Baohuanghui;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Tung Wah News
Subsequent to the Wuxu Reform,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went into exile and continued their political endeavour by founding the Baohuanghui, an extensiv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organisation. Compared to the voluminous studies on Kang and Liang,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details on the origin and operation of this important organisation. This article i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Tung Wah News,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Australian chapter of the Baohuanghui, and the archives of this chapter.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then circumstances in Australia, the author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path to explore and imagine the large picture of how overseas Chinese took part in the political change of the late Qing Empire.
D634.361.1
A
1002-5162(2017)03-0075-09
2017-04-29;
2017-07-31
李海蓉,女,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兼新西兰怀卡多大学历史研究部协作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澳新华侨史、晚清政治、媒体传播。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澳洲保皇会研究”(批准号:14BZS092)之阶段性成果。作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