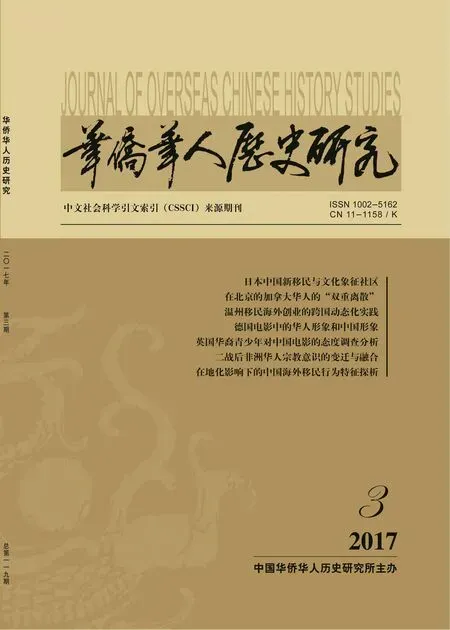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研究*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研究*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福建;侨务;归侨;社团;侨商;海外华侨协会;国民党党部
论文分析了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的发展及其原因、其会员特点及组织结构;探讨了国民党对归侨团体的渗透与控制以及归侨团体的日常活动,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的历史面貌。民国肇建,福建归侨团体方兴未艾;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团所需各项条件更为成熟,形成了归侨团体发展的高峰。其会员以归国侨商最多,并以联络海内外侨胞为宗旨展开活动。政府在社会区域治理过程中,需要借助归侨团体作为“中间人”,在华侨、归侨侨眷与侨乡政府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但由于内在结构松散和国民党党部的控制,归侨团体在协助处理涉侨事务中处于附属地位,其功能与角色难以充分发挥。
华侨社团大体上可分为侨居国社团与归侨社团。早在民国时期,在华侨联合会的带动下,各地归侨社团迅速发展。福建作为重点侨乡,归侨社团有较大发展。福建归侨团体在协助侨务机构处理华侨出入国等侨务工作方面贡献良多,是政府在侨乡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中介。福建归侨团体的作用在抗战时期尤为明显,其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地方史志中常可见对民国归侨团体的简单记载,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尚不多见。目前学界对于华侨社团之研究,更多聚焦于侨居国社团,对归侨社团则少有涉及。就民国时期的全国性归侨社团而言,对华侨联合会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夏斯云的《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一文,分析了华侨联合会成立的背景、过程、活动及其特点,肯定了其发挥的作用,促进了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发展,“为华侨谋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陈民、杨立强、杜裕根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华侨联合会进行了研究。①参见陈民《吴世荣与华侨联合会》(《华侨历史》1986年第4期)、杨立强《华侨联合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1912—1919)》(张希哲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杜裕根《论华侨联合会的创建及历史作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夏斯云《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等。而对于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研究,则十分稀少,目前仅见骆曦对泉州华侨公会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该文结合福建政局,梳理该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国民党对该会的渗透与控制,并阐述其作用与影响,②参见骆曦《民国时期地方华侨团体研究—以泉州华侨公会为例》(《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和《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藏民国时期华侨团体文书》(《福建文博》2014年第3期)。对本文颇有启发。以上研究成果,聚焦于单个归侨社团个案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其他归侨社团及其相关问题则未有足够的关注。福建归侨团体整体上的历史演变及其处境等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以福建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之福建归侨团体相关档案及前者编纂的《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为资料,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的发展及其原因,分析其会员特点及组织结构,进而探讨国民党对归侨团体的渗透与控制,择要阐述归侨团体的日常活动及其扮演的角色,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的历史面貌。
一、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之发展及其原因
(一)民国初期福建归侨团体兴起的原因
民国初年,第一个归侨团体—华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归侨团体遂在各地发展起来,福建亦是如此。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革命,成为革命功勋,颇受重视;民国的创建使他们备受鼓舞,民族情感得到极大激发,而此时百废待举,为归侨团体的建立提供了政治条件。福建省历经都督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及蒋介石嫡系统治时期,[1]其间战事频发,政治动荡,盗匪横行,“特殊的政治氛围和要求为华侨创建自己的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2]侨乡时局混乱,致使出国者众,归侨人数也颇为可观。据统计,1911年—1915年,福建归国华侨有294,602人次,年平均达58,920人次。[3]尤其是海外侨领的回归提供了干部保证。各级政府中可见华侨身影,如林文庆任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庄银安任福建革命政府顾问、厦门参事会议长兼副财政长;黄乃裳任福建军政府交通司司长筹饷局总办;杨豪侣等人也在福建省政府任职。[4]他们在社会中享有声望,且具备较强的领导与组织能力。此时,海外侨胞热切期盼参与侨乡建设,需要搭建沟通政府与侨民的桥梁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归侨团体设立之风在民国初期兴起。
(二)民国福建归侨团体之演变
早期归侨团体的创办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曾倡设厦门华侨公会,保护回籍侨商。[5]与华侨联合会成立同年,厦门华侨公会成立,庄银安任会长,这是福建省内最早的归侨社团。随后,归侨蒋报策等人发起组织泉州华侨公会,后因福建局势变幻,几经变迁。1914年,南安县华侨分会成立。在下一个归侨团体发展高峰期来临之前,尚有1926年由永春县归侨和海外华侨发起组织的“永春旅外华侨联合会”;1927年,华侨协会福建支会德化分会成立;1927年华侨协会福建分会在厦门成立。[6]此后,福建政治局势愈发动荡,归侨团体发展浪潮暂时回落。
至20世纪30年代初,十九路军入闽,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虽然新政府昙花一现,但它拉近了海外华侨与福建侨乡的关系,不少福建籍侨领参与新政府的组织与建设。归侨团体也因此得到发展,福州、莆田、长泰的海外华侨协会相继于1932、1933年成立。据厦门侨务局统计,至1935年,福建共有10个归侨团体,具体情况如表1。
及至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归侨团体的设立进入了高峰期,各地华侨协会相继建立,至“几无县无之”。①据1943年统计,福建省设有海外华侨公会的市县,有福州、泉州、南安、永春、安溪、同安、德化、龙岩、华安、惠安、漳浦、永安、龙溪、连城;设有海外华侨协会的有福清、兴化、仙游;设有海外华侨协进会的有南安诗山。参见《福建省设有海外华侨公(协)会市县》,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63页。初步估计,成立于这一时期的华侨公(协)会至少有16个,约占民国整体华侨(公)协会的80%,除厦门、泉州、福州、莆田、长泰及部分分会外,其他县市华侨公(协)会皆于此时成立,可见归侨团体兴办之热烈。这一时期,厦门还建立了许多包括联谊性质在内的其他归侨社团。②如鼓浪屿华侨联欢会、华侨互济社菲律宾支社、厦门市归侨团体联谊会、厦门越南归侨协助会、马来亚华侨联谊会、厦门市华侨产业保障委员会、华侨协会厦门分会。参见郭瑞明编著:《厦门侨乡》,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
早期福建归侨团体普遍以“华侨公会”命名,后来泉州、厦门侨团内部分裂,另组织“海外华侨公会”。193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国内侨务团体组织办法》,规定国内侨务团体之命名,“如用华侨二字者,须标明事业或国外侨民所在地之名称”,[7]因此“华侨公会”皆奉命易名为某地“海外华侨公会”。[8]1946年1月24日,政府又要求各县市“归侨团体名称应统称协会”。[9]
1949年,福建各地相继解放,各地华侨协会亦告解散。
(三)民国后期福建归侨团体兴盛原因
民国初年与后期时代背景迥异,却同样为归侨团体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民族感的激发密切了华侨与侨乡的联系,重侨政策以及华侨大量回国,特别是侨领的回归,使归侨团体设立成为可能和必要。民国初建,许多原为同盟会会员的归侨,成为归侨团体的骨干,如缅甸同盟会的庄银安、印尼同盟会泗水分会的蒋报策等人。而这些因素在民国后期因二战到来而尤为凸显。据各口岸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6年间,福建省归国华侨达10万余人,①其中一些口岸缺乏记录,因此数据并不准确,但通过出入国人数对比,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归国华侨众多,尤其是1940年以后,归侨人数大大超过出国人数。参见《1938—1946年福建省各口岸华侨出入国统计表》,泉州市档案馆:《民国时期泉州华侨档案史料》,第81页。另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1945年编印的《侨务十三年》记载,仅在太平洋爆发后的一年半内便有1,351,655人回国,其中福建华侨就有40多万人。参见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为了团结抗战,动员一切力量,政府注重拉拢侨领,争取海内外华侨社团的支持。行政院曾致电刘建绪,指示归侨“多有为当地侨领或党部负责同志而素为侨众所推崇之人,亟应设法加以罗致”,并将他们加入下一届临时参议会改选候选人中。[10]另一方面,战争使侨汇断绝,归侨侨眷的生存环境恶化,亟待救济,更多归侨团体应运而生。因此,在民国后期,归侨团体呈兴盛之势,或许非因归侨侨眷的处境变好,或人民团体意识的发展,而是因处境变差,此即侨团产生的必要性。这与前期侨团初兴之原因不同,前期是由可能性主导,后期则由必要性主导。
二、福建归侨团体的会员特点与组织结构
随着归侨人数增加,归侨团体的会员人数也得到大量增长。至1947年6月,福建省华侨协会成员共有13,632人,以晋江3263人为最多,会员人数达千人以上的还有福州、南安、仙游。会员以男性为主,女性在其中的比例极低。数据显示,女性会员仅159人,占会员总数之1%。[11]会员调查数据出入较大,归侨协会成员应远不止统计所得之万余人。②同为1947年的另一份侨团调查资料显示,会员超过1000人的大规模华侨协会至少有长泰、莆田、福州、南安、仙游、龙海、南靖各地,且莆田、福州超过2000人。参见《福建省华侨公(协)会调查呈报表》,《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70~78页。此份材料缺少晋江数据,因此难以对比最大数。仅时隔半年,数据却有极大差异,尤其是南靖县海外华侨协会,此处记载会员为1554人,而据《福建善救月刊》载,仅为63人。南靖县作为重点侨乡,华侨与归侨侨眷众多,且南靖县海外华侨公会成立于1943年11月,至1947年会员应远不止此数,且前者来自详细调查材料,因此更为可信。但总体上,会员人数基本上与各地海外华侨人数呈正比,重点县市之会员人数多一些。
(一)会员特点
归侨团体会员包括归侨、侨眷和少数海外华侨,以归国侨商为最多,他们曾侨居于世界各地,以东南亚为主。1938年,兴化海外华侨协会有会员98人,其中侨商达69人;1937年,仙游县海外华侨协会中,146名会员都是侨商且皆来自东南亚;1940年,南安县海外华侨公会会员607人中,579人为侨商。[12]
归侨团体征求会员的标准宽松,年满20岁有正当职业者、海外侨居满一年者、对侨民移植及保育事业有深切研究者、热心公益对华侨有兴趣者,皆可入会。简单的入会条件,使福建归侨团体吸纳了大量从未涉足海外以侨眷身份入会者,团体得到大规模发展。如南靖县海外华侨协会1554名会员中,普通会员(归侨身份)291人,特别会员(侨眷身份)1263人。[13]而对泉州华侨公会研究可见,前期,归侨团体的国民党不多,尚有少数在海外从事过教员的归侨;后期,本土力量对归侨团体的渗透加强,国民党人数在理事会及普通会员中的比例增加,理事会成员逐渐年轻化。③后期国民党对泉州华侨公会的渗透,参见骆曦的《民国时期地方华侨团体研究—以泉州华侨公会为例》,《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侨眷人数远超归侨,党员人数增加,这是入会标准宽松和政府加强管控的共同结果。归侨团体需要广泛吸纳归侨与侨眷成为其会员而壮大自身,而政府则希望通过党员对团体的渗透,加强控制。入会成员除享有团体一切权利外,还在兴办实业、归国、蒙冤或困苦时,可得团体援助。[14]归侨团体的承诺得以吸收广大归侨侨眷入会,但在实践中如何兑现上述承诺成为一大考验。下文将在分析团体日常活动中述及这一问题。
(二)组织结构
归侨团体内部组织结构完整,实行理事会制,属民间团体,不具行政效力,无政府固定经费支持。规模大的团体,开支消耗必然也大。团体经费仰给自筹,包括会员的会费、常年费、日常捐、特别捐、归侨捐助,部分侨团能获得政府补助。侨团经费常入不敷出,财政困难。如长乐县海外华侨协会经费岁入会员费123万元,而经费岁出办公费360万元。福州海外华侨协会等亦是如此,①福州海外华侨协会经费岁入200万元,支出却高达4800万元。此处疑有误。参见《福建省华侨乡(协)会调查呈报表》,《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74页。收支严重脱节。南安县海外华侨协会称该县区域辽阔,按月征收会费甚觉困难,所有开支由理事长、常务理事垫支。[15]财政上的困难,要求归侨团体领导人由有财力、有声望或具有较强社会网络的人员担任,这是传统海内外华侨社团的共性。
在福建不同层级的归侨团体中,跨社团的会员比例较高,理监事会成员具有较强连续性。南安县海外华侨公会第三届至第七届理监事选举可见,理事会成员连续性强,洪志超、柯敬宇、傅冰清三人由始至终均为理事。[16]这反映了团体领导层呈稳定状态,[17]或亦可说明领导层竞争力不大。[18]为抗战需要,统一领导机关,社团间实现了大规模整合。[19]1942年,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组织了全省性并颇具官方色彩的团体—福建省归侨团体联合办事处;1947年12月,厦门市归侨团体联谊会成立,该会由厦门市侨务局及部分归侨团体负责人组成。[20]归侨团体的联合是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源于政府力量的推动,体现了政府管控力量加强,通过整合社团来动员民众,团结抗战力量的意图。
三、渗透与控制:国民党党部介入侨团
(一)侨务系统与党务系统之争夺
民国初年,社团组织独立。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成立,开始注意对民间团体的领导与管理。1928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管理归国侨民团体办法》,“各省党部及特别党部管理归国侨民团体得直接商承中央侨务委员会,但须呈报中央训练部备案。”1934年2月,又公布《国内侨务团体组织办法》,规定“本项团体之指导机关为会址所在地之高级党部,其主管官署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1938年修正为,“本项团体之主管机关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指导机关为会址所在地之高级党部,但会址所在地高级党部关于本项团体组织之指导,应商承中央海外部办理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对于本项团体认为有纠正或撤销必要时,应函由中央海外部转指导该团体之高级党部办理之。”1942年,福建省通过了侨务团体备案办法,对归侨团体的领导机关及备案章程、会员信息等内容做出详细规定。[21]1945年,国民党中央五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行政院通饬施行,“凡属国内侨务团体,以社会部为主管官署,侨务行政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为目的事业指挥监督机关”。[22]
侨务系统与党务系统长期以来在侨务工作方面互相配合,[23]然而,二者分立造成的权利争夺亦始终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难题。侨务委员会虽然是侨民团体的主管机关,但作为所在地侨团之指导机关的党部却保持对归侨团体的主导权。厦门侨务局认为,“过去因缺乏联系,无从明了协会办理情形,难收督促之效”,借此请求社会部将各县华侨协会划归其与当地政府指挥,以发挥侨务行政之效。刘维炽②刘维炽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据既有规定,指出国内侨务团体经行政院决定社会部为主管机关,厦门侨务局的请求未获成功。[24]虽然在确认社会部为主管官署之时,也规定侨务行政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为目的事业指挥监督机关,不过党部系统对归侨社团更有话语权。即使早前社会部已由党务系统转移至政府系统,[25]其党部属性却不易改变。国民政府内部党务与侨务的分歧还延伸到地方社会中。1932年以后,泉州华侨公会重组过程中,公会分别在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和侨务委员会支持下分裂成两派,主任之位几易其主,皆受党部干扰掣肘,直至晋江县党部完全控制华侨公会。[26]福建归侨团体会址所在地之党部逐渐对其渗透并最终控制团体之领导层选举,海外侨务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党部将党务纳入侨务,[27]致使归侨团体内部产生纠纷。
(二)党部的渗透与控制
党部对归侨团体之渗透与控制,从成员身份可见一斑。理事会成员中,具有党员身份且担任福建省政府行政职务的成员在侨团理事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由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组织的福建省归侨团体联合办事处体现得尤为明显,该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有陈联芬(省党部委员)、丘汉平(省政府委员)、黄哲真(永安县华侨公会常务理事)、陈济民(前华侨联合会理事)、江秀清(福州海外华侨公会常务主席),以上均为党员。[28]会员中的党员人数日渐上升,一方面是源于海外党部中的华侨回归,另一方面党部渐占上风,得以渗透与控制侨团。
侨民团体从1928年起便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之重要内容,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归侨团体的增加及会员人数的增长,政府注意到归侨团体遍陈各地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风险,因此着手规范社团组织,限制其规模,并要求其呈请政府备案。
1938年11月17日,修正后的国内侨务团体组织办法规定,“除有特殊情形呈经中央许可外,不得在国内外各地设分支机关”。[29]但随着规模扩大,一些归侨团体请求允许建立分会,采用灵活方式管理社团。晋江县县长林逸生曾就华侨协会组织问题向福建省政府提出三点请求:(一)本县华侨众多,华侨协会会员数达千人以上,若照规定无分会组织,则管理联系困难滋多,可否准予设立分会及支部小组组织,抑或其他补救办法,并乞核遵;(二)华侨协会会员既多,整理成立大会时直接选举势不可能,可否采用通讯选举或代表选举,如代表选举名额如何规定,如通讯选举应否先行报准办理;(三)除县华侨协会外,地方侨民可否再有华侨联谊会或类似社团之组织,如地方确有需要可否视同公益团体准予设立,名称如何改订。[30]但无一例外被驳回。福建省政府称,华侨协会依法不得组织分会,如因会员众多无法管理,建议按照会员分布情形划分小组;否决通讯选举的请求;并称凡属该县海外华侨均得依法申请加入华侨协会为会员,毋庸另组其他联谊会等团体。[31]这些请求若得到准许,将使归侨团体具备自主权,中央机关难以管理,其权威也将有所损害。然而,分支机构却未得到有效禁止,南靖县海外华侨协会、龙海县海外华侨公会、仙游县海外华侨协会等皆明确领有若干个分支机构,其类型包括招待所、诊所、学校、通讯处等。[32]
此外,1944年1月31日,福建省社会处处长郑杰民签署了对现有归侨团体的会员身份进行审查并调整健全其组织的命令,其原因在于,福建执委会了解到归侨团体冗繁,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①“据报福建归侨团体几无县无之,甚至一地有同等性质之华侨组织达二三个之多,而主持之人有未出国门者,有仅往南洋为学校、报馆募捐者,故名为华侨团体,实则多为地方派别所利用,成为争权夺利之工具,而若干侨眷之痛苦竟至告诉无门,甚盼中央能在侨区设立机构,为侨民做主。”参见《社会处关于审查调整归侨团体训令》,《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63~64页。有些归侨团体首领借归侨团体之名行谋取私利之实,“假借公会名义,反向侨胞多方压迫”。[33]鉴于归侨团体泛滥的事实及其存在的弊端,1947年,政府撤销了龙海县海外华侨协会和闽海区海外华侨协会。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政府日益加强管理、控制和渗透,福建归侨团体仍得到极大发展,并由早期独立分散渐至有序。
有学者认为,“人民团体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对传统社会改造的一种手段,它是国民政府对社会重构的一种措施。”[34]党部对归侨社团的渗透与控制,正是在国民党初掌大权的社会背景下开始的。民国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央权威丧失和社会失范危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薄弱。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转为控制体制”,社团成为国民政府社会管理与控制的突破口。[35]而作为政府控制和改良侨乡社会的“中间人”,归侨团体的一些日常活动陷入困局。
四、归侨团体之日常活动
根据团体管理办法,“凡归国侨民团体须以关于侨民移植、保育事务为目的”。[36]1947年10月至12月,福建省对省内华侨协会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归侨社团所秉承之宗旨各有表述,但大同小异,普遍以“联络海内外侨胞感情”为宗旨,谋求侨胞福利,以侨民移植、保育事务为目的。福建归侨团体在日常活动中,大多致力于侨乡事宜,下文择要进行阐述。
(一)协助办理归侨出入国手续
20世纪上半叶,华侨出入国频繁。为管理侨务事宜,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增设第四科专管,[37]配合各侨务机构,但仍难顾及全面,亟需遍布各地之归侨团体协助办理。归侨常因无法提供证明而遭致出入国受阻,归侨团体除了负有告诫职责之外,尚需在归侨缺乏证明材料时予以帮助。然而,归侨出国手续成为归侨团体与政府冲突的集中体现,其症结在于福建省为防止逃兵役而在出国手续上设置障碍。
国民政府1937年国民工役法规定:“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男子,除本法另有规定外,每年均有服工役三日之义务。”[38]自全面抗战以后,为保证兵力,福建省政府宣布限制壮丁出洋,归侨壮丁出洋也因此颇受阻挠。福建省政府此举实不为限制归侨,而是防止当地壮丁假借归侨名义逃避兵役;且按照兵役法施行条例第二十七条,兵役适龄之男子,侨居外国三年以上者免常备兵役,而服国民兵役。因此,若归侨壮丁有旅外三年以上之证明者,“可准其出国重理旧业”。归侨出国所需材料包括中国驻外领馆登记证或回国护照与证明书;当地政府出口字;如无领馆地方,由该地中华总商会负责证明,归侨壮丁如具有上项之一证明者,可准其出国。但归侨向中国驻外领馆登记者少,侨居地政府亦有不发出口字者,且训令在地方上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实施。此后,侨居地社团与归侨相继报告各县政府各保甲等对归侨仍多有刁难。[39]1939年,永春海外华侨公会也曾因英属侨居地所发之出口字限期短促,向福建省政府请求准许归侨出洋。[40]
为地方势力留难归侨提供合法性的,便是出国证明书的存在。政府要求归侨提供出国证明书在于防止当地壮丁假借归侨名义出洋,须由当地保甲长证明其归侨身份。然而,归侨出洋便因此深受当地保甲长牵制,常被推诿延缓。永春与南安县海外华侨公会欲申请由归侨团体代替保甲长出具出国证明书,遭到省政府拒绝。[41]其间可见归侨团体角色之尴尬与在实际执行事务中面临的困境。福建归侨团体旨在为侨谋利,但因其受制于党部与政府,不仅内部不宁,且在政府决策与侨胞利益相矛盾之时,难以维护侨胞利益。幸而,因出国证明书弊端重重,致使华侨怨声载道,终于1942年由中央侨务委员会命令福建省政府予以取消。[42]
海外华侨公会致力于简化华侨出入国手续,提高效率,为华侨提供便利,亦可扩大自身职权;省政府则不会轻易下放权力,且另有顾虑,壮丁出国即意味着兵源流失,其时正值战祸频仍时期,政府对兵役一节殊为上心。归侨团体与政府的立场及角度有所区别,其服务对象为华侨、归侨侨眷,因此能为涉侨之事向政府提出建议陈请,为侨谋利。在侨乡社会不靖之期,其角色颇为重要,但前提是不抵触政府决策。
(二)请求与协助赈济侨胞
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华侨失业回国者众,厦门侨务局曾提倡“开荒自救”,但收效甚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以后,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福建沿海县市相继沦陷。侨乡沦陷给侨乡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侨汇中断,甚至因战争因素,遭民信局积压侨汇。[43]据1942年调查,福建省困难侨眷共有150万人,其中晋江县29万多人,南安县28万多人。[44]
生活困难之际,归侨侨眷还受当地政府非法摊派。各县区署暨乡(镇)长及保甲长,间有假借政府名义妄行非法摊派,稍不如意即行拘捕押缴。[45]永春县海外华侨公会常务理事郑世隐、苏智贞、郑振经曾请求降低该县出国侨胞所需缴纳捐款。[46]勒派现象屡禁不止,尤其是各乡镇保甲人员对禁令视若无睹,对归侨侨眷强行分配侨捐,且私扣政府救济金,归侨侨眷及各地归侨团体多次上诉,仍难以杜绝。在不安定时期,地方政权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上级政府也无暇顾及,难以深入地方掌控政局。
此外,因侨乡匪患未除,身在侨乡的归侨侨眷常因经济原因成为勒索对象,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匪患劫杀侨户不绝于史,现有档案中,保留着极多海外华侨个人或社团请求政府惩办匪首,以伸国法,以慰侨情的记载。如谢新谟及其党羽劫杀安溪侨眷刘惠民;晋江归侨苏义炮家为匪劫杀等案,不胜枚举。
归侨团体既然赋予其会员享有“如有枉曲不白事情,经本会调查属实得转呈政府申剖之;如有困苦情事,可得本会集合同志援助”的权利,因此在地方政府勒派侨捐、劫杀侨户屡禁不止的侨乡社会中,归侨团体须担负起归侨侨眷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二战期间及战后,社会救济成为当务之急。归侨团体的作用在于通过社团力量,动员海内外华侨及侨乡政府力量协助侨乡赈济,并传达侨眷困苦及向海外华侨申诉,请求政府救济贫难侨,将侨眷受到之不公正待遇传达于政府,请求予以调查及施予公正待遇。归侨团体也是海外团体筹赈后的资金对接者,同时监督救济金发放,以防被中饱私囊。但考虑到归侨团体之性质,对救侨效果须谨慎评估。
(三)协助与指导闽侨投资
不论是民国初立后民族感激发,还是太平洋战争后东南亚侨居状况的恶化,都推动着海外华侨将投资目标转向侨乡以及侨乡以外的中国广大适宜发展之地。归侨侨眷也将部分侨汇用于投资。
民国时期,侨乡匪乱是萦绕在投资建设和侨眷生活间挥之不去的恶梦,20世纪30年代,十九路军入闽后,对侨乡进行了较为可观的整顿,其功卓著。但因福建人民政府昙花一现,并未根本扭转侨乡的不安定局面,匪乱从未停止,华侨投资仍面临困难。此外,土豪劣绅、保甲长时有欺压侨胞眷属,宗族械斗之风也影响着华侨回闽投资之热忱。[47]一直以来,尽管侨乡投资环境不佳,或出于帮助侨乡建设、支援祖国,或被政府投资奖励政策吸引,或出于战后侨乡投资环境的好转,华侨对侨乡的投资从未间断。据1950年报告,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华侨曾投资于福建铁路、闽南私营汽车公司等,“侨资占百分之七十”。[48]
抗战时期对实业投资的需求增加,争取与指导华侨投资作为归侨团体的重要工作内容,包括联络海外华侨、归侨与侨乡,以保持信息通畅,倡导华侨回国投资,帮助他们了解侨乡环境,“代为调查设计指导并转呈政府之保护”,促进国内经济建设。1939年,澄海石角东海外华侨公会常务理事郑太奇、黄玉麟等人,为菲律宾侨商于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后创办龙溪私立四维农场向福建省政府陈仪转达请发通行证请求。[49]1940年,汪竹一、庄心在等人发起建立华侨经济建设协进会,倡导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发展国内经济建设,促进海外文化事业并加强各地华侨相互联系。[50]此项内容于抗战时期及战后对侨乡重要尤巨。
此外,福建归侨团体在侨乡创办学校、诊所,指导侨生回国升学,支持报业发展等,都是侨乡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归侨团体取得成效之体现。
五、结语
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为福建归侨团体的设立提供了可能,归侨团体发展迅速,并于20世纪40年代迎来高峰。但值得思考的是,由社会团体兴盛而断定“市民社会的发展”似乎不太准确,[51]这种兴盛也可能源于政府管控下的有序安排,是为控制社会而做出的主动性选择,政府希图通过渗透并控制归侨团体来控制侨乡社会。归侨团体与侨务机构立场、出发点不同,后者是政府的代言人,前者更贴近侨胞利益。福建归侨团体在出入国手续、侨乡救济与归侨侨眷的利益保护方面,积极参与;但囿于归侨团体性质及不具独立性,因此在侨务处理效率与主动性上略显不足,日常活动常受掣肘,其所能呈现之成效也难免乏善可陈。
政府在社会区域治理过程中,需要借助归侨团体作为“中间人”,在华侨、归侨侨眷与侨乡政府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但事实上,从会员组成来看,归侨团体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团体,侨商占据绝对比例;会员具有共同利益,但团体本身又不具备足够粘合力,成员流动性较高;政府虽利用其控制社会,但无法指望归侨团体的“控制力即凝聚功能能够持续”,[52]因此难以赋予它更大的权限。从另一方面来说,归侨团体的首要负责对象是其会员,团体活动也基本围绕如何实现其对会员的承诺,如差序格局一般,由这个中心向外推广,侨乡的全体归侨侨眷是归侨团体服务的次级对象。福建省归侨团体作为地域组织,其活动范围更多局限于侨乡事务,在具体事务处理中,鲜少超出侨乡之外。因此在实现沟通海内外侨胞情谊的宗旨及保育华侨中,实际作用有限。
归侨团体之困局,不仅源于其内在特点,也因于外部压力。党部控制归侨团体,旨在通过团体来控制社会。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中,政府对社会进行“保姆式”管控,[53]将归侨团体作为控制与改造社会的中间人。这就决定了归侨团体在协助处理涉侨事务中,处于附属地位,中间人之角色显得不间不界,致使其日常活动开展困难,成绩颇为泛泛。归侨团体存在着功能与角色难以发挥的局限,在政府日益强化管控下,普遍陷入有心无力的困境,始终未能突破政府的强势控制,这是民间团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注释]
[1] 徐天胎编著:《福建民国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2] 夏斯云:《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 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四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
[5]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86年,第91页。
[6] 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泉州市侨联志》,2012年,第369~370页,转引自郭瑞明编著:《厦门侨乡》,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7] [3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国内侨务团体组织办法》,《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8] 《厦门华侨公会奉令易名》,《华侨半月刊》1934年第48期,第32页。
[9] 《省府关于归侨团体名称应统称协会致各县市府代电》,《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65页。
[10] 《行政院关于归侨侨领及党部负责人应加入省临时参议会候选致刘建绪电》,《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111页。
[11] 《福建善救月刊》第5期,转引自《福建省各县市华侨协会及会员数》,《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68页。
[12] [14]《福建省海外华侨公益团体章程名册指导人民团体改选调查表及有关文书》(1940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社会部档案,档案号:十一/7422。
[13] 《福建省华侨公(协)会调查呈报表》,《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77页。
[15]《福建省华侨公(协)会调查呈报表》,《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70~78页。
[16]泉州市档案馆:《民国时期泉州华侨档案史料》,第6~10页。
[17]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领导层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8]王苍柏:《香港的归侨团体研究—以巨港(香港)校友会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9][27]陈国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团政策研究》,《八桂侨刊》2014年第1期。
[20]郭瑞明编著:《厦门侨乡》,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
[21]《福建省侨务团体备案办法》,《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41~45页。
[22] 《侨务委员会关于海外侨民团体及国内侨务团体划分管理办法的通告》,《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64页。
[23]张应进:《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外部的侨务工作》,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9页。
[24]《厦门侨务局关于国内侨务团体隶属关系的签呈及侨委会指令》,《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79页。
[25]陈长河:《国民党社会部组织概况》,《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6] 骆曦:《民国时期地方华侨团体研究—以泉州华侨公会为例》,《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28]《关于福建省归侨团体联合办事处成立的函件》,《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58~59页。
[29]《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国内侨务团体组织办法》,《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44页。
[30] [31]《福建省政府关于晋江归侨团体组织三点疑义的代电》(1947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11-009-006519。
[32]《福建省华侨公(协)会调查呈报表》,《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70~78页。
[33] [47]《福建省政府关于派秘书处王继禹宣慰侨眷的训令》(1942年2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3-000532。
[34] [51]杨焕鹏:《民国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东方论坛》2004年第5期。
[35] [53]宫炳成、刘会军:《大历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7]《省府为设立侨务科致海外侨胞函》,《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24页。
[38] 《南安县华侨公会提解释海外华侨家属应否受征服工役的呈》(1939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8-000621。
[39]《福建省政府归侨壮丁免禁出洋的训令》(1938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1-000376。
[40] 《南洋荷属泗水安溪公会、永春海外华侨公会常务理事关于备寄应摊赈济金、处理捐款、因居证限期短促请给出洋等》(1939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9-000780。
[41] 《福建南安县海外华侨公会第五届职员履表及福建省政府关于侨民出国证所有本会会员出国申请书拟改由本会证明》(1939年7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9-000784。
[42]《侨务委员会关于归侨出国不必再领出国证明书致福建省府函》,《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153页。
[43] 《福建省政府关于各县侨眷赈济的指令、代电》(1945-1948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11-010-007342。
[44]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45]《永春县府关于省府切实制止非法摊派的训令》,泉州市档案馆:《民国时期泉州华侨档案史料》,第424页。[46] 《福建省政府对永春县海外华侨公会呈该县出国侨胞缴纳捐款请依照晋江成例办理的批》(1939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9-000765。
[48]《厦门侨汇估计及其用途》,《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第441页。
[49] 《福建省府南洋侨胞慰问团活动简报及福建省政府秘书处有关侨务的指令、代电、函》(1939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01-009-000788。
[50] 《华侨经济建设协进会章程草案》(1940年4月—1940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社会部档案,档案号:十一/9011。
[52][日]村上卫著,王诗伦译:《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59页。
[责任编辑:乔印伟]
A Study of Fujian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of Republic of China
SHANGGUAN Xiao-hong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Fujian province;overseas Chinese affairs;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associations;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the Kuomintang par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Fujia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members’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Kuomintang’s penetration, the control of the associations, and its daily activitie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Fujia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umbers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rising. In 1930s-1940s, the foundation of associations reached its peak when conditions were mature. The largest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 associations wer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its purpose was to contact overseas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uses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s the “middle man” to build communication bridge among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spouses and the Qiaoxiang government. However, due to the loos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the Kuomintang party’s control,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re in a subsidiary position in dealing with relate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for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cannot be fully achieved and performed.
D634.2
A
1002-5162(2017)03-0084-10
2017-01-04;
2017-08-10
上官小红,女,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史、中外关系史。
*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课题“华人社团与华侨跨越侨乡心态的形成”之阶段性成果,受2016年度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2016GF034)与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侨乡研究博士论文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