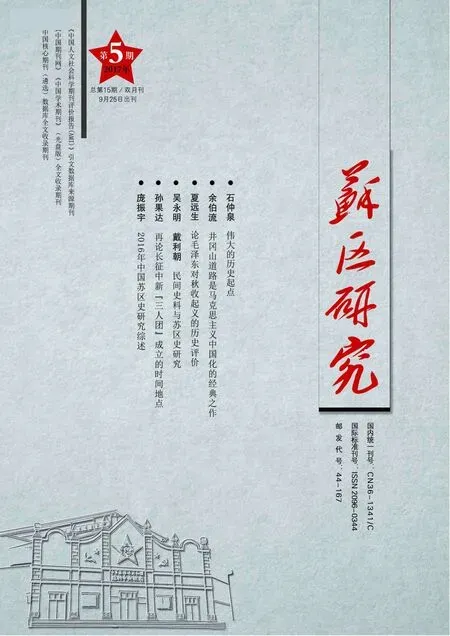伟大的历史起点
——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等三大历史事件90周年
伟大的历史起点
——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等三大历史事件90周年
石仲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奋起抗争,领导了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创建,最有影响的是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这三大历史事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伟大历史起点。探讨这三大历史事件的内涵和特质,对于理解党的历史和弘扬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历史起点;毛泽东
90年前的夏秋时节,神州大地血雨腥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一年多时间,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有2.6万人,革命群众近30万人。党员数量由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的残暴所吓倒。他们高擎革命大旗,带领继续革命的广大群众举行如火如荼的武装反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陆续建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三大历史事件。这三大历史事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伟大历史起点。
一、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时,是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就是这么个很不显眼的小党,却胸怀伟大抱负,要改变饱受苦难的神州大地面貌,用与以往仁人志士不同的办法来开天辟地。次年,中共制定出民主革命纲领,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前途;提出团结国民党等革命党派,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主张。
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发展到近200人,但要实现肩负的历史重任,显然不能单枪匹马,而需要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因为“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它成立得比共产党早好些年,党员数量比共产党多好多,而且党的影响也大得多。特别是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会晤发表联合宣言后,国民党的联俄、联共倾向愈益明显。国共两党都有合作意愿,关键在于以什么形式实现牵手。中共最初倾向于党外合作,但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经过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中共中央最后同意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既有利于改造国民党,使其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广阔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共产党员20多人参加,他们既参与了大会的许多重要筹备工作,又还有不少人被选入国民党领导机构担任若干重要职务。大会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共合作共同纲领。随后就开始了以发动工农群众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大革命运动。但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夺取了革命领导权,在北伐胜利进军途中,到达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接着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剥去“左派”外衣,发动了七一五事变。蒋汪集团先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对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工农运动高潮、推进北伐战争蓬蓬勃勃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大革命运动中唱主角的毕竟是“人高马大”、实力雄厚的国民党。它背信弃义,狠毒地将并肩战斗的同志投入血海。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诚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这就是以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三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武装反抗。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区域,创建苏区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红军,继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什么说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三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呢?
第一,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继续革命的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三大历史事件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进行的。面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束手待毙。为了求得生存发展、继续实现革命任务,不能不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独挑历史重担,实际上在七一五事变后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于是有了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后,就有了以湘赣边秋收起义为代表的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说“独自领导”,是就决策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而言的。至于参加者,当然有非共产党人。八一南昌起义之所以打着国民党旗号,并有不少国民党左派参加革命委员会,那是策略性的。因为孙中山还有很大的号召力,这样做便于团结更多的革命者继续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遗志而奋斗,同时也便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真面目。因此,决不能以打有国民党旗号来否认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
第二,尽管前些年已在宣传鄂南秋收起义的时间早于湘赣边秋收起义,但这丝毫不影响湘赣边秋收起义是当时农民武装起义的主要代表这一论断。八七会议确立武装起义总方针时,就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而湖北省委早在7月底已在酝酿发动鄂南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中央政治局3名常委中就有2名(瞿秋白和李维汉)参与研究此事,并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亲赴鄂南部署起义事宜。这样,从8月中下旬到月底,崇阳、通城、通山三县农军秋收起义点燃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烽火。它比中央规定的两湖秋收暴动的统一时间(9月10日)提前了半月左右,也比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早了许多天。
那么,是否因此影响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呢?丝毫不影响。因为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不是单纯以时间的早晚排座次的,而是对那个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综合评估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全国秋收起义进入高潮的标志。它无论在规模、声势和影响方面都比鄂南秋收起义大许多。特别是通过那次起义转移“上山”后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成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发端,并在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这是其他地方的起义都无法相比的。对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这一特殊功绩要充分认识,绝不能因为鄂南秋收起义时间较早,就贬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地位。过去对鄂南秋收起义的历史意义认识不够,现在加强宣传,可以认为鄂南三县秋收起义,同湘赣边秋收起义一起,都属于全国秋收起义最早的一批。但若选代表,当然还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所以,说湘赣边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不应当成为问题。
第三,不能因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去盘踞了袁文才、王佐等绿林中人,就否认它是我们党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摇篮。在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上山前,宁冈茅坪、遂川茨坪一带确是“山大王”袁文才、王佐的地盘。但袁、王是农民自卫武装。袁文才是宁冈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王佐是遂川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和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袁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出身贫苦,对地主豪绅有刻骨仇恨。毛泽东引兵井冈,结交“绿林朋友”,不是寄居袁、王篱下栖生,而是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改造这两支具有绿林习气的部队。不仅王佐本人入了党,他们的部队也改编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团。他们接受党的领导,按照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思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样,绿林地盘变成了红色摇篮。这无疑是党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历史起点的重要内容。
这里还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不将1927年4月至7月间广东党组织发动的海陆丰地区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二是既然共产党惨遭国民党屠杀,那么怎样看待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运动?
关于前一个问题,是因为那时大革命的全局形势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四一五事变属于局部反共。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武装反抗,从4月中旬到7月间,广东全省以海丰、陆丰和紫金地区为代表,约有34个县举行了40多次武装暴动,参加的群众共达8万多人,工农武装超过6万人,其中有近10个县还建立了有国民党左派和非工农阶级成分参加的县级革命政权,其声势不谓不大。但那时从大革命全局来看,国共还没有完全分裂。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七一五事变,才是国共两党全面分裂的标志。此前的广东“夏季暴动”,从大局意识讲,算局部事件。因而不好说是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
关于后一个问题。大革命运动后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这个结局,是最初决定国共合作时未曾料到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结论。因为共产党那时太弱小,不能单独担当已经明确的革命重任,而必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这是正确的。大革命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三大功绩。
第一,大革命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空前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党自身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投入大革命洪流:一方面,参加国民革命军,不畏艰苦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另一方面,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革命群众投身革命斗争。短短6年时间,共产党就拥有了5.8万党员,直接领导14个省地方党组织,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革命政党。
第二,党领导的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经受了政治洗礼,提高了革命觉悟。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不断高涨的湘、鄂、粤、赣等省的农民运动,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大革命的狂飙使党的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得到空前广泛传播。这场革命运动是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神州大地急剧展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对历史应当辩证认识。那种对大革命运动产生“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
二、独自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在思索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尽管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明确理念,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这种意识还是有的。比如,党的二大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前途,实际上初步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提出了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党的三大除作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这个战略性重大决策以外,还对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有益探讨。党的四大除了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经验教训,指出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开始成为党内主要危险的“右”的倾向外,还对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了探讨。即它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指出无产阶级不是附属于资产阶级而参加国民革命,应当保持自己阶级的独立地位,并且只有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得到胜利;它也首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参加,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必须充分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后者对推进大革命蓬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那时的党毕竟还处在襁褓之中。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有基本认识,但不明晰、不深刻、不具体。这集中体现在党的五大。这次在重大历史紧要关头召开的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思想,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能提出有效的具体举措,因而没能承担起在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重任。
为什么说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三大历史事件,开创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呢?
首先,八一南昌起义以革命实践回答了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核心问题——党一定要掌握革命武装。党积极投身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做了许多发动工农群众的工作,但一个重要缺点是忽视了掌握革命武装和开展党领导下的军事斗争。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党的五大不能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提不出如何建立党领导革命武装的具体举措,正是大革命以来这一缺点的充分暴露。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实际行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这不仅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而且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发展历程看,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要义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八一南昌起义掌握了枪杆子,就有了夺取政权的武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是先认识“武装夺取政权”,后认识“农村包围城市”。八一南昌起义开启了这个认识过程。所以,说它是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是符合党认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实际的。
过去有一种观念,认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没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不承认它是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端的内容。这是线性思维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验论者,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只能从实践探索中得到正确认识,不可能预先设定一个认知模式。在当时,党只有城市武装起义观念。就毛泽东而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的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是非打下长沙不可,而是打不了就掉转队伍上井冈,在反动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这是实践认识论。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尽管没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但在南下广东途中经过赣南闽西宣传的革命思想,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播下的革命火种,为一年半后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这些地区开辟中央苏区奠定了群众基础。此外,换一个思维方式,从另一种历史维度辩证地看待八一南昌起义的话,正是由于有了这次起义,以及此前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此后的广州起义这三大城市起义,都没有保住革命成果,才为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城市向农村转变,形成农村中心论,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奠定了历史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也是不为过的。
其次,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是孤立的三个事件,而是三位一体的燎原之火;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革命军会合,才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得以坚持和发展。八一南昌起义虽然在八七会议前举行,但它符合八七会议决定的总方针。湘赣边秋收起义是根据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发动的,同时党还发动了其他省的农村武装起义。从1927年8月至1928年8月的一年间,党至少在13个省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达200次左右,掀起了暴动风潮。在这200次起义中,湘赣边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之所以脱颖而出,就在于它不是一味地攻打县城、省城,而是攻打两个县城失利后,再无力攻打省城,即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另辟新径。这支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引兵井冈后,于1927年10月到11月间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到三河坝实行分兵,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打散。由朱德率领的部分起义军经过艰苦转战,又发动湘南暴动,于1928年4月带领这部分起义军(包括南下潮汕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支部队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军,大多是北伐时期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的,装备比较整齐,枪支近千支,优于其他各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师后,指战员由2000多人激增至10000余人;组成的红四军领导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坚持井冈山斗争,击溃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指战员也发挥着主力作用。所以,井冈山斗争的坚持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合力作用的结果。朱毛会师,标志着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大历史事件融为一体,揭开了党领导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历史新篇章。这是党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的先占领农村后占领城市的新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
第三,立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现在井冈山道路是网络的热词之一。但是,井冈山道路的内涵是什么,不仅一般读者不甚了了,就是一些宣传媒体和通俗著述的表述也不甚专业。不少人往往将井冈山道路说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其愿望是很好的,但这是井冈山道路的科学内涵吗?恐怕值得商榷。我不反对将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内涵重新定位,但是一定要有文本依据,要讲学术义理,不能想当然。
从我所接触到的史料看,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无论是全党还是毛泽东都还没有形成中国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思想意识。1927年秋冬以后,尽管各地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地不断爆发,但党的指导思想还是以夺取城市为中心,各地武装起义设计的目标模式是通过暴动攻占县城乃至省城,以为这样,革命就能成功。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产生了革命力量到哪里落脚安身的问题。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农村割据”主张。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到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是对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回答。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暴动割据”“农民割据”“农村割据”一类的主张,在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文件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中开始广泛使用。
但是,由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城市中心论,党的领导层对于实行“农村割据”一类主张有不同看法,乃至产生两次激烈争论。反对实行“农村割据”最有影响的是两个人,而且正是他们将“农村割据”一类主张称之为“以乡村包围城市”,认为这是错误的而加以指责。赞同和支持“农村割据”、认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可行的主张,也有两个代表人物。这里先讲第一次争论,它发生在1928年6月党的六大期间。先是夏曦在六大发言时将“农村割据”概括成“以乡村包围城市”,认为这是“农民意识”,主张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3天之后,在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发言,不同意夏曦的看法,明确表示应当实行“农村割据”。他认为中国革命有割据可能,南中国的几个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做割据局面的准备。
毛泽东远在井冈山,没有参加党的六大,不了解当时争论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回答了党的六大争论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这集中地体现在1928年10月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之中。这两文,一是提出了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概念,相比较于此前的“农村割据”一类提法,更能准确表达革命斗争的内涵和方式。这就是在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的三位一体思想。“‘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二是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日益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回答了创造割据局面的可能性。他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概括为“1加5”条,写道:“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这就是“1”。所谓“5”,是紧接着的下面一段话:“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页。这个分析比此前《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论述向前推进了。如果说这里“1加5”中的“1”带有“纲”的性质,那个“5”则属于“目”。而这里我们视为“纲”的“1”,在此前则是作为第一“目”来论述的。显然,这个提升是认识的很大进步。三是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的正确方针政策,包括深入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和武装帮助地方的党和武装;集中用兵,反对分兵,避免敌人各个击破;扩大割据地区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
为什么说这些思想还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明确党领导革命的重心在农村,没有确立农村中心论。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时就说的很清楚:“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页。这就是说,实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还是为了准备在将来湘鄂赣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必要的使命,而实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就是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
井冈山道路的内涵虽然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不伟大,也不意味着它比“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说法不光鲜。况且它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基础的“农村中心论”的必要前提,即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直接来源。两者只是“一步之距”。一年多后,毛泽东的思想就达到了这个新的高度。因此,说井冈山道路开创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起点,或者说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的历史起点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凡人物的特质。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做个奇男子。因而,他获得一个“毛奇”外号。其间,有几件“奇事”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一是在省立一中写论商鞅变法的作文,老师给予极高赞誉:“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在90多年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似还难以找出有此盛誉者。二是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注重考察社会,读无字书。“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邀同学利用暑假,步行千里,“游学”农村,作社会考察,了解广大民众的生活实况。此举被同学们赞之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三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学子有50多人,为全国来京之最。这是那时大规模出国潮的一波。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的组织者。他将好友一批批送走,好友也动员他一起走,但他却坚持先留在国内,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项工作,与其出洋回来后做,“不如现在做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个决定,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积极投身革命,在大革命洪流中崭露头角。但是,他的领袖特质却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显现出来的。他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的历史起点。
第一,毛泽东是将革命暴动从城市转向农村,乃我们党做“革命的山大王”第一人。毛泽东的“上山”设想早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已萌生。为了应对国共两党分裂危机,他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八七会议后,他婉拒瞿秋白,不愿到上海中央机关去住高楼大厦,而要上山交接绿林朋友。秋收起义爆发后,绝大多数起义的目标是攻打县城,唯有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是奉命攻打省城。起义军攻打县城已经失利,遑论攻打省城?毛泽东的高人之处正在于,不是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决定,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浏阳文家市决定退兵,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在那时200次的武装起义中,敢于冒着违抗中央决定的风险而做出“唯实”的决策,除毛泽东外似没有其他人。经过三湾改编和莲花引兵井冈,毛泽东开辟了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做“革命的山大王”的第一人。如他本人所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何长工:《红旗插上井冈山》,《革命回忆录》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在井冈山全盛时期,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和遂川等5县局部地区的这个不小地域的“山大王”,是他成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的历史起点。
第二,毛泽东后来概括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在井冈山时期实际上已初具雏形。1939年10月,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这三个主要法宝,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已初步炼就。尽管有的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正因为初步有了这三个法宝,才能开辟我们党的这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关于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最先遇到的问题。因为井冈山已有袁文才、王佐两个山大王,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这是直接面对需要解决的。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长工:《红旗插上井冈山》,《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0页。
毛泽东是我们党最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上井冈山做袁、王统战工作,是“小菜一碟”。那时袁、王都非常缺枪,没有枪支就没有战斗力,何谈占山为王?毛泽东与袁、王初次见面,就分别给了袁100条枪、王70条枪。袁、王见毛对他们以诚相待,又慷慨馈赠,非常感动,疑虑消除,即引毛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山,先后进驻他们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和茨坪。随后,袁、王主动请毛派人改编他们的部队。毛泽东决定实行团结、改造方针。这样,袁、王部队也成了工农革命军。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改编过的袁、王部队是红四军的主力之一。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谭震林等老同志说:“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毛泽东团结改造袁、王部队是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成功范例。
其次,关于武装斗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巨斗争,毛泽东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并作了初步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时,毛泽东鉴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叶挺每团只有一个支部,经不起严峻考验的教训,率先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从而保证了党对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朱德上井冈山前来会师后,军队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古田会议后,又发展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
——关于军队的宗旨和任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说: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个宗旨实际上源于井冈山时期。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首次出现“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和“革命成功,尽在民众”提法。*《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2、53页。随后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根据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帮助地方党和武装的发展、建立县区乡政权的工作的经验,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这些思想的缘起,还可以追溯至1927年底毛泽东在砻市宣布的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即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后来,毛泽东将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同时还是宣传队。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经过政治教育,都有了阶级觉悟,知道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军队政治工作包括对敌军的宣传。毛泽东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新来的俘虏兵,感觉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是两个世界。“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毛泽东还认为,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在红军内部,官兵平等。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是红军具有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后来,毛泽东等将军队政治工作提升为军队的生命线,并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概括为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
——关于军队纪律。1928年4月初,毛泽东为了迎接前来井冈山会师的朱德部,亲往湖南桂东,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条纪律是: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参见李自仁:《红军在沙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两年后,红军在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后又不断完善,使之成为人民军队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也有初步总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都不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4、81页。这些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发展的最初基石。
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尽管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已经逐渐形成。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大规模战争的进行,其思想日益丰富和完善。如周恩来所说,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思想,正说明他是人民军队伟大统帅的历史起点。
再次,关于党的建设。我们党成立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却提出了丰富的党建思想。作为对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系统总结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初步形成。邓小平指出:“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历史起点。
一是关于思想建设,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任务。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一年后,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给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了的。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据此,他列出了8种错误观念,逐个地论述了每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就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言,明确提出:一要反对主观主义。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二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加强教育,说明绝对平均主义的危害和实际生活中的不可能;另一方面,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三要反对享乐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等个人主义思想。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同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改善物质条件。
二是关于组织建设,初步地但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党的组织建设任务。在井冈山初创时,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党组织大发展,许多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但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于是,1928年9月后,开始“厉行洗党”(即整党),着重于组织上的清洗和整顿,党员重新登记,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同时,也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这样,“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页。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整党运动。《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组织建设经验,首先明确提出“党的组织路线”概念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三大举措: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三湾改编时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不仅是建军的重要原则,而且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有重要意义。为了使党员参加支部会有兴趣,提高会议质量,《决议》要求要使与会者明白会议的意义,强调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反对空论,发动与会者的心思才力,从而激发党的战斗力。这些要求对于提高党的基层组织会议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二)首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条件。为了解决在红军中入党太随便,使党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倾向,《决议》根据在井冈山洗党的经验,提出对不够党员资格经过教育不改者“一律清洗出党”外,第一次提出了“新份子入党条件”。*它有5条: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当时规定这一条,是因为红四军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旧军队改编过来的,吃鸦片、赌博的坏习气带到红军中和党内来了。为了杜绝此等恶习,不能不将此作为入党条件之一严肃提出。条件的规定很朴实,是根据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后来的入党条件比那时表述的更规范,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三)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极端民主化倾向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决议》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由此必然走到革命失败。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这要求党的指导机关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以建立领导的中枢。这一条旨在说明,有了正确的指导路线后,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毫不留情地与极端民主化现象作斗争。
三是关于作风建设,初步地展现了党的三大作风的基本内涵。当时没有提出党的作风建设概念,但事实上存在作风问题。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包括纠正不好的作风。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作风问题比较突出,否则不会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决议》初步地提出了后来明确的党的三大作风。
——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的初步内涵。首要一条,是确立并坚持实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那时党内普遍存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上级领导下车伊始,一些决定、命令不符合客观实际,但要求下面绝对执行。下面不少干部对上级领导特别是中央指示带有盲目性,以为上面的指示一定是正确的,也形式主义地机械执行。这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致使井冈山斗争在1928年先后遭受前往湘南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有鉴于此,1929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一封信中已使用“思想路线”概念。半年后的《古田会议决议》,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评,就包括前述“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又过半年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进一步批评了那种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表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已初步形成。
——关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的初步内涵。在井冈山时规定严格的组织纪律,就是为了纠正侵犯群众利益的不良行为,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龙源口大捷后,永新县完全处于红色割据之下。这里人口稠密、特产丰富,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复杂,有利于造成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提出“大力经营永新”方针,要求红军短期分兵,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他本人深入塘边村,在贫农家住,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并领导当地群众建立政权、发展赤卫队等组织、开展土地革命。该县各项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年半后的《决议》指出:红军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任务;否则既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既是批评单纯军事观点,也具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普遍意义。《决议》还明确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见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48-549页。尽管正式出版的“毛选”,将“路线”二字删去了,但它说明当时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实际上提到了群众路线的高度。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的初步内涵。在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正确开展,致使党内、军内领导层的一些认识分歧没能解决,在下山后的转战中还加深了领导层的裂痕。红四军七大、八大没有开好,就暴露了这个缺点。在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了鲜明支持态度后,九大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开展批评要注意政治,分析“主观主义的批评”主要表现为:将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无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决议》指出:这样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或者使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决议》要求坚决纠正,指出开展正确的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积累的革命经验异常丰富。他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主要法宝在此已见端倪。
第三,毛泽东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实践开拓者和理论阐发者。这里先介绍中央第二次争论的情况。这次争论发生在1930年春夏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那时,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战争,另一方面各地武装起义后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在全国许多地区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它遍布赣、闽、湘、鄂、桂、粤、豫、皖、浙等9省7片。但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李立三不断发表文章,声称“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没有中心城市和产业区域的罢工高潮,“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并批评“朱毛和鄂西红军还不十分了解红军集中进攻的策略,还多少存留着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是忽视城市工作的重要,农民意识的表现”。同时,中央还致信红四军前委,批评四军关于“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观念是“极端错误的”,“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这时,不赞同李立三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何孟雄和周恩来。何孟雄以周子敬的名义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不赞同李立三的看法。他指出:现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比城市工人运动快得多,“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中为好”。“若是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现在既然做不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平衡地发展,“为什么不可以暂时放弃城市而以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呢?”*以周子敬的名义写的文章,发表在1930年5月24日出版的《红旗》第104期。他的这个意见没被李立三采纳,但所表达的党的工作应以农村为重点,先占农村,用乡村包围城市、封锁城市、进攻城市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应当说,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观点的最早雏形。
周恩来也不赞同李立三的意见。他早在1929年审定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中就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在1930年春离开上海中央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途中,他在德共《赤旗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又强调在中国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义。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批评周恩来的意见是与中央路线不同的“割据观念”,待他回来后再开展斗争。但是,周恩来的观点却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这样他们才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在周恩来回国后,经过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以农村工作为重点的思想在全党明确起来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没有参与中央领导层的争论。但是,他在井冈山的实践斗争,却对推动党中央的认识转变,确立“农村中心论”思想发生着重要影响。因为周恩来在中央分工一直主管军事斗争,非常关注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的斗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认识多有互动,上述中央“九月来信”就是一个生动典型。不仅如此,立足于“农村中心论”基础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战斗在一线的毛泽东,可谓是这条道路最早的实践开拓者和理论阐发者。
说毛泽东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实践开拓者,是因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立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井冈山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井冈山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先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井冈山道路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如前述,井冈山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因而,毛泽东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实践开拓者。
说毛泽东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理论阐发者,是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我们党最早明确党领导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从而有了农村中心论指导思想的理论文本。毛泽东那时的思想发展很快。1929年1月,他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在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一年多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相比较,思想有了明显的飞跃。
第一,该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即不再是单纯地论述红色区域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件事,而是通过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将农民斗争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新的境界,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第二,该文既批评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也批评了犯着革命急性病的盲动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对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作了不切当的估量。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中国革命主观力量要作正确估量,认为现在虽然弱小,但其发展是很快的,“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提出必须反对单纯地流动游击思想,确立有计划地建设根据地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98页。由此,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特点的正确分析而对中国革命在农村发展具有的长期性和必胜信念的新认识。
第三,对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高瞻远瞩的科学估计,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空洞之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高度的政治定力。该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农村中心论的思想,但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的新认识和充满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说明其思想深处已蕴含着农村中心论。它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最早的理论基石。后来这一革命道路理论,也在毛泽东的著述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阐发。因此,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早的理论阐发者。
90年过去了,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三大事件已成为历史。但是,这三大事件的革命精神却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弘扬三大事件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继续为实现党的理想和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Abstrac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ose up to fight, and led the armed struggle,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e areas. The most influential events were the Nanchang upris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se three historical events created a great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lone, to explore the revolutionary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begin Mao Zedong's lea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historical event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Chinese revolu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olutionary road; historical start; Mao Zedong
责任编辑:何友良
GreatHistoricalStartingPoint——The90thAnniversaryoftheEstablishmentofJinggangshanRevolutionaryBaseAreaandOtherTwoHistoricEvents
ShiZhongquan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5.001
石仲泉,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