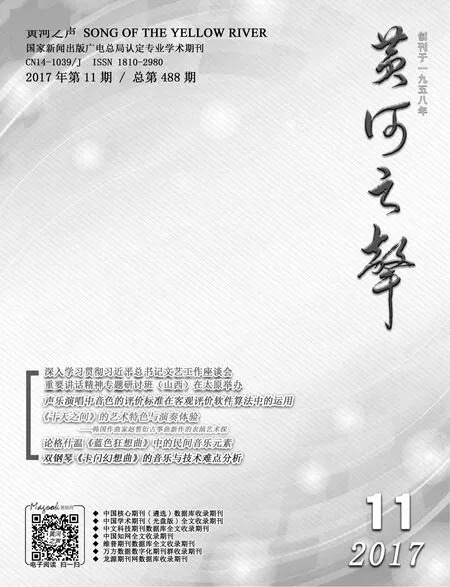《西藏素描》中的藏族音乐元素探析(一)*
缪函格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西藏素描》中的藏族音乐元素探析(一)*
缪函格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本土音乐家对于传统“地方性”音乐元素的日益关注,西洋作曲技法与传统作曲方式的不断碰撞,中国艺术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多产年代,出现了许多具有少数民族音乐特色的优秀钢琴作品,其中,崔炳元的钢琴组曲《西藏素描》就是极为经典的一部作品。其第一乐章“谐——牧歌与对歌”以藏族民间歌舞元素为主导,结合“中西相容”的现代作曲手法,向人们生动诉说了川西藏区的民俗故事。通过解析此曲的创作背景、音乐本体及演奏要点,我们既可以深入剖析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并对藏族音乐元素应用于钢琴音乐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关键词:《西藏素描》;藏族音乐元素;“谐——牧歌与对歌”;音乐本体
崔炳元曾说:“作为音乐家,在你所处的环境中,所有的文化事项都有你的参与与介入,甚至有你的主导,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用自身的创作影响所在区域的艺术发展。”[1]在他的言语中,我们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出他对中国“地方性”音乐元素传承的关注,以及对这类音乐创作的热情,本文所论述的《西藏素描》“谐——牧歌与对歌”正是他将地域文化与钢琴创作相结合的一首上乘钢琴小曲。
一、“谐——牧歌与对歌”创作背景
崔炳元,国家一级作曲家,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他与王洛宾、赵季平相识相交,并受二人影响与西部音乐结缘,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也与中国西部密不可分。本文所分析的“谐—牧歌与对歌”就是崔炳元为川西高原而作。
(一)藏族音乐风格特色
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的西南地区,宽广辽阔,属于多民族文化的集合体,是拥有极深文化积淀的地域。身在这片土地上的西藏人民,生性豪迈、自由随性,常以歌舞为伴,以游牧业为生,所以结合地域特点、人文情怀等因素,随之产生的音乐就常常以空旷嘹亮、纯粹朴实、宗教色彩强烈为显著特点。其中“谐”作为藏族地区的一种音乐形式,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谐”是西藏民歌的一种体裁,西藏民歌一般分为两类:“鲁体”和“谐体”,“谐体”民歌是以每首四句、并带有伴舞的歌唱形式呈现。[2]第二种“谐”是主要流传在藏族民间的圆圈舞蹈,以集体歌舞的形式为主,分为“果卓、堆谐、果谐、康谐”四类。[3]而针对“谐——牧歌与对歌”来说,笔者根据崔炳元描绘“第一乐章‘谐——牧歌与对歌’,这是一幅富有诗意的高原的咏唱,空灵而婉转。”[4]以及藏族民歌根据内容又可细分为劳动歌曲和生活歌曲,其中劳动歌曲中所包含的牧歌(山歌)、爱情歌、风俗歌、诵经歌等形式,其中牧歌音域宽广,节奏自由,旋律起伏大等特点,与“谐——牧歌与对歌”旋律特色极为类似,因此笔者推断这首作品应该偏向于西藏民歌的一种题材。
(二)“谐——牧歌与对歌”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界掀起了一场民族钢琴音乐热潮,《西藏素描》应时而生,它是崔炳元在1984年去西藏采风时有感创作而成,当时还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崔炳元,在西藏采风归京后,被那片黄土地上的人事物景深深吸引,便萌生了极强的创作欲望。然而,在那个年代所产生的钢琴音乐早已渐渐度过了漫长的探索时期,突破了直接借鉴、空有其表的作曲模式,当时的作曲家们将东西方作曲方式融会贯通,并以最自然的方式谱写乐曲。《西藏素描》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其中所植入的藏族音乐元素,展现出地域文化意蕴和西洋击弦乐器独特魅力,都使其成为了中国80年代大文化背景下的一次成功见证。
二、“谐——牧歌与对歌”音乐本体
《西藏素描》是崔炳元创作早期的钢琴作品,它以民族调式体系为创作基准,通过多变的和声支体和创作手法,显示出这首乐曲的藏族音乐韵味。此部分笔者将通过对其第一乐章“谐——牧歌与对歌”的音乐本体进行分析,借此来思考藏族音乐元素对崔炳元的音乐创作有何影响,以及对其表现音乐有何价值。
“谐——牧歌与对歌”结构笼统上讲是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为多调性,主要以C宫、F宫、D宫之间的同宮系统内的调性转换。呈示部(第1—21小节)由第一主题a(第1—4小节)以及三次衍生变化组成,此部分集音域跨度较大、节奏平缓、速度随性自由等特点于一身,以此呈现出一种宽广悠扬的旋律色彩,让人直接感受到一股浓郁的西藏风情。除乐曲衔接处,呈示部的第一部分及其变化,作曲家均使用了三行记谱方式,在高音声部,以“mi、re”和“sol、la”为动机和弦以非三度音的形式叠置,并通过级进式的和声连接进行开放式排列,赋予了乐曲浓烈的西藏神秘色彩。而这两组中高音区的琶音背景通过改变节奏音型不断重复变化展开,加之在小字组和大字组之间不断游离的低音旋律,都完美奠定了乐曲高原民族牧区音乐的整体基调。特别要注意的是,主题的音高材料均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就拿全曲和弦首音来说,出现了C宫调式中的所有音“do、re、mi、fa、sol、la”,创作技法上作曲家还运用了三连音、五连音、六连音、前倚音来润色主题,这都为作品注入了更为纯正的“藏族味道”。
第20—23小节作为乐段之间的连接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为给展开段做好导入准备,最明显的标志就在于呈示部的三行谱变为两行,节奏也由原先舒缓悠长的气氛跳出,过渡到跳跃灵动的旋律。第22小节进入乐曲展开部,共30小节,E角调式。此部分整体的音乐风格与呈示部宽广自由的感情色调相较,节奏感更为强烈。左手伴奏和弦从过渡句开始就一直延续呈示部“sol、la”为核心的动机材料,营造一种载歌载舞的藏族音韵。从整个谱面上看,展开部大致是由新主题b及其三次发展变化组成,其中在b1之后曾出现5小节的短暂新材料c(第34—38小节),之后又再次回到b主题,在此部分,在主题旋律上,作曲家以小幅度的二、三度级进、四度小跳和倚音加花等手法,除了运用装饰加花、移调变化、高低音区主题对应,主题分裂展开等作曲技巧,将藏族民歌中节奏简练、装饰性强、曲调婉转、线条流畅、动力十足的音乐特性都表现了出来。
再现部(第52—71小节),从51小节“mi、re”和弦自然过渡,旋律从欢快的情绪又回归至乐曲起始的主题旋律,在此部分,作曲家截取呈示部和展开部的旋律材料进行创作,并应用综合再现和缩减再现的手法,将谱面回归至呈示部的三行谱表,左手仍然延续展开部的伴奏织体。在第57—62小节中,作曲家加入6小节的b段主题,这种做法不仅有效避免了旋律过于重复单调的创作问题,也成功缓解了听觉疲劳,恰到好处地加深了主题旋律。在呈示部主题渐慢再次出现之后,作曲家以原速的大连线下行琶音将旋律推向尾声,在四分音符“re、la、#sol”的三连音形式和延长音“mi”上,将整条旋律线拉长,最后以藏族曲调中常见的减五度和声音响,将音乐停止在D徵调式之上。
三、“谐——牧歌与对歌”演奏要点
如何解读作曲家心目中的“谐——牧歌与对歌”正如崔炳元所说:“只要作品具有审美价值,演奏者认同他的审美逻辑,肯定它的价值,在这个共同的坐标上向前走,怎么走怎么说怎么演都不为过,经演奏者二度创作后展现出来的作品风貌与作曲家不一样,这太正常不过了。”[5]这首作品在陈述方式上属于标点俱全的乐段式写作手法。乐曲呈示部属于中国传统民乐中常用的“散板”节拍,展开部第二主题则是通过八分音符柱式和弦与主题旋律声部的两手交替形式,来模仿藏族民歌中的对歌。因此,针对两个主题旋律的触键音色、节拍节奏方面,笔者将如下做出重点阐述:
触键音色:在乐曲呈示部主题旋律中,作曲家运用了两个琶音和弦来表现出缥缈神秘的音响效果,谱写的是一幅蓝天绿草、经幡飞扬的高原美景。演奏这两个和弦时,要注意音符的准确性,两手由低至高同时逐个进行,下键要轻避免音量过重,要时刻控制在“mp”力度上。在下键前,因为整体旋律处在高音区以及琶音音型的演奏要求等因素,要求演奏者腰腹、手臂和手腕手型都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手臂要相对放松,肩膀下沉,用大臂带动小臂,灵活运用肘关节推动,并将力量传导集中至指尖,通过手指惯性带出音符,避免手指敲击下键而形成过于颗粒的音响效果。其中小指在波音演奏时要避免过于下力,在演奏前掌关节需提前做好准备,将重心稍稍前倾,下键时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轻巧的感觉。展开部主题对应的是藏族民歌中的对歌,旋律声部在高低声部之间不断转换,在演奏旋律声部时,为营造热情的“对歌”风格,指肚下键要求偏深偏沉,来很好地传递力量,手指通过敲击式下键,带来干净颗粒的音质效果,伴奏声部也要时刻保持稳定性,控制指尖下键力度,避免喧宾夺主。
节奏节拍:在藏族民间音乐中主要可分为散板式音乐和有板式音乐。[6]“谐——牧歌与对歌”中就包含了这两种音乐类型,所运用的节奏组合也将不同情境的西藏表现得淋漓尽致。乐曲呈示部主题即描绘藏族独特的散板音乐风格,弹奏这条旋律时,左右手琶音弹奏上文已经有了详尽说明,仍需注意每次旋律出现手指尖下力都需逐次加强,从弱至强制造层层递进的情绪攀升,并注意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节奏转换。下声部短小零碎,要利用指尖、手指站稳,切忌“滑音、跑音、吞音”,而在演奏倚音与和弦外音时,只需依靠手指惯性,通过指尖自然引出音符。在低音旋律声部中,多连音节奏型出现得极为频繁,因此在演奏中,要利用指腹触键、注重音头、手腕下沉,并利用小臂带动后续音符的连贯发展,营造出一种牧歌对唱的感觉。展开部,作曲家采用了规整的两个八分音符为一组的伴奏音型,来模仿中国打击乐中的鼓点节奏,演奏时手腕放松,肩膀重力下沉,掌关节保持手型和指尖用力。旋律声部要注意小连线的呼吸感,以及要根据不同的音符时值来调整乐句的演奏力度。
四、结语
在《西藏素描》中,作曲家不拘泥于传统编制,积极地开拓新的音色组合,拉近了作曲家、演奏者和欣赏者的距离,扩宽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通过上文,笔者对《西藏素描》第一乐章“谐——牧歌与对歌”的创作背景、音乐本体及演奏要点的论述,可以发觉,崔炳元是通过这首钢琴音诗来抒怀叙事的,它融人文思考、地域情怀、音乐语汇于一体,既打开了中国传统创作的思维模式,又扩展了钢琴演奏技巧的可能性,予以听众不一般的西藏体验。在传统民族音乐探索的道路上,这首小曲的成功问世,可以说是崔炳元在音乐创作中融入西藏音色特点成功尝试的第一步,也为其后来的音乐探索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麟曾这样评价过崔炳元的音乐创作:“是西部秀美的山水和风土人情养育了崔炳元的生命,养育了他的音乐,更养育了他丝丝入扣的西部情怀[7]而恰恰也是这一首首满怀作曲家情怀的作品,点亮了他的世界,吐露出崔炳元内心对祖国大地最诚挚的热爱和对民族音乐最向往的追求。■
[1] 刘蓉.只为追寻音乐中的沧海一粟——崔炳元访谈录[J].音乐天地,2015,02:55-59.
[2] 吴晓韬.钢琴曲秦俑中的陕西地域音乐风格探析[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02:140-145.
[3] 王江波.钢琴组曲西藏素描的分析与演奏[D].河北师范大学,2011.
[4] 徐雁来.键盘上舞出的藏族音乐[D].西安音乐学院,2010.
[5] 张巍.藏族音乐元素在钢琴组曲西藏素描中的运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6.
[6] 陈哲.崔炳元钢琴作品秦俑的创作及演奏探析[D].西安音乐学院,2016.
[7] 苗文青.崔炳元钢琴作品的演奏技术探析[D].西安音乐学院,2014.
2017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地方性”音乐元素对中国钢琴音乐之影响研究》研究成果(CX2017B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