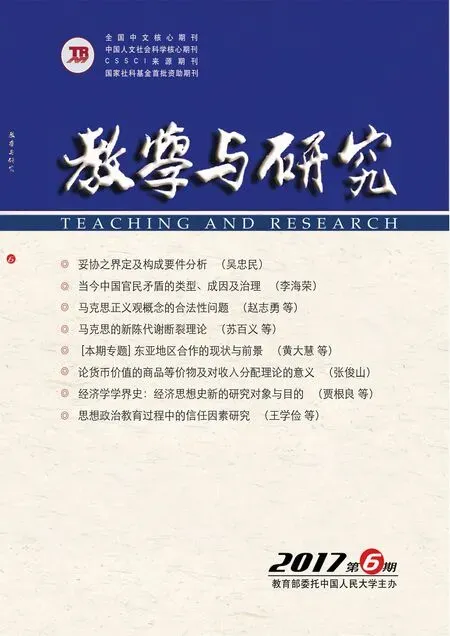经济基础、民主促进、非正式制度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个分析视角*
费 钧
经济基础、民主促进、非正式制度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个分析视角*
费 钧
农村公共物品;经济基础论;民主促进论; 非正式制度
本文主要综述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的三个分析视角:经济基础论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取决于村庄经济发展状况;民主促进论认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提升了公共物品供给的绩效;而以宗族网络、文化惯例和社会资本等为载体的非制度因素也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产生影响。上述三个视角代表了学界对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的主要思考进路,不过它们各自存在一定的不足。
尽管依照国家《宪法》和《村民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地区以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为载体,实行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公共物品供给是有关村庄治理中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广大农村并非完整意义上“自治”的单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中,国家税费制度改革、乡村行政组织的变迁、干部管理体制的调整等都在深刻影响着作为基层自治单位的村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也为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研究既成为一门“显学”,同时又是一个存在众多学科交叉的讨论话题。这其中,由于不同学者所属学科领域的差别,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研究也存在不同的分析进路。
从现有中国农村公共物品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供给现状和理论分析两类:一类研究的重点是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供给绩效以及供给模式等主题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措施*参见张鸣鸣:《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检验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邓蒙芝:《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绩效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冯华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一类研究则关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尝试从理论上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进行解释。当然,理论研究大多需要建立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本文主要是归纳现有理论研究中三类具有代表性的分析视角,并反思这三类分析视角存在的不足。
一、经济基础论
经济基础论认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这个视角之下,已有研究分析了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村庄的经济收入水平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性;二是农村税费改革对公共物品供给所产生的影响。
(一)经济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从经济收入水平来看,似乎在村庄经济条件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例如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相对富裕的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工商业活动多的村公共投资活动及投资水平也相对较高。[1]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乡镇一级财政是最基层的财政组织,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资金主要依靠自筹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去集体化”的政策变动下,中国农村原依靠集体公社来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失去了基础。在政府对农业投资和公共物品投资削减的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越来越受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2]
在“更高的经济收入水平”与“更好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得到了相关研究的验证。例如约翰·奈特(John Knight)和宋丽娜(Lina Song)发现尽管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去集体化,但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增加了在卫生保健上的需求和消费,农村的卫生保健状况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恶化。[3]但是其他研究却对上述推论提出了质疑。例如蔡晓莉(Lily Tsai)的研究就发现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却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她认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重点在于是否存在问责机制来将村庄收入转化为公共物品支出。如果缺少问责机制来确保资金的投入,很有可能出现违背上述推论的情况。[4]同样,庄玉乙和张光的研究也发现财政收入较高的地方政府并不一定会确保公共支出的高比例。一些资源丰裕地区的地方政府对教育、环境保护、医疗社保等社会民生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但是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则明显高于前者。[5]
(二)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自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在全国各地区推广。进行税费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由农村税费征收所激化的“干群矛盾”,但是税费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的状况,这也使得税费改革在事实上造成了既积极又消极的后果。
税费改革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田秀娟和周飞舟对湖南省2个县市8镇16村350余农户进行了抽样调查,他们发现农村税费改革使该地区农民的负担总量下降了1/4左右。[6]贺雪峰和罗兴佐对湖北省荆门市两个镇的调查同样发现,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另外,税费改革后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建立在公共财政和农村社区基础之上,这还增强了农民的自主性。[7]
不过更多的研究则发现税费改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集中体现为乡镇一级财政收入的减少,使得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了困境。[8]根据中央制定的政策规划,税费改革后公共开支的财政亏空可以通过国家转移支付来弥补。但由于相关配套改革措施未能跟进,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给县乡财政的支持难以弥补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缺口,从而影响到农村公共品供给。[9][10]例如研究发现在税费改革后,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乡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公共卫生等等的投入都不够,其中尤以农村基础教育为甚。[11]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却对农村公共投资产生了短期负面影响。[12]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围绕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物品所产生影响的讨论,普遍表达了担忧的态度。从政策设计的主要目的来说,税费改革可能有利于减轻农民原承受的税费负担,但是这种成功必须建立在中央政府加大财政资助的前提之下,如果不进行财政再分配制度的根本性改革,现有的税费改革可能是伤害而不是帮助贫穷的农民。[13]
二、民主促进论
民主促进论的分析重点是民主选举及问责机制的完善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效应。在西方民主国家,对民主制度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关联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艾迪特(Aidt)、杜塔(Dutta)和洛克伊安洛娃(Loukoianova)三位学者考察了1830年至1938年西欧国家公共开支与民主扩展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随着选举权覆盖面的扩大,国家对基础设施与国内安保的开支也同步提升。[14]阿萨特里安(Asatryan)和威特(Witte)以德国巴伐利亚州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直接民主制改革为例,发现当公民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时,政府会更加负责的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15]民主选举成为一种提供公共物品的交换过程。当执政者无法满足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之时,选举确保了一个相对安全和低成本的途径来罢免现任官员。而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地方政府必须确保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16]
在此进路下,中国农村研究的许多学者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村委会选举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持有较为乐观的看法:其一,民主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的公共支出份额,并减少了行政支出份额。其关键在于在村庄所进行的选举强化了对乡村的问责机制。[17]其二,从公共投资的分布状况来看,村委会主任直接选举可以有效地促进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增加。[18]其三,中国的村庄选举对农村的基层治理具有显著的选举效应。民主选举的积极效应清晰地体现在选举能够增加村级公共品供给、减少管理费用和增加公共支出的比例几个方面。[19]当村委会主任是直接选举产生时,相对于非其他方式产生的情况,民主选举能够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而选举与公共物品投资之间相关联的机制在于村干部谋求竞选连任。[20]其四,村庄层面“一事一议”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的创新也为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创造了渠道。[21]
但是,也有研究者质疑民主选举是否真正提高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村委会选举与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研究认为单靠选举不一定能增加村账务支出中公共投资的比例(相应地降低行政开支的比例)。只有真正实现决策权分担以后,公共支出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例才会增加。这是由于选举只代表了村民的参与,而实际当选的干部是否有决策实权,才是影响公共投资比例的关键。[22]只有当村委会的决策权力是分享型时,即主要决策在村干部间进行商定的情况下,民主选举所带来的公共投资比例才显著增长。[23]此外,宗族势力的强弱也影响着村庄的选举,进而影响着村庄的治理绩效(公共物品供给)。对于村庄的治理绩效而言,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强的村庄,如果只存在宗族而不能引入民主,那么宗族的治理绩效并不会太好。同样,那些不存在宗族的村庄,仅仅引入民主是不够的,仍然需要其他形式的非正式的民间组织,才能更好地增进治理绩效。[24]
尽管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在中国农村进行了30多年的实践,相关的法律与政策也在不断完善。[25](P147-164)不过总体而言,村委会选举的民主化程度并不高,村庄治理一方面受到上级政府(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制约。在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的乡村社会中,农民并不能对村干部进行有效的约束,这样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往往形成“供给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也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错位。[26]
三、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它们并非经过人们有意识的设计,而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27]在近期对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中,宗族网络、文化惯例和社会资本等非制度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非正式制度代表了一种非正式问责机制,这使得村民具备了监督村干部履行公共物品供给责任的渠道;其二,非正式制度提供了由社会组织或个体自主供给公共物品的条件。
(一)对村干部的非正式问责
与村委会选举、村民理财小组、岗位责任制等正式问责体系不同,非正式问责(informal accountability)关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乡村干部履行公共物品供给责任的影响。一方面,非正式问责提升了乡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的主动性。肯特·詹宁斯(M. Kent Jennings)发现当乡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往联系时,这一“嵌入性关系”将使得村干部倾向于满足村民的需求。[28]此外,村干部还会受到村庄内非正式组织的监督和约束,例如在宗族传统保留较完善的村庄,其公共物品投资水平明显高于没有这些组织的村庄。陈捷和呼和那日松以乡村干部的“社会嵌入性”作为标准,发现乡村干部的宗族组织的成员身份和参与度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正面影响。乡村干部在社会宗族组织和其他社会网络中的嵌入度,增强了非正式问责,进而提升了供给公共物品的动力。[29]
另一方面,非正式问责机制也使得村干部具有了社会动员的权力。例如在宗族社会中,村干部可以利用宗族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来进行资源动员,此时的非正式制度诱使村民配合村干部的公共投资。[30]其关键在于来自最大姓的村主任可以利用其在宗族中的相对位置说服宗族成员支持其决策(代表了一种非正式权威),使得行政权力充分发挥,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达成“权威耦合“,进而增加村庄公共品的投资。[31]蔡晓莉也认为,非正式问责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一个嵌入性(embedding)和涵盖性(encompassing)的连带团体,其中当乡村干部同时是单姓宗族组织和民间寺庙的成员时,能够为村庄提供较好的公共物品。这些社会组织培育了地方干部的社会嵌入性,以及强烈的道德奖励,而这些道德奖励又成为地方干部的权力组成部分。[32]
(二)社会组织或个体的自主供给
非正式制度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还体现在对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体行为的形塑作用。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在其中声誉、道德和习俗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村庄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本对村民自发合作提供公共物品起到基础性的作用。[33][34][35]例如在乡村水利建设方面,罗兴佐和贺雪峰认为水利建设不仅与宏观层面的乡村组织体制相关联,也与微观层面的村庄性质相联系。在荆门这类“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中,原子化的村民不能进行有效合作,导致乡村水利供给严重不足。[36]
同样研究也发现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并不一定造成公共物品的衰败。由于存在类似村庄理事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利用村落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上的合作。在其中,村落自组织利用宗族网络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利用声誉机制、舆论机制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37]当然,理事会之类的村落组织之所以能够发挥强大的动员作用,在于它背后具有较强认同和行动能力的载体——宗族组织。[38]
在华南地区宗族组织保留较为完善,较多的案例研究也验证了在这一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与宗族的相关性。例如温莹莹在福建的案例研究表明,由于历史和宗族因素而在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即“头家轮流制”和特有的习俗惯例,促进了村民在村庄宗族性活动和村庄修建水泥村道中的捐资行为,最终对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作用。[39]同样,陈天祥、魏晓丽和贾晶晶在广东的研究也强调基于宗族组织所产生的文化传统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积极作用。[40]不过,以宗族为载体的非正式制度需要一个文化传统的积累过程,这就使得非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四、几点评论
(一)经济条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从经济基础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各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关联。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带来较高的公共服务质量。以2012年江苏省各地级市为例:南京市的人均GDP在省内排第三位,其公共服务评价结果却排在全省第九位。相反,公共服务评价结果最高的连云港市,其人均GDP只排在全省第十二位。[41]
而税费改革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在一些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中西部地区,税费改革使得乡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下降,这是由于税费改革使得税源较窄的乡镇政府陷入了财政困境,并且由于税费制度的完善,原来的税费摊派不再可行。[42]但是在一些原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税费征收对于村民和当地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们可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获取资金。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基础论忽略了村庄治理结构的问题。张劲松和金太军以湖北鄂州市z乡东大堤为例,发现税费改革之后乡村基础设施之类的公共产品投入面临困境。而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市县政府、乡镇政府以及农民都根据自己的理性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乡镇政府最终倾向于继续收费,农民被动缴纳。[43]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是有关经济条件的问题,而更加需要关注其中村干部、村民以及其他行为主体的角色和行为。[44]改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不仅仅需要更多的国家资源投入以及社会权利组织的培育,它本身还受到农民和地方官员互动方式的极大影响。[45]
(二)民主促进论的不足
首先,现有对于民主选举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关联的研究,很多都是通过定量的方式进行相关性的统计分析,对具体的传导机制分析欠缺,这就有可能忽视在村委会选举之外其他影响到公共物品供给的因素。正如一部分研究所揭示的民主选举可能对于公共物品供给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还需要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在一些定量研究中,将村庄民主选举简单操作化为“是否进行差额选举”,这样的概念操作可能产生误导,实际的村庄民主选举至少还应该重视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过程,即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46]
其次,民主选举或许解决了村庄公共支出比例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村庄内部经济基础的问题。也就是说民主选举可能只是解决了公共支出决策的程序问题,而公共支出的来源问题,民主选举并不能处理。就如一些研究所发现的,经过改制村办企业集体企业之后成为了私营企业,村庄从私营企业主那里征收公共开支变得困难。[22]这样,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就不再是民主选举的程序完善,而是如何能让私营企业主有意愿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
(三)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的局限
由于中国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关于非正式问责机制对于公共物品的影响需要更多的个案分析来寻找其中的机制性因素。在非正式制度视角中,宗族组织以及相关联的文化传统是能够发挥公共物品供给功能的关键。但是,宗族性的要素并不是在各地区都具备,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是相当弱的。同样是对宗族组织与公共物品之间关联的影响,也有研究发现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47]
此外,宗族组织功能的发挥渠道是通过传统权威、乡土关联来进行动员,它主要对于农村道路修建发挥影响,也就是说宗族组织所能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在温莹莹的调研中,她发现农田水利、生活饮用水、学校这三项公共物品或由国家政府承担或已经放弃,T村的村民也不再参与供给。只有道路修建这一项依照“公办民助”的原则,T村村民在这一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率依然很高,她将这一类公共物品称为“宗族性公共品”。[39]因此,可以发现非正式制度作用下所能够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着类型差异。
[1] 张林秀,罗仁福,刘承芳,Scott Rozelle.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1).
[2] 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革,1996,(5).
[3] 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The Length of Lif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Economic Influences on Premature Death in China[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3,30(1).
[4] Lily L.Tsai.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 庄玉乙,张光.资源丰裕、租金依赖与公共物品提供——对山西省分县数据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5).
[6] 田秀娟,周飞舟.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效果、分布和征收方式[J].中国农村经济,2003,(9).
[7] 贺雪峰,罗兴佐.农村公共品供给:税费改革前后的比较与评述[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5).
[8] 周黎安,陈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J].经济研究,2005,(8).
[9] 李琴,熊启泉,陈铭恩.税费改革前后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以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为例[J].调研世界,2004,(12).
[10] 徐琰超,杨见龙,夷恒.农村税费改革与村庄公共物品提供[J].中国农村经济,2015,(1).
[11] 李芝兰,吴理财.“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J].社会学研究,2005,(4).
[12] 罗仁福等.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投资[J].经济学(季刊),2006,(3).
[13] Ray Yep.Can Reform Reduce Rural Tension in China? The Process,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J].The China Quarterly,2004,(177).
[14] T. S. Aidt, Jayasri Dutta, and Elena Loukoi-anova. Democracy Comes to Europe: Franchise Extension and Fiscal Outcomes 1830-1938[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6,50(2).
[15] Zareh Asatryan and Kristof De Witte.Direct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39).
[16] David A. Lake and Matthew A. Baum.The Invisible Hand of Democracy 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1,34(6).
[17] 王淑娜,姚洋.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18] Luo Renfu, Zhang linxiu, Huang Jikun, Scott Rozelle.Elections, fiscal reform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7, (35).
[19] 刘荣.中国村庄公共支出与基层选举: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8,(1).
[20] Renfu Luo et al.Village Elections, Public Goods Investments and Pork Barrel Politics, Chinese-Style[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46(4).
[21] 孙秀林.当代中国的村庄治理与绩效分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2] 张晓波等.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与公共物品提供[J].经济学(季刊),2003,(3).
[23] Xiaobo Zhang et al.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12).
[24] 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1,(1).
[25] Björn Alpermann.Village Governance Reforms in China: Paradigm Shift or Muddling Through?[A]. in Eric Florence and Pierre Defraigne edit.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3.
[26] 冯海波.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J].财经科学,2005,(3).
[27]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8] M. Kent Jenning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91(2).
[29] Jie Chen and Narisong Huhe.Informal Accountability, Socially Embedded Official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The Role of Lineage Groups[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3,18(2).
[30] Yiqing Xu and Yang Yao.Informal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5,109(2).
[31] 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正式与非正式权威、问责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村庄的经验数据[J].管理世界,2012,(1).
[32] Lily L. Tsai.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7,(2).
[33] 符加林,崔浩,黄晓红.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农户自愿供给——基于声誉理论的分析[J].经济经纬,2007,(7).
[34] 苏杨珍,翟桂萍.村民自发合作: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第三条途径[J].农村经济,2007,(6).
[35] 王宇新.社会资本影响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5).
[36] 罗兴佐,贺雪峰.论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04,(2).
[37] 罗小峰.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村民利用自组织自发供给公共物品的实践探讨[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38] 田先红.国家与社会的分治——赣南新农村建设中的理事会与乡村组织关系研究[J].求实,2012,(9).
[39] 温莹莹.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1).
[40] 陈天祥,魏晓丽,贾晶晶.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乡村治理——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5,(1).
[41] 姚兆余等.江苏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2] 马宝成.农村税费改革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4,(1).
[43] 张劲松,金太军.多重博弈:税费改革后乡村基础设施投入面临的困境——以湖北鄂州市z乡东大堤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3,(6).
[44] Hiroshi Sato.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J].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8, 6(2).
[45] Chen and Huhe.Informal Accountability, Socially Embedded Official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The Role of Lineage Groups[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3,18(2).
[46] 牛铭实.经济因素对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J].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8).
[47] 卫宝龙,凌玲,阮建青.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J].农业经济问题,2011,(5).
[责任编辑 陈翔云]
Economic Base, Democratic Promo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ree perspectives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Fei Jun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rural public goods; economic base theory; democratic promotion theory; informal system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The economic base theory insists that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conomy; democracy promotion theory holds that 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 autonomy system will enhanc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performance; the non institutional factors with clan network, cultural practices and social capital as the carrier also have impact on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he above three perspectives represent the main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China’s rural areas, but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respectively in these three explanations.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战略、路径与对策”(项目号:12&ZD040)的阶段性成果。
费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