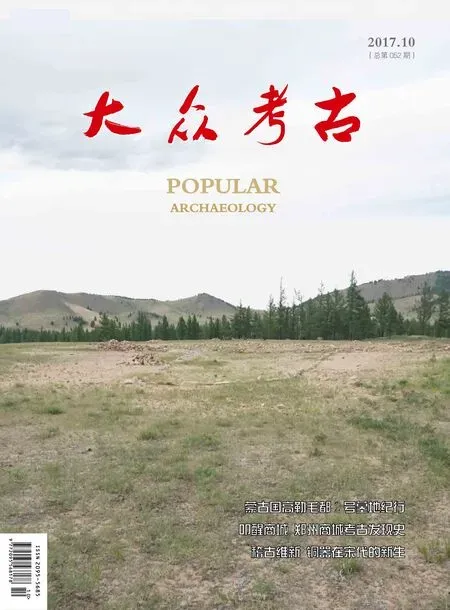稽古维新铜器在宋代的新生
文 图 /蔡明
中国青铜器最辉煌的时代莫过于商周,器型种类众多、造型庄重典雅、纹饰繁缛绚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核心角色,宗法礼制与礼仪活动的物质载体。
三代以后,青铜礼器趋于没落,此后历代虽偶有出土,却多被视为“祥瑞”。如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六月,汾阴巫锦挖土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毋款识……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泰山封禅后,行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于是追加年号为“元鼎”。
直至宋代,文人士子好古、藏古、考古之风蔚然而兴。吕大临所著、成书于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是此时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宋太祖称帝后,鉴于唐末五代的纲常沦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皇权。一是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二欲“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改革并完善礼乐制度,恢复天下纲常伦理,将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作为朝廷及地方祭器的范本。然而,《三礼图集注》有个很大的问题,其记录的很多商周青铜礼器的造型,多为臆想出来的。如铜爵,汉代人早已不知铜爵器型,根据字义猜测“像雀鸟之形”,《三礼图集注》也遵从此说,因此《三礼图集注》描绘的爵,还真是个鸟的样子。

《考古图》

《三礼图集注》中的爵

清代依据《三礼图集注》制作的铜爵(湖南省博物馆藏)
宋徽宗即位后,他发现朝廷所藏的新制铜礼器与民间私藏出土的三代铜礼器有很大差别,于是“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蓄藏古礼器者,遣人即其家,图其形制,送议礼局”。朝廷由此系统性地收集古器,参考金石学研究成果,于宣和五年(1123)编纂完成《宣和博古图》,又以此为模本,重新铸造礼器。这些祭祀礼器,不但器型仿真、做工考究,铭文字体多为小篆,文体也仿自商周铭文。
至此,宋代礼制与礼器均已完备。铜器寂寞了一千多年,终于在宋代迎来了新生。这时的铜器,大致可归为堂供祭祀、四般闲事、文玩娱乐三类。及至元明清,宗庙、社稷、郊祀、岳镇海渎、宣圣等祭祀,皆承袭两宋旧制。

《宣和博古图》
岳镇海渎 祭祀的一种,可追溯至远古先民的原始崇拜,有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经由图腾崇拜—山形祭祀—山镇祭祀—封禅行典—五岳行典—岳镇海渎祭祀。岳镇祭祀在国家祀典中最为重要,岳(镇)成为皇(王)权和国家社稷的象征。“五岳”为“天”的代表,是仁德和尊严的象征;“五镇”是“地”的标志,是国土和统治的化身,标示天下一统。五岳即岱、华、衡、恒、嵩。四渎即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
堂供祭祀
宋元明清四代,朝廷的祭祀体系已完备,有祈愿国泰物饶的天地社稷祭祀、体现孝悌与家国观念的宗庙祭祀、标示天下一统的岳镇海渎祭祀、强调帝王统绪与尊德表功的帝王功臣祭祀、彰显国家意识与儒学地位的宣圣祭祀等。
这些祭祀所用的祭器,多以商周铜礼器为模本。据传南宋朱熹所著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详尽规定了祭祀孔子的祭品、祭器、礼仪程序等,其祭器可能参考了《宣和博古图》的图样,原型为商周铜器。一般而言,笾盛肉脯、果实,豆盛肉酱、菜酱,簠盛黍、稷,簋盛稻、粱,尊、爵盛酒,洗、罍盛水。
与朝廷祭礼中铜器盛放粮食、肉菜不同,民间的铜礼器有了新的使用方式,即烧香、插花、燃灯,前两者所使用的铜器可谓旧器新用。
商周时期盛贮牺牲、粮食佳肴用以祭祀的鼎、鬲、簋等铜礼器,因造型庄重典雅,在宋元时期成为祠堂供养的焚香炉具,甚至被陶、瓷炉具所模仿。以瓶插花也是这一时期供养佛神的普遍方式。陕西甘泉柳河湾村金代明昌七年(1196)墓中,就有一幅关于香花供养的壁画,可知香花在此时庶民祭祀活动中的作用。而商周时用于盛酒水的尊、壶、觚等,因小口深腹,便被借过来用以插花。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部分祭器与商周青铜器造型对比
自此,一香炉、二花瓶、二烛台(或灯台)组成的“五供”,或一香炉、二花瓶组成的“三供”,成为祭祀、供养时最主要的供具。

柳河湾村金墓东北壁壁画香花供养图

“四般闲事”之挂画、插花、点茶 (台北故宫藏宋人物画)
四般闲事
南宋《梦梁录》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戾家,外行之意。古人认为这四事雅致,应亲自掌握并享受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不应交给外行人来做。也有引作“不宜、累家”,意即这四事花销不菲,容易败家。
宋代文人尚雅忌俗,审美偏向于平淡。自宋以后,对于文人来说,普通的日常生活皆可成雅事,普通的材料皆可为雅具。正如这四般闲事,本是日常、普通的事情,也能被文人发现其中的乐趣。
这四件事情中,唯有烧香、插花可用铜器。与严格遵照礼图范式、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仿古礼器系统不同,文人生活中所用的铜器,造型特征与纹样装饰都更为自由多样,既追摹古风,又不乏新意。礼书图谱虽为民间仿古器物的制作提供了式样参考,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根据材质取舍变化。
焚香一炉,或晴窗抚琴,或秘阁夜读,是宋元明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人文意境。陆游曾写道:“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若有美人在侧,“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清席佩兰),不失为一种唯美的生活情致。最能与文人心意相通的焚香炉具,便是古鼎了。宋人郑刚中的《焚香》一诗有云:“覆火纸灰深,古鼎孤烟立。悠然便假寐,万虑无相及。” 还有一种动物形熏炉,宋人洪邹的《香谱》云:“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火烟自口出,以为玩好。”狻猊,形如狮,传说龙生九子之一,喜烟好坐,所以古时香炉多做其形。鸭形香炉也受文人欢迎,北宋晏殊在《燕归梁》中就曾赞道:“金鸭香炉起瑞烟,呈妙舞开筵。”

广东省博物馆藏明铜狻猊熏炉
宋元时期,香炉、花瓶与盛放香料的香盒或放置取香用具的匙盒,常用于供奉与祭祀场合。当时的用香,多为香饼、香丸,盛之用盒,取之以箸、匙。至明代,部分花瓶用以放置取香用的箸、匙,称为“匙瓶”。自此,香炉、香盒与匙瓶构成的“炉瓶三事”,常陈设于书斋、厅堂的案几之上。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对此就有评价:“斋中用以陈香炉、匙瓶、香合(盒),或放一二卷册,或置清雅玩具,妙甚。”
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代表了宋人对古铜插花的看法:“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商周时期的铜觚、铜尊、铜壶成为文人最心仪的插花器,偶尔也见用鼎插花的。
宋人晁公迦的《咏铜瓶中梅》:“折得寒香日暮归,铜瓶添水养横枝。书窗一夜月初满,却似小溪清浅时。”同时代的刘克庄也写道:“日日铜瓶插数枝,瓶空颇讶折来稀。出城忽见樱桃熟,始信无花可买归。”不论作者身世与诗词背景,单看诗文,就能发现宋人拈出铜瓶和花寄意抒情言志,都写得很家常亲切,而鲜花插瓶差不多就是每天的清课。“小瓶春色一枝斜”(宋陈与义),插花,为平淡的书斋生活增添了几分雅趣。

新安沉船出水元代铜三足蟾水滴

新安沉船出水元代铜双螭笔架
文玩娱乐
南宋周晋有词云:“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书斋,不仅是宋元明文人士大夫的读书之所,也是他们寄情人生的文化载体。宋代正处于中国家具的变革时期,由低矮向高脚转变。尺寸的增加带来了空间的变大,书案上放置水滴、笔架、镇纸、砚台等文房之具,柜架上还可装饰钟鼎彝器、古董清玩等。文人收藏、鉴赏书具文玩,并非仅为把玩,而欲养心怡性。北宋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道:“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在宋元明文人的心目中,投壶与棋、琴等一样,皆为书斋中陶冶心性之物。
投壶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游戏,出现于春秋时期,由儒家六艺中的射礼发展而来,投壶失败的一方需接受罚酒。宋代流行有耳投壶,即壶口两侧增加了两个耳。形制的改变带来了玩法的变化。《经说·投壶》载:“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倍多,人争偶尔之侥幸,舍中正而贵旁巧。”投入两耳的计分多于壶口。据记载,宋以前投壶的招式不过四五种,宋代有四十种,明代则达一百四十余种。投壶既可做文人娱乐之用,也可用于室内陈设。
韩国1983年发行的1000元纸币,就印有投壶的图案,而印在同一版面的人物,是朝鲜李朝的朱子理学代表人物、儒学大师李滉。儒家学者与投壶印在一起,可见投壶与儒学的渊源关系。
《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西汉孔安国:“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代陈奂:“维新,乃新也……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正因为宋人对三代青铜器的考证、欣赏,才让这些早已没落千年的铜器,在宋代古树开花,焕发出新的生命。
——唐三彩投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