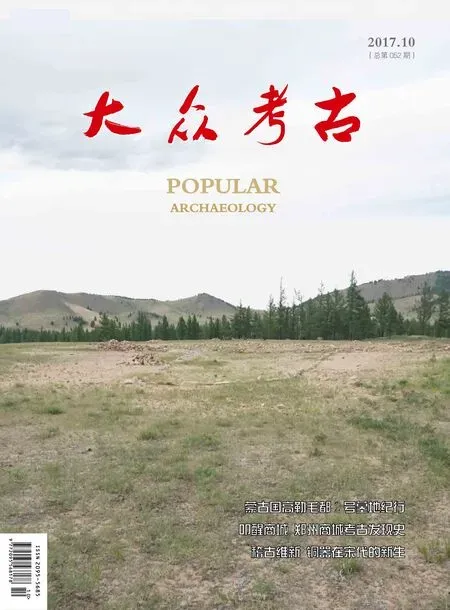探索匈奴文化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纪行
文 图 / 周立刚
2017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代表团一行4人出访蒙古国。此行是对中蒙联合考古项目“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进行进一步洽谈并对项目实施地点开展实地考察。院里计划安排我作为联合考古项目的中方队长,因此随代表团一同出访,有幸得以走进近年来匈奴考古的重要发现地——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Gol Mod 2)。
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历史
高勒毛都2号墓地位于蒙古国中部偏西后杭爱省温都乌兰县境内。熟悉匈奴考古的同行很早就听说过在后杭爱省有一个高勒毛都墓地,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2号?蒙语中Gol Mod 是丛林之中的意思,在后杭爱省境内有两个小地名叫作Gol Mod,这两个地方先后都发现了大型的匈奴贵族墓地。蒙古考古学家也是按照小地名来给墓地命名,因此较晚发现的这个墓地,也就是即将探访的地点,就在后面加上了2号来表示区别。两个都叫作高勒毛都的墓地相距150公里左右。

M1主墓葬出土金质车马器
据我们的合作方、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额尔登巴特尔教授介绍,十多年前是当地牧民先发现了这个墓地,然后告诉了他。2001年开始,他组织了蒙古国和美国联合考古队对这个墓地进行实地调查测量,发现了近百座大型匈奴贵族墓葬和数百座陪葬墓。随后,教授和他的团队用十年时间对主墓葬(M1)及其28座陪葬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银车马器、铜器、玉器和罗马玻璃器,成为近年来匈奴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M1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墓地是匈奴高等级贵族墓地,甚至可能是王族墓地。但是由于墓地规模太大,这一座墓葬的发掘只能算是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新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墓地的内涵和相关问题,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决定再选择其中一座墓葬进行发掘。蒙古国内对于考古项目的资助有限,因此他决定再次寻求国际合作,这也是促成本次中蒙联合考古的根本原因。

M1主墓葬出土银质车马器

马器装饰示意,图片来自Cultural Heritage of Xiongnu Empire P.51
先遇见器物
该墓地的调查和发掘成果主要以蒙文或英文发表,目前中文的匈奴考古研究文章中,只能看到一些简短的介绍。我们只能从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在3月份访问郑州期间所介绍和展示的材料中获得一些片段信息,至于这些考古发现的震撼程度,仍然是停留在我们的想象中。做考古研究的同行都知道,照片和出土实物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抵达乌兰巴托的第二天上午,代表团跟乌兰巴托大学校长会谈之后,去参观了考古学系的博物馆,这才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考古发现的魅力。

M1陪葬墓出土罗马玻璃碗

M1主墓棺内出土汉代玉璧
博物馆很小,里面陈列了几十年来考古学系师生的工作成果。当然是以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及其陪葬墓群出土遗物为主。正中间的三个展柜分别陈列着M1主墓葬出土的成套金银车马器、玉器以及陪葬墓出土的罗马玻璃碗。
国内近年来最吸引人的考古发现莫过于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麟趾金让人惊叹不已。然而这些成套的金银车马器在眼前出现时,带给我们的却是另一种震撼。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无疑是财富的直接展示,而这些金银车马器除了展示财富之外,同时还展现了草原文明的高超艺术造诣。最大的圆形金器直径13厘米,长条形金器长度也近30厘米,除了尺寸惊人之外,上面装饰的以雪豹、羚羊等动物为原型的独角兽更是风格独特。额尔登巴特尔教授解释说独角兽装饰是匈奴文化的特征之一,这些独角兽都是由实际存在的动物变形而来。独角兽在现代蒙古人心中仍然具有神圣的色彩,猎人如果见到只有一只角的动物,也是要放生的。
除了夺目的金银器之外,再就是那只蓝白相间的罗马玻璃碗。这只碗出土于最大的一座陪葬墓中,是典型的罗马器物,在欧美的博物馆中能见到造型和花纹高度相似的器物。至于这只产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玻璃碗是如何来到亚洲北部大草原的深处,显然是跟丝绸之路有关联,蒙古学者也正在就此进行研究。玻璃碗的旁边是一件直径18.5厘米的汉代玉璧。保存如此完好的汉代玉璧连我们长期在中国从事汉代考古的专家都十分惊讶,我们跟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开玩笑说,这件玉璧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他介绍说,这件玉璧的发现十分幸运——安放人骨的棺室被盗掘一空,这块玉璧因为紧贴棺壁而逃过一劫。
除了这些金银器和玉器、玻璃器之外,另有一些小型陶器和铜铁器陈列在展厅周围的展柜里。有草原风格的陶器和铜鍑,也有汉代的规矩镜等。见到草原文明、汉代中原文明和西方罗马文明在草原深处一个墓群中的交汇,让人颇有时空穿越之感。
乌兰巴托大学的规模比较小,博物馆安防条件有限,不具备展览条件。教授说这些珍贵的器物一般是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这次是专门拿出来给我们参观的。除了参观遗物之外,我们还在展厅一角的电视上观看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考古工作纪录片。纪录片从队伍乘三辆大卡车离开学校到路途经过的河流和小树林,到工地搭建帐篷开始工作及发掘中的各个精彩场景,工程结束时所有工作人员围成一圈在遗址周围转动并欢呼庆祝,简要但完整地展示了M1及陪葬墓的发掘过程。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制作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这点让我们也很受启发——我们往往只注重了考古现场的记录,对于现场前后的故事多少有些疏忽。

装载满满的汽车
向墓地出发
看完器物和纪录片,我们对这个遗址已经十分向往,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它的真容。午饭之后,就驱车上路了。这种出发并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洒脱,因为遗址在无人区,路途十分遥远,路上也没有很便利的餐饮住宿条件,因此一切都要按照野营的方式准备。一辆越野商务车先是在学校装上了帐篷、睡袋等必需品,又开到一个老师家里装了炉子、水壶、锅碗瓢盆等用具,此时后备箱已经基本塞满,顶上的行李架也派上了用场。离开市区之后车又停在一个大型超市门口,补给了成箱的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瓶装瓦斯气体等,当然还有啤酒和伏特加。再次花了半个小时整理、装车之后,车顶的行李架已经像个小山一样了,每个人的座位底下也都塞满了东西。这才算是正式出发,此时是下午五点左右。
这次启动之后就是一直向西了,路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敖包处祭拜。很多人一直以为敖包是蒙古包,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在西藏照片上看到的飘着彩带的石堆。石堆一般在路边,有的先有萨满做法,然后就成为大家祭祀的一个地方。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在此停下,顺时针绕敖包转三圈,带着酒的要向敖包敬酒三杯,然后给敖包加上几块石头。额尔登巴特尔教授说这种做法的寓意是石头给你,好运给我。敖包的石头堆上也可见到很多其他物品,比如拐杖、药瓶等,大概是生病的人希望敖包带走疾病,留下健康。这个仪式简单却很严肃,我们也跟着教授一起敬酒、加石头。沿路还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敖包,旅行的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敖包,并不是每个都要祭拜。如果说因为时间紧没下车,对着敖包鸣笛三声也是一种祭拜方式。这大概是古老的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新形式吧。
这一路一直走到凌晨三点半。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草原上的夜奔,完全没有路,汽车的灯光在茫茫的夜色中显得十分微弱,只能看见车前几米的地方。草原一眼看去是平坦的,但是地面并不像马路那么平,总是有大大小小的坑或者水冲出的沟。我们已经完全辨不清方向,对车辆在夜路上的颠簸也十分担心。但是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和司机对此完全习以为常。这台现代商务车几乎是遇山爬山,见河过河,没有一点迟疑,犹如坦克一样强大。车上的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从20多度一直降到零下2度,我们终于到达了路途中的营地,在蒙古包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早晨起来摸到手机时,手居然跟碰到冰块一样,很难想象十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都是穿着夏装出发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看到营地其实是一片很美的地方。因为有水,草地已是绿意盎然,还有成群的牛马。虽然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么浪漫,但跟路途中见到的大片接近荒漠化的草地完全不一样,算是真正的草原美景了。无暇领略这样的美景,大家在蒙古包里用便携瓦斯炉生火煮方便面,吃完之后继续赶路。
中午时分抵达后杭爱省省会,停下来对汽车进行简单维护并吃饭。随后在公路上行进六七十公里之后,再次进入完全没有路的草原。经验丰富的司机根据地面情况准确地切换着二驱、四驱模式,车在小树林和河沟之间任性地颠簸穿行,有惊无险地穿过一片片沙地和一条条河沟。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则拿着GPS,指挥着方向。到下午六点左右,终于到达目的地。

草原美景

暴露在地面的墓葬轮廓
初访匈奴贵族墓地
下午六点,北纬48°的地方依然艳阳高照。整理完露营设备之后,教授就开始带着我们参观遗址。遗址位于一个南高北低的小山坡上,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片松树林,林间草地上草皮稀少,大部分地方露出了沙子。从远处眺望可以看得很清楚,遗址所在区域正是大片松树林中树木稀疏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命名为“丛林之中”的原因。周围视力可及之处,见不到任何蒙古包或者动物,除了地上偶尔钻出来的草原鼠。
在静静的松树林里,散落着近百座大型积石墓葬。平面形状和我们熟知的甲字形墓很像——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墓室,斜坡墓道。不同的是墓室和墓道边都有石块砌成的高出地面的石墙,中间以石块和沙土填充。整个墓葬就是一个高出地面的甲字形台地,墓室和墓道的形状都十分清晰,露出地面数十厘米到两米高度不等,与我们国内所见的封土完全不同。外国学者称这种墓葬为terrace tomb,或可译为台形墓,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形态。每个主墓的东侧都呈弧形分布着数量不等的圆形积石陪葬墓,如众星拱月一般。因为地面草皮较薄,大部分墓葬的积石形状也很清楚。已经发掘的1号墓东侧有28座圆形陪葬墓,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的。教授介绍说,也有个别墓葬的陪葬墓在西侧,或者东西两侧都有。这些比较特殊的现象还需要继续研究。
十多年前,教授和他的团队就是根据这些地面暴露的积石进行调查并绘制出了墓地的总平面图。据说当年的草还有四五十厘米的深度,现在基本上只能没过脚背了。虽然远离人烟,这里并不是没有人光顾。几乎每个大型墓葬的墓室顶部正中都有一个圆形凹坑,教授解释说,一般较小的凹坑可能是因为墓内棺木塌陷所形成,但是较大的凹坑肯定就是盗扰所致。从他们的调查情况看,大部分墓葬都被不同程度地盗扰。有意思的是,已发掘的M1主墓盗扰活动似乎主要是针对安置人骨的棺室。相邻的两个放置金银车马器、铜器和陶器的棺室保存完好。看来盗扰活动似乎并不是以珍贵器物为对象,更像是一种报复性的活动。《汉书》等文献也有记载,乌桓人曾经大规模破坏匈奴国王墓葬以进行报复。目前发现的现象是否就是这种报复性活动,也是值得研究的线索。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疑似盗扰形成的凹坑上部已经长出了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也说明这些盗扰活动是很久之前发生的。
已经发掘的M1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匈奴墓葬,墓室长宽都在50米左右,墓道长约37米。东侧有27座陪葬墓呈弧形分布,弧形陪葬墓链与主墓之间还有另一座规模较大的陪葬墓,也是出土罗马玻璃碗的墓葬。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这个墓葬并没有低空影像资料,所有外景照片都是教授在树上或者梯子上拍的。做田野的专家们都知道,对于这么大规模的遗迹,没有气球或者无人机,是很难拍到全景的。教授也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在相关技术上提供一些帮助。整个M1及其陪葬墓群的发掘前后持续了十年,其中主墓葬的发掘持续了两年,最多的时候有150余人参加发掘,甚至还有士兵参加了这项工作。除了工地上遗留的前些年发掘留下的木柱、炉灶等生活设施之外,很难想象此处曾经有上百人开展过几年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墓群发掘完毕之后就进行了回填,大量的积石堆在远处,地面用石头标出了墓葬原来的形状和位置。墓葬的东北角位置有一个小的敖包,教授说是他堆的,每次来到此地都会去敬酒、奉献一些食物。

回填后的M1
露营在墓地

墓地上的敖包
教授带着我们在树林间穿行,给我们介绍着不同位置的墓葬以及他对这个墓地的一些研究情况。不到现场很难相信,草原深处的这片树林就是驰骋草原大漠的匈奴国王和他们的贵族最后的归宿,现在只剩下静静的松树林和稀疏的草皮。

墓地露营
我们很惊讶当年这个悍勇的民族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们国王和贵族的墓地——远离匈奴王庭,而且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山坡。这些松树林据说也是近300年内由风从西伯利亚一带带过来的树籽落地发芽生长的。也就是说,2000年前这里完全就是一片草地。葬于此地的匈奴贵族们也并不是有意要在茫茫草原中隐藏自己的最后归宿地,当时他们在地表堆砌数米高的石台,从远处的山顶就能看见。近百座大型墓葬表明这个墓使用了多年,先后数代国王或贵族都葬于此地。额尔登巴特尔教授团队对M1出土的皮革制品进行了14C测年,表明M1及其陪葬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也就是我们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至于这个墓地究竟使用了多少年,葬了多少代国王,目前只发掘了一座墓葬,还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联合考古项目能够为这些问题找到线索。
那些呈弧形分布在主墓侧面的陪葬墓,教授认为从布局特征判断应该是经过仔细规划并跟主墓同时形成的。这就意味着陪葬墓里的人也是与主墓里的国王或者贵族同时下葬——因此与我们所理解的陪葬有着明显差别,更像是一种殉葬的形式。已发掘的M1陪葬墓弧形链南部几个墓葬中葬的都是未成年个体,至于这些殉葬个体与墓主的关系,就需要借助DNA分析等现代手段来研究了。
我们跨过北边那条叫作鹿河的小溪流,到了位于墓地北边的小山坡上,眺望着这个埋葬了数代匈奴贵族的地方,脑海里想象着两千年前这里可能发生的一幕幕场景。下午八点多,太阳才缓缓落下,夕阳余晖洒落在松树林和草地上。或许,只有这些阳光才真正地见证过那段历史。
夜色降临,我们在墓地上露营,旁边几十米的位置就是埋葬着一代匈奴国王的M1。睡袋直接放在这片埋藏了数千年历史的草地上。树林比较稀疏,没有松涛声,也没有听见狼叫。梦里,似曾听到千年前的马蹄奔腾,我们盼望着能够早日走进这段历史,继续揭开这个墓地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