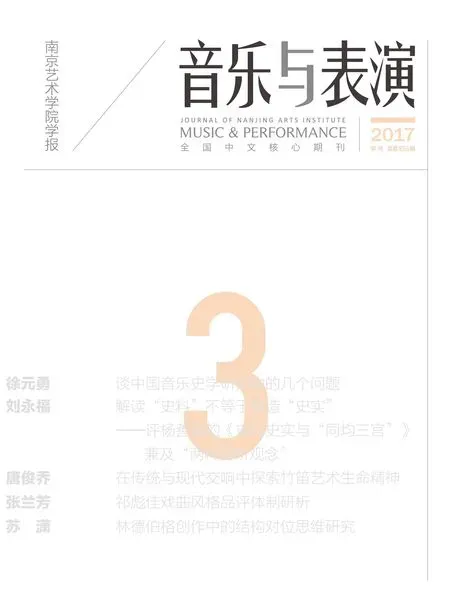祁彪佳戏曲风格品评体制研析①
张兰芳(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祁彪佳戏曲风格品评体制研析①
张兰芳(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戏曲批评作为中国古典艺术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批评形态、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古代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批评的影响。明代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相关戏曲作家、剧作风格的品评,结合戏曲艺术创作实践与特殊性,对创作风格的差异与成就高下进行品评,提出了“妙”“雅”“逸”“艳”“能”“具”六品体制,不仅是对古代“分级品第”批评方式的一脉相承,而且极富创造性地将古代文学艺术风格品评推向了新的高度,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批评传统,彰显了中国古典艺术批评理论的民族特色。本文对比吕天成《曲品》对祁彪佳提出的六品体制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旨在加强对其品评标准、分品视角以及品评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祁彪佳戏曲风格;《远山堂曲品 剧品》;品评体制
戏曲批评作为中国古典艺术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批评形态、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古代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批评的影响。明代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相关作家作品风格的品评,结合戏曲艺术创作实践与特殊性,对创作风格的差异与成就高下进行品评,提出了“妙”“雅”“逸”“艳”“能”“具”六品体制。这不仅是对古代“分级品第”批评方式的一脉相承,而且极富创造性地将古代文学艺术风格品评推向了新的高度。本文拟对六品体制进行系统深入的辨析研究,进而加强对“妙”“雅”“逸”“艳”“能”“具”的品评标准、分品视角以及品评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
祁彪佳戏曲品风格评体制,是对前代批评理论的承继与发展,近袭明代吕天成,远袭魏晋六朝、唐宋诸家。对祁彪佳戏曲品评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明吕天成《曲品》,其《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旨在弥补吕品之不足,为戏曲品评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而作:“予素有顾误之僻,见吕郁蓝《曲品》而会心焉,其品所及者,未满二百种,予所见新旧诸本,该倍是而且过之。欲嗷评于其末,惧续貂也,乃更为之。”[1]5就品评数量来看,祁氏《远山堂曲品》残稿已达466种,《远山堂剧品》专论杂剧(包括少数元杂剧与大量明杂剧)数量多达242种,较吕天成《曲品》品评数量(戏曲作家90人,散曲作家25人,作品192部)要多得多。
就品评方法与品级区分来看,吕天成《曲品》直接承袭魏晋六朝诸家,自述“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采用人、作相分的品评方法:“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即上卷论作家,下卷论剧作。尽管这种品评方法,有助于对作家、剧作整体面貌、风格特色的认知,但在实际品评当中,却由于品评过于简单,未能深入细致地对作家、剧作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评价,不利于对作家、剧作的整体关照。更为重要的是,吕氏将作家风格与作品风格直接画等号的做法,即对作家品级的区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品级,简单套用古代久已成型的品级模式,未能考虑到个人创作风格多样性的问题。对此王骥德曾毫不讳言地指出:“勤之《曲品》所载,搜罗颇博,而门户太多……概饰四六美辞,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2]172-173。而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对这一问题却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采用人、作合一的方法,即将作家与剧作合在一起品评,充分考虑到个体风格多样化的问题。在《曲品凡例》中指出:“文人善变,要不能设一格以待之。有自浓而归淡,自俗而趋雅,自奔逸而就规矩。”[1]7可见,作家的创作风格并不是从一而终,随着周遭环境的改变与主体自身的思想观念、艺术技法、审美倾向等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艺术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可一概而论。正是认识到吕品的诸多不足,祁氏才对戏曲风格品评进一步完善与体制建构。
就品评的品类和体制来看,祁彪佳对古代风格品评的品类与体制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有取有舍,有继承、有发展。不同于吕天成简单照搬古代风格品评的品类和体制模式,把“作旧传奇者”分为“神、妙、能、具”四品,只在传统的“神妙能”三品之外增设“具品”;对“作新传奇者”,也是直接套用南朝梁代庾肩吾《书品》“三品九等”品评体制,这是魏晋九品论人的在戏曲批评领域的又一次挪用,无论品类、体制设置上都无多大建树。而祁提出的由“妙”“雅”“逸”“艳”“能”“具”六个品类建构的体制框架,大胆舍弃了古代风格品评的重要品类“神”,继承了传统的“妙”“逸”“能”以及吕氏的“具”品,并增加“雅”“艳”两个新品类;完全摒弃了以“上中下”(三品九等)体制简单评定高下优劣的做法,而采用更为纯粹的、富有审美性,且能标示风格特色 的语 汇 作 为 品 类 名 称。“ 妙 ”“ 雅 ”“ 逸 ”“ 艳 ”“能 ”“ 具 ”品评体制的确立,真正实现了戏曲品评等级性与审美性、风格性与类型性的融合。这一极富创见的品评体制是专属于戏曲的品评体制,体现了祁彪佳对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和戏曲艺术特性的重视。
一、舍“神”重“妙”,尚属首次
祁彪佳舍“神”重“妙”,是对古代艺术风格品评体制的极大挑战,但却是他结合戏曲艺术作出的理性选择。自唐张怀瓘《书断》提出“神、妙、能”三品体制以来,便确立了“神”居于“妙”之上的品第次序。其后,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提出“神、妙、能、逸”四品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出:“自然、神、妙、精、谨细”五品制以及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提出:“逸、神、妙、能”四品制等,对“神、妙、能”三品制予以增补、拓展,甚至改造,但他们都始终未能脱离“神、妙、能”体制的基本框架模式。尤其是宋黄休复旗帜鲜明地将“逸”提升至“神、妙、能”之上,高度强调审美情趣由“再现”向“表现”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神”品的至尊地位,对古代风格品评体制的改造,可谓富有“颠覆性”意义,但对于神、妙二品,依然保持着“神”前“妙”后的品第次序。当然,黄氏有意抬高“逸”的地位,在艺术风格批评领域毕竟是个别的、局部的。宋元时期采用“品第化”方式品评作家作品风格,更多的是对“神、妙、能”体制的坚守,如宋徽宗提出:“神、逸、妙、能”品评体制,宋刘道醇《宋朝名画评》从不同画科角度品评画家画作风格,以及朱长文《续书断》品评书家书作风格,都沿用了“神、妙、能”体制。即使到元代,文人画引领画坛,“逸品”成为绘画创作实践备受瞩目的风格类型,但在理论批评领域,依然坚守着“神、妙、能”体制,如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论及“三品六法”时对“神、妙、能”体制的再次强化与概念重申。可见,中国古代艺术风格品评中,“神、妙、能”三品体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且被不断承袭的品评模式。然而,到祁彪佳这里,其舍“神”重“妙”的做法,不仅前所未有地舍弃了“神”品在古代艺术品评体制中的至尊地位,而且极富创见性地将“妙”抬高至众品之上,这在古代艺术批评领域尚属首次。
祁彪佳缘何舍“神”重“妙”,其间恐怕渗透着他对戏曲艺术特殊性的理性思考。张怀瓘最早提出“神、妙、能”体制,但却未曾对诸品内涵予以释义。宋代黄休复最早解释“神格”:“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3]120可知“神”的变幻莫测得益于“天机”,创作在思与神合、得心应手中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易传·系辞上》曾曰:“阴阳不测之谓神”[4]272,《系辞注》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4]272,说明“神”具有变化莫测,难以捉摸、出神入化的特点。
而相对于依靠人的语言、形体进行实体性表演的戏曲艺术来说,一招一式的舞台表现,尽管离不开“天机”禀赋,但更多的是从后天勤学苦练的“功夫”中得来,用“神”来概括其风格特征,显然有失妥当。而且“神”被引入品评体系,尤其被用于晋唐以来书画艺术风格品评,与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影响不无关系。吕天成《曲品》承袭前制,将高则诚列入神品,缘于其对戏曲创制有功,这种列品方法,显然是对前人品评体制的套用和效仿,有牵强附会之嫌;而祁彪佳舍弃“神”品,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到戏曲艺术的特性,注重舞台实体性表演与展示,将“神”用于戏曲品评,显然是不妥当、不合理的。因此,舍“神”重“妙”,是祁彪佳基于戏曲创作实践的理性选择。
“妙”,据黄休复释义:“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3]120,可知,“妙”表现为主体对笔墨技巧的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此来抒发主体个性、才情,表现精微情景(境)。这种“可表现”“可操作”的现实性特点,不仅是书、画艺术所能体现的,同样符合注重舞台表演实践的戏曲艺术。“曲品凡例”指出:“如汤清远他作入‘妙’,《紫钗》独以‘艳’称”[1]7,说明汤显祖除了《紫钗》之外的传奇作品,都具有“妙”的风格特征。虽然祁氏《曲品》残稿中“妙”品亡佚不见,但通过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的唱词,可以窥见“妙”的风格特点:
【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红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倦,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5]
此两段唱词将主人公的心理思想与自然美景巧妙融合,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如果创作主体没有较高的艺术天赋与才华,不具备独特的个性才情与高超的写作技巧,无法将戏中情境描绘地如此微妙精深,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正是戏曲之“妙”所在。另从《剧品》中列于“妙”品的剧作品评来看,同样可以感受到“妙”的风格特点。如:
周藩诚斋《苦海回头》:境界绝似《黄粱梦》,第彼幻而此真耳。及黄龙证明,钟离呼寐,则无真、幻,一也。
周藩诚斋《继母大贤》:其词融炼无痕,得镜花水月之趣。
评周藩诚斋《团圆梦》:只是淡淡说去,自然情与景会,意与法合。盖情至之语,气贯其中,神行其际。肤浅者不能,镂刻者亦不能。
徐渭《渔阳三弄》:此千古快谈,吾不知其何以入妙,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
陈继儒《真傀儡》:境界妙,意致妙,词曲更妙。
沈自徵《簪花髻》:人谓于寂寥中能豪爽,不知于歌笑中见哭泣耳。曲白指东扯西,点点是英雄之泪,曲至此,妙入神矣![6]139-144
可见,“妙”的风格特征体现为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来营造一种“象外”之境。其词曲融炼无痕,有如镜花水月之趣,虽然平淡自然,却能情景融汇、意与法合,此等浑然天成之作,非肤浅者、镂刻者所能,无论其境界、意致,还是词曲皆可称妙,使人难以觉察作品是如何渐入妙境的,只觉作品情境中散发着妙不可言的情感力量,体现出一种超乎象外的境界,这与古代艺术风格品评关于“妙”的实质内涵是相契合的。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作为最早以品第化方式进行风格品评的著作,曾对列于第一品的张墨、荀勖评价说:“风范气候,极妙参神……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7],认为追求“妙”的境界,并非抓住一个有限的物象,对其进行逼真刻画,而在于取之象外;东晋画家顾恺之也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说明作品之“妙”并不在物象之形似,而贵在通过有限的物象体现无穷的意境;如果“妙”能至“极”,则可接近于“神”。
祁彪佳的“妙”品,正是抓住了“象外”之境的内涵,“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能于“寂寥中能豪爽”“歌笑中见哭泣”“曲白指东扯西,点点是英雄之泪”,皆以有限蕴涵着无限,给人以妙趣无穷,妙不可言、回味不尽之感,其“妙入神矣”的说法与谢赫“极妙参神”内涵也是一致的,都强调作品微妙之变化妙不可言,可近“神”品的特点。可见,祁彪佳舍“神”重“妙”的品评,并非简单套用古代风格品类内涵,而是以戏曲创作实践作为品评的基础。
二、增设“雅”“艳”,乃为新创
增设“雅”“艳”,是祁彪佳对古代文学艺术风格品评体制的创造性发展。
“雅”的内涵及运用较为丰富。其一,“雅”有正统、正规、标准之意:《诗经·小雅·鼓钟》郑笺云:“雅,正也。”《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8]此处的“雅言”,指周朝的官话,也即当时通行的标准语言。又如曹丕《典论·论文》提及“奏议宜雅”,奏议是古代臣下上奏帝王的文书,当然要讲求规范。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提出“八体说”,其中“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9],指出“典雅”风格要以儒家经典为学习楷模,做到文质雅正。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也提出“典雅”风格品类,其释义为:“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随。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10],但此“典雅”不同于与刘勰之“典雅”,这里的“雅”,是一种“以‘典’为重要文化依据和基础的高尚不俗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受到了重视‘典’的儒家文化和疏远‘典’的道家文化的共同沾溉,它同样是典雅艺术风格的重要的内在依据。”[11]可见,“雅”强调对正统、法度、规范的遵从,同时还蕴涵着高尚而不俗的审美趣味,此为“雅”的特征之一。
其二,“雅”还可以指向一种抒情性文体风格:《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12]《大雅》多以歌功颂德为主,不表现个人情感;《小雅》则多与《国风》相类似,其中有《采薇》《杕杜》《何草不黄》等篇什,多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从普通士兵角度出发,抒发他们对战争的厌倦和思乡的情感,可以说是“诗言志”的最早体现。钟嵘《诗品》评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13]“无雕虫之功”,说明阮籍的作品不以人为雕琢取胜,而以质朴无华为本。可见,以质朴的语言,抒发下层百姓的忧虑、感伤之情怀,是“雅”的又一重要特征。
祁彪佳在“曲品凡例”指出:“沈词隐他作入‘雅’,《四异》独以‘逸’称。”[1]7可知沈璟除《四异》之外传奇作品,都具有“雅”的特征。虽然目前所见《远山堂曲品》之“雅品”对沈璟作品的品评只剩残稿,但依然能从只言片语来感知“雅”品之风格特点:
《分钱》:“盖欲人审韵谐音,极力返于当行本色耳。”
《双鱼》:“写书生沦落之状,全(?)令人神魂惨淡。”
《义侠》:“此记于武松侠烈之概、潘金莲淫奔之状,宛转写出。”
《珠串》:“崔妻磨折于伯母,虽未脱套,而描写妇人反唇之状,非先生妙笔不能。”
《结发》:“中间状白叟之负义、莺娘之守盟、萧生之异遇,一转一折,神情俱现。”[1]126-128
从以上几则被列入“雅品”的传奇作品可知,沈璟崇尚本色当行,十分擅长对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生活情状的细致描摹与生动再现。祁彪佳认为,沈璟能将“沦落之状”“侠烈之概”“淫奔之状”“反唇之状”“负义”“守盟”“异遇”等生活情状以宛转的手法写出,极尽本色情态,神情俱现,并赞其为“妙笔”,将其列入“雅品”,表明他将“本色”描摹作为“雅品”的基本特征。而且从《远山堂剧品》中被列入“雅品”的作品品评中,同样传达了以“本色”为“雅”的审美观念,如:
周藩诚斋《福禄寿》:钟馗之语带趣,想其作躯老俱在画图中。以俗境耳独入雅道,盖繇韵胜其词耳。
杨诚斋:《十长生》:然构词之工,几能化雕镂为淡远矣。
《蓝采和》:“度脱蓝采和,境界平常。词于淡中着色,有不衫不屐之趣。”
王骥德《倩女离魂》:方诸生精于曲律,其于宫韵平仄,不错一黍。若是而复能作本色之词,遂使郑德辉《离魂》北剧,不能专美于前矣。[6]148、150、152、162
以上几例评语,再次证实了祁彪佳以“本色”为核心的“雅品”观,表明其对本色的理解,要求作品在内容上是对生活情状的真实再现,而且要求曲词也体现自然本色,以质朴、平淡的语言取胜,而不尚雕琢,“不衫不屐”点明了祁彪佳“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与品评思想。这一点与古代“雅”的涵义之二相吻合。
除了表现“本色”之外,“雅品”还特别强调对意境的追求和情调的婉转。虽然戏曲作为一种俗文化,在表现世俗情态时难免以生活“本色”之语,甚至以俚语来实现生动再现,然而在情感传达上,却强调不必以过激或极端的方式来体现悲欢离合,而是以隐深婉转、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来营造美好的意境和情调,以便收到以少胜多,含不尽之意的艺术效果。如:
周藩诚斋《乔断鬼》:本寻常境界,而能宛然逼真,敷以恰好之词,则虽寻常中亦自超异矣。
汪道昆《高唐梦》:名公巨笔,偶作小技,自是壮雅不群。他人记梦以曲尽为妙,不知《高唐》一梦,正以不尽为妙。
汪道昆:《洛水悲》:陈思王觌面晤言,却有一水相望之意,正乃巧于传情处,只此朗朗数语,摆脱多少浓盐赤酱之病。
叶宪祖《骂座记》:灌仲孺感愤不平之语,槲园居士以纯雅之词发之,其婉刺处更甚与快骂者。
《豫让吞炭》:忠臣、义士之曲,不难于激烈,难于婉转,盖有心人觉不作卤莽语。此剧极肖口吻,遂使神情逼现。[6]147、153、154、157、152
祁彪佳提倡以“恰好之词”追求“超异”之境,希冀摆脱“浓盐赤酱之病”,而以“朗朗数语”追求“不尽”之妙,反对“感愤不平之语”和“卤莽语”的简单粗暴,而倡导以“纯雅之词”予以“婉刺”,都是为了追求一种美好的意境、雅致的情调以及高尚不俗的审美趣味。这一点与古代“雅”的涵义之一相吻合。
可见,祁彪佳将“雅品”视为雅俗统一体,内容、曲词之俗,体现着生活之本色;意境、情调之雅,体现着戏曲作为艺术之本色。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雅品”是生活与艺术之“本色”合一。
“艳”,也是首次被引入风格品评体制的新品类。据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艳”:“好而长也”[14],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注曰:“容色丰满也”[15],《左传·桓公元年》载:“美而艳”,孔颖达注疏云:“美者,言其形貌美;艳者,言其颜色好,故曰‘美而艳’。”[16]《小雅·十月之交》载:“艳妻煽方处”,毛诗正义云:“艳妻,褒姒。美色曰艳。”[17]汉代扬雄《方言》:“艳,美也。”[18]可见,“艳”多指容貌或色彩的美丽。“艳”是多种色彩的集聚,五彩斑斓,令人眩目,方能称之为“艳”。
“艳”用于文学品评,始见于南朝“宫体诗”,即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多写女性之美或男女情爱,形式上追求辞藻靡丽,声律严整,具有“轻靡”“妖艳”的风格特征。宫体诗在文坛上颇具影响,自南朝梁文帝到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时期,一直弥漫于文坛。北宋欧阳炯《花间集序》曾描写道:“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19]说明“艳品”在文学领域是久已存在的一种风格类型。
音乐领域,最具“艳品”特色的典型代表是楚歌,《御览·古乐志》曰:“楚歌曰艳”,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谢灵运《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中有“楚艳起行戚”。而且《楚辞》中《九歌》中也有大量关于男欢女爱的描写,说明楚地民间歌舞具有“艳”的特色。明王骥德《曲律》也提及“吴歈、楚艳,以及今之戏文,皆南音也。……南音多艳曲。”[2]56从中可知,包括吴歈、楚艳在内的“南”音,大多为“艳”曲。可见,祁彪佳将“艳”列于戏曲品评体制当中,并非是求奇新创,而是缘于创作实践中由来已久,存在着“艳”这种风格类型。
戏曲创作领域,以“艳”为风格特色的传奇或杂剧比比皆是。如:
沈璟《红渠》: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韵,句句有移宫换羽之工;至于以药名、曲名、五行、八音及聊韵、叠句入调,而雕镂极矣。
吕天成《蓝桥》:字字皆翠琬金镂,丹文绿牒,洵为吉光片羽,支机七襄也。
郑若庸《玉玦》:以工丽见长……此记每折一调,每调一韵,五色管经百炼而成,如此工丽,亦岂易哉!
陈汝元《金莲》:至于韵金屑玉,以骈美而归自然,更深得炼字之法。[1]18-21
陈汝元《红莲记》:藻艳俊雅,神色俱旺,且简略恰得剧体。
周藩诚斋《踏雪寻梅》:以殊艳之词,写出淡香疏影,而艳不伤雅,以是见文章之妙。[6]177
以上这些作品,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尤其在对女性之美与情节描绘上,极尽藻饰艳丽之辞,使欣赏者在移宫换羽、错彩镂金、精工富丽的描绘中感受到一个个色彩斑斓的美艳世界。这些艺术手法恰到好处的运用,不仅能够极其细致入微地表现物象、刻画人物心理,为整个戏曲增光添彩,更重要的是,能够使欣赏者从中获得高度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洗礼。
然而,如果过度的人工雕饰或者运用不当,往往会适得其反:如评汤显祖《紫钗》:“先生手笔超异,……会景切事之词,往往悠然独至,然传情处太觉刻露,终是文字脱落不尽耳,故题之以‘艳’字。”[1]17在“曲品凡例”也指出,该作“独以‘艳’称”,且对该作的品评有褒有贬,肯定的辞藻的细腻精工,“会景切事”能做到“悠然独至”,否定的是“传情处”太过刻露,也许正是由于其辞藻堆砌、过于工巧富丽,才致使祁氏题以“艳”字。又如评谢廷谅《纨扇》:“一意填词,虽绮丽可观,而于阖辟离合之法,全是瞆瞆”,评戴应鳌《钿盒》:“纵笔于绮丽之场,用唐律供其挥洒。……但字雕句镂,微少天然之趣。”[1]22可见,不顾忌题材内容、布局章法等的实际需要,一味地在辞藻堆砌、声律变幻以及色彩雕琢上下工夫,不仅导致作品“文”“质”失衡,不能恰到好处地传情达意,而且还会破坏戏曲的整体美感。这也恐怕是祁氏将“艳”品置于“妙”“雅”“逸“之后的第四品之缘故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祁彪佳增设“雅”“艳”二品,均是基于戏曲创作实践的理性选择与理论回应。
三、“逸”“能”“具”沿用,赋予新意
“逸”“能”“具”,是对古代风格品评体制中的“逸”“能”与吕天成“具”的承袭沿用,但却被祁彪佳赋予新意。
(一)“逸”
“逸”用于戏曲批评,受到古代书画风格品评体制的影响。唐初李嗣真《书后品》在汉魏六朝“三品九等”体制基础上,将“逸”引入品评体系,既没有阐释其内涵意义,更未对缘何将其置于最高品位说明理由。但提出的“逸品”名称,对其后艺术风格品评和审美趣味的转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晚唐朱景玄将“逸”置于“神”“妙”“能”之后,使其成为与前三品并立的风格品类,并将“逸”初步界定为“格外不拘常法”“非画之本法”,也即把“逸”看作对传统常规法度的突破。宋代黄休复不满朱景玄对品评体制的排列次序,在《益州名画录》中公然将“逸”置于“神妙能”诸品之上,并将“逸”概念界定为:“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3]120。可见,“逸品”特征体现在不为传统画法所限制,不追求物象的逼真再现,笔简形具即可,贵在体现“自然”之本性,创作主体之“意表”。虽然,朱、黄二人对“逸”理解有所差异,但在敢于突破法度、表达主体情性上,却是类似、相通的。
祁彪佳抓住了“逸”的本质内涵,将其纳入戏曲风格品评体制。“曲品凡例”指出:沈璟“《四异》独以“逸”称,并进一步评其:“巫、贾二姓,各假男女以相赚,贾儿竟得巫女。吴中曾有此事,惟谈本虚初聘于巫,后娶于贾,系是增出,以多其关目耳。词之稳协,不减他作;至于脱化,乃更过之。净、丑白用苏人乡语,谐笑杂出,口角逼肖。”[1]9《四异记》今虽未见,但从品评中可知,该传奇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奇”“异”的特点,尤其是净、丑两个行当的说白,用“苏人乡语”“谐笑杂出”,这些表现方式与之前戏曲“正统”相比,都是令人颇感意外的艺术手法。在祁彪佳看来,“逸”是可与“奇”“异”画等号的品类,“奇”“异”可视为“逸”的风格特征之一。这一点从其他作品的品评中也可以看出:
沈璟《博笑》:词隐先生游戏词坛,杂取《耳谈》中可喜、可怪之事。
陈与郊《樱桃梦》:炎冷、合离,入浪翻波叠,不可摸捉,乃肖梦境。
苏元俊《梦境》:传黄粱梦多矣,惟此记极幻、极奇、尽大地山河、古今人物,尽罗为梦中之境。[1]9-12
祁豸佳《眉头眼角》:“词情宕逸,出人意表。”[6]173
可见,“奇”确实是祁彪佳评定“逸品”的一个标准。明中后期思想领域弥漫着强烈的自由主义解放潮流,由此引发的“尚奇”艺术观念,不仅影响到当时的各门类艺术创作,同样体现于戏曲批评中。
对“奇”的崇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主体对于“情”的自由宣泄与表达。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唯情主义,可谓是戏曲趋“奇”求“情”的导火索,戏曲创作者们不仅极尽想象、幻想之能,采用各种离奇、怪异,甚至突破常规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翻新戏曲,以博得观众的眼球;而且特别注重主体情感的表现与理想境界的追求。从这一点来看,又体现出“逸”的另一个特征,即“主体个性的回归”。
为了传达独特主体个性,创作者们尤其注重艺术语言的表达,无论是情节、曲词,还是音律、结构等,都力求做到精致、精准,不留余地,尤其注重细节的生动描绘、词藻的精雕细琢,着意追求余音绕梁、刻入骨髓,乃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境界。如:
陈与郊《鹦鹉洲》:此记逸藻翩翻,香色满楮,衬以红牙,檀板、则绕梁之音,正恐化彩云飞去耳。禺阳自诩为“写之无逸景,用之无硬事,铺之无留情。”
范文若《花筵赚》:洗脱之极,意局皆凌虚而出,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单本《露绶》:全是一片空明境界地,即眼前事、口头语,刻写入髓,绝不留一寸余地,容别人生活。此老全是心苗里透出聪颖,真得曲中三昧者。[1]11-13
评吕天成《缠夜帐》:以俊仆狎小鬟,生出许多情致。写至刻露之极,无乃伤雅?然境不刻不现,词不刻不爽,难与俗笔道也。[6]169
对于戏曲形象超乎意想的精细刻写,在祁彪佳看来,是主体为了抒己胸臆,表达个性的体现。如果不是出于个人对生活对艺术的独特见解,不会在戏曲创作中有“出人意表”的刻画;如果不具备任意恣肆、狂放不羁的个性和勇于向传统挑战、突破法度的革新意识,不会创造出一个个活灵活现艺术形象。戏曲中的“或哭或笑”“牢骚怒骂”“淋漓感慨”等极致刻画,在祁氏眼中,就是“得之自然”,是生活之自然、个性之自然的表现:
冯惟敏《僧尼共犯》:本俗境而以雅调写之,字句皆独创者,故刻画之极,渐近自然。
来集之镕《红纱》:痛骂糊涂主司,或哭或笑,豪气拂拂纸上。
朱京藩《玉珍娘》:朱君于剧中直自叙其姓名,而写其一段淋漓感慨之致。
董玄《文长问天》:牢骚怒骂,……借文长舒写耳,吾当以斗酒浇之。[6]169、172、175、175
可以说,祁彪佳对“逸”的理解,渗透着强烈的思想解放意识,在继承“逸”之“不拘常法”“得之自然”“出于意表”等基本含义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戏曲反映现实生活与表达主体情感的特性,巧妙地将“逸”与戏曲舞台表演相结合,赋予了“逸”新的时代意义。从唐朱景玄到宋黄休复,“逸品”的人群指向都在“方外”或文人,而祁彪佳却将“逸品”拓展到世俗。戏曲创作中无论是追求“奇”“异”、细节的刻骨描绘,还是突破传统常规、情感的慷慨激荡,都是回归主体、张扬个性的表现,正符合晚明“逸品”的本质内涵。
(二)“能”
“能”,最早出现于唐张怀瓘《书断》提出的“神、妙、能”三品体制。列于“能品”的书家,大多擅长某种书体,虽不乏特色,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宋代黄休复界定“能格”为:“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曰能格尔。”、[3]120可知,“能格”作者大多天赋平常,主要靠后天的勤学苦练,只要达到形象生动即可,虽然缺乏鲜明的个性风格,甚至尚未脱尽模仿痕迹,但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祁彪佳戏曲品评,对“能品”的理解大略与此相当。如:
《琼台》:其意境俱无足取,但颇有古曲典型。
汪廷讷《威凤》:曲尽惨苦。构词虽未超轶,亦自有大雅体裁。
杨文炯《玉杵》:文采翩翩,是词坛流美之笔。惜尚少伐肤见髓语,而用韵亦杂。
汪潾《轩辕》:意调若一览易尽,而构局之妙,令人且惊且疑;渐入佳境,所谓深味之而无穷者。词甚轻快,虽偶有数字不叶,亦无愧于大雅。[1]24、34、56、58
《功臣宴》:曲有讹处,衬字亦太多。然而出口松利,下韵轻稳,亦是词坛不易得者。
《泣鱼固宠》:事侭有逸致,传之尚未委婉,词亦多堆积之病。[6]182、185
以上这些作品,虽然在意境、才情、衬字、辞藻、腔调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在曲词、陈事、构局、文采以及意调等方面也不乏令人赞叹的艺术特色。可见,这类作品只要稍加修改弥补缺陷,其格调品位还是可以提升的。当然,能品中也不乏令人满意的作品,如:
王元寿《击筑》:激烈中转为悠扬之韵,觉满纸萧瑟,令人泣下。
王元寿《异梦》:此曲排场转宕,词中往往排沙见金,自是词坛作手。
史盘《唾红》:叔考匠心创词,能就寻常意境,层层掀翻,如一波未平,一波复起。词以淡为真,境以幻为实,唾红其一也。[1]37、41、44
这些作品,或曲词、或情感、或韵律、或曲调、或布局等方面有着令人称道之处,然而,就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说,某一方面的特长,并不能代表整体艺术水平与风格特色。“能品”在祁彪佳戏曲品评中所占篇幅最多,也代表了大多数作家的戏曲创作水平所属的层级,真正艺术成就卓然超强,风格独特的作家作品,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
(三)“具”
“具”,是列于末位的戏曲品类。虽由吕天成引入戏曲品评,但并未对其内涵予以阐释。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曾对“具”有所提及:“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20]“具”在此处是俱备、俱全之意。这类作品,尽管将物象的形貌、细节点滴不落地列举铺陈开来,然而却因过于谨细、只求形全,而丧失了神情和意趣。这是艺术创作所忌讳的,说明作者的创作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尚不具备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有机融合的能力。祁彪佳将这些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甚至可以说不懂作法、粗制滥造的作品,列入了“具品”:
《青楼》:全无作法,止是顺文敷衍。犹稍胜于荒俚者。
黄粹吾《胡笳》:此记以蔡琰结局,遂称《续琵琶记》。白俱学究语,曲亦如食生物不化,是何等手笔,乃敢续《琵琶》乎?
夏邦《宝带》:他人一语可了者,此数十语不了。取境既俗,出吻亦庸。
程良锡《负剑》:作者不明音律,半用北调,效颦《西厢》,遂为衬字所误;虽运词骈丽,亦不足观也已。[1]87、90、95、98
樵风《宦游济美》:满纸是塞白之语,索然无一毫趣味。
《相送出天台》:“集唐律成曲,如食生物不化。”
《同心记》此剧粗具情节,曲、白无一可取。[6]194、196、199
从中可见,祁彪佳品评“具品”,以指摘缺陷为主。这些作品无论在曲词、作法、布局方面,还是音律、故事、用古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挪用、拼凑、抄袭及生搬硬套的问题,完全没有个人独立见解,尚处于“食生物不化”的阶段。一般来说,对于创作粗糙、品位不高的作品,还谈不上“风格”问题,批评家一般不会将其纳入批评的范围,然而,这一品类自吕天成引入戏曲品评之后,祁彪佳将具品的品评发挥到了极致,他真正将具品作为一个品级,对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予以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引以为戒。可见,祁彪佳对戏曲品评所持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并非简单套用前人的品类体制。
四、附设杂调、详尽周全
此外,祁氏还在《远山堂曲品》中附设杂调,这是吕天成《曲品》所没有的。吕天成对于不入流、无品格的作品持排斥态度,其《曲品自叙》说:“多不胜收。彼攒簇者,收之污吾箧”[21],攒簇是指写作粗糙,类似于杂调的作品。而祁彪佳却采取宽容的态度,在“曲品凡例”指出:“吕品传奇之不入格者,摈不录,故至具品而止。予则概收之,而别为杂调。工者以供鉴赏,拙者亦以资捧腹也。”[1]7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吕品的不足,祁彪佳才将46部杂调作品附设于品评体制之后。
《三元》:然境入酸楚,曲无一字合拍。
《双璧》:作者有意构局,终未大雅,而又无奈其不识音律何也。
《勤善》:全不知音调,第效乞食瞽儿沿门叫唱耳。无奈愚民佞佛,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哄动村社。
叶俸《钗书》:龙女配陈子春生三子,乃天、地、水三官,一何荒唐也!此等恶境,正非意想可及。
朱少斋《破镜》:朱弁之忠,玉英之节,奈何以俚语辱之,一至于此![1]112-122
从以上品评可以看出,祁彪佳对杂调的评价也以指摘缺陷和否定为主。这些剧作虽然在表现形式方面,字不合拍、构词错杂、不识音律,而且存在故事离奇荒唐、拾掇旧曲余唾的现象,甚至曲词中充满低俗的俚语或不懂曲调类似于乞儿沿门叫唱,然而这些粗鄙的艺术样式,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乡民来说,却能“三日夜演之,哄动村社”,令人“捧腹”。说明这些通俗易懂的剧作,虽然艺术性不高,但其形式却是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这些作品对于宣扬伦理道德教化观念,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作品作为戏曲创作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同样不可忽视。可见,祁彪佳另设杂调予以品评,具有详尽周全之意。
结 语
综上所述,祁彪佳在继承前人品评体制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戏曲创作实践,对戏曲作家、剧作风格特色及成就高下作了系统而深入的品评,其戏曲风格品评体制是全面而周详的,富有理性思考的选择。他的品评既有褒扬性的夸赞,也有贬斥性的指责。他以宽容大度的胸怀,将戏曲创作领域众多作家、作品纳入品评的视野范围,以客观、中肯的态度,冷静理性的思维、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洞察力,对作家、作品风格特色、优长不足与高低优劣,逐一进行分析评价,将他们纳入极具审美意义的品级框架之中,真正实现了戏曲品评等级性与审美性、风格性与类型性的融合,克服了以往对作家作品风格一概而论、模糊定位的弊端。尤其是其所创立的“妙”“雅”“逸”“艳”“能”“具”风格品评体制,是对古代“分级品第”批评方式的承继,又一次将古代文学艺术风格品评推向了新的高度,巩固并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批评传统,彰显了中国文学艺术批评理论的民族特色。
[1][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明]王骥德.曲律[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四[G].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潘运告,主编.宋人画评[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4][战国]易传,系辞上[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第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2.
[5][明]汤显祖.牡丹亭,惊梦[M]//金宁芬.明代戏曲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4.
[6][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39-144.
[7][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M]//潘运告,编著.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303.
[8][战国]孔子及其弟子.论语,述而[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第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1.
[9][梁]刘勰.文心雕龙,体性[M]//张长青.文心雕龙新释[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314.
[10][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39.
[11]张国庆.《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18.
[12][汉]诗大序[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第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
[13][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3.
[1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208.
[15][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94.
[16][战国]左丘明.左传,桓公元年[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3.
[17][汉]毛亨,毛苌.小雅,十月之交[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第十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25.
[18][汉]扬雄,记,郭璞,注.方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19][宋]欧阳炯.《花间集》序[M]//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上[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3.
[20][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潘运告,主编.唐五代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178.
[21][明]吕天成.曲品[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07.
J809;J801
A
1008-9667(2017)03-0115-08
2017-03-09
张兰芳(1974— ),女,山西太原人,艺术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古典艺术理论、艺术传播。
① 本论文为2016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范畴整体研究”(项目编号:16DA01)阶段性成果;2016年度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唐宋艺术风格范畴的转型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01176B)阶段性成果;2016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的艺术风格范畴研究”(项目编号:2016SJD760016)阶段性成果;2015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5ZSTD008)阶段性成果;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艺术学经典理论文献研究”(项目编号:2010JDXM00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晓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