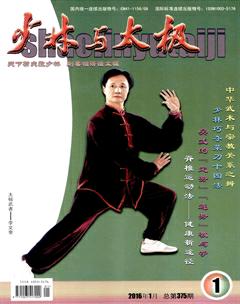中华武术与宗教关系之辨
张秉山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同属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和交集。所以对武术文化性质的定位及其与宗教关系如何界定,有些人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武术具有神学性质,是宗教的附庸,还有人认为中华武术是经达摩祖师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所以“天下武功出少林”。所谓“少林武功是佛教功法,武当武术是道教功法”之说,似乎更加印证了武术的宗教属性;一些拳种标榜自己是“神传仙授”以及武林中供奉“武圣关公”,更增加了武术的神学色彩。那么,我们就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武术文化的定位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进行辨析厘清。
一、武术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独立文化体系
武术萌生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已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正值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同时也是学术活跃、思想繁荣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华武术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武术的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并成为两千多年来武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源泉。中华武术于此时实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大飞跃,使武术从单纯的搏击格杀之术,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上,至此,中华武术具有了“思想灵魂”。
张岱年和程宜山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在人类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在批判宗教方面却是相当雄辩的。中国古代哲学将事物内部阴阳对峙视为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第一推动力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宇宙是一个整体和过程,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和与此岸世界截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之类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亦即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因而像佛教那样以世界虚幻不实的观念受到最坚决的排斥,如此等等……它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置于哲学的控制之下却有着决定意义。而这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推行道德……另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去论证政治……这就是避免了政教合一……近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就是古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硕果。”冯天输、吴积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奥秘》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概括的主要是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并没有与宗教意识混淆……各种道德意识又左右着中国文化,这就使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較淡薄……”以上专家学者的论述,正是对武术文化的属性及其与宗教关系的很好说明。
二、武术与佛教的关系
僧人练功习武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个特点,特别是还开创了影响世界的武功门派——少林武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把武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认为“武术是佛教的附属”,是宗教的产物。
笔者在认真研究了佛教的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组织和活动、佛教文化等方面之后,没有发现支持武术与佛教有必然联系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武术不是佛教本质属性的一部分,就像很多僧人懂得中医,能治病救人一样,不能说中医就具有宗教属性。不论僧人和俗家百姓,练功习武都要符合人体生理结构特点,都是肢体的运动。正常人与宗教信徒都是人,生理结构是相同的,所以武术技能也是相同,佛教武功常人也能练,民间武术僧人也能练。
在少林寺之前,僧人练武术早已有之,只是在隋、唐之际,少林寺僧人协助过李世民受到朝廷的褒奖以后,寺院武术才蔚然成风。佛教寺院僧人练功习武,并不是佛教信仰、教义的要求。其真正的原因如下:其一是为了保护寺院田产不受兵、匪及饥民的抢掠,也就是同民间的“看家护院”相同;其二是,佛教徒除了佛学功课和必要的劳动之外,其他活动很少,生活单调枯燥,通过练功习武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消遣娱乐。所以,僧人练武的原因和目的同民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佛教寺院武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少林武术了,其历史之久远、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既是中华武术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殊现象;既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世界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嵩山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是魏文帝为印度高僧佛陀扇多译经传教所建。从文献资料中找不到关于佛陀练功习武的记载,但他的两位高徒僧稠和惠光都是民间武术高手出身,可见少林寺僧人在建寺之初就开始练功习武,并且这也说明了少林寺武术也是从民间或军旅传入的。
少林寺作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其创始人菩提达摩于梁代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自印度来华弘扬佛法,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于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圆寂,葬于熊耳山。后人据此而传说“少林武功为达摩所传”,“达摩所传授的《易筋经》、《洗髓经》为少林武术之祖”。这些说法纯属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因为武术史学界从古代典籍中从未见到有关达摩练功习武的记载。据武术史学家唐豪考证,此种传说出自明代。
事实上,除少林寺外,中国大多数佛教寺院都有练功习武的传统,比较有影响的如南少林寺以及峨眉山、五台山等地的佛教寺院。很多武术拳种、拳械套路及招式都有佛教的色彩,如罗汉拳、佛家拳、佛汉拳、僧门拳、空门拳,以及童子拜佛、老僧入定、金刚抱琵琶等,但它们并不是少林寺独有,也不是由宗教所决定,它们只是一些汇集了宗教成分的武术形式。但同时,佛家思想和寺院僧众丰富了武术的练习方法和内容,并开创了享誉世界的少林武功,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寺院武僧都能勇赴国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的爱国篇章。
三、武术与道教的关系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以老庄哲学思想为教义基础,并继承了先秦神仙传说与导引养生方术,因而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道教与武术有着极为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思想上,中国武术的阴阳辩证观、五行生克观及因敌变化、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等思想均与道教来自同一渊源——老子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气功多来自道家内丹学,以吐故纳新、除欲净虚为要旨,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炼虚合道”之说,就是气功的“积精累气之学”,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实用价值。道教的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具有独特的强身健体增益健康的作用。无论武术的任何门派或拳种,对于“行气”和“运气”、“气达四稍”、“舌顶”、“津液满布”、“沉气”、“清升浊降”、“精养灵根气养神,养精养气见天真,丹田养就护命宝、万两黄金不与人”之类渗透着养生之本思想的修炼方法都有记载和传承。
如同佛教与武术一样,道教教义信仰与武术没有必然的联系,武术不是道教的本质属性的一部分。而道士习武同常人一样,都要遵循武术技法原理,都是人的肢体综合运动,都要符合人体生理结构特点。
同样,道教文化对中国武术贡献极大。“佛有少林,道有武当”,武当山道众开创了中国武术的另一大宗派——“武当武功”,其贡献及影响不亚于少林武功。以武当武术为核心的内家派武术的特点是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后发制人,“不以硬而犯力”,冈0柔因敌而变。它的功理功法更具哲理性和辩证法,更加注重内功修为和人与天地的和谐统一。道家武术更注重健身和养生,它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养生术。道家武术以道教哲学及道教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医学、内丹学、养生学的成果,将武术技击和健身术融为一体,讲究经络穴道,以练好坚实内功为筑基,以气发力,借力打力,擅长以柔克刚,具有刚柔相济、技巧性强、以静制动、避实击虚、灵活圆转等特点。习道教武术者“外能技击抗敌以自保,内能强身健体以养生”,可兼得技击和养生之效。在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身心健康和高品位生活的现代社会,道家武术因所具有的良好的健身效果而备受青睐。武当武功的影响对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当代流传的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太极拳不是直接来自道家武术,而是来自民间,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与道家武术具有同一文化渊源,即老庄哲学思想。
四、武术与民间宗教的关系
在中国下层社会中,秘密组织教门传习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相互帮助的事古已有之,到了清朝时期更加活跃,很多秘密会道门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组织武装斗争,因而遭到清王朝的严厉镇压。清廷在严禁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的同时,对民间武术传习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在这种“禁教不禁拳”的环境下,民间教门和秘密社团大都借传习武术来掩蔽其宣传教义、社旨,并以此发展组织和蓄养武装力量的宗旨,如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以及义和拳(团)、拜上帝公等。这些组织都利用武术作为凝聚民众的主要手段,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传播与发展。他们注意吸收习武者入教,在教内设有拳场武场,在演武的旗号下秘密传教,有些组织结构相当严密。
白莲教以后衍生出了清水教、罗教、八卦教(天理教)、弘阳教、三阳教、羅祖教、混元教等支派。天地会内称“洪门”,别称“洪家”、“红帮”,以后繁衍出青帮、匕首会、双刀会、棒棒会、平头会、江湖串子会等支系。这些组织的骨干都是武林高手,有些甚至为一代武林宗师。很多民间拳师和武术习练者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清斗争,促成了拳会与教门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播与发展。
由于拳会与教门混杂,也有些歪门邪教宣扬迷信,什么“神仙附体、刀枪不入”或神仙下凡传授“神功真法”的故弄玄虚的宣传无限夸大了武术技击功能,这就使武术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同时也使人们把武术误解为“迷信活动”或“神学运动”。武术在冷兵器时代既是军事手段又是大众文化,在人民群众当中影响很大,因而各种教门会社利用武术为其服务,即使是宣扬迷信也不能说武术木身具有迷信色彩,而只能说是这些教门具有迷信色彩。
五、武术与关帝崇拜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被立庙祭奠最多的莫过于孔子和关羽,一个是“文圣人”,一个是“武圣人”,其祭奠的庙宇俗称文庙、武庙。在民间,供奉“关圣帝君”恐要多于孔子。关羽为三国时期蜀汉大将,追随刘备功劳显赫,公元219年被东吴所杀。一部《三国演义》使关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忠义仁勇”,是儒家推崇的典范;佛家尊关羽为“关公”“关帝”,把他列为“咖蓝神”之一进行供奉;道教尊关羽为“关帝圣君”。关羽在世时被封为“汉寿亭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被追封为“忠惠公”,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帝圣君”。儒、释、道的尊崇和历代皇帝的追封加爵,使关羽被神化,进而形成对“关帝圣君”的全民崇拜。
对关羽的崇拜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封建迷信和神祗尊崇。因为关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生前表现的“忠义仁勇”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典范,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儒、释、道和历代君王对关羽的尊崇正是对他的精神的肯定和宣扬,所以“关帝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现象。即使在当代,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关公神像,就有关帝崇拜,可见其影响极其深远。
关羽忠义仁勇、武功高强、勇贯三军,已达中华武术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因而他更加受到武林中人的崇拜。同时小说中关羽使用的“青龙偃月刀”即“关刀或“春秋大刀”的形制(三国时没有“刀”这种武器,刀为宋代以后的兵刃)一直延用到今天,成为中国传统武术主要长器械之一,习练者大有人在。所以,关羽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极其深远,并得到古今武术界的供奉崇拜。
然而,不能因为武术界对关羽的顶礼膜拜,就把武术看成“神学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行业崇拜”,正如读书人尊崇孔子、营造业尊崇鲁班、医学界尊崇张仲景、茶叶界尊崇陆羽、梨园界尊敬李隆基一样,武术界对关公的尊崇也应属于行业崇拜,只不过对“文武圣人”的崇拜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六、结语
通过以上的辨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华武术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是中华文化巨系统中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不从属于任何宗教,也不具有神学色彩,尽管我国文化中有多神崇拜,宗教与武术有交集,封建迷信活动利用武术等,这些也改变不了“武术作为无神运动的本质属性”。
(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