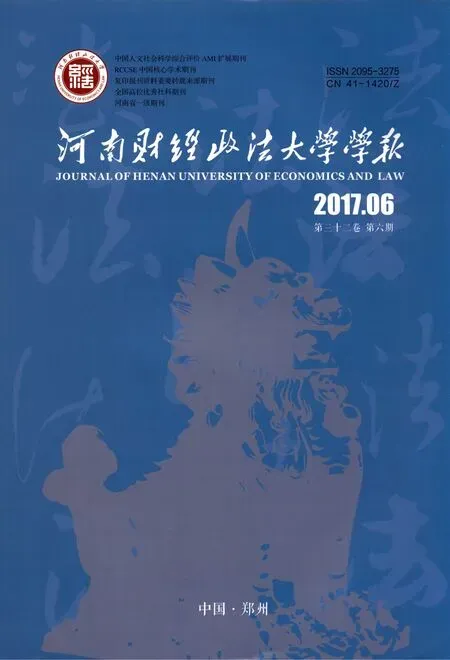著作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
罗 祥 张国安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著作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
罗 祥 张国安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362021)
人工智能创作丰富了作品市场,同时也带来了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利用著作权制度规制的难题。狭义著作权制度与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存在难以解决的理念冲突与规制困境。邻接权保护则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与著作权原理的冲突,同时能合理配置人工智能创作的利益关系。我国应该就人工智能创作邻接权保护增设新类型,从邻接权主体、客体、权利内容、保护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邻接权
当前国内研究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的主要争议有二:一是人工智能能否成为作者或者著作权主体,二是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成为作品,二者都关系到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目前有关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术语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人工智能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物、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等不同的表达。。之所以存在上述争议,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创作颠覆了著作权视野中关于作者的基本理解,也颠覆了法律关于主客体不能互换的基本原理。对此,学者之间分歧较大,有学者坚持传统认识,主张人工智能创作物不能成为作品而排除著作权保护,有学者则认可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的可行性,比如熊琦等学者主张适用著作权法上的单位(法人)作品制度[1]。本文在检视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观点与理由的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保护。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之障碍
(一)著作权主体之障碍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能否成为作者;二是人工智能能否成为著作权人。基于“作品著作权归作者”的基本规则,作者与著作权人往往具有同一性。我国《著作权法》将作者分为自然人作者和单位作者。前者是指创作作品的公民(自然人),后者是指“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参见《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单位作品条款凸显了特定情况下作者认定的困境:一方面,真正的作者只属于创作的自然人[2],但在特定情况下对于创作没有决策权,只能听命于人,徒有作者之表,无作者之实;另一方面,法人等组织虽然不具备创作的生理基础,但是能够指挥自然人创作,贯彻其意志,并且承担作品所能产生的责任。换言之,能够借助自然人作者之手,像自然人作者一样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实际创作的自然人或者作为组织者的单位,与典型作者场景都存在本质性差异,只具备典型作者的部分特征,谁被认定为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问题。如果坚持自然人作者观,那么单位就不能成为作者;如果不那么坚持自然人作者观,单位就可以成为作者。不过鉴于只有自然人才能实际创作,单位只能被“视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表述在承认单位可以成为作者的同时,也承认单位作者仅仅是一种拟制,旨在确定著作权人。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人工智能能不能成为作者,成为著作权人;如果不能,接下来需要讨论有无拟制解决的可能,一如单位作者。人工智能成为作者的障碍与单位作者有相同之处,即二者均不存在血肉之躯,无创作的生理基础;不同之处在于单位借助自然人之手完成创作行为,而人工智能则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模拟自然人思维,从而独立完成创作行为。从实际效果看,人工智能可以脱离自然人创作出“作品”;从价值角度看,确立作者的基本目的在于授予作者著作权,激励作者的创作活动,而人工智能不需要这样的奖励,这样的奖励也无法激励其创作。真正需要激励的主体是使人工智能能够创作的人或组织,不过这样的人或组织并不执行具体的创作活动。对此有学者主张区分事实作者和法律意义的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事实作者,法律意义上的作者只能是自然人或者自然人组合(组织)[3]。笔者以为该组概念提出的益处在于能够将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区分开,从而可以更好地考察人工智能创作从第一性的社会现象上升到第二性的法律规范所发生的变化。尽管人工智能有成为事实作者的可能,但是绝无成为著作权人的可能。因为根据主客体不能互换的基本原理,人工智能绝不可能超越客体层面而成为著作权人,否则会颠覆整个法律体系。
在人工智能事实上能够创作但又不能成为法律上作者和著作权人的情况下,能否通过拟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呢?一如单位作者。笔者以为难度很大。单位作者存在的基本前提是,单位作为“人之联合”可以作为承担法律权利义务的主体,但人工智能无法承担法律权利义务,因此拟制的立法技术无用武之地。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客体化之障碍
人工智能创作物面临着著作权客体化的障碍。著作权客体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前者主要将作品与创作行为的概念相关联,后者主要将作品与独创性的概念相关联。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的话,版权所讲的是作品的创作。”[4]从行为论的角度来看,审视机器人的“创作”行为会颠覆传统观念对行为的定义,缘由是行为属于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一旦脱离了人对机器人的指令,这种行为显然不能独立存在,故机器人“创作”不能用创作行为论进行解释。这和版权的概念出现冲突[5]。“创作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主要形式,是一种观念性活动,具有鲜明个体性特征”[6],即使是电脑进行的“创作”行为,其仍然依赖人的能力并靠人的能力工作。一件纯粹由机器“创作”而成的“作品”不可能归于精神生产的范畴。
从独创性角度来说,著作权法视独创性为作品的必备条件和本质属性,这是各国著作权立法通例。作为作品的必要属性,独创性意味着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拥有独创性的思维与独创性的方法,否则就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机器创作常见于两种模式:其一,按照人已经设定好的信息筛选程序,机器人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得出结果,然后由人完成最终写作。其二,根据人预先设定的模板程序,加工后直接得出作品。从法教义学角度来看,上述人工智能创作模式不具备独创能力;即便承认人工智能因具备模拟人的某种感知和判断能力,能够脱离算法预设能动性地解决新问题,在生成内容过程中省去了人的参与,但是在法教义学上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上仍然存在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独创性的判断实质上是以生理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作为前提的。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化之现实需求与解决路径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化的现实需求
人工智能市场前景广阔。乌镇智库发布的《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7]显示,美国、中国、日本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上位列前三甲,三国专利申请数量总和占到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73.85%。自2001年,我国每年新增人工智能专利数增幅较大,申请数、授权数增长了40倍左右,共计15745项,位列全球第二,而且自2012年开始我国的专利申请数及专利授权数超越美国。随着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上的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将更多的关注度与资金投入到人工智能领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一个名为“任性的人工智能之我是作家”的团队,用人工智能创作出来的短篇科幻小说《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通过了日本著名科幻文学奖“星新一奖”的初审,评委们的意见是情节无破绽[8]。2015年9月,索尼用人工智能Flow Machines通过分析一个包含13000首流行歌曲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歌曲库,探索出独特的编曲风格,写了两首流行歌[9]。今年1月20号,由机器人自主撰写运营的凤凰号“小凤百事通”正式上线,它具备较为成熟的短语生成、句法语义分析、文本精炼的能力,同时还能够自动依据上下文内容,给文本搭配相应的图片和图表[10]。今年微软的人工智能“小冰”推出了“个人”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风靡网络,“掌阅科技”擅自在其APP上自主发布,还有一些网友在网络终端上传小冰诗集的链接[11]。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既给社会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任由人工智能创作物被侵权,无疑会阻碍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法经济学告诉我们,立法兼具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属性,对立法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分析成为必要。对人工智能著作权法规制不仅要从传统法律视角,也要从经济效益的直接收益,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公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与社会秩序的安定等间接收益来制定法律[12]。人工智能创作需要法律保护,方能激励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人工智能创作物作为一种信息内容,无疑与作品非常接近,因此利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具有天然的基础条件。不过,人工智能创作毕竟不同于自然人创作,人工智能创作物利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面临着很多障碍。这些障碍能否克服是个中关键。
(二)解决路径
“运用著作权理论”认为著作权不仅具有一般财产权属性,其价值更应体现于潜在的应用能力,或者说著作权的价值依赖实际运用和转化为产业的行为[13],这对著作权制度宗旨和规则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立法宗旨上,很多国家开始将推动文化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著作权法的终极目标。日本著作权法规定,确定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广播和有线广播的著作权或邻接权,保护作者、传播者的权利及相关文化产品的正当合理的使用,最终促进文化发展*Article 1 of Copyright Law of Japan(2010)。韩国著作权法也如此规定*此处依据2009年4月韩国英文版本著作权法第一条目的英文表述:本法目的为推动文化和相关产业的提升与发展作贡献而保护作者著作权与邻接权并促进作品合理使用。。韩国和日本作为工业发达国家,著作权立法宗旨的规定符合TRIPS对于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规范期许,即通过传播知识,改善和提高民众生活*Article 7 of TRIPS agreement。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相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等。”显然,我国同样将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保护著作权以及邻接权,促进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成为手段或者次要目标,其中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确定了基本目标的外在形式,而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则提出了内在要求。《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征求意见稿强化了现有的立法倾向,比如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改为“传播者的相关权”,强调了传播者地位;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改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第一稿及第二稿第一条。,进一步强调著作权立法的经济目的。当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成为发展文化科学事业的手段,那么根据基本目标对手段性目标进行相应调整成为可能。
著作权理论和规则随着作品生产与传播实践逐步发展。自然人创作仅仅是文化事业发展的起点,著作权法传统理论与制度都立基于自然人创作这个相对简单的社会现实,但是随着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首先是传播者的地位日益重要,对传播者的保护逐渐诞生了邻接权。其次,内容产出也渐次产生变革。最初主要是自然人的个人创作占据主流,传播者被动接受自然人作者的作品;随着传播者实力的壮大,对文化市场运作的理解,开始主动介入作品内容生产,确定目标读者,策划选题,组织自然人进行创作开始成为常态。与法人等组织通过人工组织和内容控制干预内容生产相比,人工智能是以机器代替自然人创作或者自然人的集体创作,是一次更高的内容生产模式变迁。内容生产模式变迁对著作权规制提出了挑战。是继续坚持自然人创作的基本理念、制度结构还是与时俱进推动理论与规则更新成为著作权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
对此,作者权法系和版权法系呈现出不同的解决方式。作者权法系主要立基于自然人创作的事实,试图在坚持自然人作者观的前提下解决新问题。首先,在个人作品之外,出现了委托作品、职务作品等规则,用以解决传播者参与创作的情形。其次,对于个人创作作品之外的内容生产行为,设立邻接权制度予以保护,比如各国普遍对录像制品、广播节目信号给予邻接权保护。《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对科学版本提供某种邻接权的保护,作品的科学版本是诸如古籍点校、古画临摹等为原作品赋予新的版本的创作[14]。欧盟议会与欧盟理事会颁布了《关于数据库保护的指令》,给予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See DIRECTIVE 96/9/EC,Article 1.2。
深挖和外设在解决内容生产模式的变迁上各有适用空间。前者在坚持自然人作者观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即自然人创作是共同基础,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传播者的利益。后者主要处理与传统的自然人创作迥异的情形。基于著作权与邻接权区分的预设,邻接权保护不必遵循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理念。与作者权法系不同,版权法系主要源于图书专营制度,从传播者需要的角度设计规则成为其起点,因此作者是一个多变的概念,可以根据具体内容生产情形进行具体设置,不必囿于自然人。作品独创性概念也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提出将“额头滴汗”作为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因此在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上,版权法系主要需要解决的是保护的正当性问题,即人工智能创作物有无必要根据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规则设计本身不存在太多理论障碍。在作者权法系内,鉴于人工智能创作与自然人创作完全不同,因此以深挖的方式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几乎不可能,外设式的邻接权保护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
三、我国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保护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适用单位作品制度的困境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我国有学者建议适用单位作品制度。单位作品制度规定在狭义的著作权制度中,属于自然人作者的例外规定。这与本文有关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的观点相悖。不过,单位作品制度是我国学习引进版权法系立法经验的不成熟的产物,本身不值得提倡。而且,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与单位作品制度也不是很契合。
单位作品制度与狭义著作权基本原理相悖。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作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由单位主持,代表单位意志和由单位承担责任。该条件设置一方面承认单位本身是无法直接从事创作活动的;另一方面,以单位介入、干预创作活动为由将其拟制为作者,背离了作者的真实含义,本质上是对单位作为原始著作权人合理性的论证。故单位作品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作者概念误解的结果。作者权法系与版权法系对作者的理解之所以大相径庭,主要源于概念设置功能的不同。版权法系将原有的图书出版特许权投射到作者身上,是根据出版商的需要设计版权,作者的界定并无特别限制。而作者权法系的著作权是针对自然人创作的典型场景设计,作者的概念不能随意扩大;著作权不仅包括财产权,还包括人格权,将作者外延扩大到单位,就会与以自然人创作为基础建立的理念、规则相冲突。其次,在坚持自然人作者观的情况下,单位介入、干预创作活动的情形已有委托作品、职务作品的规则处理;引入单位作品规则,会与前述规则相冲突。因此单位作品制度在狭义著作权制度中,显得孤零零的,无法与其他的相关规则协同[15]。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有时可以适用单位作品制度,但二者不是很契合。单位作品制度以单位代替自然人作者的情形与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单位取代实际创作人成为作者,法律效果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单位组织自然人创作与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的情形不同,以前者的认定条件来处理后者的情形,前者适用条件的表述很难理解。如代表单位意志创作的条件就无法解释,因为当人工智能仅仅被视为机器的时候,不具有意识意志,那么怎么能够代表单位意志创作呢?而且,人工智能创作不一定全部是单位投资人工智能进行创作,可能是个体自然人利用人工智能创作,这时就无法适用单位作品制度。
(二)邻接权保护的合理性
鉴于狭义著作权保护的严格性,作者权法系产生了邻接权制度。二者在制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第一,制度宗旨要求不同。著作权主要保护自然人作者创造性,激励其创作;而邻接权主要保护传播者的投资,激励创造性不是其主要目的。第二,客体要求不同。著作权一般保护作品,而邻接权一般保护作品传播媒介以及作品以外的劳动成果[16]。著作权法对作品有独创性的要求,邻接权客体不要求独创性或者对独创性要求比较低。第三,权利主体有别。狭义著作权主体一般是自然人,而邻接权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非法人等组织。第四,权利内容设立有别。著作权包括人格权和财产权,而邻接权一般不包括人格权,财产权内容因邻接权种类不同而进行区别化设计,根据保护需要进行增减。更为重要的是,邻接权不是一个封闭的制度体系,而是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增设。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是各国普遍设立的三项邻接权。除此之外,各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行设立,比如我国设立了出版者版式设计权;德国对独创性比较低的照片、科学版本保护设立邻接权保护。
基于下列原因,人工智能创作物适用邻接权保护更为合理。首先,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与邻接权保护投资的宗旨更为契合。机器写手的诞生凝结了创造者的大量心血,人工智能的诞生需要投入大量的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比表演者的演出、广播节目信号要付出更多的脑力劳动和资金投入;如果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不进行保护,那么就会存在投资激励不足。其次,人工智能依托大量的信息,在逻辑算法基础上对信息进行整合最后得出文稿,这种工作模式不同于普通的作品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舞台上的表演方阵,录音制品的制作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信号制作。故人工智能创作本质上是文化工业发展的产物,其客体更符合邻接权客体的一般特征。再次,采取邻接权保护更容易解决人工智能狭义著作权保护面临的理论难题。狭义著作权坚持自然人作者创作观,结果无法找出合适的作者,人格权内容无法安置、权利保护范围过广可能会造成激励过度等一系列难题。而在邻接权保护中,作者实际上就是文化产品生产者,不必囿于自然人;人格权保护可有可无;权利内容可以根据需要设计,不必担心激励过度的问题。
(三)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的具体制度设计
1.增设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新类型。现有邻接权类型无法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各国普遍规定了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除此之外,各国根据各自需要还增设了一些特殊的邻接权类型。如意大利著作权法将戏剧舞台布景、个人书信及肖像、工程项目设计归入邻接权保护[17]。德国将独创性较低的照片、科学版本、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等纳入邻接权保护,我国则规定了版式设计权和录像制作者权。因此邻接权类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增设,针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增设新的邻接权类型不存在理论障碍。在实践中,鉴于邻接权种类有限,在实务操作中对相关的利益保护往往借道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过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仅限于具有竞争关系的商业主体之间,主体限制明显。且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利益平衡机制欠缺,无法对相关利益保护进行精细的利益衡量。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可能性不影响邻接权保护的正当性。我国现有的邻接权类型都是针对特定的文化产品类型设置的,无法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因此有必要专门就人工智能创作物增设新的邻接权类型。
2.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的具体规则设计。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制度应该包括客体、内容、主体及权利归属、保护期限等必备内容。其他诸如侵权保护、权利限制等规则可以适用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则,从而最大限度的节约立法成本。
第一,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客体。目前存在人工智能创作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人工智能作品、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等不同的术语表达。鉴于需要注意区分作品与人工智能客体,本文选用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术语表达。人工智能创作物是指人工智能首次生产完成的具有独创性的内容表达。其界定参照了作品的界定,同时限于人工智能所生产。独创性的要求旨在将人工智能生产的普通信息与具有作品属性的信息区分开,防止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过宽保护。
第二,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主体。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旨在保护投资,那么投资人应该为权利主体。参照单位作品定义,投资、组织、控制人工智能创作的主体应为权利人。英国版权法规定,为计算机所生成之作品进行必要程序者,视为该计算机生成之作品的作者*英国版权法第9条之3。,该规定可供参照。
第三,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内容。在人格权保护方面,鉴于人工智能没有思想和情感,应该排除人格权保护,不过“署名权”可以保留。署名有助于在特定人工智能与其创作物之间建立起联系纽带。经过训练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可以形成自身的创作风格,读者可以形成相应的阅读体验预期。这有助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销售。因此署名有助于将不同人工智能的创作物区分开。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财产权,相对于著作财产权设计应该予以缩减,适度降低保护水平。缩减财产权内容是各种类型的邻接权保护的普遍做法。如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只有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组织者权的内容,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只有转播、录制以及复制录制品三项权利。权利内容的缩减固然与前述客体的市场有关,但同时也是适度降低保护水平的必然选择。比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的财产权内容,可以发现只保护客体的主要市场,录音录像制品主要存在复制、发行市场以及网络传播,广播组织者权主要保护广播市场,甚至连网络转播市场都被排除在外。借鉴其他类型邻接权内容的设计经验,人工智能创作物财产权应该包括复制权、发行权以及网络传播权,这是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主要市场,予以保护可以保障投资人收回投资。
第四,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期限。邻接权保护期限长短不一,我国对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者权保护期限是50年,而版式设计权的保护期限是10年。德国对邻接权保护期限规定更为丰富,比如特定版本保护期限是25年,数据库的保护期限是15年,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广播组织者权是50年。经过分析,可以发现邻接权保护期限普遍短于著作权保护期限。而且,各种不同的邻接权保护期限因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别,一般来讲,越接近作品的,保护期限越长。鉴于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发展迅速,作品更新很快;人工智能创作产量大,容易产生信息爆炸,建议我国可以给予10年保护期限,从人工智能创作物发表之日起计算;创作完成后10年没有发表的,法律不再保护。
四、结论
人工智能创作给我国著作权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人工智能创作物需要法律保护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如何保护则成为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存在单位作品这样的制度资源,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够提供某些保护,但是无法针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特殊性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故本文提出人工智能创作物邻接权保护,并初步设计了具体的规则内容。目前我国正值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有必要将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纳入修法规划。这对促进人工智能产业以及文化事业发展都意义非凡。
[1]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3):7-8.
[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4-55.
[3]Annemarie Bridy,Coding Creativity:Copyright and the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Author,2012Stan.Tech.L.Rev.,5.
[4][美]保罗·戈尔茨坦.论版权[J].著作权,1992,(1).
[5]曹世华.版权理论中的创作概念[J].法学研究,1997,(6):80-81.
[6]曹世华.论作品独创性之合理规定[J].法律科学,1996,(6):34-35.
[7]网易科技.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EB/OL].http://tech.163.com/photoview/6PGI0009/13525.html#p=C5TF7OCJ6PGI0009,2016-11-15.
[8]观察者网.日本科研团队用人工智能写小说 参加比赛已可过初审[EB/OL].http://news.dahe.cn/2016/03-23/106618815.html,2016-03-23.
[9]腾讯科技.索尼用人工智能写了两首流行歌,你觉得怎么样?[EB/OL].http://tech.qq.com/a/20160927/011089.htm,2016-09-27.
[10]中国青年网.小凤百事通”上线,开启人工智能新时代[EB/OL].http://finance.youth.cn/finance_jsxw/201701/t20170122_9057957.htm,2017-01-22.
[11]IT之家.微软小冰新诗集版权遭侵犯,人工智能著作权应被保护[EB/OL].https://www.ithome.com/html/it/312145.htm,2017-06-06.
[12]刘瑞瑞.立法成本的法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2006,(8):64-66.
[13]马忠法,孟爱华.论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修改——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视角[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3):103-109.
[14]雷炳德.著作权法[M].张恩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00.
[15]邹晓红,许辉猛.智力投入者和财力投入者分离下的著作权归属研究——评我国的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制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26-130;许辉猛.论委托作品条款的适用范围——以非独立创作的作品类型为视角[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05):88.
[16]梁慧星.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与利益衡量[J].法学研究,1995,(2):81-89
[17]郑思成.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1-61.
Protec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WorksfromthePerspectiveofCopyrightLaw
LuoXiangZhangGuo’an
(LawSchool,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Fujian362021)
The wor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riches the works market,but also brings problems about whether to regulate it with copyright system.There are conflicting between the ideas and rules’ dilemmas in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copyright system and the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ighboring right protection helps to mitig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copyright,and can also reasonably configure the intere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s.In China’s copyright law a new type of neighboring right should be created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orks,that includes specific provisions on the subject,object,content and duration of protection.
artificial lntelligence; artificial lntelligence works; copyright; neighboring right
2017-07-05
罗祥,男,华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张国安,男,华侨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D923.41
A
2095-3275(2017)06-0144-07
责任编辑:许辉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