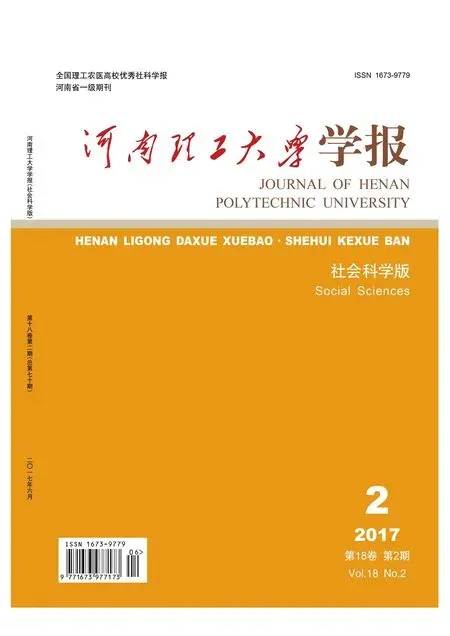“技术垄断”之思之道路:波兹曼和海德格尔
陈皓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技术垄断”之思之道路:波兹曼和海德格尔
陈皓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美国著名媒介环境学家尼尔·波兹曼提出的“技术垄断”时代的论点,得出了文化在向技术投降,并沦为技术的奴仆的结论。他通过阐释“技术垄断”提出的背景及其含义,得出了人类文化历史进程可划分成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个时期的结论。当今世界正在向技术垄断文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历史的传统符号、经典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之路与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的哲学思考就成了抵挡这股洪流的人类自我救赎之法门。只有永远地批判、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永远地追问技术的本质,人类才可以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技术垄断;波兹曼;传统符号;技术之思;海德格尔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家、理论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创作出了“媒介三部曲”,即《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而这三部作品又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技术时代的来临给人类的文化、生活、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技术垄断》一书里,波兹曼正式提出了“技术垄断”时代的命题,并且指出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技术垄断”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正在面临着传统世界的消亡,以及失去驾驭技术的能力,就像《技术垄断》一书的副标题揭示的一样——“文化向技术投降”。因此,我们应该反思世界是否会走向技术垄断的时代,一切文化生活是否会向技术投降。
一、技术垄断时代
(一)技术垄断文化
首先,我们来回顾波兹曼提出的媒介环境下媒介技术对人类产生影响的背景。尼尔·波兹曼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精神领袖,其第一代精神领袖即是大名鼎鼎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他们提出的“媒介环境学”为传播学的三大流派(传统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之一。其中,经验学派主要是以经验性、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为主,并以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为代表。批判学派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批判理论倾向的聚合体,主要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为代表)、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达拉斯、乔姆斯基、席勒等为代表)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霍加特、威廉斯、霍尔、汤普森等为代表)组成。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是人的交往和人交往的信息以及信息系统,具体来说是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知觉、情感、认识、价值等,即人类与媒介互动是怎样促进或阻碍人类生存的,该学派主要以芒福德、伊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莱文森等为代表。媒介环境学派所关注的焦点是技术,以及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媒介技术是如何塑造或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社会构造、文化生活、心理建构、行为举止等。
波兹曼认为,技术的迅速发展会给我们的传统生活及文化带来极大的危害,会给我们的传统印刷文化以及文化素养等带来不可消除的侵蚀。尤其到了技术垄断时代,文化向技术投降,并沦为技术的奴仆。“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1]30所谓的技术垄断论就是表明在技术垄断时代,我们的一切文化生活甚至是经济、政治、身体等生活方式,都是被技术所统治着,所有的文化生活也均臣服于技术的统治之下。波兹曼认为,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是:汽车大王福特开启的流水线生产,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1925年美国南方关于科学与信仰的争论进行了“猴子审判”,标志着上帝创造世界的失败,以及生物进化论的胜利;1911年泰勒发布《科学管理原理》(认为科学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三个标志奠定了技术垄断时代问世的基础。在波兹曼的书中,他将技术垄断比喻为文化的“艾滋病”,即“抗信息缺损综合证”。技术垄断确实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化、泡沫化、委琐化,并使得我们难以把握世界,并沦为信息的奴隶。
(二)工具使用文化和技术统治文化
为了使“技术垄断”的概念得到充分的解读,我们需要对尼尔·波兹曼的其他两个媒介时代概念做一个简单的阐释。对于人类历史文化时代的划分,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划分方式,而媒介环境学派如麦克卢汉、伊尼斯等则是利用媒介与相关技术的发展来划分人类历史的。麦克卢汉通过分析媒介技术的历史发展,将历史分为口头媒介时代、文字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伊尼斯则对麦克卢汉的历史划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口语时期、拼音时期、纸笔时期、印刷初期、电影时期等九个时期。波兹曼虽然也是利用媒介技术的演变发展来对历史文明进行划分的,但他也表明了对历史前路危险处境的担忧。波兹曼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相应地,文化类型亦或形态也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从人类历史开始一直到17世纪,不管这一长久阶段中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文化活动呈现出怎样的变异,波兹曼将这一阶段都统一称之为“工具使用文化”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技术力量的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前进的。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是和平共处的,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1]12这一时期的技术虽然是依靠人的力量的,但在文化历史的定位中,技术力量的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工具使用文化”源于文化中工具和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1]13。在这一阶段,技术力量的发展永远是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的,永远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发展的。我们以欧洲中世纪为例,这是神学家统治的世界,他们认为一切历史文化、技术工具、思维方式都是上帝的产物,人类的发展也是为上帝服务的。如牛顿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推动了世界科学的发展,然而牛顿最终还是回到了神学世界。世人皆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达·芬奇,实际上更是一位技术专家,他曾经设计了潜水艇、机器人、滑翔机甚至机关枪,但他却把这些设计藏之于深山,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工具的发明使用,会对人类的文化造成伤害,上帝是会谴责的。这一时期,神学思想的预设是工具使用文化中具有强制控制力的意识形态。所以,不管发明什么样的技术工具,都必须符合其中的意识形态。甚至我们上推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思考的也是形而上的,认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效率的发展是奴隶们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将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看作是“低贱的机械技艺”。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技术是向前发展的,且几乎是与人类和平共处的相互推进式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不断推进,技术统治时代即将来临。技术统治滥觞于中世纪钟表、望远镜、印刷机这三大发明的出现。钟表的发明使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新的观念;望远镜的发明撼动了中世纪神学的权威命题;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了口头传统的认识论。“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于工具发展的需要。”[1]15波兹曼不同于康德认为开普勒或牛顿是引领和寻找文明运行规律的人,他认为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人是弗朗西斯·培根,是培根将数学以及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发明拉回到了现实中来。虽然培根并未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就,但却是他完善了技术统治时代的理念,表明了时代进步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但技术统治时代的真正开始则是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和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不断涌现出机械制造发明的工具;虽然亚当·斯密不是发明家,但是《国富论》的出版则正式确立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所以,一般认为,这两大事件是技术统治时代正式来临的标志。自此以后,技术统治走向了康庄大道,包括工厂制度的建立,机械机床产业的发展,都为技术统治文化创设了条件。由于工业文明的大力发展,人们越来越依靠技术,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对人造成的阶级划分和异化越来越严重。人们对技术的期待、欢迎、追捧是热烈的,但此时的技术尚未完全统治文化,也没有摧毁传统世界观,原因是“产业主义的狂热刚刚出现,范围有限,还不可能影响人们的内心生活,也不能驱逐工具使用文化留下来的记忆和社会结构”[1]27。这个时期是文化的阵痛期,传统文化的理念与技术统治的世界观相互并存,然而却是不安与紧张的共存。
波兹曼根据媒介技术的发展将人类文化历史进程划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大时期。人与技术的关系从共同发展到紧张共存到最后人被技术控制,人的自主性逐渐在丧失。波兹曼还详细叙述了在技术垄断时代来临后,人们对世界的难以把握而导致的心理防线的崩溃;同时,他还运用详细的事例加以说明美国已经进入到了技术垄断时代。电脑的普及,人类对机器的迷信越来越严重,“起初的暗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1]64。这样的唯科学主义导致了文艺精神的消磨,造成了传统符号的流失。但波兹曼并不是反对技术,他在序言中就说了“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波兹曼这样的批评是有他的深刻用意的,即他希望在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还能保持传统的精神,使人与技术世界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要被技术所吞没。
二、波兹曼的思之道路
(一)传统符号的消亡
在工具使用文化和技术统治文化时期,文化艺术与波兹曼书中称之为“传统符号”的命题还是存在的,但却是在逐渐消失或者随着其他技术力量的发展而逐渐被遗弃。如电视对人读写能力的破坏,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抹煞了成年人与儿童的界限。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也是不同的,波兹曼所叙述的三种文化类型实际是共存于这个世界上的。当然以美国最为先进,其已进入技术垄断时期。
波兹曼身处美国,看到了技术垄断文化的各种事件,看到了广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对传统信仰、文化、符号、仪式的亵渎。如加利福尼亚夏敦埃酒刊登的广告是耶稣手捧夏敦埃酒,今天一喝,你就会成为主的信徒。等等。传统符号的猥琐化、庸俗化、泛滥化,使符号的神圣性也自然被消解。波兹曼通过对广告产业的分析以及教育方式问题的分析,展现了美国传统符号的流失过程。正如波兹曼所指出的,未来的世界正如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并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而不像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所预言的,人们会接受外来压迫而愿意被奴役。因此,真正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恶的东西,而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2]!最为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庄》等,他提出的人类文化的消亡方式是一种监狱式的方式,一切人、事、物都是被监控的,并认为是专制统治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后果。波兹曼认为,我们的人类文化、传统符号的消亡方式正像阿道司·赫胥黎预言的一样,我们的世界将会成为一个“美丽新世界”。他将故事设定在公元26世纪,那是一个以福特为纪念方式的世界,人类将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奉为神明,并将生产出T型汽车的1908年认定为福特元年。该书一开始,就是一位科学人士带领着一群新来的学生参观生产人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人是通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孵化出来的,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技术垄断时代。在繁育中心,通过干扰、条件反射等手段将人分五个社会阶层孵化出来,即“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前两种是统治阶层,“伽玛(γ)”是普通平民阶层,“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是被统治阶层(相当于奴隶阶层)。在生产阶段,通过人工机械干扰,使“厄普西隆(ε)”这个阶层一出生就大脑缺氧,并且只能进行体力劳作。在他们的世界里,人类的一切的优秀的文化符号都成了历史并被永远封存,“家庭、自由、平等、爱情、信仰”等都成了过去时,在他们的脑海中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对这个世界的唯一记忆就是“共有、统一、安定”。阿尔法中的生物学家博纳为了完成学业论文,和好友列宁娜一起来到美洲的“野人保留区”进行研究。两个人结识了似乎也是唯一我们认为非孵化的而是胎生的正常人约翰,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故事。约翰是生活在“野人区”的,即我们现在生活的正常世界,但在福特的世界中,约翰则是“野人”。这里似乎是世界中唯一有人类尊严和自由的领域,约翰长期也是唯一阅读了一本书——《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人类历史上倡导人性、发现人性、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传统符号被完全磨灭,历史文化也完全消亡,人类成为技术的产物。但是,作者还是希望在这样的世界里有人性的存在,或者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认真阅读《莎士比亚全集》。著名的“反乌托邦”三大小说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都提到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发现人性、张扬人性的《莎士比亚全集》。他们认为,有自由人性的人都会阅读文艺作品,思考人性。只要还有人阅读人类历史文化经典,人类文化就不会消亡。只是波兹曼看到了在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技术垄断就会越来越严重。
(二)波兹曼的抵抗之思
波兹曼不只是提出问题,而且也给予了解决办法,如在《技术垄断》的最后一章,希冀有抵抗美国技术垄断的“爱心斗士”。他提出的“斗士”的原理是[1]110: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设问,否则就不要理睬民意测验;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既不把计算当做替代评判的充足证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要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波兹曼还在教育课程设置上提出了解决技术垄断时代来临应该有所抵抗的方法,即将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讲授,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宗教、历史、语言、文学。波兹曼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抵抗技术世界迅速发展的凶猛势头。
波兹曼针对现实世界中美国的技术垄断文化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看到技术世界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即如果任由技术的发展,必将导致我们进入“美丽新世界”。为了阻止这一状况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和技术的世界拉开距离,以阻止传统符号的消亡,正像希利斯·米勒在千禧之年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我国学者金惠敏教授也认为,文学终结论只是终结了该终结的一部分,整体的文学是不会终结的,每一次终结论者提出时,只是终结了已经坏死的部分文学,文学也在不断地以更新的方式生生不息),即“文学总在终结着,终结着其自身内部不得不终结的部分,文学作为家族没有终结,而这家族之结构实则在与时俱变”[3]。我们还认为,文化并不会灭亡,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被不断地更新而已。
三、海德格尔的思之道路
对于“技术”问题的追问并不是波兹曼首创的,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了关于人与技术、技艺的关系性思考。到20世纪,人类受了各种现代化进程的洗礼及战争的侵害,为此,海德格尔展开了对技术的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大多是形而上的思考,当然他也把技术作为形而上的思考对象。在他的著作中,对技术的思考并不是很多,但是《技术的追问》一文却影响深远,发人深省。
《技术的追问》一文提出了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与技术的本质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一条思之道路。海德格尔指出,我们不能把技术当成某种中性的东西来思考(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流俗的技术概念了),而应当把技术看成是工具或者是人的行为。海德格尔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技术作为真理显现的发生方式而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他说:“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4]正是形而上的完成规定了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走向,但海德格尔的思考还是回到了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上来了,即事物的构成均依赖于“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从事物产生的原因,海德格尔发现了技术的数种发生方式:招致、考虑、显露、引发、产出、涌现、解蔽。对技术的本质,他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5]12。这时,开始思考什么是现代技术。首先,承认现代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但在现代技术中,起到支配作用的这种解蔽方式是一种促逼。这是与传统技术不同的一点(现代技术带有一种强制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带有摆置自然的强制性特征的解蔽方式。如三峡大坝建立在长江之上,并不是长江摆置三峡大坝,而是三峡大坝在摆置着长江。长江的水流通过大坝而进行发电,通过机器的制造而发送电流,长江成了某种被订造的表现,促逼着长江的产出。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都成了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这样的订造、持存只有人本身能够去展开,但实施摆置的也是人本身,当然人也是在被摆置中展开的。
在现代技术的本质追问最后,海德格尔提出了“集置”(有诸多译本翻译为“座架”)说。集置就是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集置就是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意味着那种摆置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集置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但其本身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5]19。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在集置中的,集置就是摆置聚集者,这种摆置摆弄着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且人也处在被摆弄的位置。但如何解开人被摆置的命运就要从集置来思考(集置归属于解蔽之命运的展开)。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对人类的威胁不仅仅是来自致命的技术机械配置,同时还有现代技术本质的危险触动着人类本质的自由。最后,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所以海德格尔说:“技术之本质的现身,就在自身中蕴含着救渡的可能升起。”[5]33
对于《技术的追问》一文,人们常常关注的是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本质的思考以及现代技术对人的摆置的思考。虽然前文也略加阐述了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本质的思考,但他的思考却展现了一条思想之路。海德格尔一步一步的关于形而上的思考,揭示了技术的形而上之本质,但这样的思考方式却展现了一种思想道路,即追问的道路。我们应该一直不停地思考追问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从古代到现代,其技术的本质一直是解蔽,但现代技术的本质却多了一种“集置”。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也许后现代、后后现代……也有不同于古代技术解蔽本质的增加。这就需要我们展开不停的追问。文章的最后,海德格尔说:“追问乃思之虔诚。”[5]37对于现代技术的本质追问也就是为人类寻求自由的维度,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生活。
四、结 语
我们通过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追问之思,发现海德格尔不仅仅展现了技术本质的形而上思考,而且为我们构筑了一条思之道路,即永远地追问技术的本质。殊途同归,尼尔·波兹曼疾言厉色批判技术的危险也不是完全否定技术,而是希望人们与技术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我们持久的思考技术,并与技术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我们人类的自由生存。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6]只有我们一直在追问或在思索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技术的控制。波兹曼实际也和海德格尔一样,在永远地批判技术的危害。只有永远地批判,才能使我们永远地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殊途同归,对于技术问题,我们要永远地思索,永远地追问,以此来保持人的独立性、自由性、批判性。
[1]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陈皓钰.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点思考——兼论人文知识分子的缺失[J].教育文化论坛,2013(4):13-16.
[3] 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55-64.
[4] 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J].求是学刊,2004(6):33-40.
[5]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7.
[责任编辑 杨玉东]
Thinking on the road of “Technology Monopoly”: Postman and Heidegger
CHEN Haoyu
(SchoolofLiteratur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Shanxi,China)
Neil Postman, a famous American media ecologist who put forward the thesis of “Technology Monopoly”, pointed out that the culture is going to yield to technology so that everything will fall as its servant. Firstly, the author explained the background and meaning of Postman’s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Postman divided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to three periods: the period of tool-use culture, the period of technical domination culture and the period of technical monopoly culture. The world today is transforming to the third period.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traditional symbols in history and the classical culture are in danger. However, it is Postman’s path of media criticism and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QuestionsonTechnologyare the ways of human self-salvation to prevent this torrent. Only to criticize and notice the harm which the technology might cause and ask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at all times can keep the human spirit independent and free.
Technology Monopoly; Postman; traditional symbol; thinking of technology; Heidegger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2.020
2016-12-29
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YZ15082)。
陈皓钰(1992—),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当代文化理论研究。
E-mail:haoyue1137@163.com
G206.2
A
1673-9779(2017)02-0119-05
陈皓钰.“技术垄断”之思之道路:波兹曼和海德格尔[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