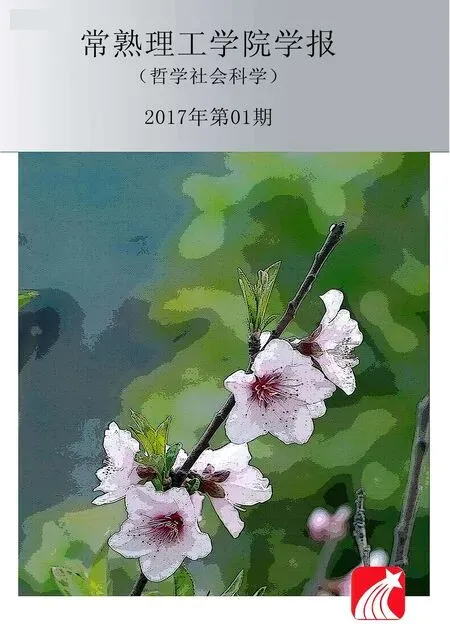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建设的路径转向
——基于S市T县的调查
周 艳,张国平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常熟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建设的路径转向
——基于S市T县的调查
周 艳1,2,张国平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常熟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基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S市T县的长期跟踪调查,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社区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以及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路径下所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并通过对当前社区建设中的几大主体(自治组织、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处境及其采取的应变行动进行深入剖析,试图从地方社区变迁的现实和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揭示出我国社区建设路径转换的背后逻辑。
社区建设;治理现代化;政社互动;三社联动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搞好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而要达成社区治理现代化,则需要厘清基层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充分激发社会活力;需要汇集各地多年实际探索基础上已经形成的先进经验,并在理论上进行好好总结凝练和提升,从而发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性,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建设的理想构型和实现路径,并使其上升为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指导。
本文所考察的对象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某县级市,文中简称为T县。T县曾经荣获过“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市”“全国规范化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等称号,其社区建设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因此,对它进行剖析就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县域,T县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并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和社区变迁并思考中国模式的一个生动的且相对完整的样本。
本文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课题组自2011年3月至今多次在T县进行的实地调查,其中包括两次一个月左右的较长期调查,以及数十次一周以内的短期调查。持续5年的跟踪调查保证了资料的连续性。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实地观察、部门座谈、深度访谈等。
二、T县社区的巨大变迁及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
(一)T县社区的巨大变迁
二十年来,T县的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表1和表2所示,1995年,T县下辖22个乡镇,329个行政村,60个居委会;到目前,演变成为1个街道6个镇,74个行政村,73个城市社区。
图1则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展现了三十年来T县行政村和城市社区数量的巨大变化。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在这个进程中,人们的居住地点、居住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除此之外,经济的强劲发展也吸引了与户籍人口等量的外来人口的涌入,外来人口以租房、购房等方式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社区空间内。上述种种改变,隔断了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纽带,打破了原有的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带来了不适应、陌生感、甚至矛盾冲突。

表1 乡镇/街道级行政区划的沿革

表2 村(社区)级行政区划的沿革

图1 行政村和城市社区数量的变化
(二)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
T县的社区建设始于2003年。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T县一开始的社区建设也遵循着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路径。具体的做法就是民政部门制定政策和标准,通过文件层层下达,市县级地方政府则是最终的执行者。建设内容主要有:(1)基层社区组织架构(包括社区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干部队伍等)的建立;(2)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包括领导机制、投入机制、人才机制等)的建立;(3)社区服务体系(包括各级社区办公和活动设施、便民服务信息网络等)的构建;(4)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决策日制度等)的建构或完善;(5)特色活动(包括娱乐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的开展。可以看到,在T县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之下,再加上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每个村(居)都有了统一标识的标准化的社区办公服务场所,挂牌了各种服务站和活动室。如今,城市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平均达到1100平方米,农村社区平均达到1400平方米。社区干部也逐步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专职化的“坐班”人员,有了固定的收入。依托优良的硬件设施,各个社区也组织起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文娱活动和志愿者活动。
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路径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社区,这个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没有行政色彩的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社区建设中被赋予严格的行政意义。所有的政策、措施源于政府,始于政府。[1]90由于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行政逻辑替代了社会逻辑,因此,一方面削弱了社会联系纽带、社会共同体的自主与自治能力,另一方面在资源配置上也存在低效率、不合理以及供需错位等问题。现实操作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创建、评比、考核活动虽然对政府工作的快速推进大有助益,但是却造成了社区的行政化,将城乡社区建设导向了对上不对下、重形式而轻内容的道路上,进而排斥了绝大多数社区居民的参与。表面上看,社区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各种功能似乎也健全,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多少作用,能否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呢?这样建设起来的社区,投入不小,但却只是一种机械的、僵化的社区,是一种缺乏内聚力和活力的社区,也缺乏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当然,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面对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路径及其存在的问题,自治组织、居民和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性的行为选择,对当前社区建设进程中这几大主体的处境及其采取的应变行动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揭示出我国社区建设路径转换的背后逻辑。
三、T县社区建设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处境及应变
(一)社区自治组织:定位模糊下的“两难”与选择性应付
所谓社区自治组织,就是指居委会和村委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村)民委员会是居(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伴随着社区建设的步伐,政府管理重心逐渐下沉,造成的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权力向自治组织无限延伸,政府责任向自治组织无限转移;二是自治组织行政化十分严重。
自治组织行政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组织设置的行政化、人员安排的行政化、工作职能的行政化、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经费保障的行政化等五个方面。[2]目前,居(村)委会更多的是在履行上级政府各个条线上下来的行政职能,如下岗再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事务、社会治安等等,而且每年都要签订政府下发的责任书。除此之外,还经常要应付上级各部门下派的各种各样的评比和检查工作,与国家法律规定的城乡居民的自治组织的性质有很大的差距。在访谈中,许多村(居)委会干部都在抱怨“社区规模比以前大了,社区干部现在工作量也比原来大了,可人越来越少。每条线上都有任务下到社区里。各项检查、创建、达标,卫生、安全、环保等,主要精力都放在这方面。有时候上面要来检查,就造台帐,糊弄上面。另一方面还要面对老百姓琐碎的事,两头受气。”有学者将这种“城市社区居委会有选择地采取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乃至欺骗的办法应付上级派发的各种工作压力的现象概括为选择性应付行为”。[3]
总之,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村(居)委会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主体,其行动逻辑必然是充当政府的“腿”,而不是居民的“头”。在社区居民的眼中,村(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也是领取政府工资的政府的代表,是乡镇和街道权力向基层的延伸,而背离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
(二)居民:被组织到自组织行为初现
对于政府的社区建设,社区中的居民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和逐渐认识的状态。为了能够完成上级政府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有限的社区干部只能采取动员社区积极分子的方式把任务传达和布置下去,形成了“社区居委会——积极分子——普通居民”的动员路径。这些积极分子通常是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而且以女性居多。除了少数的积极分子之外,社区广大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他人和社区事务、社区活动漠不关心,参与度很低。[4]面对居委会以自治主体的身份背向社区居民为政府谋事的现状,社区成员不自觉地陷入“以居委会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两大群体的二元区隔格局。“社区外群体”以惯习判断并拒绝“居委会文化”,而“社区内群体”不能认同“社区外群体”在社区中的冷漠和不参与。[5]全国绝大部分的社区均是如此。
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它们说明社会的发展向来不是单向度的。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破坏传统社区共同体的过程中,社区中的居民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社会的修复和重建。例如,在一个当地农民的集中居住小区,我们就发现了居民主动重构“邻里”概念的有趣现象,他们把“联排别墅的一排、独栋别墅的前后左右、楼房的一个单元”界定为新的邻里,在操办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时,以新居住地为依据的新邻里取代了传统的以累世而居的自然村落为依据的旧邻里,提供了社区所具有的重要的交往和支持功能。在另外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新型商品房社区,我们也发现了居民积极主动担任志愿者、自发成立各种类型的互助或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再造公共性的途径。这些案例的发现,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人类的社区本能”,即“社区的基础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需要。人类的生命个体不能独立生存,它必须与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群建立联系,并依存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人群,从中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精神、社会方面的资源,这是生命的共同体本能,或者叫作生命的生态系统。在社会学意义上,称其为社区。”[6]这些,是我们进行社区建设可资利用的宝贵的社会资源,值得引起关注。
(三)地方政府:“治理”理念指导下的反思与政策调整
在社区建设取得不小的成绩的同时,T县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一些问题。似乎社区建设中所有的事情(从基础设施到人员配备到具体的服务)都是政府在做,一方面政府感觉负担很重,另一方面这种单一渠道的供给无法满足老百姓具体的多样化的需求,造成社区建设的供需不对接,最后的结果反而有可能是出力不讨好,且助长了老百姓对政府“等靠要”的思想。
鉴于此,T县政府积极寻找解决办法,2008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政社互动”,近几年又启动了“三社联动”方案。所谓政社互动,是指“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互动衔接机制”,取消社区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建立平等的契约关系,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在政社互动的基础之上,T县还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骨干的“三社联动”工作运行机制,形成“政府扶持监督、社会组织承接、项目化管理运作、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参与”的社区服务新模式。这些方案的提出,既源于当地政府多年来扎根实际的探索和思考,也源于与密切合作的科研机构的交流和合作研究,还源于到上海、台湾、成都等地的取经与学习,而背后则是“治理”理念的指导。
当然,要想打破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并非易事,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做到厘清政府和社区的边界,通过“两份清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实现社区减负与转型,社区与政府的关系从行政命令到平等协商,社区干部的工作重心从应付行政事务和各项创建、评比、检查上转移到社区自治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之上;其次,鉴于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的现状,通过成立社会组织孵化和服务中心,实施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的创建、发育和成长;再次,注重专业社工人才的培养与专业社工岗位的开发。由此,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工,这些以往并不存在于大家脑海中的陌生词汇,开始逐渐在社区中生根发芽,并逐步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认可。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摸索,变化还是在悄然发生,社区的社会资本在逐渐积聚,居民的社区参与度和社区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结论与启示
T县的社区建设与变化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变迁和社区建设的一个缩影。通过对T县的考察,我们发现: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基层社区发生了重大的重组和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维护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政府为主导展开了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运动;但是,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这种社区建设的路径也展现出诸多的问题,到了需要进行转变和调整的转折点,而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基层政府则是路径转换的基本主体和主要力量,正是在三者之间的不断互动之中,我们看到了社区建设路径转换的动力和内在逻辑。
政社互动,其本质是要处理好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使社区自治组织跳出自上而下的行政化路径。但仅仅有政府和社区村居委会之间的互动显然不够,还必须激发起社区内部的活力,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和社工的作用。有学者提出社区建设重在公共性的重建,而公共性的基础又是公共的社会资源,其主体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资本”。[7]但问题在于经历了社区的变迁和共同体的解构,新社区中人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社会资源已经相当匮乏,前述发现的社区居民的自发自组织行为虽然可贵却毕竟有限。那么社区社会资本如何重建呢?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的作用就在于此,运用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并与本土结合,根植需求、链接资源、促进参与,满足了居民需求,促进了居民交往。
因此,如果说起初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路径是“建起来”,着力点主要在制度框架、硬件设施和行政事务上;那么,T县近些年的做法可以概括为“活起来”,其核心是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协商、合作、融合、共治,这恰恰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本质内涵,是新常态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义。因此,打破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路径和由此带来的僵化的社区治理,要靠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等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1]丁元竹.社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徐昌洪.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及其治理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4(1):103-110.
[3]杨爱平,余雁鸿.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 (4):105-126.
[4]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185-208.
[5]闵学勤.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J].社会学研究,2009(1):162-183.
[6]丁元竹.理解社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4):141-149.
[7]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79-80.
Community Building Path Steer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Survey of T County in S City
ZHOU Yan1,2,ZHANG Guoping2
(1.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China)
Based on the long-term follow-up survey of T County in S City in the developed eastern China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reat changes the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have experienced,and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government-led top-down community-building model.Besides,the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logic behind the path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s of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ve practical experience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several principal parts(including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resid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and the corresponding actions in the community-building process.
community building;governance modernization;politic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ers
C916
A
1008-2794(2017)01-30-05
2016-06-25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政社互动与苏州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研究”(14SHB002)
周 艳(1979— ),女,山东文登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社会建设;
张国平(1964— ),男,江苏苏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非营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