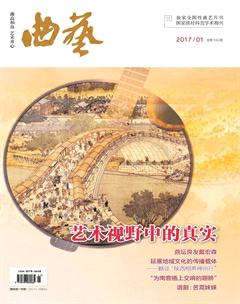吴丹:在谐剧的表演中实现自己
丹妮
三年前,吴丹任职的成都市曲艺团团长任平问她:“你喜欢什么?”当时吴丹已在团里呆了八年,然而却并没有一个定向的专业。她小声回答说喜欢表演。任平又问她:“你愿意去学谐剧吗?我可以介绍张廷玉老师给你认识,但是她教不教你我就不知道了。”吴丹和任平说那就去试一下嘛。
作为谐剧创始人的王永梭老师,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培养“女谐剧”,张廷玉是第一个专业的谐剧女演员,团里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张妈妈。退休后,她想过过自己的生活,而且家里还有两位9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照顾,她想尽尽孝道,所以就没有再教学生。
张老师退休后,曲艺团里的“女谐剧”基本上就断代了,这件事也引起了她的深入思考。成都市曲艺团的领导班子特别好,很重视这件事,四川省曲协也非常关注、支持曲艺的发展,这些年轻人的努力张老师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她自己也当过院长、团长,理解他们的苦心,“就像我当时的那份心一样”。
任平把吴丹带到张老师家的时候,张老师并没有立刻决定要教她,她对任平说:“要看我和这个孩子有没有缘分。”吴丹一开始觉得张老师不太好接近,就安静地坐在旁边装淑女。任平和张老师一直在交流,谈到现在的艰辛,也谈到她想要培养学生,想一代一代把曲艺传承下去。不经意间已经中午11点多了,张老师说为了方便只能吃面了。吴丹在老师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最喜欢吃面”,然后她们就吃面。吴丹说的第二句话是“张妈妈,我可不可以加点臊子?”问完这句话张老师马上对她感觉很好,觉得这个孩子很单纯,很真实,不做作。吴丹吃完一大碗面后,接着说“我可不可以再吃一点?”任平心疼张老师,对吴丹说你不要把张妈妈累着了。吴丹看任平碗里还有面,问“你吃得下吗?”还未等任平答话,她已经把任平的半碗面扣进自己碗里大口吃起来。这是张老师对吴丹的第一印象,“我们见面第一天就很有缘分,我要教她就是这样决定的”。
很多人对谐剧的认识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谐剧就是在台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就是搞笑。张老师说:“谐剧,是诙谐之剧,也是在塑造人物;幽默和搞笑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幽默叫黑色幽默,并不是把自己装扮成异类逗大家发笑,是‘一人独演,独演一人,是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
刚学谐剧时,张老师问吴丹结婚了没?有孩子了没?家人支持不支持?在得到她全部肯定的答复后,张老师说:“那好,你来学吧,我不希望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杂念,也不希望你学了一点点就到处炫耀。谐剧现在很少人演,收入和付出是不成正比的,但是不能因为别人不做我们就不做,总有人要做。我希望你能做,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演好谐剧,做好传承。”张老师给吴丹上课付出了很多辛苦,而且没有收过一分钱,让吴丹特别感动,说张妈妈对她比对亲生女儿还好。
据吴丹介绍,她刚从学校毕业时对自己很有信心,觉得可以当明星了。单位老师要她排个小品,演完后老师说:“我覺得你表演有障碍。”这句话宛如晴天霹雳,给了吴丹重重一击。自此她开始质疑自己,又难过,又害怕,任何节目都不敢演了,怕演砸了,从此整整八年不敢上舞台。吴丹第一次来张妈妈家学习的时候,连路都走不来,张老师试着慢慢教她,在教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孩子很有潜力,也很努力。
首次触电谐剧,张老师要吴丹先从基本功学起,一切从头开始。吴丹很兴奋,进步也很快,但是到了平台期就很枯燥,觉得自己卡在了瓶颈,总也上不去,于是开始烦恼。张老师对她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会重复练习好多好多遍。当时吴丹曾问过自己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也产生过想要放弃的念头,张老师跟她说:“不跌倒怎么能够爬得起来?不失败你也看不到成功的喜悦。你必须重回舞台,找到那份自信。”
张老师教育吴丹要实行“海绵主义”——吸收好的,挤去不好的。刚开始学习谐剧时,选用的都是王永梭老师的传统剧目,如《自来水龙头》等。张老师也有很多自己的段子,如《三上成都》《春梦姑娘》《媳妇》等,但是吴丹演的话可能会有难度,也会与现在这个时代有些距离。刻苦学习两年多后,张老师说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段子,于是她带着吴丹四处筹集新本子,登门拜访四川几位知名的编剧老师,把他们聚在一起,每人送了一本王永梭老师的传记,张老师言辞恳切地表示:“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一下谐剧事业,现在‘女谐越来越少,有一个女孩愿意学,特别不容易。为了谐剧的发展,也为了谐剧的传承,大家能不能想办法创作几个剧本?”就这样,在短短的两个月,吴丹就有了五个本子。
挑选谐剧本子的时候,经过反复琢磨,她们决定先排《苦蒿妹妹》。吴丹清楚记得第一次看到《苦蒿妹妹》本子时的状态,她直接傻掉了。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演员要迅速进入角色,情绪由喜到悲,再由悲到喜,悲喜交加,要抓住观众,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张老师安慰吴丹:“《苦蒿妹妹》对你难度确实有点大,但是难度大咱们就把起点定高一点。”排这部剧时,张老师快要崩溃了,因为吴丹哭不出来,她无法理解剧中女孩的命运怎么那么悲苦,为什么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觉得世界上不会有这种事情。张老师平时教吴丹从未凶过她,那天她凶了吴丹,因为老师每示范一次,自己都会感动到流眼泪,而吴丹却根本找不到感觉,怎么也哭不出来。张老师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必须给我哭出来!你太让我失望了!”她一骂吴丹哭了,可是表演时吴丹又哭不出来了。张老师就反思不能用这种方法,她说:“我现在不说你了,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哭得出来你就哭,哭不出来你就不哭。”吴丹压力更大,还真就哭不出来。后来她强迫自己每天听特别凄惨悲伤的歌曲,像《小白菜》啊,《九儿》啊,《白发亲娘》啊,还是没用。有一次排练完吴丹还是哭不出来,内心特别痛苦。回家时,张老师把她送到站台,车子已经开出了很远,吴丹猛一扭头,看见张老师站在雨中遥望着汽车远行的方向,她当时眼眶就红了,特别想哭:“我要是还演不好,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她和张老师请了几天假,窝在家里仔细琢磨,明白了哭不出来是因为她游离在角色之外,而要演好这个角色,就必须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张老师对吴丹说你要有信心,我们共同努力,你是能达到的。她问张妈妈这个“苦蒿妹妹”是真事吗?张老师说是真事,苦蒿妹妹是2015年全国十佳“最美孝心少年”之一,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吴丹把视频调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挺受冲击的,慢慢地她开始找到点感觉了,渐渐地能把老师演哭了。
为了演好《苦蒿妹妹》,师徒二人征求了许多老师的意见,大家认为苦蒿妹妹要一直很阳光,她们也曾试着这样演,但是在演到一定程度时张老师觉得不太对。她们又一起反复看视频,分析剧本,张老师告诉吴丹,“我们在塑造‘苦蒿妹妹这个人物时一定要让她是多层次的,既是快乐的,阳光的,又能够担当,懂得爱,我们要把她最脆弱最敏感最深沉的感激最阳光的性格表现出来”。所以这部剧反复修改了数次,直到“牡丹奖”比赛前半个月,张老师还在给吴丹改剧本。
张老师告诉吴丹,塑造人物一定要入木三分。她们正是一步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每个角色都力争表演得最朴实最自然,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情,都是反复打磨之后的结果。张老师教她特别辛苦,一句一句台词都要给她示范,怎么讲这句话,逻辑重音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这样说,让吴丹一定要把里面的道理弄懂。十几分钟的剧,用什么去打动观众?简简单单一个转头动作,张妈妈就不知道示范了有多少次。例如,《苦蒿妹妹》中有一句台词“我的妈”,吴丹演绎得就很精彩,配合台词的转体是事先设计好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转的。说出“我的妈”的同时,“苦蒿妹妹”的眼神要慢慢地回来,沉浸在对已逝妈妈的思念中……就是这么个细微的动作,吴丹也练习了很久。吴丹的眼睛很美,又大又亮,很传神,张妈妈跟她讲一定要让观众记住你的眼睛,一定要把“苦蒿妹妹”这张美丽的脸深深地印在观众脑海中。在无实物交流的过程中,吴丹反应“对方”说话要有一个时间差,张老师告诉她把看不见的对方说的话、表现出来的情绪设计得越丰富,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就越准确,剧情节奏也就把握得越好。
吴丹学习谐剧的心理感受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好奇,到后来的喜欢,进而再到枯燥,直到现在的热爱。她是真正地热爱谐剧,《苦蒿妹妹》从排练到搬上舞台,吴丹说像孕育了一个生命一样,看着她一点一点地成形,经过不断打磨,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张老师说:“《苦蒿妹妹》演完了,你虽然凭此获得了‘牡丹奖新人奖提名,但是你的路还长,下一个剧目可能对你的挑战更大。我给你的任务是一年出三个不同类型的角色,现在我还能教你,再过几年我可能教不动了。我希望你学得扎实一点,拿到一个剧本,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塑造人物,希望你学到这个方法,学会方法比单纯学一部剧要有益得多。”现在的吴丹在家也能隨时入戏,往往吃着饭就开始“演”,弄得家人一头雾水;有时候走在路上也时不时地蹦出几句台词,搞得路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盯着她,指指点点。吴丹开玩笑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她练习眼神,看一米八、一米六和一米四的人的眼神高度是不一样的,站着、坐着、蹲着看人的眼神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她经常在超越时空地找“位置”。
经过多年的磨合,张妈妈和吴丹现在配合得特别默契。师徒二人一个认真教,一个用心学,彼此心照不宣。吴丹每天早晨赶到老师家,离老远就在门口大喊“妈妈——”,而张妈妈早已给她买好了早饭、泡好了茶;知道她爱吃面,70余岁高龄的爹爹(张老师的老伴)中午又张罗着给她下面吃。她在老师家一待就是一整天,困了就睡,饿了就吃,一点都不生分,就像家人一样……吴丹说自己很惭愧,从没为师父做过什么,反而给她增添了许多负担,但是张老师却管这叫“甜蜜的负担”。有段时间,张妈妈为了给她挑选适合角色的服装而不慎扭伤了腿,虚弱地躺在床上,还打起精神跟吴丹说:“你过来,再给我演一下人物的眼神。”排练到后面,由于强度较大,时间拉得太长,张妈妈每晚要靠吃安眠药才得以入睡。
张老师是一个特别讲究内在的人,得知吴丹看书不多,她摇摇头,说:“别人都认为我们演员没什么文化,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她掰开揉碎地和吴丹讲要想更好地了解角色、揣摩角色,自己心里头一定要有“货”,你读了世界名著,表面看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实际却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你对人物的理解,而且对于分析剧本也会非常有好处。有了老师的教诲,吴丹在排练之余乖乖听话在家自习,看书,她经常感慨:和张妈妈在一起那么久,不仅学到了怎么表演,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还学会了怎么学习。
看着吴丹每天一点一滴的进步,张老师很欣慰。吴丹感谢张妈妈,“学习谐剧,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而且感动大于欢乐,我除了找到自信,也找到了精神的寄托,感觉生活有了目标,有了方向”。张妈妈也很感谢吴丹,“感谢她带给我的快乐,我在教她的同时也在学习,也在提高,她给了我再学习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谐剧的希望”。
吴丹总说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如果没有任团的举荐,没有张老师的悉心教导,没有家人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今天。早在教习谐剧之初,张老师就给吴丹定位要走一条“唯美”的路,即不管演什么角色,都要自然、流畅、朴实、美丽。张老师经常语重心长地对爱徒吴丹说:“谐剧,甚至曲艺不仅要出人出书,还要继承和发展。所以我对你的要求不是简单做一个‘谐星,而是要内外兼修,做内外都美的艺术家。我希望你在未来能够创作出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