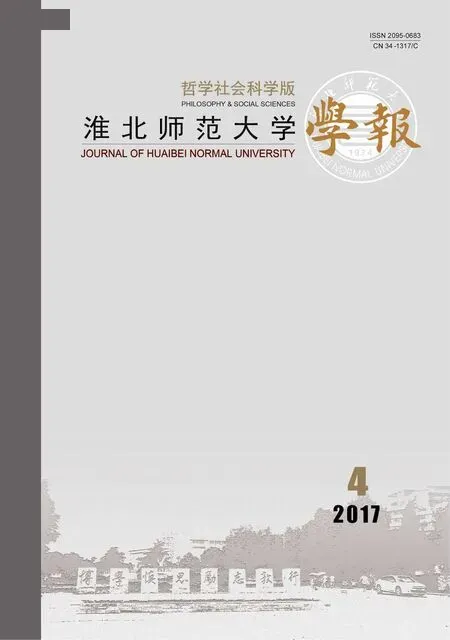口述史角度的民间反切语研究
陈 娟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口述史角度的民间反切语研究
陈 娟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语言观创造了语言研究方法。民间反切语是流传于我国民间老百姓口头上讲说的一种隐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民俗现象、文化现象。调查发现,靠口耳相传的民间反切语正以很快的速度萎缩,成为一种濒危的、亟待抢救的民间语言。现有研究虽然已逐渐展示出我国各地反切语的现实状态,但基于反切语口耳相传的特性,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讨。口述史为民间反切语研究带来了方法和观念上的更新,运用口述史方法对民间反切语研究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完成:明确研究目的、确定调查区域和访问对象;搜集口述史料;整理、分析访谈资料,完成理论诠释。口述史研究更加关注使用语言的人,而并非仅仅语言现象本身,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复杂的符号互动过程”中构建起对研究对象的认知。
民间反切语;口述史;方法论
“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1]5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近年口述史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并渐由一门专门的学问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一种研究理念。反切语是流传于我国民间老百姓口头上讲说的一种隐语,它通过反切的原理达到交际的目的,渗透于社会多层面,既是一种语言现象、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民俗现象、文化现象。但调查发现,靠口耳相传的民间反切语正以很快的速度萎缩,已成为一种濒危的、亟待抢救的民间语言。口述史着眼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对意义的描述与诠释,为民间反切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使我们能够设法找出现存民间反切语的各种语言碎片的社会意义和社会碎片的语言意义,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民间口头存留的反切语有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认识。
一、民间反切语的研究历史及现状
据文献记载,反切语在我国自汉代始一直流传至今,对其关注和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限分为两个时期,之前主要是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如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从谈”条:“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领,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以盘为勃兰,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陀,以圈为屈栾,以蒲为鹘卢。”[2]404
这类文献记载唐宋之前较少,多在探讨反切注音法的创始人、反切的来源等相关问题时提到,唐宋以后笔记资料中渐增多。相关文献显示,这是一种一直活跃于“俚人”“闾阎”间某些社会群体或团体中的隐语,其原理同反切原理一致,“以音切为呼”,遁词隐义、谲譬指事,其功能或讽谏、或调侃、或密言,在使用时“随拈两字,皆可成音”[3]104。文献记载的反切语有诸多叫法,如“反语”“闾阎鄙语”“俗语切脚字”“黑鬼切”等。传授方式为“非有师学授习之”,记录下来的反切语大多仅以个别词条形式出现,且所用切字多不一致,语音亦有所差别。如“孔”,有“酷宠为孔”“窟笼为孔”“窟垄为孔”等不同切语,“精”,有“鲫令为精”“鲟领为精”“即零为精”“只零精字”等切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容肇祖、赵元任先生率先开始用现代科学的观念研究这一语言现象,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各地、各语种反切语的描写,主要描写各地反切语的语音结构规律、使用人群、现存状态等,并得出如下结论:反切语在我国广泛流行,分布在华北、华南、东北、西南等区域;反切语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使用;各地反切语的原理基本一致,均是利用反切的原理,在形式上二合、三合、四合,或正序、或逆序等,以达到“隐而又隐”的目的;反切语已成为一种濒危语言现象,面临失传的危险,亟待整理记录研究。二是从民俗学、文化学等多角度研究反切语。“多学科视点的导入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尤其有助于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深化和发展。”[4]反切语作为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现象,除了语言学的研究以外,还可以是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学、公安语言识别等研究领域。主要成果认为反切语“源于商贸”“产生流行于市井下层社会”“反切语与优伶演艺如影随形”,是一种亚文化群体的语言代码,一种非主流文化现象。从民俗语言学视点来考察,民间秘密语则是一种属于非主流语言文化的特定民俗语言现象。三是考察反切语的历史来源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研究指出,我国隐语滥觞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兴于明清,传承流变至今,我国秘密语是世界上诸同类(秘密语)语言现象中最大也是最为丰富的一系。四是利用反切语考察汉语方言发展史及方言区划。反切语在我国重要的方言区都有分布,覆盖地区多为过去的商业繁华地,现在大多分布在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城镇地区,反切语反映出来的语音特点为方言研究提供了线索。五是辞书编纂。构成汉语隐语有三种类型:词语型、文字型、语音型。由于语音型秘密语口耳相传的特性,所以各类辞书中所收录的俚语行话隐语多以前两种为多,所收词条形态为语词式,故固化成词的反切语词条有所收录,但数量有限。
综合来看,现代学界对民间反切语的研究文本主要两大类:一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有关记录文献,二是田野调查所得的材料;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记载了解的反切语,大多为零星词语,且许多已进入书面语,固化成词,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反切语使用的完整状态,而且将历史文献记录的切脚词放到一起比较会发现各家所记词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雷同。赵元任先生在《反切语八种》中提到清小说《镜花缘》里记录了一条较完整的反切语,“吴郡大老依闾满盈”的切语,意为“问道于盲”。但也是仅存的相似的记录而已。所以考释文献中的反切语时,学者提醒“对反切不诉诸听觉,而在字面上求助于视觉,必然错误。”[5]立足于田野调查法对民间反切语的全面调查研究始于赵元任先生。《反切语八种》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八种反切语进行了详细描写,成为我国现代秘密语研究的开创者,掀开了反切语研究的新的一页。其后诸多的语言研究者纷纷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我国各地反切语进行了调查描写,克服了文献研究的片面和不足,清晰地展示出各地反切语的现实状态。但基于反切语口耳相传的特性,关于民间反切语尚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作出回答,回答这些问题尚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改进。
二、口述史与民间反切语的关联
语言观创造了语言研究方法。民间反切语存在了几千年,是一种流行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民间秘密语形式,在它身上既印有历史和群体的文化痕迹,也带有政治和经济的烙印。对民间反切语的研究应当是一种整体、全面的研究。“口述史学的出现对于民俗学而言,既是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的支持,同样也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方面的借鉴与深刻变革。”[6]口述史学在民俗学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同样也反映在语言学领域,口述史学与语言学二者之间既有方法论的关联,也存在研究观念的一致。
首先,口述史研究与语言研究在观念上的重合之处,表现之一即历时与共时概念的结合,以再现某一历史现象的完整面貌。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考察研究一种现存的历史语言现象应有三个角度:它既是该语言的直接反映,也是该语言历史演变的现今面貌,同时还是该语言处于自身变异变化的一种现实状态。以往对民间反切语的调查基本限于共时状态下语言状态的描写,或以文字形式零星记录反切词语;或借助于文献资料,形成对某一历史阶段反切语语言状态的分析;或通过被调查人之口,记录反切语的语音构造规律;或通过调查人的观察统计得出反切语的使用人群、使用场合等。这样的研究无疑不能得出民间反切语的完整面貌。语言既是显现的又是潜藏的,语言研究中有时会忽略一些重要的语言事实,如有学者就指出,“可惜的是,由于棉湖秘密语产生、流行于市井下层社会,《揭西县志》等史志均不记载,文人学者对此也视为下贱者之鄙俗之语,未加注意,使得今天我们已无法了解它产生的确切年代。”[7]口述史研究借助于使用者的讲述和回忆,就可以还原历史的真实,回答文献文本所留存的空白。另外,共时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关于反切语的使用人群,结论颇多,“实际上用反切语的大多数是小学生、算命瞎子、流氓、做贼的等类人”“使用反切语最普遍的则为:流氓、唱摊簧的、道士、礼人、裁缝、小学生等六类人”“粮商”“盲人成堆的地方”“大都是‘吃百家饭的’”“城镇居民大家共用的隐语”“风行于下层市民中间”,只能说,这是对民间反切语共时状态下调查得出的结论。
口述史最重要的特点即生动地再现历史,将同被访谈者有目的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作为构建恢复原历史面貌的重要史料文本,“它给了我们一个场地,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借当事人记忆里丰富的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真实面貌的工具。”[8]78从简单记忆到历史再现,使用者即是反切语发展的见证人,作为“知情者”,他们是反切语现象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继承者。口述史的研究将反切语的研究范围扩大至亲历者或见证者的生命区间,甚至更长(继承者关于上代的传承记忆),通过梳理使用者的经历,得出反切语的历史发展面貌,回答相关的问题。
其次,口述史研究与语言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合即田野调查方法。语言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历史悠久,从汉代扬雄到今天的语言研究者一直秉承“强调田野调查,强调语言事实”的原则。自赵元任先生起诸多学者致力于对民间反切语的调查描写。现实状态下的民间反切语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存在,在缺乏文献资料的状况下,田野调查法无疑是无可替代的。
借助于口述访谈,口述史研究一方面为我们拓展了文本,另一方面使反切语的研究不再仅仅是公布材料,而将材料与社会发展相联系。马福威认为,“一种语言的生命与活力取决于其寄主(即该语言的使用者)的行为和性情,以及其寄主所形成的社会和其寄主所处的文化背景。”[9]17语言既是个人能力也是社会财富。针对民间反切语展开的口述史田野调查把被访者的经历、情感、话语语境等作为调查记录的重要内容,访谈获得的人们的历史记忆,“从历史记忆、社会意识、文化观念上对它加以利用。”[10]231口述史将反切语使用者个体的人生与历史挂钩,口述记录反映了多样的语言生活,通过口述史方式的研究,获取访问者的生活经历,了解个体语言习得、使用语言的历史,从中得出使用语境、心理、受众群体、语用效果等诸多信息,可以提高描述性研究的效度,也为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就这一意义上而言,口述史研究成为语言学上田野调查法的延伸。
另外,从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区分来看,口述史研究更倾向于质性研究,是一种重视社会事实诠释的方法。“研究者常常是在极为自然的情境下,运用一种或多种资料收集方式,针对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收集。而研究者对所收集之资料进行诠释的过程,必须是从被研究对象的立场与观点出发,融入当事人研究情境中,充分了解被研究者主观的感受、知觉与想法,进而理解这些研究现象或行为之外显或蕴含的意义。”[11]49利用口述史除了获取反切语使用的片段外,更注重对社会人的研究,站在话语者本人的角度去了解其言语行为,注重对使用者心理、情境的感知。当然,量化也能提供有利的数据,如受访者的抽样选择,能使得口述访谈对象更具有代表性。将社会语言学的观察、采访法与口述史的访谈相比较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重合之处。
第三,从民间反切语的语言性质来看,它是依托于自然语言,为适应特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人为的语言符号。一般情况下,在展开对某一对象的调查研究之初,研究者往往已经形成了对该对象的先入为主的认识,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展开调查研究不可避免要受影响,被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要让熟识、使用、经历它的当事人之口说出才是客观的,研究者本人的意识形态与观点也不能强加于口述资料的分析与阐释。作为一种长期活跃在我国民间老百姓口头上的语言现象,民间反切语究竟是什么,其规律、其特征要经由被研究者的观点体现出来。“口述史既是一种资料收集的方法,同时也应当是一种知识主体建构的概念。”[11]6在研究过程中为避免用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想法,限制被研究对象的语言与行为的主动反应,口述史的调查伊始仅仅提出预示性问题,之后在调查过程中根据实际提出开放性问题。
作为一种附属语言现象,在民间反切语的使用和流传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如固化成词的反切语可以丰富语言中的词汇,语言的发展演变也会在反切语身上留下印迹,反切语中存在的怪诞音节就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如何对民间反切语进行管理?在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中谈到,目前隐语行话仍然活跃在我国民间众多社会群体中。语言管理的过程即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可以从个人或群体的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中找到。在语言使用领域的最底层,语言使用者都体现了一种语言信仰,他们选择语言要选良好的或有价值的。口述史的学术理论蕴含之一即常人方法论,将平常百姓的生活纳入历史的书写,“能够真正地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变迁、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11]4口述史研究重视社会事实诠释,而“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形式和语言社会功能之间的相互渗透,是语言的功能赋予了语言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表现形式。”[12]10反切语历经千年的演变,它的演变机制是什么,语言的功能选择和社会选择怎样导致反切语的变异变化,要在使用者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形态中考察,以此确定语言管理的标准。
作为一种“人为”语言现象,民间反切语研究材料来源的对象是能说会动的主体。对反切语的全面研究,应该包括对使用者语言的生成性能力与言语的一般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观察,这体现在具体场景中人们对反切语的运用中。口述史研究采用现场直接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可以长期保存,随时重现当时的场景、语境及访谈过程和原貌,为研究提供便利。
另外,利用口述材料还可以回答其他的相关问题。如在调查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过程中发现,回族人认为反切语是他们的语言,而据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资料,反切语是在宋代传入少数民族的,通过传承者的回忆无疑为了解回汉民族接触和回族历史有一定的意义。
三、口述史角度的民间反切语研究
口述史是一个二重概念,即作为学科的口述史的“口述史学”和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史的“口述史料”。[13]民间反切语的口述史研究是语言学与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结合,借助口述访谈的方法,运用社会语言学相关理论对口述访谈资料进行解释,即通过访谈对象表达、讲述个人或家庭、团体甚至族群学习反切语、使用反切语的经历,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也可以文字记录,获取史料,整理分析资料得出结论的过程。具体分为以下步骤完成①以下阐述以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调查研究为例展开。笔者对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调查始于2007年。:
第一步,明确研究目的、调查区域和访问对象。
首先确定研究目标。对“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课题”确定的目标是:综合语言、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维视野,通过综合对比,形成对民间反切语的全面认识;民间反切语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承扩布、转换功能,结合语言的变化以及历史研究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一语言现象,反映语言在社会中的运动机制,为解释语言演变提供实证性的社会动机;民间反切语是现实社会中濒临消失的语言现象,回答制约民间反切语生存的诸多因素。
其次确定调查区域。“反切语风行于下层市民中间,多在人口、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城镇地区说用”[14]这个结论是可信的。我们在对相关调查点进行了地理、人文的考证研究后,对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调查,仅安徽境内自东向西依次确定主要调查点有凤阳县临淮关、五河县临北回族乡、蚌埠市、淮南潘集区古沟回族乡、凤台县城、寿县县城、正阳关等地,这些地区的反切语使用者比较集中,是比较理想的调查区域。
最后明确调查对象。我们寻访和联系了与反切语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历史见证人(主要是使用者)。在调查对象的问题上,对受访对象的选择以判断抽样为主,我们尽量选择了解反切语、会说反切语、熟练使用反切语的人为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尽量具有包容性,尽量考虑到怎样把他们和其他人群区分开来的所有因素,包括阶层特点、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行业、种族背景、宗教信仰等。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要熟悉受访者的语言和文化,并向他们解释研究目标以及他们贡献的潜在价值,让被访者意识到自己也是该研究课题的成员,揭示他们的认同,肯定他们的作用,为后来的访谈做好准备。
该步骤最后是形成系列预示性问题。
第二步,搜集口述史料。
根据研究对象及相关群体的特点,在访谈形式上选择以个人口述访谈为主、兼以多人口述访谈为辅的形式。如对正阳关反切语使用者展开的访谈中,发现使用反切语的群体,以年龄、职业、宗教信仰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群体甚至相互并不熟识,而群体内部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访谈中,首先进行个人访谈,之后再将相互熟识的小群体聚在一起,在交谈中形成对往事的集体回忆。由此获得的两份口述资料可形成比较和印证。
在访谈过程中,个人访谈前可提出如下“预示性问题”:您的职业是什么?您把反切语叫什么?您是怎样学会反切语的?能教教我吗?会说反切语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吧?您周围还有哪些人会说反切语?等等。
由于被访问者大多生活经历曲折,被访者个性也存在差异,他们有的豪放,有的小心,所以事先要解除其心理负担。我们用反切语形式向访谈者问好开始访谈,这样很容易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另外,面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受访者时,也注意尽量减少语言差异带来的隔阂。
访谈过程中访谈者要始终积极地倾听,与被访者形成互动和默契。访问期间一定注意被访问者说了什么内容以及如何表达这些内容的,避免仅作单纯的语言记录,仅关注话语本身,而忽略了对话语的内容分析。甚至要注意观察受访者叙说过程中的手势和面部表情。
无论实施哪种访谈形式,在访谈过程中,口述访谈者事前要作大量准备工作,厘清思路,不能信口开河,在访问的过程中访问者不能误导,如提出一些带有主观倾向的问题,或做出主观评价,比如在提出的预示性问题中,其中一个设计为“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反切语?”和设计为“会说反切语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吧?”两种提问方式无论是对被访谈者的有效启发还是获取信息量方面都是不同的。整个访谈过程中记录者认真录音,适当做笔录,之后完成对材料的整理、查证工作。
第三步,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完成理论诠释。
访谈获得的资料包括访谈内容和文本资料,为了维护口头资源的原始性与客观性,对受访记录不能作任何形式的增删改动。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对其中关键信息的梳理与连结。首先整理出每位访谈者的个体经历,注意捕捉、分析事件过程中的情节和人物细节。注意“那些话可能意味着什么”,留意资料的语言意义、社会文化意义、时间和空间背景、叙述者表达的意图、重大生活事件对人的影响等。然后反复阅读文本文稿,在访谈者的历时经历中梳理出该访谈对象的阶段性特征,最后完成不同访谈对象的横向比较,找出其共性和差异。
“反映历史记忆的口述史料事实本身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记忆层面,侧重于从历史记忆、社会意识、文化观念上对它加以利用。”[15]在对访谈内容多角度做出尽可能详尽的内容分析后,发掘反切语现象的主要概念,建立概念间的联系,从而形成理论,提出译码构架,与之前预设译码构架比较,如反切语语用功能的转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传承人何以成为传承人以及他们的态度价值体系;反切语在社会中的运动机制如何为语言的发展变化提供方向性信息;作为一种历史语言,作为汉语的附属语言,如何适应汉语的发展存在下去,以及与语言政策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作出修改参考,形成研究的具体假设,在此基础上完成理论架构的整合。
对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的调查研究已实施了近十年,这是一个长期观察,获取资料、分析综合的过程,只有结合使用者的角度细致分析现存民间反切语的状态与特征,才能得出民间反切语的真实完整面貌。
结 语
事实证明,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语言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口述史研究为我们拓展了文本。口述史研究是一种重视社会事实诠释的研究方法,着眼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对意义的描述与诠释,更加关注使用语言的人,而并非仅仅语言现象本身,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复杂的符号互动过程”中构建起对研究对象的认知。
[1]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J].社会科学辑刊,1997(1):41-47.
[5]傅憎享.反切语杂谈[J].寻根,2005(2):99-103.
[6]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3(4):126-132.
[7]林伦伦.广西揭西棉湖的三种秘密语[J].中国语文,1996(3):192-193.
[8][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9]Mufwene,Salikoko S.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0]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1]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2]张廷国,郝树壮.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闫茂旭.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J].唐山学院学报,2009(4):16-20.
[14]张天堡.中国民间反切语简论[J].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16-117.
[15]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校 人云
H17
A
2095-0683(2017)04-0079-06
2017-06-16
2015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5D105)
陈娟(1970-),女,山东淄博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