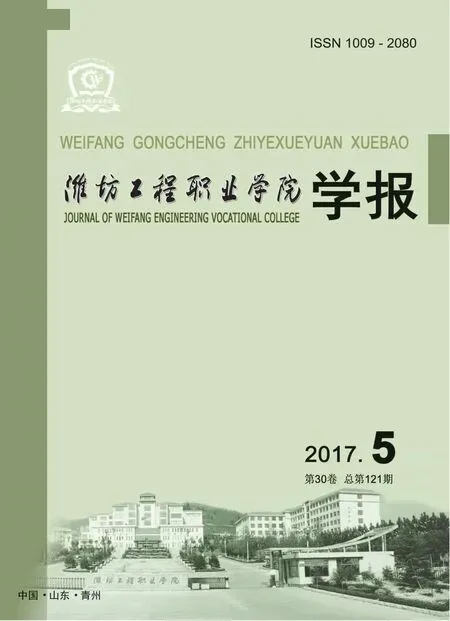论儿童冒险故事中的叙事元素及教育功能
袭 祥 荣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济南 250014)
论儿童冒险故事中的叙事元素及教育功能
袭 祥 荣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济南 250014)
冒险故事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亮眼色彩,其“冒险”元素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招致了许多成人的担忧。以经典儿童冒险故事为蓝本,从离家、大自然和回家等叙事元素入手,挖掘冒险故事鲜明的娱乐功能和内隐的道德教化功能,重申冒险故事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冒险故事;要素;功能;
刘绪源老师将儿童文学划分为爱、顽童和自然三大母题,分别从成人、儿童和人类三个角度来审视童年的印记[1]。三大主题并非泾渭分明,在同一则故事中总会交叉出现,冒险故事便凭借自身的包容性将三者完美融合:有成人“爱”的规训,有顽童的“离家”成长,有自然的隐性教化。从遵循“本我”的快乐原则出发,到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认知的确立[2],冒险故事为儿童提供了情绪宣泄的机会,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儿童的道德成长。然而,冒险故事中所含的离家、历险等成分使部分成人进行文本选择时对该类文本持怀疑和犹疑态度。本文以经典冒险故事为依托,深入挖掘其构成要素及深刻内涵,解读冒险故事娱乐性中隐含的道德教化功能,探求该类叙事文本中的“成长”意味。
一、叙事元素解读
追求梦想、勇敢探险的汤姆·索亚;变成大拇指,跟随鹅队去旅行的尼尔斯;莫名被带到奥兹国的多萝茜;跟着小飞侠奔到永无乡的温蒂和孩子们……每一则冒险故事都有自己的个性,彼此间又充满着共性,他们共同涵盖了三个要素:离家、大自然历险和回家,这三个要素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冒险故事对儿童成长的意义。
(一)离家:“本我”与享乐原则
离家和回家是冒险故事的永恒话题,几乎所有的冒险故事都是孩子在逃离家庭庇护的前提下完成的:孩子对自由的追求与成人掌控的世界规则的博弈中处于下风,这推动着孩子离家行为的产生[3]。婴幼儿时期的孩童习惯于父母对其愿望的无条件满足,一旦父母开始提出要求,他们会感受到严重的期望幻灭,转而主动与外界建立更重要的接触。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结构层次来说,个人的行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精神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潜意识的“本我”作为与生俱来的、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依据“快乐”原则来运作,驱动个体追求快乐回避痛苦[2],为了追求自由快乐的离家出走都是潜意识里的“本我”的要求。
故事中孩子离家的情况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反抗现实教条的捣蛋鬼的离家,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尼尔斯,两个调皮鬼难以遵守和认同成人以社会的需要为标杆塑造儿童形象的要求;另一类是对乏味生活厌倦的“乖”孩子的离家,如《小飞侠彼得·潘》中的温迪和《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茜。在多萝茜眼中,草原上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彼得·潘诱惑温迪时,温迪也义无反顾追随他到了永无乡。儿童的“本我”受现实原则压抑,难以释放,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在享乐原则驱使下,儿童的离家行为产生。
(二)大自然:自然崇拜和人格重塑
汤姆·索亚探险的山洞、多萝茜到达奥兹国时穿越的大森林、尼尔斯的坎坷旅行……冒险必然意味着与大自然正面交锋,这是孩子们成长的必经考验。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拜,既是儿童人格重塑的过程,也是智慧启蒙的开端。
离开家庭庇护的儿童急切需要建立保护机制,重塑自身人格,冒险旅程中带有“威胁”性质的大自然是儿童心理危机的象征,如黑暗的森林、不测的天气……故事中大自然的力量将儿童成长中的困难外化,有利于“泛灵”阶段的学前儿童理解。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独立,儿童必须学会应对这些挑战,尼尔斯在追随雁队旅行的过程中战胜各种威胁;多萝茜勇敢面对被龙卷风带走的遭遇……儿童战胜大自然,或者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意味儿童无意识中的恐惧、悲伤、愤恨等心理危机被解决,儿童自我人格得以重塑[4]。此外,冒险故事中渗透出的对大自然的敬畏成为儿童的智慧启蒙教育。正如美国学者艾莉森·卢里在《魔法森林和秘密花园:儿童文学中的大自然》所说,“如果儿童文学中食物代替了性,宗教就已经被对大自然的崇拜所替代了”。[5]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人类的能力被无限夸大,自然被视作被征服者,然而,在冒险故事中,大自然成为推动幼儿发展的源动力,这也是中国古代提倡的“万物有灵”的体现。例如,在尼尔斯最为窘迫的时候,太阳告诉他“只要我在这里,你就不必担心害怕的”,重获信心的尼尔斯变成了勇敢的小孩。大自然力量的凸显激发了幼儿敬畏自然、尊重一切的情感,智慧启蒙于敬畏,这也是儿童智慧的启蒙教育萌芽。
(三)回家:“自我”与成长
儿童冒险故事有一个共性:离家的孩子最终都会选择回家。由于依赖性的存在,儿童最初难以离开父母,因此,最初的顺从不过是暂时性妥协,冒险旅行促使儿童真正将成人教导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知。汤姆·索亚最初的归家不过是出于幼稚的自大和炫耀心理,最终在良心的驱动下指控坏人伸张正义;当尼尔斯见证了独居老人孤独的死去时,他瞬间领悟了自己对于父母的责任。尽管孩子们离开了家庭,但长久以来的家庭生活依然为他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固有的认知在幼儿的冒险旅途中进一步印证了现实世界的生存法则,他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追求自由的同时,要担负起对他人的责任,对规则的认知由“我不得不”转化到“我愿意”,自我人格得以发展。离家必然要回家,成长就意味着承担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儿童的归家既是故事的结束,也是成长的开端。
二、冒险故事的教育功能
(一)鲜明的娱乐功能
卢梭作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在《爱弥儿》中便旗帜鲜明地点出:“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是纯粹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6],主张将孩子带到乡间大自然,在儿童尽情玩耍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体力和活泼的精神进行充分发挥”[6]。冒险故事是“儿童本位”教育观的体现,其亮点就在于儿童的绝对自主,儿童释放天性、拥抱大自然的冒险之旅反映了冒险故事的娱乐特质。
1.冒险故事利于幼儿负性情绪的释放
卢梭的“儿童本位”为我们认识儿童开启了新世界,成人视儿童为“无邪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因此儿童需要被重塑和改变。如福柯所言,现实世界的儿童生活在一个充满规训与监视的社会,“包裹式儿童”的教养方式使儿童的成长完全受成人控制,儿童依赖性较强,难以察觉自身发展需要。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儿童自身意愿与成人发生冲突,受现实原则压抑,儿童积攒的负性情绪无处释放,心理危机的根源由此埋下。冒险故事恰好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将儿童的无意识用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坏女巫是“生气的父母”的象征、突如其来的恶魔是儿童心底恐惧感的象征……生动的故事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自比为故事中的小主人公,在战胜坏人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想象自身生存困境得以解决,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获得精神上的快感,阅读的过程便是情绪释放和自身无意识调整的过程。
2.冒险故事有利于幼儿想象力的发展
切斯特顿在《回到正统》中说道,童话中没有“定律”,只有“魔法”。[7]与成人世界不同,童话故事中没有必须建立连接的固定套路,刻意避免因果联系,故事走向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却又扣人心弦,有利于幼儿的阅读兴趣的激发和想象力的发展。冒险旅途的风光总是美妙神奇:汤姆带领小伙伴在小岛上钓鱼、烤乌龟蛋;尼尔斯跟随雁群去观赏百年难得一见的舞会……趣味十足的旅途激起幼儿对自然和未来的无限向往;冒险的情节总是一波三折,每一个主人公总要经历艰难才能成功,主人公战胜困难的神奇经历开拓了幼儿视野,幼儿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被带入到主人公的处境,在脑海中为故事的发展走向提出无限可能;现代教育理念倡导亲子共读更是发展幼儿想象力的良好途径,在阅读过程中成人可以与孩子共同探讨故事情节,成人适时鼓励幼儿对故事情节进行猜测并予以改编,这些手段在促使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提升的同时,极大推动了幼儿想象力发展。
3.冒险故事有利于幼儿自信品质的培养
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将人格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个体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矛盾,3到6岁儿童的主要矛盾是主动感对内疚感阶段,这一时期他们创造性思维发展,并开始对未来进行规划,如果父母肯定儿童的主动行为和想象,儿童的成长危机便能顺利度过,并收获目的的美德。[2]这一阶段儿童主动感高度发展,与成人要求之间的矛盾增加,儿童在与成人对抗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柔弱,负性感受致使儿童产生自我怀疑、焦虑等心理危机。冒险故事中存在大量小主人公凭借自身力量战胜成人的情节,如不爱读书的汤姆·索亚成为小英雄,多萝茜打败了女巫……“儿童战胜成人”这一隐喻给予儿童信心,暗示儿童要相信自身的力量。儿童在故事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不再为自己的弱小而苦恼,相信自己可以凭借努力改变命运,转而对成长充满期待,幼儿自信品质得以培养。
(二)内隐的道德教化功能
冒险故事带领孩子们酣畅淋漓地开启冒险征程的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给予孩子道德教化。卢梭在《爱弥儿》中尖锐地指出:“仅仅在孩子们的头脑中填塞一些他们无法理解的词儿,怎么就能说是把他们已经教育的非常好了呢”[6],因此,卢梭主张“教育应该是行动多于口训”[6],儿童在自身经验中获得道德认知是实施教化的最好途径,冒险故事就是在孩子的亲身经历和自然后果式的惩罚中传递道德认知、激发幼儿道德情感、磨练儿童道德意志,最终促进儿童道德行为的改变。
1.冒险故事有利于儿童道德水平的提升
幼儿道德发展不仅是道德认知学习和教育的过程,更是道德情感升华和道德行为矫正的过程。处于自我中心阶段的幼儿由于理性发展尚不完备,思维具有直觉性和冲动性的特点,容易受到暗示和影响,道德发展受道德情感影响较大,冒险故事是激发幼儿道德情感,促进幼儿道德水平提升的有效手段。首先,冒险故事中正面形象主人公的塑造激发了幼儿的道德认同,为儿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儿童对道德的认知不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倾向于“我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4]根据班杜拉替代性强化的观点,儿童的发展是通过观察学习而实现的,榜样的存在为幼儿提供了行动指针[2],尼尔斯最终成为爱护动物的小英雄,汤姆·索亚勇敢与坏人作斗争……对人物形象的喜爱驱动儿童自觉认同故事传递的道德观念并做出相应道德行为;其次,冒险故事中自然后果式的惩罚方式传递着“有条件的欢乐原理”[7]。如由于伤害小动物和不爱学习,尼尔斯变成大拇指,这就是自然后果式的惩罚,儿童在故事中意识到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为了变回原形,尼尔斯必须改变自己,这就是有条件的欢乐原理,主人公任何成就的获得必须以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为前提,粗浅的公平观念由此树立。
2.冒险故事利于儿童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的发展
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在亲子关系的基础上幼儿同伴交往的需求增加。然而,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学前儿童处于自我中心阶段,合作水平较低,难以建立良好的同伴互动关系,冒险故事中人际关系的呈现为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参考。首先,冒险故事利于幼儿获得人际交往意识。冒险旅程一般都会有同伴的存在,性格各异的同伴代表着现实儿童开始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冒险之旅绝非独自进行,多萝茜的探险离不开小狮子、铁樵夫和小狗托托的陪伴,尼尔斯的旅行也离不开大鹅们的帮助,甚至不愿长大的彼得·潘也需要其他小孩子的陪伴……战胜困难必须借助与同伴的合作,与同伴合作情节的设置暗示幼儿必须接受自身与他人的差异,促使幼儿意识到同伴互补的重要性。其次,冒险故事利于幼儿掌握合作技巧。故事中的“小伙伴们”有合作,亦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合作方式和冲突解决为幼儿提供了模仿对象,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学会各种应对冲突的方式,学会与人交往的技巧,为进一步融入社会做准备。
小结
童年是充满希望和犹疑的可能性存在,冒险故事中蕴含的冲突是幼儿心理危机的折射,兼具娱乐特质和教化功能,是成人人生体悟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的结果。许多家长在选择文本时,总会担心冒险故事中的“冒险”“离家”等元素会将孩子引向“邪路”,在娱乐与教化之间摇摆不定。我们要做的,是在教育实践中努力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因此,在与儿童分享冒险故事时,成人除了与儿童一起欢笑,更要挖掘故事的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儿童领悟成长的真谛,在阅读中悄然成长。
[1] 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第四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3-11.
[2] 王振宇.儿童心理发展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0-119.
[3] 张欣媛.成长中的独特体验——论儿童文学中“离家出走”情节的审美价值[J].时代文学,2015,(9):204-205.
[4] [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M].舒伟,丁素萍,樊高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
[5] [美]艾莉森·卢里.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M].晏向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2.
[6] [法]卢梭.爱弥儿(上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社,2015:90-115.
[7] [英]切斯特顿.回到正统[M].庄柔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52-55.
(责任编辑: 高 曼)
10.3969/j.issn.1009-2080.2017.05.014
2017-08-06
袭祥荣(1993-),女,山东莱芜人,山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I207.8
A
1009-2080(2017)05-00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