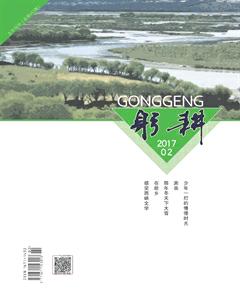乡村美味(三题)
林文楷
焖全花
“队长不批,农田不离。”说的是几十年前生产队大唿隆时,人被管得紧,一个农村劳动力,不经生产队长批准,得天天困在地里干活。爷爷虽是守纪公民,却有离谱的时候,且长而久之,每年端午节(晴天)期间,总要破了这个规矩,无论队长批与不批,爷爷都会脱离集体劳动,跑到门前小河里去一天,直至八十几岁高龄。
爷爷嗜鱼,嗜一种门前小溪河里的全花鱼。
门前的小溪河叫艾家河,小巧得有味,它发端于上游几十里的大山谷,一个叫三岔溪的去处,在诸多溪河中,它不出名,且过于独立王国。说它独立,真是独立得可以,犹如阎锡山的山西铁路,轨窄,他地的列车都进入不了。从小溪河的源头到注入长江,远不过五十公里,常年水流大不过一到两个流量(下雨除外),就这五十公里,分成两段,下游十公里,亲密长江,上游四十公里,拒绝长江。
淙淙清流从三岔溪行来,一路荡荡悠悠,平平缓缓。河面是一种山里的宽阔平展,蜿蜒曲折,徐徐向前,很有绅士君子风范。将到尽头,已能看到奔涌的长江了,小溪河一改平静悠闲,在一个叫倒巴溪的地方,突然飞泻而下,断而成瀑,一道百余丈高的绝壁横空出世。在下相望,疑似银河落水。
悬崖断壁,溯江而上的水生动物被阻绝了,望水兴叹,上游独立王国就此形成。
造物主伟大在于无所不能,隔了飞瀑绝壁的上游小溪河并不孤单,上游河段水族们依然繁盛,仍不乏鱼虾蟹鳖之类。
小河里的鱼肯定是独立进化而来的,至少有一些品种是,比如全花,我这么认为。我生平到过不少的大江小河,再没见过与之相同的。全花的成鱼长不过十几公分,重莫过二三两,色青黑,红蓝相间的网状花纹布满全身,非常漂亮。全花鱼不单美丽,其味道更是极其鲜美,特别是每年端午时节交配繁殖的时候,其味绝美。端午节时,爷爷“大逆不道,敢悖于生产队长,全坏在好这口上。
爱鱼,善渔者,爷爷,且渔得悠闲,这是我见过最为悠闲的渔者。他捕鱼时用小网,不贪不竭,每年最多只到小溪河里去捕捞一两次,都在五月端午期间。爷爷捕鱼不仅带自制的鱼网,还要带小炉灶小铜锅,带油盐酱醋,带葱白生姜,带用头年秋季大青菜腌制的盐菜细丝和老烧酒。
小溪河山阴水凉,尽管是大夏天,也只能近午入水。小溪河离家有一公里开外的路程,爷爺起得早,下河不早,准备家什,一段路途,到河边也就十点钟多了。来到河里,爷爷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撒网捕鱼,而是看水情,选了全花鱼群出没频繁且河滩平缓的地段,放了什物,拣了石块,在河滩上支起炉灶,再进到树林里拾掇些柴禾晾晒。
接下来是抽旱烟,抽过旱烟,已近晌午时分,爷爷这才去布网。网是两张,一张布到小河的下段,这是一张死网,待鱼自投的。还有一张活网,爷爷再从上游散开,一头我牵了,一头爷爷牵了,至上而下,徐徐围盖,直到两张网会合。
两张网会合,必有很多收获,虾,蟹,鱼等。鱼有白鳊,乌斑,烧火佬、全花等,爷爷一一告诉我。一只只,一尾尾死死卡在细密的网眼里,馋眼喜人。爷爷挑剔,从不滥杀,从网上一一取了白鳊,乌斑,烧火佬之类放生,单取了红蓝网状花纹的全花放入鳖篓。
一网就足够了,数数,几十来尾。收获再丰,爷爷也不再布网,而是提了鳖篓到河滩走向架好的炉灶边。生火、烧锅、煎油、刺鱼、下料。油盐酱醋,葱白生姜辣椒粉,一一到位,小铜锅哧哧嘶叫,乱吐白气,最后压上盐菜丝,添一两勺洁净的溪水,减火缓焖,十来分钟后,一锅腌菜焖全花鱼成了。
没有坐椅,选一方干净的石头,爷爷坐上去,杯子里斟满酒。锅盖揭开,鱼躺在盐菜中,挑一尾稍大的,爷爷递给我。吃!
微酸。盐菜味儿。辣。葱、姜、花椒,辣椒味儿。鲜香微辛,全花鱼味儿。是,不是,不全是,妙在是与不是之间。舌尖而至,至舌根,浸入五脏六腑,透出暖流,发至全身。五月端午,天闷热,细密的汗从发际、额头、面颊、背部浸淫而出,浑身通透舒服。
重新夹起一尾,丢入自己嘴里,和着老烧酒,闭目咽下,入喉。喉结鼓起滑动。一尾、两尾、三尾……爷爷视我不在,怡然如痴,缓而有至,既夜。
网影游移于阳光下,鱼骨乱飞于沙石中。天上的飞鸟闻香醉了,山里的走兽闻香醉了,河里的鱼虾也闻香醉了,不是酒,是端午时节盐菜焖全花鱼,只有我没醉,呆呆地站在炉灶边,馋得涎流及地,待等明年。
荡秋千
荡秋千,一项古老的体育活动,已传承了千年。没想,荡秋千一词还有他说:中秋时节泥鳅炖南瓜丝儿,成了一道别致的乡间美食。流行于下堡坪高山水乡。
刚入伙(参加工作)那会儿,吃饭大食堂,陈谷烂米,菜一锅煮,时间久了,叫你一点儿胃口都没有,尤其是夏季,实难下咽,肚皮空空,一个暑期过去,我瘦了十几斤,人笑骨瘦如柴。
总算熬过了最热的一段。
除劫三伏,处暑白露,暑气裉尽。一日中秋,领导安排下乡,时间一周,我去下堡坪,名曰抢种抢收,群众那儿去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磨砺锻炼,实则是给我们这些刚从学校毕业的青仔杀杀青。
杀青不怕,我血里就是小乡巴佬,还怕吃二遍苦不成。
到了下堡坪,还再下一次乡,进到杨柳池村里,住一朱姓农民家,人称老朱。
老朱不老,年不过三十,嘴有髭须,故而得名。老朱是农民兼兽医,不仅务农,而且走村串户为人劁猪骟牛牲畜瞧病,踏百家门,吃百家饭,人不赖,好吃。
我到朱家,老朱自认荣耀。那时的山村封闭,家境条件不好的农户,是不会安排干部去住的。县里干部,上方来的人,犹如旧时朝廷钦差,进住农家,普通百姓,怕是几辈子也不会有一次。老朱什么人?跑世外的,心知肚明,村里信任才安排,自然不会亏待于我。
乡间长大的孩子,最不怕的是劳动吃苦。自从重新回到学校,都好久没下过地了,去劳作松松筋骨,不但不怕,心里还想呢。住到朱家后的第二天,我提出下地里去。成。老朱笑笑,一口应了,说去荡秋千。说走就走,老朱拎了竹篮,拿把镰刀,带我出发。
何为荡秋千?我不解,心里暗自思忖。路隔十里,乡风不同,这里也有劳作叫荡秋千的?也不问。
稻子已经收割,昨天老朱请人过了板桶,背回家摊在门前的谷场上晒太阳。地里只余寸余高的谷茬,間或还有一些没被放干的白水。水不流鸟不鸣,慵懒的太阳升在了半空,坎沿小田沟里的泥浆和得稀烂,一切是那么的祥和与安宁。
白水处映着逼窄的日头,闪烁斑驳耀眼的光。泥浆中有一处处小孔眼,时不时有的孔眼中会冒出个半圆的小气泡来。到了地里,老朱放下竹篮,在泥浆处脱鞋赤足,挽起了裤腿,他低头弯腰,手对着泥浆中一个正在冒泡的小孔眼插进去。老朱侧着脸,手插得很深,在泥里深处慢慢搅动,似在搜寻什么。看得出,他手很用劲,臂上暴着青筋。搜过片刻后,他手拔出来了。随着手起,泥浆飞溅,一物落进竹篮,似有动物挣扎,活脱脱一条小泥鳅在里面乱蹦。到了这时我才似有所悟,老朱说的荡秋千,莫非就是这秋后在水田里抓泥鳅?
老朱一处处地搜寻,搜过几个田块,两三个小时过去,太阳已近当午,累得老朱一头的汗。看竹篮里的小泥鳅,少说也有了大几十条,抖抖家什,有些沉,收获颇丰,该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块玉米地,玉米已收过,桔杆还站着,缝隙间几蓬南瓜藤蔓,叶片肥硕青绿,茂盛而葱郁,秋生胜过春生,几只小南瓜安静地躺在叶片下,闪着油嫩的光。进到地里,老朱把它们采了,还采了些暗红的嫩紫苏叶,说带回家炖泥鳅。
回到家里,老朱拿瓷盆盛了清水,将竹篮中的小泥鳅倒入。小泥鳅个头儿虽小,却尾尾肥圆,活力四射,在水里奋力穿梭游动,搅起一团团气泡。过一会儿老朱为盆里换一次水,来回几次,水渐清了。后又在水中放入些许食盐,再泡半日,泥鳅翻肠刮肚,吐出泥水,经过再几次加盐换水反复,直到水清,泥鳅也被折腾得失去了当初的活力。
日头渐西沉了,我的肚子咕咕地叫,还没吃饭,老朱还在外面折腾。饿了,几个月来就饿,加之跟老朱在水里荡秋千,肚子闹腾得厉害,的确是饿了。
老朱的老婆在屋里一声吆喝,叫吃饭了。我和老朱赶紧进屋。
餐桌上放着一尊铁炉子,炉火正红,上面架着盛满鲜汤的火锅。一瓶烧酒,几只空杯、碗和竹筷。火锅里是空的,除了几碟咸菜和一盆刨得很细的南瓜丝,再无它物了。
火烤得锅汤滚动,泛起赭红的辣椒粉末。香葱大蒜一青二白,新鲜的姜块在锅里沸动。
盐菜丝一盘,煮火锅用的,老朱说。饿我大半日,盐菜火锅待我,未免太抠了点吧,我的老朱,不得好死!心中暗自愤愤。回头一想,自己过了,谁让你来三同的,人家没让你流汗就足够了,还想大鱼大肉?你靠!
看了桌上的陈设,早没了对酒的兴趣,力拒斟酌。老朱还是给我酌了一杯。
下乡原想慰劳一下久饥的肠胃,没想老朱这抠?正嫌没劲,老朱回头端来瓷盆,一手捞了水中的小泥鳅放入火锅。他老婆抓了大把的南瓜丝等着,如临大敌,几乎是与泥鳅同时入水,死死将泥鳅镇住。
盖在厚厚的南瓜丝下面,来不及挣扎,小泥鳅就毙命了,有几条命长的拼命钻到了南瓜丝的中间,也是淹淹待毙。汤再次沸腾,锅里溢出泥鳅、南瓜丝的香气,飘满一屋子。老朱又往里添了些紫苏叶,香气愈浓愈甚。
竹筷落汤,老朱在大沸的火锅里均匀不断地操动。
熟透了,南瓜丝,小泥鳅。荡秋千开始了,按老朱的话说。他荚了箸熟透的南瓜丝,内芯裹有小泥鳅,悬在半空,小眼睛弯成细缝,笑眯眯地看着我。意思我当然明白,示意请我先来。
南瓜常吃的,从春吃到秋。泥鳅也没什么巧,满水田到处是,一撮一篮子,还请我先来?我心里不屑。 饥不择食,况且饿了一个夏季,尽管心里不爽,还是生出欲望来,拿了筷子,学老朱夹南瓜丝。泥鳅南瓜丝入口,啊!太妙了,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差点叫出声来,香、甜、嫩、滑、爽,达到极至,其鲜其美难以言喻。
诱惑难挡,终是不能自已,无法抗拒了,泥鳅、南瓜,菜之单一菜之简朴。秋季,高山水乡小鲜泥鳅,鲜嫩南瓜刨丝,嫩紫苏叶,三秋合一恰到好处,相辅相存炖制火锅,神仙享受。筷子顿生了翅膀,来回不停奔波于火锅和口齿之间,老朱然,老朱老婆也然。
一轮夹完了,再添一些,泥鳅、南瓜丝一次次地添加,酒也一次次地再斟,谈笑风生,人不知饱,只嫌肚窄,直至夜半。
荡秋千,千古一食。自此以后,每年秋季,我都会设着法儿去找老朱,几十年不疲。
吃新鲜
吃新鲜,恐怕是我今生印像最深刻的美食了。
每临冬至,山里规矩,年猪开宰,会把四邻五舍的人请到家里来吃新鲜。
农活忙过了,进入一段闲适的日子。各忙各的,好久没在一起聚聚。到了猪肥粮丰,冰天雪地的时节,宰一头肥猪,张三李四邀在一块儿,挑一块好的鲜肉为食,话话家长里短,丰饶得失,温馨而美好。
大肥猪头一日就没喂食,平时爱吃的自然野生鲜草和玉米、大豆纯粮精料已与它无缘了,胃肠空空,在栏里嗷嗷叫,唤食,候宰。户主事前早做了安排,杀猪佬什么时候到堂?揪猪尾巴的人请哪几位?一一心中把握。火笼里的劈柴烈焰熊熊燃得大旺,早到的食客围在火笼边抽烟喝茶,谈论哪家的猪大膘肥,粮满果盛。
主妇(母亲)的心情最为复杂,一年的相处和猪有了深厚的感情,灵敏得只要嗅到她的气味也会嗯嗯。给自己喂食来了,若能说话,肯定会亲昵地一声声叫娘。
吆喝一声,猪乖乖地吃食,粗饲淡料也不挑剔。稍闲时挠它一爪,就会撵过来困在你腿上擦痒,是那样地温驯可爱。就要拉出去宰了,舍得么?就如自己的孩子要远行,心里不舍。
然而,主妇又高兴忙碌着,为猪的后事,洗格子刷灶台,刨老南瓜洗大白菜准备油盐酱醋配料。一年的辛苦,终于要收获了。帮忙是平日隔壁最亲近的五大姑六大姨,开心得脸上抹满了蜜。
注满水的大铁锅里开着。猪感到了终期,凄厉地尖叫,长叹一口气,撕裂着主妇的心和肺。
嗷叫声转弯低沉嘶哑了,滚水舀出锅外,刨子噗噗地响。杀猪佬心狠手辣,在给猪开肠破肚分脊,一刀劈下,肉开骨裂。
主妇的忧容全换成了笑脸,给刚清洗干净的竹格子垫上鲜嫩的白菜叶。撒拌了少许苞谷面的老南瓜丝弄进格子,跺到锅上。
有人进入厨房,手提红鲜,刚才挑开水出去的老爷们。这回不是为了水,送一块肉来,大大的,不看就知道,从猪软窝里割下来的,半瘦半肥,五花肉。主妇接过来,滚热、洁净、肥白,还在微微颤抖,很沉,细听犹在呻吟。主妇挤一下鼻子脸,百感交集状。
手脚麻利的五大姑六大姨赶紧接了,将肉放在案板上,比画比画,三下五除二切了,一块块一摞摞,方方正正。
以细碎苞谷面为主的拌合料早备好了,盐,花椒粉,辣椒粉,柞广椒面,自制的胡豆瓣酱,细仔拌和。生姜、大蒜、鲜葱和味精之类味重的东西是绝对不能要的,突出的就是鲜肉的本味。抖一抖,不黏,正合适。
肉片上到竹制格子里,皮在上腹在下,一片片摆好,满满的一层,没有缝隙。格子一层层跺在锅里了,如高楼,数一数,五层。打开灶门,撩几把,添两块劈柴,尽可能加大火力。
水在锅底下翻滚咆哮,腾腾大气穿过一层层老南瓜丝和鲜肉片奔向格子的顶端,欲喷薄而出,实在挤不过去的再回过头来往下钻。
格子上大气了。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主妇上下来回倒腾,一次次,直到从格子里射出喷喷的香,里面的蒸菜和肉透熟。
香飘十里,蹿过来了,逗得客人们按捺不住,一张张脸侧向厨里,垂涎欲滴,只恨时间过得太慢。
终是时机到了,一只格子出锅,架到了八仙桌上。一声吆喝,主人请声未了,客人们君子顿为勇士,奋力争先踊向餐桌。谗虫泛起,搅扰得我哪甘落后,奋力挤进了大人的队伍。
操起竹筷,夹了肉,剜了蒸菜投入小嘴里。好烫!嘴里发出咝咝声响。
鲜,热,甜,香,嫩,糯……
爽!绝非一般粉蒸肉同日而语。其味道之鲜美难以言状,只恨自己学识浅薄,语言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