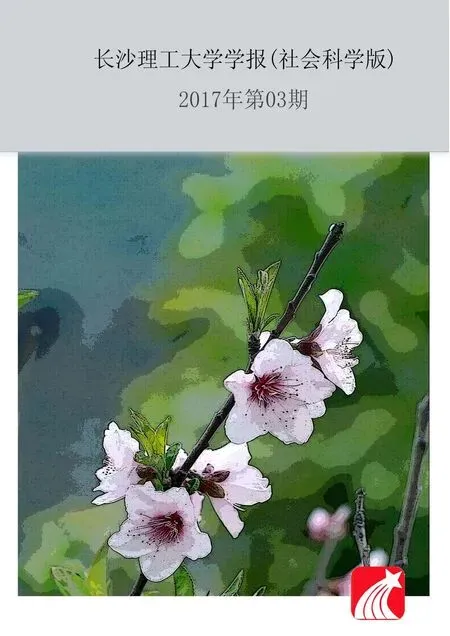陈克华:一个“败德”的身体测绘学家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陈克华:一个“败德”的身体测绘学家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陈克华以惊世骇俗的身体表达成为华语诗界的标志性诗人。身体美学是陈克华诗写的出发点和最终旨归。他对肉体尤其是男体做了全方位的测绘,试图打破符号和意义给身体设定的陷阱,通过肉身化呈现自我主体。他以“败德者”的姿态,来审视自我,突破性别阈限,拆解异性恋霸权,释放自己的生命激情,倔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在本质意义上讲,他的诗歌创作是其纳西色斯情结的外化。陈克华有待于以身体的“在场”为基点,从“个体化生存”拓向“社会化”生存,在更大的场域中建构起诗人的自我形象。
陈克华;身体美学;纳西色斯情结;异性恋霸权;同性恋
陈克华以惊世骇俗的身体表达成为华语诗界的标志性诗人。之所以用“惊世骇俗”一词,并不仅仅意指陈克华的诗写行动本身具有行为艺术的性质,而更多指向陈克华诗歌接受过程中的震撼效果。他的诗写具有很强的行动性和颠覆性,与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诸如“灵与肉”“男与女”“异性恋与同性恋”等的问题产生了强烈抵牾,这种强大的张力构成了“惊世骇俗”的文学场景。陈克华通过诗歌,对肉身尤其是男体进行了全方位测绘。可以说,身体美学是陈克华诗写的出发点,也是最终旨归。
陈克华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自我发现、自我认同意识。他的自我认识与发现,虽然也通过社会化存在来完成,但更重要的关注点在于对自我身体的生理、欲望、情感的深挖,通过身体建构来达到对自我的确认,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1]因此,他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具有极其浓厚的那西色斯情结。他一天天在自己的诗歌的倒影中凝视自己肉体,通过身体镜像释放自己的灵魂,甚至与诗歌融为一体。陈克华的诗歌正是他的灵魂之河滋养的一朵摇曳生姿的那西色斯之花。
一、那西色斯情结:镜像中的自我审视
早在1985年,陈克华有一首广泛流传的诗《我与我的那西色斯》:
最近,
逐渐体力不继。我发觉不能够
再只用我这一对枯干下垂
塌陷的乳房
哺育自己。
“今天该理发了吧?”我问
一种对美的质疑
陡然暴长,如一株造型凶恶的盆景
久久我与镜子对峙
蓄起的鬓角钉挂在墙上,偶尔
可以窥见一种命运的小丑脸谱
正偷偷对我仔细端详
“也爱过了吧?”
我说。是的,而且
早就疲倦已极了——我走过去
强吻我自己
在每一面镜子上留下指纹
和唇印,一如我怪异的签名
然而我是如此丰富地恋着(你自己看罢)
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存活着的
有无数种延伸与歧义
的可能——然而
我只选择了你这一种
“而且连这选择都可能是虚妄的。”我想
因为事实上
别无选择。
在这首诗里,“我”既是审视主体,又是审视客体,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他者”。“自我”构成了一种虚妄乃至别无选择的精神镜像。这首诗歌所呈现的那西色斯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陈克华诗写的一种原动力。
作为一位同志诗人,找寻自己精神镜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父亲”,父子两代之间的肉身延续与隔断、精神血脉的流淌与阻滞,是重要问题。陈克华的《父亲节想到父亲》里的“父亲”是又一个精神镜像。当“我”面对“父亲”的时候,忽然发现父子都是“内在冷漠”,互相感到不可交流的“惶恐”;然而,随着“父亲”的苍老,随着“我”的长大,随着“我”找到爱的时候,对于“爱”的追求和理解促使父子之间达成了灵魂层面的“和解”。
屈原是陈克华另外一个精神共振的那西色斯人格镜像。在《河——端午写给屈原》里写道:
在消失你的罗盘上
那曾经以你命名的方向
终究成为我宿命的漂移
无法觉察的漂移呵
当整个时代正漂离你
在无岸之河,我却缓缓朝你靠近——
……整个时代也正逐渐漂离我,这一切
仿佛都只是旗的飘动
而又仿佛都只是时间之风
正是由于陈克华将屈原作为自己的精神镜像,他才真正理解在历史的河流里反复漂洗的屈原的精神境遇:“身体是甜的,河水是苦的”“权力是甜的,诗词歌赋却是苦的”。被时代漂离驱逐的共同命运,使我“缓缓朝你靠近”。一位伟大的同志诗人屈原,成为陈克华的精神镜像,具有情感认同和诗人角色认同的双重意义。
那么,是谁塑造了“镜像法则”?是谁规定了合法的“欲望法则”?陈克华的《寻人启事》里有一句“你先替我穿上欲望/再给我一面镜子”,动作的实施主体“你”很明显是公共规则的拟人化。随着“身体就开始发育”,公共规则给定的欲望法则不再合身,也就“深深厌恶着镜子”,但是,无力彻底打破镜子的束缚,无法摆脱给定的欲望的束缚,只好不断增加补丁,以进一步限制身体。悲剧由此而生。他在一首散文诗《藏镜人》里写道,在这个“原是雌雄同体然而异体受精的洪荒时代”,他的欲望里含蕴着宇宙奥义,大脑与肉身谈判最终破裂。镜中的局限使肉体的生命欲望像火山引爆,从而对“镜像法则”和“欲望法则”提出激烈示威、抗议。
因此,陈克华的身体镜像表现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是在对自我身体镜像的建构中,折射自我的灵魂律动,以此实现自我确认;二是对营构身体镜像的外在律令进行拆解。
二、自我主体的“肉身化”呈现
在中国历史上素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训,反对躯体,敌视情感,视肉体为仇寇。一部人类史成了理性与感性的斗争史、灵与肉的冲突史。劳伦斯说:
躯体本身很洁净,只有受困牢笼的头脑
充满污泥。它不住地污染着
五脏六腑、睾丸和子宫,把它们腐蚀得
只剩一具空壳
矫揉造作、十足邪恶、连野兽
也觉得相形见绌
肉体并不邪恶,关键是要解放头脑,洗却灵魂的污垢。周作人说:“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作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得很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把自身焚化了才对。既然要生存在世间,对于这个肉体,当然不能不先是认可,此外关于这肉体的现象与需要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拒绝。”[2]
在历史上,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面临着同样的缺失命运,甚至男体更是忌讳。埃莱娜·西苏说:“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3](P188)人的机器化进程是越来越严峻的,正像18世纪的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中所说,人的躯体已成机器,机器使人的躯体摆脱了自然的奴役,然后机器又开始奴役人,人已陷入机器的重重包围中,理性化和机械化压制着躯体本能的冲动、生命的燃烧。关于现代科技对人的身体和肉欲的压制与异化,陈克华在诗中多有体现。《类固醇物语》写道,借助类固醇针剂的手段,人虽然顿时成为肌肉膨胀的“猛男”,但是带来的“鸡鸡委顿”的代价,着实是一个有力的反讽。当一座城市也打上类固醇,建筑物也都阳具般纷纷勃起,最终会在地球的皮肤上留下“永远美白不了的斑块”。《天线》一诗表达了高科技的现代都市语境下肉身的虚幻感。陈克华有一首理性较强的《头颅》,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状写头颅内在的宇宙意识,揭示了现代高科技时代“电脑”的诞生使“肉体”正式消失,造成了肉体的异化。
在陈克华的笔下,身体不再充当知识和意义的占位符和替代物,因为意指的身体为身体设置了符号和意义的陷阱。哲学的、神学的、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身体”将“肉身”紧紧裹住,“身体”成为“去肉身化”的身体,而脱开了身体内部的所有感官、知觉、直觉、欲望、记忆、观念、意识等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他勇敢地将自己的肉体放在十字架上,如《肉体十字架》:
于是我舍弃天地和屋宇,衣服如兄弟妻子
只定居在自己的肉身里
日夜用贺尔蒙洗濯昏昧的大脑和性器
造访小小隔绝的胰岛
生养一些体毛和菜花
并殷勤练习如何膨胀大胸肌和血管丛
早晨趁市嚣的瘴疠尚未随风造访
我便打开幽门喷门肛门卤门命门
浇灌逐日成熟复将委顿的松果体
涌泉穴有泉涌
便日日是好日
便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皆是人间好时节
地,徜徉在我自身的肉体宇宙里
春有青春而冬有老病地
把一切闲事
挂在心头。
究竟是意义的身体,还是肉身的身体?在道与肉身,道与器的孰先孰后的二元对立思维中,陈克华选择了后者,他以肉身触摸思想,以感觉触摸理性,以身体的能指为出发点抵达身体的所指。身体是一座活的庙宇。身体通过“感觉”的自在性而获得肉身意义。不是从意义出发,而是从身体的感觉生发出意义,拆解符号学、症状学、神话学、现象学对身体的劫持,才能分享身体的存在,在身体的感觉中敞亮生命的意义。《我对肉体感到好奇》以大量笔墨涉及到精液、唾液、痰液等各种体液,“真理原是如此猥亵而粗暴致死”的极端诗句,夸张地表达了作为欲望的身体释放生命的意义。
身体“body”一词,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哲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他的《行为的结构》《知觉的优越性》《知觉现象学》等著作中都涉及到“身体”一词。在他看来,身体与主体(body—subject)可以互为取代,“我”即我的“身体”,并认为,“身体”并非只是一个外在的认识对象,它具有经历知觉的能力,可使万物在躯体感知中彰显出潜藏的奥秘,进而在主客体的感知中确立躯体所属的人的主体性。所以说,“主体”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带有肉身体温的所有生命感觉形成的统觉的释放的凝结。作为对象性object的身体与作为主体性subject的身体,并没有决然的界限。陈克华的《我的肛门主体性》开门见山:“一夜之间,我的肛门,就突然有了他的主体性。”肛门不再只是一般的生理器官,而是明确发声 “拥有绝对的主体性”:
他可以随时拥有全身上下独一无二的
内外痔或
梅毒淋病菜花强烈主张
一切的“经过”之主体性
只要带来更强烈的抽搐、颤抖、撑裂、爽、还要更爽——
虽然,我们的肛门只是个洞
虽然,他主张拥有一切主体性
他调动出所有的性体验,渲染肛门作为性器官的主体性需求。有的时候,陈克华的身体描写,还融入了诗人的形而上的生命思考。如《植入》一诗,可谓是一部关于肉身的简史。从植入子宫开始诞生与发育,一直到出生、成长,性器的植入(青春期的欲望享乐)、到皱纹、记忆、倦怠的植入,再到一切的植入开始松脱、瓦解、剥落,人的一生在时间的缓慢进程中,消耗殆尽。这首诗呈现了肉身主体性从建构到耗散的整个过程。
在越来越高度集约化的社会结构中,千差万别的个体化身体都被一个共通的“意义”,整合到公共话语逻辑,从而使每个人都处于“身体政治”的规训之下。社会化的规训机制就是政治技艺,因政治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规训,要想治理得好,就要泯灭身体个体之间的差异,按照集约化的类别或地位高下之分,将异质的因素按相异的程度逐级剥离出去。每一个身体都有所属的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陷于一个律法空间,每一个身体规定了专有管辖权。陈克华确然走在与时代逆行的方向。他将个体化的身体进行了全方位呈现,让我们逼视久违了的陌生而异己的身体,呈现出被切割、被标记、被规定的身体的受难图景。他在《包皮》里质问身份政治:“我必须割舍我的包皮/而换取高贵族群的身份证明吗?”他有一组《狂人日记》,集中写出了人的肉身的异化:或写人肉相食的悲剧;或写为逃避文明规约而主体性隐遁的肉体;或写人类与苍蝇基因的结合异变;或写垃圾制造者马桶人;或写“任意统计我预测我杂交我复制我”的豆荚人的悲剧;或写幻想中在大自然里播撒生命而现实中却“逐日腐败的肉躯”的植物人;或写镜中的局限使肉体的生命欲望像火山引爆意义产生激烈示威、抗议。《蛇人》揭示人的异化更深刻:“让肉体化约再化约,成为概念”的蛇人,“为了以腹行走,他为自己的肉体设计出如此简单的几何。不可思议地让生命臣服如此单纯的定律”,“他弧形优美的身形,也将以无比的愚蠢,逼近死亡。”《透明人》则是另外一种异化,“他们透明化的身躯你无从确认器官的确实部位。包括翅膀、唇、髭、指甲、关节、鸡鸡。”
陈克华在诗中就像戳穿皇帝的新装的那个孩子,肆无忌惮地调侃着伪善的政治规训和道德规训。《肌肉颂》将身体拆解为“肱二头肌”“比目鱼肌”“肱四头肌”“大胸肌”“阴道收缩肌”“竖毛肌”“肛门括约肌”“腹直肌”“提睾肌”“吻肌”等二十种肌肉,每一种肌肉下拼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诸如“万岁,万岁,万万岁”“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祖国的山河更是多么壮丽”“爱国、爱民、爱党”“胜利第一。情势一片大好。”“服从、服从,还是服从。”等,同时又夹杂了私密话语,诸如“你爱我吗?”“快乐吗?很美满”,“正确的性爱姿势”“真他妈的虚无”。后现代拼贴的杂耍和戏谑风格,让我们从严酷的政治话语的缝隙里窥视到一丝私密的个人话语。他的组诗《不道德标准》乃是向着所谓的道德重整委员会用力掷出的第一块巨石。其中《人人都爱马赛克》批判了无所不在的压制人性、实现道德催眠的“封建力量”。《我只好脱、脱、脱》,以脱的方式解除对“裸体”的忌讳,并以此讽刺贪官、污吏、奸商、刁民。《如果我是封建小阳具,那你就是礼教小淫娃》,直击封建礼教的性爱观念。他们假宗教慈善之名,推行精神专制,精神独裁。《第一块石头》对“道德重整委员会”的讽刺更是辛辣:“于是你们一干人等人多势众的道德重整委员会的委员们,唱完了道德重整之歌,做完道德重整的处女膜整形,抹上了道德重整的KV润滑膏,喷完了道德重整之杀精剂,戴上了道德重整的保险套,叫完了嗯啊嗯唉道德重整之床,流了满床道德重整的淫水,吞下了道德重整的精液,做完了道德重整之爱,洗净了你道德重整的屁眼,穿上了道德重整之内裤,念完了道德重整阿弥陀佛,上完了道德重整的耶稣基督教堂”,伪善面孔昭然天下!
陈克华不仅蔑视伪善的道德对身体的戕害,而且对既定的性别霸权进行了批判。主流视野中的“历史”(history)是男人代表的历史,男性视角、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而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被拒斥,被抹去,被忽略,被视为特殊性。历史的话语主体是男性,女性只能被规定,女性的声音被男性盗走了,整个历史是菲逻各斯中心论话语(Phallaogocentric),现代社会是阳具中心(Phallaocentric)社会和词语中心(logocentric)社会的交融。陈克华不惜以大量猥亵风格的语词,对公共话语进行汪洋恣肆的撞击!《闭上你的阴唇》一诗以《恶之花》的风格嘲讽那些已经烂熟了的公共规则:“性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颓废的屌与神经错乱的屄”,戳穿了谎言:“当正义之师策马转进围城/这土地已被谎言包裹得无比光荣”。《婚礼留言》以第一人称“新娘”的口吻给对方留言,批判了男女二元对立的霸权婚姻结构。男方赠送一只指环,就作为交换而拥有了女方的身体。在一系列句子中,诸如:“你合法使用我的屄的权利”,“你将喂食我以中餐西餐日本料理……/还有你的阴茎和精液/你的脚趾和体毛,/你的性病和菜花”,“你”(新郎)成为句子的主格,而“我”(新娘)则是宾格。在《请让我流血——爱丽丝梦游阴道奇遇记》里,陈克华则为女性代言:“我厌倦了继续做一名光明的处女”,大声疾呼“让我流血流血”,尽情释放肉体的感官享乐,批判了世界的伪善。由于世界在抑制生命,“阴道里最深处神秘的光,竟照不亮生命终极的秘密”,所以,“我”才“渴望流血”,“快乐地流血”“放心地流血”“虚无地流血”“趋于极乐地流血”,渴望失去完整性,渴望尖锐而割伤的阳具闯入摩擦的光。
陈克华正面表述过他的猥亵诗学:“猥亵原只是一种手段,无奈有人对其他视而不见。因为表面上的猥亵,唤醒的是他们自身人格里更深一层的猥亵,那潜伏但永远无法享用的快感。于是他们整齐方正的人格被深深激怒了——他们习于安稳的性格不容任何轻佻的撼动。”[4](P13)陈克华的意义正在于此。
三、异性恋霸权的拆解
通过身体描写,陈克华以“败德者”的姿态,勇猛地打破性别阈限,站在异性恋霸权的对面,倔强地表达着自己的立场。
由于被异性霸权的“阳光”压制太久,“我们在黑暗中的秘密之花/终于在集体催眠出的圣洁光环里/集满了足够登陆天堂的赎罪券”(《我们已在黑暗之中进化太久……》),在多数人的集体面前,“我们就是权力”的呼声十分微弱。在异性恋霸权的压制下,陈克华愤激地说:
我终于也移植了一个屄。
拥有贮制乳汁的双乳
每月一次
倒立精神的子宫,倾泻灵魂的月经
本能的腺体肥大
爱藏匿阴毛丛中的深穴
亚当夏娃不过是洞口霎时掠过的受惊吓的小兔
——《我终于治愈了这世界的异性恋道德偏执热》
他以“我是谁我不清楚”的代价,试图消灭性别鸿沟,解构异性恋霸权。在《肌肉妹与胡须哥——侧写名骏与Funky》《女人的隐形阳具(哑铃)》《男人的阴道(庆典)》等诗作中,他穿越了性别的阈限,对性别规定实行了僭越:“女人不过是一种伪装”,哑铃被视为女人的“隐形的、不带体毛血管装饰的阳具”。而男人以“肛门”为阴道,绽开的、松弛的、被敲打的、政治正确的、骨盆宽大的、些微伤风的、虚脱感里的、彻底失望的……种种男人的身体,享受着女人般的快感。“在A片流行的年代/我们都记得一名拥有三个屄的女人/她的三个屄分别被称作/现象 本质 /和屌”(《在A片流行的年代》),呈现了性别的“非本质化”倾向。《我是淫荡的》戏仿杨唤的诗作《我是忙碌的》,以肉欲之欢颠覆了杨唤诗歌中严肃庄重的理性。《一万名善男子与一名善男子》《住在我身体的50个情人》等诗作,彻底颠覆了道德重整之家。
他在诗作中,反复表达同性经验。《不道德标本》以五颜六色的性爱色彩,释放出“先天缺少道德基因”的肉体体验。尤其是那首惊世骇俗的《肛交之必要》,大胆颠覆传统的性爱方式,宣泄同性恋体验,公开宣称自己是“败德者”,“我们在爱欲的花朵开放间舞踊/肢体柔熟地舒卷并感觉自己是全新的品种”。陈克华特别强调“感觉”的丰富性:“抽搐”“感觉”“狂喜”“疼痛”。但是,背德者逐渐脱离了这支叛逆的队伍,投入到多数人的队伍,“肉体的欢乐已被摒弃”,多数者的暴力和多数者的集体逻辑的暴力,摧毁了败德者的独立与尊严。所以,诗歌不止一次地说:“肛门其实永远只是虚掩……”。“肛交”,在基督教中,往往被视为“兽交”。因为,只有人类才是唯一面对面性交的动物。教会只认可一种所谓自然的交配方式,也就是托马斯·桑切斯神父(Thomas Sanchez)在1602年所叮嘱的姿势:“女人仰躺在下,男人俯身其上,将精液射入专司生殖的器官”[5] (P192),而其余姿势均被看作禽兽行为,因为直到17世纪,教会视野中的性交实质意义在于生育,交媾的快乐只是附属的东西,单纯的肉欲之欢是罪恶的。“不可反面性交”,长期成为人类的规训。伊斯兰地狱的第一层即是肛交犯,而女同性恋者则受到以石块击毙的惩处。在现实生活中,肛门往往被视为通往地狱之门,但越是压抑,越激发起艺术家诗人的灵感,成为一种仪式、节庆。约翰·彼得在著作《管口的特性》里写道:“屁眼就是如此重要,屁眼存在,故我们存在。”[6](P116-117)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以“玫瑰花瓣”诗意地描绘肛门。愕司多·德·波里萼(Eustorg de Beaulieu)以《屁股》为题,盛赞女人的屁股。拉伯雷(Rabelais)被誉为“粪便文学大师”。彼得觉尼(Pierre Janet)还主编了《粪便文学丛书》。对于同性肛交,几乎没有例外地认为是变态和罪恶行为,是道德沦丧者的表现。法国的萨德侯爵所著小说《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即是一个极端的集成体。克索斯基(P.Klossowski)评论道:“萨德作品中所描述的肛交行为,是所有堕落行为的主要表征。”[6](P151)安龙与凯福(J.-P. Aron et R. KemPf)也说道:“总之,肛交者纯粹就是野兽的转世。”[6](P151)而陈克华的诗歌赋予了肛门一种哲学的主体性内容,本来作为生理器官肛门“拥有绝对的主体性”(《我的肛门主体性》),是拥有巨大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感性的快乐主体。
同性之爱崇尚“快乐原则”,这种生命的快乐甚至具有超越生死的力量。熊熊燃烧的《肉身之焰》虽是发自灵魂深穴的欲望流泄,但生命之火最终还是借助肉身而点燃。《即使在情人的怀里》写道:
天已经显老而海水悄悄干了
钻石腐烂
我仍执意躺进你的怀里
我执意我还是一个清醒完整的我
我执意孤独必须如恒星照耀
即使,悲哀已达极限
自银河泛滥……
这种爱欲超越了时空而抵达永恒,让我们想起了古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停车做爱枫林晚》:“我们于是停车做爱/做到直到身体里的血也都流尽/只剩下黑……”“我们要在彼此身体里/找到黄昏。”《蜷伏》中,将爱人比喻为手臂围成的阳光海湾,脸贴着海面,感受到“你体内最细致的动荡/或是海底火山浅浅地睁眼转眸/或是一株失根海草的无声行吟//我的蜷伏模拟着死/漂流在你阳光璀璨云潮涌动的热带/是的,只有当模拟着死//我才分明察觉//我正爱着。”《半生之愿》审视后半生的身体:“松弛,柔软,渴睡、警醒,满足,不满足,虚玄,实际,欲念强大,心思缜密,感官化,心灵化,狂暴,脆弱,痛快,绝望,爽而又爽,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对生命欲念的顽强与执着。”《重蹈》将爱情与身体剥离开来,试图证明性爱高潮至上,“我如何向你说明我已不相信爱情”。《写给那没有救你的朋友》,送给公开同志身份的福柯,逼视福柯虐恋的快乐带来的艾滋死亡。
虽然他在《保险套之歌》里说“灵肉根本毫不相干的两码子事,如同/鸡兔同笼/水火同源/屌屄同口”,但陈克华其实还是主张灵肉统一论的,他的《孤独的理由》即表达作为联结两个肉体的媒介——灵魂的缺失带来的孤独。他有很沉痛的一首《蝴蝶恋》,前引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的句子:“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这首诗可谓抒写夏丏尊与弘一法师超越生死的一曲恋歌。“吾爱汝心/吾更怜汝色/以是因缘,情愿/历/千千万万/劫难,一如蝴蝶/迷途于花的暴风雨。”他苦苦执念于“终究一生不过是场漫长的辞别”,终究无法“舍下了情,舍下了痴,舍下了悲,舍下了欣”。《青春猝击——写给杜二》《像你这样的朋友——写给梁弘志》《在高处——伍国柱》中,陈克华与朋友们之间的共鸣,超越了肉欲,面对共同的话题,如青春、性别、记忆、寂寞、生死等,更是体现了情感和灵魂上的惺惺相惜。他于2012年12月出版的诗集《当我们的爱还没有名字》中描写的对“爱情”和“肉体”的欲望之爱,已经走出异性恋话语霸权下的尖锐紧张性,甚至拳交和捆绑之交等虐恋形式的爱欲,也不再是嚣张与紧张,而是真正进入了自我内心世界的探究。此时的陈克华,已臻于洗尽铅华之境。典型之作是《男男爱谛》一诗:
终于,我来到长得和我一样的男孩
的身边并肩躺下
如青鸟遗落巢里的两根羽毛
那般自然 那般华美
那般理所当然的对称
且那般洋溢着幸福的暗喻——
是的,一个和我一般温暖
心如处子身如脱兔的男孩
——我们相互爱着
超越生殖 没有婚礼
也不会有花朵的盟约和节庆的祝福
……
我们或将在一下秒改变心意
但在仅存的此刻当下
我们斥退了异性恋热症的嚣张喧嚷
清明如菩萨
经历十地阿僧祗劫里誓不成佛
要以俱足的无根六识七识八识难得人身
证得佛陀在苦集灭道
之外不忍宣说的男孩与男孩之间的
爱谛
但是,同性爱依然是弱势群体,依旧笼罩在异性恋霸权的主宰下。诗集《当我们的爱还没有名字》,书名便清晰地揭示了同性爱的尴尬处境。陈克华有一首《失足鸟》,引用《圣经》语录“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表达的恰恰是人类在床笫之间流浪、漂游在众多挺立的性器丛间,而灵魂却得不到栖息的命运。由于叛逆了“不可反面性交”的告诫,人就像失足鸟被罚以失去双足终身飞翔。这种命运令我们想起了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阿飞正传》中的台词:“这个世界有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飞啊飞,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陈克华的《失足鸟》即是同性之爱漂浪天涯的象征性写照。
四、结语
陈克华在《骑鲸少年》时期,初现 “那西色斯情结”,开始以内视角关注自我,以肉身承载情感和思考;《欠砍头诗》凸显背德者的自我角色意识,显示出自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尖锐紧张关系;《善男子》时期则逐渐走向自我角色的张扬与积极肯定;《BODY身体诗》聚焦于男性身体意象,开掘了一口深井。他从“西色斯情结”出发,最终完成的是“那西色斯情结”的身体外化。而一个人的成熟,必须走出“那西色斯情结”的阈限,达成完整的自我。我们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读到关于社会公众事件的立场表达,但是陈克华给我们的感觉仍然是未能从“那西色斯情结”里面走出来。
A·马塞勒曾给自我下过定义:“一个完整的个人。”[7](P98)完整的自我,在西方现象学中,分为三部分:即“内在自我”“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三者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最良好的状态是三者协调互动。“内在自我”是“与孤独中的内在体验相伴的心理状态”[7](P98),它是维护个体自我的根本。但人类渴望完整存在是人之本能,个体必须走出内在自我的自闭情境,寻求与人际自我、社会自我的交合点,孤独才会消失。作为一位同志诗人,自我角色的实现面临的压力尤其艰巨,他所面临的生存空间也许会更开阔而艰辛。
在《笑忘录》中,米兰·昆德拉主张应学会谈论自己肉身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尼采借助于查拉图斯特拉的诗成功地将肉身重置于哲学的中心。他的七弦歌唱的是:我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己,造化的肉身造灵魂仅用它作为自己意志的一双手。“肉身”问题是每个人的核心问题。“肉身”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归宿。但是,从出发到归宿,这之间的长长的抛物线或曲线,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每个人既是“个体化生存”,也是“社会化”生存。身体的“在场”,是诗歌永葆生命的源泉。我在想:走出“那西色斯情结”的陈克华,更大场域中的陈克华,又会是怎样的?
[1][法]马克·勒伯.身体意象[M].汤皇珍,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2]周作人.读《欲海回狂》雨天的书[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陈克华.猥亵之必要(代序)[A]// 陈克华.欠砍头诗[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5][法]让-吕克·亨尼希.害羞的屁股——有关臀部的历史[M].管筱明,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6]Jean Gordin, Olivier Marty.屁眼文化(Historires du Derriere) [M]. 林雅芬,译.台北:八方出版社,2005.
[7][美] A·马塞勒,等,主编.文化与自我[M].任鹰,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Chen Kehua: A "Crusade" Body Surveyor
ZHAOSi-yun
(SchoolofLiterature,ZhejiangUniversityofMediaandCommunications,Hangzhou,Zhejiang310018,China)
Chen Kehua has become a symbolic Poet in Chinese Poetry for his shock-the world body expression. Body aesthetics is his starting point as well as ultimate goal. He has made all-around measurements on human body, especially on male body, trying to break the trap on body set by symbols and meaning, so as to show the self-subject with flesh and blood. With an attitude of a "defeating virtue" practitioner, he observes himself, breaks through gender threshold, dismantles heterosexual hegemony, releases his own life passion, so as to stubbornly expresse his own standpoint. In the essential sense, his poetic creation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his Narcissus complex. Chen Kehua has expected to establish poets' self-image in a larger scale, based on "presence" and from "individual survival" to "social survival".
Chen Kehua; body aesthetics; Narcissus complex; heterosexual hegemony; homosexuality
2017-04-10
赵思运(1967-),男,山东郓城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诗传播研究。
I207.25
A
1672-934X(2017)03-0075-09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