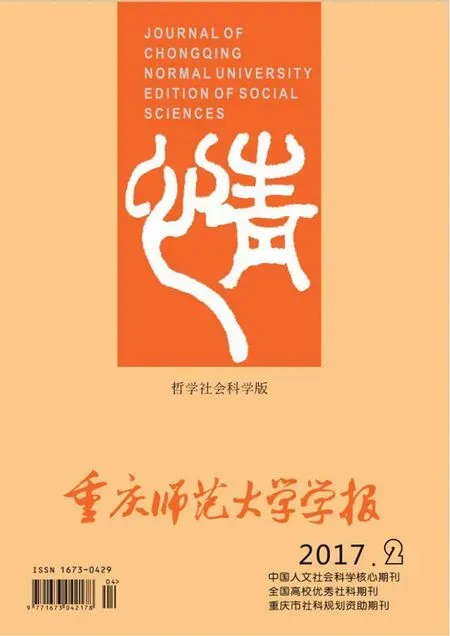“情自然”与“性无邪”
——汪曾祺新时期以来小说的解读一种
许 心 宏
(安徽财经大学 中文系,安徽 蚌埠 230030)
“情自然”与“性无邪”
——汪曾祺新时期以来小说的解读一种
许 心 宏
(安徽财经大学 中文系,安徽 蚌埠 230030)
汪曾祺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其文本中关涉性的叙事越发引人注目。大家小言的以性入文可谓“意在性外”,“情自然”与“性无邪”成为文化复归的切入口与着力点。此类小说文本坚守人欲的自然性与合情性,在谈性言情的逆向叙事中,反驳了意识形态与封建伦理纲常对日常人欲的碾压,澄明与证明了人性的自然与存在的本真。
性;伦理;意识形态;自然空间;叙事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文本中的僧人尘恋、姑侄孽缘、师生乱伦、婚姻出轨等叙事比较抢眼,一时“春色满园关不住”。前承于“十七年”及“文革十年”的“干净”文本而言,作者为何在逆向叙事中大肆谈性言情呢?作者晚年曾对自己的艺术人生理想予以了界定:“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301显然,汪老的自证有其苦心,即在风俗化、诗化的人欲叙事中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以“情自然”与“性无邪”为人性复归、文化复归的切入口与着力点,澄明与证明人欲的自然与自在。
一、根植自然空间的“情自然”
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的空间诗学上,汪曾祺《大淖纪事》中的“大淖”、《受戒》中的荸荠庵、芦苇丛等自然意象空间,使小说世界的男女生理欲望与自然空间相契无间。作者认为“气氛即人物”[2]166,而“气氛”则相切于特定的人、事与自然空间之中。如果说“感情抒发的艺术性,常常是感情的形象化”[3]83,那么“景为人设”的自然空间则为文化气氛的磁场空间,潜隐着自然空间的归真意境。定格于荸荠庵、大淖、芦苇荡等自然空间,意在构建人性的自然、自在与自由的诗学空间。放眼当代文学史,诸如刘恒《伏羲伏羲》的“庄稼地”、莫言《红高粱》的“高粱地”、张炜的“野地”、雪漠的“沙湾地”等,空间的自然性表征着“食色,性也”的自然属性。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源于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急遽转型,以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内中知识分子的性焦渴、压抑、变态等描写,潜隐着对城市工商业文化的敌意与反抗;再至新世纪的邱华栋、卫慧等“都市文学”叙事中,现代工商业社会的都市成了情感的挤压地,情感的放逐地。
自然是人类诞生的母体,是人类的生存家园。据此,新时期以来的《受戒》与《大淖记事》,内中自然空间的敞开性与目的意向性设定,凸显了人欲的野性诗学特征,意在反向突破道德语码与意识形态语码的羁绊。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等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生存苦闷与悲剧命运,如出一辙皆发生在封建社会大家庭中,而时值“五四”反封建、反传统的宏大历史语境中,旧时的封建宅院呈现出压抑、沉闷、死亡的空间诗学特征。在文学流派上,汪曾祺的创作风格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一脉相承,但与鲁迅的社会批判、文化启蒙、国民劣根性批判相比,则淡化了“启蒙”、“批判”特征。相反,作者凭依回忆的温暖与记忆的想象,重构的是自然、自由、隐逸、恬淡的高邮世界。作为“寻根文学”先期力作,《大淖纪事》之“大淖”虽未绝于“市声”,但远隔了俗世的纷杂喧嚣,内中的生活、风俗、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等,皆与“外面”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然,在结构性空间诗学内置中,指向了“桃花源”另一世界的情境营造与审美发力。但是,大淖世界又并非理想化的“王道乐土”,内中不乏“外来者”的侵凌践踏,典型的就是团总棒打鸳鸯,肆意欺侮巧云与暴打小锡匠。不过,在否定性的结构反转叙事中,乡野情侣最终度尽劫波终成眷属。只是,作者在揭示乡土世界的创伤性体验时,淡化的是血与泪的苦楚,驻守的则是乡间那份静淡的本真与素朴,特别是在退守性叙事策略中,小说题旨敲击了历史的酷烈及其对人性的戕害。但是,在畸形的历史与本然的人性碰撞中,证明的倒也是人性本然的素朴。
作者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应当发掘人身上的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4]76据此,《受戒》中的明海与其说受戒,不如说是破戒,戒与破的悖论看似难解,则实为常态欲求的自然表达,原因不外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纵观人类文化史,僧尼偷情自毁三观的艳史、野史于史不绝,但多流于猎奇、惊艳与低俗。《受戒》作为新时期小说力作,“戒”之美学效果“意在言外”,即在反抗性叙事中,题旨突破了“文革”以来的极左思想坚冰。当然,基于叙事策略的以退为进,作者将反叛化的故事情节镶嵌于大淖的乡土民俗中,策略性避开了病态意识形态的批驳与发难。基于审美的过滤与记忆的重组,乡土变得恬静幽美,继而激活了一己文化梦寻的历史性复活书写,这诚如小说结尾的附注所言,即写“四十一年前的一个梦”。当然,就“受戒”谈“受戒”终为隔靴搔痒的文本解释学,因为人总处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文化语境中,而特定历史的波诡云谲,窒息的是人性的自然与自由。据此,《受戒》解构了崇高还原了世俗。在文学史向度上,若将其与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女儿国”中的故事情节相比较,则唐僧与西凉女王的“虐恋”赢得了世人的惋叹。但与之相异,《受戒》中男女主人公“破戒”后的圆梦,虽无崇高悲壮之美,但有着俗世的烟火气息与泥土的芬芳,作者审美祈向的努力,在于将单向度人的政治书写转到了人的多维度文化书写。
根植于特定文化氛围中的特定的人物,汪老认为“像小英子这种乡村女孩,她们感情的发育是非常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跟城市教育的女孩不同,她们比较单纯,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4]75。《大淖纪事》中,就乡下姑娘媳妇的裸浴而言,所谓的“贞操观念”不过是与其无关的“外面社会”的文化规范。非但如此,她们和男人一样,口无禁忌地说荤话;再就是“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4]76。一般说来,如此野性的狂放之举殊实少见,亦与中国文化传统规范相背离,但据作者交代,则是有其人有其事。那么何以理解这一别样的文化世界呢?原因在于她们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生存于“本来这样”而非“应该哪样”的世界中。在创作自评中,作者认为那是“诗无邪,诗经里的境界”。同样,在《薛大娘》、《窥浴》等小说文本中,惯常性出现了女性“丰乳肥臀”生理特征的局部勾勒,如是“地母”文化原型的重复叙事,隐喻了人欲的历史性回潮并为其合理性证明;此外,一则典型且集中的叙事现象,在于作者对女性“脚”的描写,此于创作而言恐是无意识的,但无意识中却形成了有意识的“恋脚癖”。不过,如此之癖非“三寸金莲”之畸嗜,且“不穿袜子”亦非无袜可穿,内中的文化隐喻体现在两个层面,表层指不包裹的脚是最自然的脚,深层指“她们的世界”充满着野性的自然与自由。
二、“性无邪”:男性成长仪式
中外文学史上,乱伦描写不计其数,然汪曾祺《窥浴》中的乱伦叙事却别有品第,因为在中国水墨画的故事写意中,《窥欲》表层写的是师生乱伦的故事,但在文化根柢上,实为男性成长仪式的过程书写。在小说情节推进中,作者阳光化处理了乱伦描写的主题,略去了噱头式、猎奇式、偷窥式的惊艳、压抑、苦闷、焦灼的心理描写,亦未涉及形而上学的“性”的玄思与辩解。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尊师重道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天、地、君、亲、师”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即为俗世化的伦理规范。体现在《窥浴》中,女声乐老师娴熟端庄,既为学生岑明的老师,那么她之于岑明,则是“一日为师,终身为母”。据此,姑且不论两者的年龄差异,但“师生恋”终有“乱伦”之虞。小说中的岑明才思敏捷但生性孤独,在同事眼中被视为异己而被排斥,于是窥浴便成了引发众怒的导火索。基于叙事者“介入性叙事”视角,乐团的演员、职员痛打岑明,乃因施暴者的心理自卑,即以肉体惩戒的方式打击岑明“心高气傲、落落寡言、自以为有文化、有修养的劲儿”。确实,岑明的窥视行为确有不端之嫌。但是,过于纠结“偷窥”的解读并无多大文化意义,因为俗世业已将其判定为君子不耻的行为。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阐释岑明窥浴的失范之举呢?
其实,在男性成长过程中,就未谙男女之事的少年而言,岑明的异性好奇心是自然现象,深符异性相吸的自然规律。但是,性的自然性与伦理性发生了冲突,即后者“窥浴”成为读书人有辱斯文的不雅行为。在儒家传统文化观念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乃读书人的基本修为与礼仪戒律。然在小说结构的突转中,虞芳老师厉声喝止了乐团演员、职员对岑明的踢打。从故事结构上来说,从喝止的前奏到以身安抚的高潮,后者实为故事情节既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之处理,我们不妨来看这段师生对话:
虞芳:“打坏了没有?有没有哪儿伤着?”
岑明:“没事。”
虞芳:“他们为什么打你?”
岑明:“岑明不语。”
虞芳:“你为什么要爬到那个地方去看女人洗澡?”
岑明:“岑明不语。”
虞芳:“有好看的么?”
岑明:“岑明摇摇头。”
虞芳:“她们身上有没有音乐?”
岑明:“岑明坚决地摇了摇头:‘没有!’”
虞芳:“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2]443
在构建性的男女对话描写中,作者模糊两者年龄差距的目的,意在淡化伦理禁忌的重压。在叙事文笔上,作者以水墨写意笔法,弱化了俗世伦理的成见;而声乐老师以女性的温婉悲慈,安抚与助推了一个男孩向男人的心理转变与性别确定,在文化深层结构上体现了作者对自然人性的深度开掘。基于人性温婉的审美凝神,小说的结尾净化了性的猥琐与肮脏,开掘了性本自然的深阔尺度。源于青春期的青涩与对异性的好奇,小说结尾写虞芳对岑明说“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显然,结尾的出乎意料,松绑了伦理枷锁的束缚,诗化了人之原欲的美好与温婉,留给了读者无尽的审美遐想。
与《窥浴》题旨一脉相承,《小孃孃》《钓鱼巷》《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亦写到乱伦主题。《小孃孃》中的姑侄出身诗书世家,在社会出身上,他们本是沐浴在伦理纲常的传统中,然自然的情感、欲望却又难以克制,此乃人之本性。两者的不伦之恋有着“亲情+恋情”的特征。若解除伦理道德的禁忌,谢淑媛寻求的是男性的庇护感与归宿感,谢普天则在“红袖添香夜读书”中佳期如梦,小说因之呈现“才子佳人”的古典模式。如此审美意境的生成,得益于于空间意象的匠心设置,因为《小孃孃》中的“来蜨园”类同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两者皆脱序于外在的俗世社会,审美理想超越于道德伦理的钳制。在空间结构诗学上,两者对应的皆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乌托邦世界”。但是,人欲的“合情”难脱俗世伦理的监视与规驯,因为“中国文化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最重”[5]17。循此说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伦理监禁,两者的“孽缘”无疑被打入了另类世界,于是主人公不得不逃离“来蜨园”,继而寻求“远方的诗意”。
纵观中国文学史,情与礼的矛盾一直存在,且一再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就《小孃孃》而言,女主人公宿命式地以死亡的形式结束了情与礼的苦楚挣扎。再如《钓鱼巷》中的年少书生程进,起初本不谙男女之事,然在保姆“沐浴”的朦胧性暗示中,不期与保姆有了媾和之事。内中的情感,书生既羞涩难言又心怀感念,既有救赎式的忏悔意识,又有旧梦重温的迷恋,体现在其后继的妓游玩中亦难忘保姆的面影,保姆俨然成为其“性启蒙”老师。就程进而言,难忘的是“第一次”,而“第一次”之要义深切,在于自那以后他成了“男人”。总体说来,汪氏文本中的师生、姑侄、主仆之间的非常态人欲叙事,被打入文化禁忌的“他者”序列实属正常。但是,在人之大欲的审美自由上,若是转换人物的时空关系,不过是人性、人情与人欲的自然诉求。人性不可逆,亦不可纵,前者指人的自然属性应顺应自然法则,后者指人之社会属性应归顺现实伦理规范,然在两者的矛盾冲突中,中外文学史上的大量“乱伦”叙写,撕裂与呈现的是人欲的无法满足、难以满足、何曾满足的诸多伤口。在本土性文化规范中,以伦理本位著称于世的乡土中国,强调的是“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不过,基于展示性叙事策略,作者追求的又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恬淡风格。
三、任“性”自然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女差异既体现在自然宇宙哲学上,也体现在社会功能与家庭角色定位上,诸如天∕地、阴∕阳、乾∕坤、主∕从、刚∕柔、尊∕卑、内∕外等。性别的自然差异对位于文化的伦理秩序等差,如是差异既是本土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式,又是集体无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体现,表征的是性别观念等差与伦理秩序。源于儒家伦理的俗世伦理规范,强化的是夫为妻纲、相夫教子、传宗接代的家庭角色功能,因而就男权文化规范的“三从四德”而言,在其后期八九十年作品中,《护秋》《薛大娘》《尴尬》中的女性率性自然的爱欲表达,解构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文化伦理秩序,颠覆性的解构思维,凸显了反传统、反秩序的叙事姿态,在诗性语言的性叙事中,呈现出顺着人性写的叙事逻辑,文本中的女性呈现出主体性特征。
在叙事策略上,作者写男女性事点到即止,并非沉溺其中而过于纠缠。《护秋》主要围绕农妇“出轨”之事展开,作者使用简笔手法,并未对偷情细节做过多的铺垫与渲染。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丈夫怯懦憨厚而妻子直率阳刚。当丈夫抓奸在床后,其妻并无愧疚心理。在节制性叙事中,小说将偷情描写如雾里看花,削减的是伦理话语的层层加码,内存女性主体性的审美解放意义,叙事风格呈现显示出“去中心”“去深度”的解构主义特征。在《薛大娘》小说文本中,丈夫在“房事上不大行。西医说他‘性功能不全’,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2]431。寥寥数笔,作者假借人言而反向证明的,则是世俗传统婚姻的生育功能与合法性地位,突出了娶妻生子、延续香火的伦理要务,而至于“性娱”,则为羞于启齿的文化禁忌。但薛大娘在“偷了”吕三后,则感觉“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2]434。在俗世看来,薛大娘可谓“不守妇道”的典型。问题是,她本就是女人,那么何以理解她“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之叹?当然,答案存于薛大娘的自辩之中,即薛大娘老姊妹劝她“图个什么呢?”薛大娘答曰:“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2]434如此“性娱之论”颠覆了女性传宗接代、失节事大的伦理钳制,解构了男权主义的话语霸权,敞开了女性自我生理诉求的性的自然与自由。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中,生殖与性事两个不同的论域,不可相提并论。具体来说,生殖受到普遍的尊重,鼓励,赞美;而性的快乐却处于一种暧昧的地位。”[6]188据此,在叙事者的声音介入中,悬置了伦理话语的重压;相反,在叙事声音的隐性在场中,性既不丑陋肮脏,亦非甘之如饴,更不是道德君子的案头讲章,因为,在退守人欲原点的“减法”思维中,不过是“食色性也”的据实陈述。
在人物文化身份上,小说《尴尬》中的“尴尬”之事,指知识分子性需求的尴尬。根植于特定文化语境与政治话语钳制,城里的“右派”下放农村本为接受改造,但却发生了“出轨”的艳事。就岑春明与顾艳芬“出轨”而言,谁主动谁被动、谁诱惑谁被诱已无多大意义。解读的要义,在于两者的情欲纠葛有别于一般,因为在旁观者看来,他们的出轨委实出人意料,因为顾艳芬很丑而妻子貌美。只是他们不但发生了关系,且顾艳芬还怀孕了。那么就同为农科专家的岑春明和顾艳芬而言,到底是谁之罪呢?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是行为恐落个“不服管教”的罪名。但是,就顾艳芬而言,丈夫的阳痿使其正常的生理需求成为一种难言的缺失;就岑春明而言,两地分居的夫妻关系,使得生理诉求也成为缺失的他无法满足。据此,他们的越轨之事与特定历史语境、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道德伦理批评无关,“尴尬”之事的发生,不过是生理诉求的正常表现。诚然,儒家文化崇尚“君子慎独”,然人皆有欲望,更何况是先天的自然欲望。总之,两者的欲求与伦理无关,但与自然欲求相切,如是叙事,作者淡化了伦理批判意识,继而在悲悯情怀中,倾注了作者对人欲的理解与同情。
从知识分子到市井小民,《黄开榜的一家》中黄开榜的二儿子为“出走者”,至于为何出走以及出走后是死是活,小说并未予以交代。源于丈夫的缺席,留守的儿媳则不避公婆颜面与邻里窃议,公开地“靠上了”毛三。在叙事时间上,儿媳未“靠上”毛三前,她靠“挑箩把胆”维持衣食,但“靠上了”毛三之后,生计便有了依靠,公婆也不再干涉他们。不难发现,市井小民的食与色是那么的朴素与自然,又是那么的民间化与庸常化,继而避开了伦理道德的批判。再如《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的辜家女儿,虽家境穷困却颇有姿色,而大德生米厂王老板的扶困之举,却也难掩食色之实;至于他的两个儿子亦对辜家女儿有所觊觎,差别不过是程度上不同而已,因而,小说写的是一门三父子与一个女人的情欲纠葛故事。当然,长子王厚堃与其父其兄的情欲不同,因为在辜家女儿的主动攻势下,他有柳下惠坐怀不乱之风。但遗憾的是,王厚堃的清流与儒雅却也是在婚前保留童子之身。应该说,辜家女儿对王厚堃的爱慕不染杂念,因为,在王厚堃结婚之际,按理说她应闭门不出,但她还是挤进了王厚堃婚礼仪式的“看客”行列,在失落的艳羡中,她不是嫉妒也不是诅咒,相反则是憧憬失落的伤怀。小说结尾并未交代辜家女儿对门的老妪们为什么哭泣。其实,那不过是她们对同类小人物命运的哀叹,写出了平凡人生、俗世情理的共通文化心理。
结语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用审美的眼光阅览人间世事,则凡事皆可宽心。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小说虽无长篇巨制,但中短篇佳作连篇,特别是谈性言情简笔书写得收放自如,使叙事风格颇显自然、悠然、安然的特征,诚如其言:“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山雄奇之山,殆矣。”[7]193在大环境、大背景、小人物、小故事的叙事中,基于作者去意识形态化、去伦理化的诗化叙事,“情自然”与“性无邪”开启了“文革”以来人的文化向度的上的多元书写。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8.
[2]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二)[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8.
[3]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8.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6]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五)[M]. 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朱丕智]
“Natural Feeling” and “Unsophisticated Sex” ——One Way to Interpretations of Wang Zengqi’s Novels since the New Period
Xu Xinhong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Anhui Bengbu 233030, China)
Since new period, Wang Zeng-qi’s novel writing regarding sexual narrati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into the workings is implied, especially to the natural feeling and unsophisticated sex, which become an entrance and main focus to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the humanized culture. Such novels stick to the naturality and rationality for the human desires by way of reverse narrative, which contradicted to the everyday human crush within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feudal ethics, then clarified and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and the nature.
sex; ethics; ideology; nature space; narrative strategy
2016-12-09
许心宏(1978-),男,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博士、副教授,从事文艺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ZW028)阶段性研究成果。
I206.7
A
1673—0429(2017)02—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