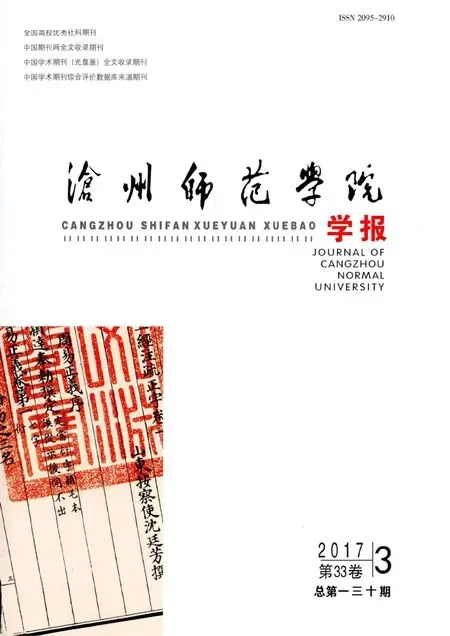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三角分析阐释法”述评
姚剑平(福建商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012)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三角分析阐释法”述评
姚剑平
(福建商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012)
费乐仁教授在汉学翻译研究方面具有很高造诣,他首创的“三角分析阐释法”,特色鲜明,自成一家。该方法重在能借助多学科之合力,探析翻译与历史互动,与宗教相互渗透,与文化相互依存,与哲学阐释学相互作用之关系。与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相比,这种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极大拓展了汉学翻译研究的空间和内涵。
翻译;汉学;跨学科方法
2016年,岳峰教授等学人编译的《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一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岳峰教授曾师从著名翻译家许崇信、历史学家林金水,在翻译学、史学与汉学方面的成果颇有特色,善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考察文献史料,进而对个案阐释细致入微。学术上的志同道合,促成岳峰教授与美籍汉学家费乐仁在学术上有长期的合作。费乐仁(Lauren Pfister,1951—)是人文学科国际知名美籍学者,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儒学、汉学史用力颇多,在中国大陆人文社科界备受瞩目。该译著经费乐仁教授授权,岳峰教授选译其部分论文,汇编而成,展示了费乐仁教授自成一家的研究方法——“三角分析阐释法”。该方法重在能借助多学科之合力,探析翻译与历史互动,与宗教相互渗透,与文化相互依存,与哲学阐释学相互作用之关系。该方法的问世丰富了翻译学、宗教学、哲学阐释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内容,促进了翻译和跨学科的研究。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成为该译著的突出特点。
一、费乐仁教授提出“三角分析阐释法”
“三角分析阐释法”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一书中初见于引言部分原作者费乐仁教授与岳峰教授的开篇对话中。费教授向岳教授介绍,该方法早在他的著作《追求“人类应尽的本分”——苏格兰新教徒理雅各邂逅中国》的第二卷第251-252页中就有陈述。这个术语借用了航海过程中的三角测量法①,将此方法运用于对理雅各的研究,费教授把自己所处的文化和历史环境比成大海,过去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就如同头顶苍穹,将理雅各视为他的恒星,船只则代表了他所受到的专业训练,而理雅各(在苏格兰和中国)的生活经历,思想及作品则代表了分析工具,就如同海员们的指南针和六分仪,海员们借助这些分析工具,通过计算确定自己相对于某一特定星体的位置。同理,费教授运用以上三个方面信息游走于两种语言文化与历史之间,从而不仅逐渐找到了头顶这片苍穹中的一些主体定位星体,解决了自己想要解释的研究问题,还催生了新问题,促使他进一步探究[1](P8-10)。由此,更直截了当地说,“三角分析阐释法”以译者的译本为出发点,追溯历史探寻译者的生活经历,进而分析译者的思想模式,最后再解读其译作,确保了译本诠释的精确性和“深度解读”[2]。运用“三角分析阐释法”,费教授在全书开篇对话中,即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剖析了历史背景信息与译者的译作及思维模式之关联性,也解释了翻译的文本与外在因素之关联性,向读者阐明了翻译与史学、宗教学之密切关系,也初步展示了自己是如何用历史与宗教的手法去解决典籍翻译实践中的困难。
二、“三角分析阐释法”解析及评论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②以三个章节详尽阐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三角分析阐释法”。该书重点论述的译者为素有“汉学经典译作之标杆”之称的苏格兰传教士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费乐仁教授通过探寻“近代来华传教士学者(尤其是理雅各)在中国典籍西译上的成就及其译作、译法和理念”来向读者阐释其自成一家的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此法所提倡的是“返古求真,追求合力”。笔者在仔细研读此书后,受到极大启发,认为此研究方法在翻译领域中很值得提倡。因为通过对本书的研习,读者能够自省,不再孤立地看待原文或译文文本,而是超越文本的语言层面,将文本置于创作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从大量史料中获得启示,从而达到对原文文本的“深度翻译”或对译文文本的“深刻解读”,读者也学会以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观理解和评价译文,这也是该方法给读者的一大启示。接下来,笔者以费乐仁教授的“三角分析阐释法”为指导,结合该书三章共十四节内容,通过探析翻译与历史互动,与宗教相互渗透,与文化相互依存,与哲学阐释学相互作用之关系,来具体评介费乐仁教授的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一)史料寻踪,探寻译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研究都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为深入钻研,获得真知,必追根溯源,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探寻译者。脱离历史背景的翻译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结果也不具说服力。因而该书第一章第一节便开始了史料追踪,让读者对“为中国典籍西译做出贡献的近代传教士学者”有个全面的认识。19世纪上叶,当第一批新教传教士,如伦敦教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的传教士裨治文来到中国,近代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自此开启。[1](P18)传教士出于传教之目的在华翻译中国典籍和出版汉语书籍,他们的译著颇具规模,成为持续至今的汉学西传的新经典或标准文献。在来华的传教士学者中,费乐仁选取了对汉语典籍的翻译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最杰出的三位代表人物,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法国传教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从三位译者的译作为世界汉学做出的贡献开始谈起,进而从译者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经历出发,来分析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历史背景及哲学阐述立场与世界观之成因。其中对理雅各的成就及其译作、译法及理念的研究与诠释是贯穿全书的重点。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影响至深且巨,且在数量上至今无人能企及,其译著《中国经典》(共5卷8册)堪称鸿篇巨制,成为汉学经典译著之标杆。那么,对理雅各的研究该如何入手?费乐仁教授以研究理雅各及其译作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走进理雅各,进一步向读者示范如何用历史学的方法,在历史的脉络中探寻译者,读懂译著。
研究一译者,必先从其作品入手。费乐仁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理雅各的作品,但因其自身为美国基督教学者,在研究初始,对现代苏格兰文化及理雅各的苏格兰非国教文化成长背景都不甚了解,甚至对苏格兰国教的新教的学术和精神传统,苏格兰常识派的哲学传统都一无所知,因此在研究理雅各作品的初期遇到了很多难题,如无法理解理雅各译本中大量的修辞现象和隐藏于评注中的信息等,为解决难题,费教授除了恶补了以上知识外,还深入探寻理雅各的宗教教育背景及其生活经历,了解其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来翻译中国典籍。由书中描述可知,理雅各出生于苏格兰公理教会家庭,在其成为基督教徒后,深受苏格兰常识哲学和苏格兰福音派现实世界观的影响,代表了较为自由开放的新教福音派世界观。理雅各在中国传教的整个传教士生涯中(1843-1874年),他始终居住在当时的香港殖民地中,殖民地的环境使他体验中国的方式不同于那些生活在大清帝国官吏以及百姓之中的传教士,并在传教时拥有一定的自由和法律保护。于是理雅各认为自己有责任将中国的传统精英文化转为基督教文化,但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如果任何基督教材料想要获得清政府领导人的关注与欣赏,就不得不采用地道的中国古典风格。为完成自己在中国传教护教之任务,理雅各不得不对当时中国社会所推崇的儒学经典传统做出“文化适应”:他全面评估了从古典时期到当代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并将重点放在古代中国儒学圣贤学者(孔子、孟子、朱熹等)身上;大规模的援引某些儒家权威经典文献术语和学说,来引导中国读者接受基督教教义;最终从早期的对抗而非适应方式转变为后期的“适应主义传教护教观之孟子模式”,即借用孟子及权威儒学的文本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堪称其为一种“儒家化”的基督教传教护教观。
但在传教护教过程中,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的敏感性,还涉及儒学传统与“一神论”的特定宗教主张不同之问题。理雅各是如何解决这一冲突?费乐仁教授在研读理雅各的《中国人的鬼神观》时发现:《书经》和《诗经》这两部儒家经典所提到的天神(上帝)相当于“一神论”传统观念中的“上帝”。而且理雅各在其后期作品中(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都认为儒学传统并不天生与基督教对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录中,上帝的观念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存在了。尤其是理雅各在深入研究中国帝王祭天仪式后,认为帝王祭拜的天神(上帝)总是明显带有“一神论”特征。由此可见,理雅各相信儒学文学里存在一座重要的神学桥梁,他对儒学古典传统是持融合的态度。正是基于儒学传统与“一神论”的融合,理雅各主张所有的传教士应认识到这一桥梁并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利用起来,于是基督教传教护教之目的借由儒学译著在中国得以顺利实现,进而也打开了跨文化交流的大门。这对当时19世纪传教士翻译及跨文化特色的理解起到积极的创造性作用,也透视了当时时代背景下西方宗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由以上分析可知,费乐仁教授从理雅各的作品入手,进而探寻译者宗教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及传教护教之创作目的。对儒家经典传统所做出的文化适应和所持融合的态度,是理雅各为实现在中国传教护教之目的,在思想上做出的重大转变,而这些转变又充分地体现在其鸿篇巨著中。由此,费乐仁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向读者展示了翻译与历史互动,与宗教相互渗透,与文化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也为其进而诠释经典、再现译者思维做好铺垫。
(二)诠释经典,思维重现
费乐仁教授从诠释学的视角再现译者的思维。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先简述了诠释学的基础知识、应用范围及其在华语圈的发展。由论述可知,诠释学(又称阐释学)是众多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的学者们主要采用的一种研究方式,无论文本的形式怎样,阐释学都能够识别并理解文本的原理。基于此,费乐仁教授推荐给读者两种阐释方式(或者说是两种阅读方式),第一种是从历史和发展观的角度进行阅读,第二种是从哲学阐释学和本体阐释学的角度进行阅读,这两种方式有助于对中国古典和现代中国哲学文本进行深度解读。随后在本章第二节,费乐仁教授以解析理雅各和卫礼贤译儒家、道家经典作品为例,向读者展示如何从诠释学角度解读经典译本:通过分析译者的译本的版式、措辞文法、音译策略、诠释依据、文法特色、文本风格、评注及索引的添加等,将译者思维理念、思维定势与倾向展现得淋漓尽致。费乐仁教授还在此节分析了理雅各的不同时期版本的译作之特色及所做的改进、编排顺序、其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及标准,以及其译作从“经典化”到“圣典化”转变的意义,这些无不透析译者的偏爱、见解和学术倾向。本章第五节进而谈到理雅各在翻译诠释过程中,受到朱熹、王韬、孟子等观点的影响,尤为奉行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诠释准则,从每一部典籍的总体意思出发,小心地寻求词义和句义之间的平衡。但在解读经典方面,理雅各并不完全依赖他们,也不追随任何一个学派,而是在儒学界择优者而从之。同时卫礼贤在阅读和比较了理雅各的经典译作之后,采取了不同的诠释框架,重塑经典,卫礼贤重塑的德文经典译著也广受各方认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读者如果采用费乐仁教授在全书第二章推荐的两种阐释方式来诠释经典,就能使译者思维得以重现。然而要读懂一部译本,不仅要探寻译者,再现其思维,最终还应深入研读其文本,在文本世界中,真正读懂译者,欣赏到其译作之魅力与价值所在。
(三)文本世界,求真务实
费乐仁教授以对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作的评析为例,向读者展示理雅各如何在自己构筑的充满人文情怀的翻译的文本世界里求真务实。
首先,体现在理雅各对孔子的认识的自我转变过程。在1861年《中国经典》最早版本的绪论中,理雅各曾以极具攻击性的国外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严厉且无情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最伟大的圣人孔子,但在他花费十多年心血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翻译及作品本质的挖掘工作后,理雅各的个人情绪在慢慢改变,且非常真诚地将自己视作一位中国学者,融入儒学传统的学习中去。在1873年之后,理雅各反而认为孔子值得钦佩且称赞孔子的诸多事迹都值得基督教徒效仿。进而在1893年的《中国经典》修订版的绪论中发自肺腑地谈到“对孔子的教学、文本和处事研究得越多,我就越来越敬仰他”。理雅各对孔子的态度从严厉批判到包容钦佩进而到褒扬敬仰直至最后的客观公正的自我转变,无一不体现在不同时期的《中国经典》绪论中对孔子学说的翻译风格的明显变化上,而这种变化恰好反映理雅各的基督教传教护教观在中国的文化适应过程。
其次,在文本世界里求真务实,还体现在理雅各与中华传统智慧密切相连的基督教学识上。该书探讨理雅各加入一个宗教文化严谨却不受政府资助的基督教公理会,这意味着他在思考关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跨文化问题时,有着更宽泛的选择余地。正是基于自身的基督教责任感使他在当时面对英国政府与清廷对抗时有义务反对罪恶,反对鸦片战争,且始终站在正义的一面。而这些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国的宗教》《中国贤者孔子》《中国经典》中窥一斑而见全豹。
最后,理雅各的求真务实还可体现在其穷尽毕生之力不断修订和完善的《中国经典》之上。理雅各习惯每篇文章在完成终稿前都要翻译数次,且都不回看先前的译文,译完后才进行对比。譬如,载于《中国经典》中的《诗经》(第一、二版)译本就有3个最终版本。1871年的第一版力求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多采用直译的方式以散文的形式再现原文,但由于过于依赖朱熹的语文学评价,强调学术性而非诗性等受到批评。1876年的第二版是以韵体诗歌的形式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诗的历史内容和意义,但也许是因为当代读者偏好可读性强的译本且因与第一版同名而被忽略。然而因为第二版是所有《诗经》译本中唯一一部采用韵体诗歌形式翻译的译著,且内容详实、注释丰富、排版多样化、风格更自由、技法精妙等,其研究价值超过其他两个版本,为汉学翻译做出了独特贡献。1879年的第三版载于《东方圣书》中,理雅各对首版《诗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重新编排了诗歌顺序,有意识地以形而上学、认识论、惯例和阶级分类方面的数据为依据,这主要缘于其基督教传教士的使命和认识。尽管世人对其《诗经》的三个译本都提出不同的批评,且译本还有许多可探讨之处,然而理雅各不断深入研究、自我反思、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值得人们敬佩。理雅各运用添加绪论、背景知识、文本资讯,大量穿插各种评注性参考文献和丰富的脚注等手法,对《中国经典》进行深入翻译和诠释,不论是第一版(1861-1872)还是修订版(1893-1895),对“真实再现”的追求远远超过了“表达精炼”,使之最终成为公认的权威版本及汉学经典译作之标杆。虽然在21世纪,我们有理由去挑战其译文中那些不够准确或者错误之处,但所有读过理雅各作品的学者都深感受益匪浅。《中国经典》是理雅各传播自由开放的基督教新世界观的一把利器。《中国经典》向我们展示的是理雅各翻译的精神世界与其宗教世界的碰撞与融合。他的成就是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是跨文化诠释学的伟大尝试。
三、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超越了单一的语言层面,在厚实的史学、宗教学沉淀中探寻翻译的系统研究方法,在内地学界尚为第一本。费乐仁教授在书中所展示的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三角分析阐释法”,使读者彻底地明白了,翻译问题远非只是形似、意似、神似[3],或直译、意译、“信达雅”层面上的问题,且同时还是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阐释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以及翻译目的、翻译受众、翻译行为、翻译效果、翻译诗学等诸多问题合力之成果[4],这实为此法一大亮点。此外,该方法的特色还在于就如何认识译者个体,如何评析译著,如何看待经典等问题进行抽丝剥茧、逐层递进式地探讨,具有极大的借鉴和科研价值。岳峰教授将费乐仁教授的研究成果整理并译成中文,促成了该书的问世,从而进一步推广了费教授的研究成果,使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尤其是对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和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大有裨益。“三角分析阐释法”所蕴含的开阔的译学视野和跨学科性带动了我们对翻译问题的创新性思考,也推动了翻译研究在其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
注 释:
① 指的是船员可以通过两个已知的可见星体,确定自己在地球表面的海洋中的位置。通常在北半球,海员们会用北极星作为轴心,再加上另一个星体作为定点,计算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当海员们穿越赤道来到南半球时,星体情况几乎全然改变,因此,他们如果不了解这些新星座(如南十字星座),就无法继续通过三角测量法进行定位,最后只能完全迷失方向。
② 全书用三个章节详尽阐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三角分析阐释法”。第一章,史料寻踪:历史学的方法,本章共五节,旨在在历史的脉络中探寻翻译与社会的互动。第二章,解读经典:诠释学的视角,本章共五节,意在从诠释学的视角再现译者的思维。第三章,文本世界:翻译的维度,本章共四节,重在以对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作的评析为例,向读者展示如何做典籍译本研究。全书三个章节的谋篇布局恰好印证了费乐仁教授的“三角分析阐释法”。
[1] [美]费乐仁.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M].岳峰等编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2] 费乐仁,岳峰.翻译研究目标、学科方法与诠释取向─与费乐仁教授谈翻译的跨学科研究[J].中国翻译,2010,(2):27.
[3] 方梦之.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4] 谭载喜.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回望与本质坚持[J].中国翻译,2017,(1):5-10.
AReviewofaCross-disciplinaryMethodologyinTranslationStudies:“AHermeneuticMethodologyofTriangulationAnalysis”
YAO Jian-p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 China)
Professor Lauren Pfister has profound attainments in sin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He pioneered “A Hermeneutic Methodology of Triangulation Analysis” with distinctive and unique style of his own. This methodology focuses on making full use of multidisciplinary joint-effort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translation interacting with history, mutually infiltrating with religion, being interdependent with culture, and interplaying with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s, this cross-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greatly expands the scop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in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inology; cross-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H315.9
A
2095-2910(2017)03-0076-05
[责任编辑尤书才]
2017-07-19
2016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A类项目(福建省高校外语教学改革科研专项)“基于语料库的高职商务英语口译教学模式应用研究”,编号:No.JZ160046。
姚剑平(1977-),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商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