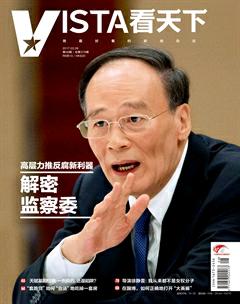艺术电影的“天真”与“世故”
张文敏
《八月》 从电影节走向院线
去年11月的金马奖,最大的黑马无疑是爆冷夺得最佳剧情片的《八月》。当张艾嘉偕评审团主席许鞍华宣布结果后,镜头迅速切换到《八月》的主创团队,一脸震惊的导演张大磊把嘴里的口香糖从台下一路嚼到台上,直到张艾嘉提醒,他才赶忙吐出来塞进口袋。
口香糖是制片人张建给的。3月17日,张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谈起这段小插曲,他虽无奈却也难掩兴奋。因为提名太多,颁奖礼又是实况直播,《八月》主创被要求不得随意离席,再加上穿得又少,“饥寒交迫”之下张建只好掏出兜里的口香糖,分发给大家充饥,“口香糖还没有化,台上就念了,我们都傻了。”
《八月》的好运气
得奖之后,许多媒体都对此前闻所未闻的新人导演张大磊提起了兴趣。
他高中玩乐队,退学,赴俄罗斯学电影,拍婚庆短片维生,2008年就开始写《八月》的剧本,到了2015年家里拗不过这个不给拍电影就撂摊子的儿子,父亲张建华这才投了六十万进去。
电影取材自他的个人经历。1994年的暑假,12岁的小雷即将升入初中,父亲所在的制片厂面临国企改制,执拗的父亲坚信能凭本事吃饭,不愿讨好得势者,家里为此焦头烂额,天真的小雷在周遭的变故中悄然长大。
夏天,电影在呼和浩特开拍,不同于拍婚庆短片时的小打小闹,二十来人的剧组在街边摆起阵仗来颇为显眼。因为资金有限,张大磊招呼来亲朋好友、发小邻居来组里串串戏帮帮忙,男主角是长自己几岁的玩音乐的“大哥”张晨,女主角郭燕芸则是他婚庆短片生意的客户。制片人张建是张大磊的高中同学。
电影一个多月就拍完了。张大磊把片子初剪出来后请张建和张晨去看,“看了四个多小时,彩色版本,我觉得棒到死,特别棒,无法形容的棒。”
聊起电影,自谦“电影行业新人”的张建,提到最多的词是“玩儿”。当时结果还没公布,“就赌,特别好玩儿。”当晚的庆功宴,除了小演员孔维,一群人嗨到了天亮。
但其实,《八月》的好运气不仅于此。
有媒体报道,早在去年7月的西宁First青年影展上,《八月》就口碑爆棚,三场放映一票难求。张建说,他们正是在First影展上认识了台湾来的发行方,发行方推荐他们报名了当年的金马奖,导演自己在家把报名表上所有能参选的奖项都打了勾,说自己没有任何期 待。
经First推荐,牵头成立“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以下简称“艺联”)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早在金马奖前就注意到了他们,《八月》后来被确定为艺联全国发行的第一部国产艺术 片。
资料馆负责艺联工作的汪忆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吐露,看到片尾全家合影,小雷伸出手假装爸爸在旁边时,她眼泪哗哗地流。《八月》是她个人2016年的“年度最佳”,而她上一年的“年度最佳”是去年上映,同样斩获金马奖的《路边野餐》。
后来汪忆岚在网上看金马奖直播,知道《八月》拿了大奖,她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遗憾”,高兴的是自己喜欢的片子被认可,遗憾的是错失了电影的主发机会。
而爱奇艺影业,也早在《八月》赴金马参展前就加入成为出品方之一,并拿下了电影的发行权。
跪求票房的艺术电影
尽管在电影界,《八月》的好口碑持续发酵,但艺术电影历来被看作曲高和寡,票房往往也不被看好。
如今的电影市场蛋糕越做越大,但艺术电影却没有因此尝到多少甜头。据统计,近十年来,每年可以步入商业院线的艺术电影平均下来不足十部,剩下的多数只能销售给电影频道和视频网站。
2014年上映的《白日焰火》,尽管有柏林金熊奖桂冠加持,但发行方在营销推广时对“犯罪爱情”类型的强化,无疑是其上亿票房的有力推手。去年《百鸟朝凤》八千万的现象级票房亦由其制片人方励的惊天一跪造就。
《百鸟朝凤》上映五个月后,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华夏发行、暖流、万达院线、安乐、微影时代6家单位发起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立。不同于以往由行业或民间发起的艺术电影放映组织,这一带有官方背景的“联盟”真正手握发行话语权和行业资源。有媒体感叹,如果艺联早些成立,或许《百鸟朝凤》就无须“跪求”票房了。
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节目与宣传推广经理杨洋告诉本刊,现在并没有所谓的文艺片的发行模式,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一部电影能够摸索出一个可供其他艺术电影借鉴的发行模式。
这种磨合阵痛从艺联与爱奇艺两方对《八月》宣发策略的不同主张就可以看出。
作为艺联成员,在联合发行中负责此次地面发行的华夏团队负责人边巍坦言,他们原本希望能在映前做一到两周的点映,等到口碑扩散开了之后再做全国范围的放映,但在与爱奇艺谈判时,对方表现出了对票房的担心。“说白了,他还是对这个片子没有足够的信心。”
不同于商业电影,《八月》拍摄初衷并非盈利,黑白色调,散文叙事,一张熟脸也没有,就连张大磊的父亲,电影界老人张建华看过之后都吐槽其为“流水账”。但可以说,它吊足了艺术电影迷的胃口。让艺联方面不解的是,为什么艺术电影的发行非得迎合商业电影市场,就像电影里头张晨扮演的父亲就是想不通,非得要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才能保住饭碗吗?
《八月》是爱奇艺院线发行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发行负责人叶笑吟此前也没有艺术电影的发行经验。在艺联看来,爱奇艺走的是他们一贯的商业电影路子;但爱奇艺认为,他们采用的是不同以往的发行策略,即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首先抓住文藝片的精准受众群,包括联合影迷发起众筹观影。
但是,问起为什么不做点映,叶笑吟承认了他们对片子受众群过窄的担忧。“毕竟我们上的是商业院线,它面临的是跟《金刚》拼场次拼票房拼口碑。”因此,他们希望避免谈及黑白片等不讨喜的元素,强化“金马光环”和进口片挤占下的“国产片”背景。上映前不给观众看整片,为的是借由“神秘感”保证上映头三天的票房。
这在艺联看来,还是很典型的商业电影宣发思路。汪忆岚说,他们并非不在乎票房,只不过,刻意追求票房未必就能求得来票房,艺术电影应当有能力自负盈亏,但盈利却不应是它的第一要义。
不健康的情怀
众所周知,现如今,好口碑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好票房。小成本的艺术电影不仅请不来大牌、“鲜肉”,甚至砸锅卖铁把片子拍出来了,还可能遭遇没钱发行的尴尬。就算有发行商愿意发行了,但如果不投入一定的营销成本或發生现象级的营销事件,艺术电影依旧很难从市场中分一杯羹。
《八月》的成功是个例。两百万的投资,到电影上映前,主创团队已经收回成本,再加上有金马这样的重量级奖项的肯定,可谓“名利双收”,接下来看的就是票房表现。
尽管爱奇艺不愿透露他们投入到《八月》的宣发预算,但作为联发方的艺联透露,他们除了主发方爱奇艺给的宣传预算外,自己又投了一百多万。艺联方面负责地面发行工作的华夏团队负责人边巍甚至直言:“这件事(就是)奔着赔钱去做的。”
可以想见,各方为电影所耗费的宣发费用,将远超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
可就算是这样,也并不是所有片方都愿意跟“艺术电影”扯上关系。汪忆岚回忆,《八月》之前,他们还找过《少年巴比伦》,但因为片方不愿意对市场释放信号说自己是部艺术片,反而乐意把自己宣传为一部青春片,所以没能争取到它的发行机会。
曾为国内外多个影展提供策划选片,也做过纪录片导演的杨洋说:“艺术片不好经营是全世界共通的东西,只不过在中国会更难。”所以,艺术电影的市场需要培养。她坦承,《八月》不算是看起来很好卖的电影,“之前卖得好的《白日焰火》,有商业元素、类型片元素,又有大明星,《八月》都没有这些东西。”因而,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筹备的针对《八月》的宣传活动里,他们会举办专门讲授黑白电影视听语言的讲座,以期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
尽管有政府扶持,但汪忆岚告诉记者接下来再推其他新片时,他们会尽力争取主发权。“对于联盟这个组织来说,如果一直向外输血,但是自己却没有建立造血的能力,时间长了,血流干了,那就挂了。”
现已有分布于全国的一百多家影院加盟艺联,它们将连续两周放映《八月》,每天保证一个黄金场次。艺联也希望电影能给加盟的影院带来好票房,并为此在宣传上尽力配合影院达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上座率,“哪怕是情怀,你一直让一个有情怀的人饿肚子,生存不下去,这个情怀也不是健康的。”
“艺术电影是有奔头的”?
有情怀的张大磊最后在电影里,让小雷用双截棍把不给他加分的老师打了。那根双截棍还发泄了父亲的压抑情绪——小雷当着制片主任的面把他一样仗势欺人的儿子给打了。母亲数落小雷,小雷却一副大人模样:“莫以成败论英雄。”
张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感慨,那么多好机会都让他们赶上了。的确,谁能想到,一个一心想拍自己远去童年记忆的“菜鸟”导演,真就把奖也拿了,钱也挣了。
但是,成的是少数,多数艺术电影在市场面前还是败下阵来了。
据1905电影网报道,去年悄然上映的艺术电影《冬》,同样到海外影展走了一圈,还拿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艺术贡献奖”,但回了国内,没有一个团队愿意帮它做营销和发行,上映十天仅收获22.5万票房,远不足以回收150万的成本。
张建华告诉记者,爱奇艺之所以选择加盟并发行《八月》,并非看中片子的市场潜力。爱奇艺影业新任CEO亚宁在First影展之后的一个小型放映上,看了《八月》后非常喜欢,这才与制片方开始接洽。
从《站台》开始就与贾樟柯合作的监制周强曾在公开场合透露,他们花了十一二年才让贾樟柯电影的发行顺利起来。如今,仅靠“贾樟柯”的名头他们就可以在剧本创作阶段通过“预卖”筹到电影的制作费。通过海外发行,他们就已经能收回成本。
除贾樟柯外,也有不少并不知名的导演拍摄的小成本电影能够借由海外影展,拿奖金,卖发行,收回成本。但艺术电影并不等于小成本电影,新人导演很难靠申请海外基金或发行来拍片。张建华说,拍制片厂职工拔河比赛那场戏时,因为资金紧张,儿子只好从街边拉人来演,但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没有他们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
况且,艺术电影也并不意味着就应该被束之高阁。张建华说,身为电影人,他对发行是“又爱又恨”,如果没有硬性规定,影院实行的是“末尾淘汰制”,如果头天票房表现不佳,第二天排片就会缩减。这就意味着不被市场看好的艺术电影很难有“出头之日”。
为了让自己的电影有观众,被认可,很多导演干脆奔着电影节去拍片。通过这一年来的参展经历,张建华琢磨出来了,《八月》在First和内蒙古青年电影周上折戟并不意外,他在台北看了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发现,原来儿子的电影不少地方是向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致敬。他说,作者电影虽然以个人创作为出发点,但也总需要有人看,电影节就是他们向外输出的窗口,甚至有导演根据国外某电影节的主题,决定自己的拍片计划,“反正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
艺联和爱奇艺都不愿透露他们对票房的预估。张建华想着,既然赶上这么个机遇,应该能超过《路边野餐》,估计能有个七八百万,后来接上的艺术电影也许还会更好。
张建也觉得,艺术电影是有奔头的。糊里糊涂踏进电影圈的他不耐烦给电影人分阵营:“无论是什么情况,只要让它发出去,让他们知道,形成影响力就够了,作为导演和电影本身来说就已经够了,再获得一些值得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就可以了。”
张建说他现在特别愿意去结识那些有才华的所谓的穷导演,他相信,作为制片人,如果能解除他们身上的现实束缚,一定能出许多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