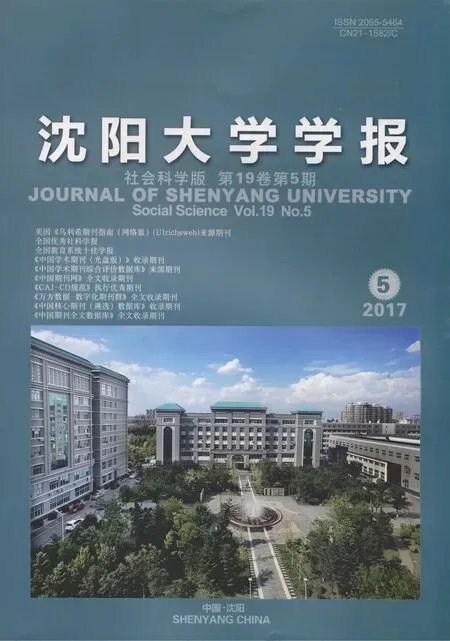近代沈阳城市“杂巴地儿”研究
张 金 春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近代沈阳城市“杂巴地儿”研究
张 金 春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分析了近代沈阳城市 “杂巴地儿” 的形成过程及特点。认为老城区的“杂巴地儿”历史悠久,具有本土化特色;自开商埠地区的“杂巴地儿”因其独特的形成背景,具有多样化时代特色。“杂巴地儿”是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的微观缩影,它的兴起与繁荣推动了沈阳城市发展的多元化。
近代; 沈阳市; 杂巴地儿
清入关后,沈阳的政治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作为“陪都重镇”,仍是清政府非常重视的城市。鸦片战争以来,内外双重因素的刺激推动了近代沈阳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使其成为研究近代东北城市史的典型城市。近年来,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很多研究涉及到近代沈阳“杂巴地儿”研究*如孙鸿金:《奉系军阀统治下沈阳城市经济的发展》,录自《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898—1945)》,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马魁:《盛京杂巴地儿》,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西园:《旧沈阳的“杂巴地”----从西门脸到第一商场》,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刘鸿儒:《旧沈阳的“杂巴地儿”》,石家庄:《文史精华》,1995年第4期。,但此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值得进一步延伸,尤其是在近代沈阳城市“杂巴地儿”与沈阳城市发展的关系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
“杂巴地儿”这一地域概念,最早源于中国北方民间的俗语称谓。“杂”,即复杂之意;“巴”(也称作是“八”)是语气助词;“地”,指的是区域。故“杂巴地儿”就是指混杂着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人等的场所*其他城市也有与“杂巴地儿”类似的区域,比如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和成都“扯谎坝”等。可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0页。。在近代东北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沈阳的“杂巴地儿”则最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笔者所选取沈阳“杂巴地儿”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指“九一八事变”前的这一时间段。。而沈阳“杂巴地儿”的形成与发展也与沈阳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渊源密不可分。
一、 本土视域下沈阳老城区的“杂巴地儿”
明代之前,沈阳多是夯土围成的方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指挥史闵忠将其修建成砖城,城内有呈“十”字形交叉的两条大街。“周围九里三十余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阔三丈,深八尺,围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围十一里有奇。门四:东永宁,南保安,西永昌,北保定”[1]。沈阳城市规划与建设也正式开启。
后金政权建立之后,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沈阳也成为后金统治者重点建设的城市。努尔哈赤保留了沈阳都城原有的“十”字形的大街,只对城墙、护城河等进行了加固。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即位后,逐渐开始对沈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他下令增拓沈阳都城,使其达到“东西宽三百九十三丈八尺,南北长四百二十五丈六尺,合计一千六百七十六万零一百二十八平方尺,为两千七百九十三点四亩”[2]。并将原有的四门改为八门,之前的“十”字街开辟为“井”字街。城内划分的区域也从之前的“田字格”变成了“九宫格”布局。这也为沈阳“杂巴地儿”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区域地理条件。
在沈阳顺城街的西门脸(城外的墙根部分,按方位称作某“门脸”),分为三个等长的部分:从西北城角南到小西城门;从小西城门南至大西城门;从大西城门南至西南城角。在沈阳老城区被称作“杂巴地儿”的就是指中间的街段。沈阳城西门脸“杂巴地儿”是沈阳最早形成的杂巴地儿,“这块杂巴地儿,南北长一华里左右,东西宽约一百多米”[3]138。由于其优势的地理位置,在街区两侧逐渐形成了餐馆、粥铺、茶馆、鞋铺、估衣铺、中医诊所等店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回民风味的于家馆和马家馆、东海轩粥铺、德泰轩茶馆、天足方鞋铺、王回回诊所。在街区中间地段则是江湖上的医、卜、星、相、蜂(风)、麻(马)、燕(颜)、雀(缺)的“八大生意”。
西门脸 “杂巴地儿”最核心区域当属德泰轩茶馆*另据《沈阳市志》和《沈河区志》所载,将其称之为“洪泰轩”,据笔者查证,应是异名同馆。此处则引用《沈阳文史资料》中的“德泰轩”称谓。。德泰轩茶馆历史悠久,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就已开业。“茶馆五间青砖瓦房……茶馆室内墙上贴着红纸黑字的条幅,上书:‘休谈国政’和‘莫论人非’。每天早场是从中午到午后四点,晚场是六点到九点”[3]142。为了招揽客人,德泰轩茶馆从八王寺运来“甜水”以备茶水之用*八王寺原名大法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寺院主持为感激阿济格王爷施舍修寺之恩,故改名为“八王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东巡盛京祭祖,饮用该寺泉水后大加赞誉,称其是“东北第一甘泉”。八王寺“甜水”由此得名。具体可参见齐守成:《盛京老字号》,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8页。,为了买卖方便,小吃摊和点心摊也经常摆在茶馆门口,茶客可以请堂倌出门为其购买可口的小吃和点心,这种附加服务,实际上延长了人们在茶馆的时间。茶馆里还经常安排多样的曲艺表演,在当时享誉东北的评书艺人李庆魁和卢醒生就经常在此演出。“在民国十年(1921年),有一次说书艺人未到,茶客中有人提议那些‘撂地摊’的说相声的,唱小曲的,变戏法的艺人到茶社‘票一段’以补空白,不料演出获得了意外效果,又引来不少茶客,洪泰轩茶社从此将说书场改为‘杂耍’园子”[4]。茶馆雅俗共赏的文化形式使茶馆经常座无虚席,是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1923年,为了整合城市建设,在奉天市长曾有翼的主持下,计划从大西门经太清宫至小西边门开辟八丈余宽的有轨电车路,两侧的商铺民宅一律拆除,重建二三层民房,将原来撂地摊的商贩安置在城隍庙的常设市场,将原来占卜算卦,江湖艺人、茶肆酒庄移到太清宫至小西边门中间的路北,即“回回营”内,开辟了“奉天第一商场”(兴游园)。至此,西门脸的“杂巴地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西门脸的“杂巴地儿”,沈阳还有几处本土色彩浓厚的“杂巴地儿”。如在老城区东南角的小河沿“杂巴地儿”,其兴建的万泉公园也是近代沈阳市民休闲娱乐的绝佳场所。在郊县,有新民县的老爷庙头、辽中县的关帝庙附近、康平县的裤裆街等,也都是五行八作各色人等相对集中,具有浓厚本土气息的“杂巴地儿”。
二、 殖民背景下自开商埠地的“杂巴地儿”
由于近代东北地区中外势力的长期交织,使东北重城沈阳深受影响,沈阳城市发展也呈自主化与殖民化同步演进的趋势。
1896年6月,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沙俄以修建中东铁路为由,将势力进一步延伸至中国东北。1900年,沙俄又向东北出兵干涉剿杀义和团,于年底威逼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允许沙俄在盛京等处驻兵,遣散中国军队交出军火,拆毁全省炮台火药局,允许俄国派员驻盛京”[5]。此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与日本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其中规定“俄罗斯帝国之政,当以长春旅顺之铁道及其一切支线,及在该地方附属之一切权利、特权财产,及在该地方属于该铁道之产业,不受一切补偿,而以大清国政府之承诺,转移割让于日本帝国政府”[6]。至此,沙俄在南满铁路的特权地位逐渐被日本取代。由于沈阳正处在南满铁路的中间位置,并且还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日本殖民当局十分重视对沈阳满铁附属地的商业与市场建设。“一般日本商民来满逐年增多,金融业、仓库业、保险业,交易所及商业会议所等现代的事业设施也发展起来,日本方面的流通机构也日渐齐备了。这种局面,由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一般经济兴盛”[7]。
在沈阳殖民化不断渗透的过程中,也刺激清末沈阳开启了自主化的建设进程。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认为“今者时局日迫,交涉日艰难,中外企望日切,即今改除成格,犹可挽救”[8]。随即他着手进行官制改革,裁撤盛京五部与奉天府尹。1905年,赵尔巽奏请朝廷在奉天省城设立商会,并于次年获准成立奉天商务总会。在商会有序的规范下,为沈阳城市市场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盛京时报》记载“1907年初,奉天省城共有烟馆416家,客栈101家,伙房358家,妓馆52家,土庄60家,当铺7家,古董店12家,刀剑客12家,菜床138家,茶馆102家,酒馆26家,饭馆299家”[9]。近代沈阳初步形成了行业齐全的城市商业体系。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应对东北地区的殖民扩张危机,仿照开放口岸的形式,在东北中心城市或者边境沿海城市自行划出一部分区域,允许中外商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该区域也被称作是自开商埠地*东北地区最早开埠活动从1862年的营口开始,也由此引发了东北一系列的开埠示范效应。具体可参见荆蕙兰:《近代营口港的开埠与东北城市近代化研究》,录自《东北早期近代化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4页。。作为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也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为了阻止奉天满铁附属地向老城区的扩张,实现对奉天满铁附属地的“合围”,1906年6月1日,盛京将军赵尔巽宣布奉天省城自开商埠。自开范围是省城西门外,南至官道,北至官道,东至城墙根,西至火车道, 约一万一千余亩[10]。 但是,各国领事并不承认沈阳自开商埠的行为, 尤其是对其界址的划分更是存在分歧。 经过长期的谈判磋商, 1908年3月,终于与各国达成协议,奉天交涉司将自开商埠由北向南分为:正界(现时或近期开发)、副界(5~10年开发)、预备界(远期开发)。 沈阳自开商埠后,将土地按级拍租, 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商业与市场的繁荣发展。 奉系军阀主政东北时, 原有的市场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1918年,张作霖命令奉天省长王永江开辟南北市场, 并于次年开工, 南北市场在两年内基本完成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其中,位于自开商埠地北市场的“杂巴地儿”最具特色。北市场地处商埠地正界的北端。在开辟之前,这里曾是不毛之地,仅有西塔、实胜寺、太平寺和关帝庙等庙宇和十间低矮的平房,故人们也称此地是“十间房”。开辟此地后,地方当局准许商贾租地建设,他们在此广建茶社、剧场、妓院。因为南市场开辟在前,故将其对应称为“北市场”。后来,北市场发展成为了中国北方地区独具特色的杂巴地儿,成为可以与同时期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等齐名的“杂巴地儿”[11]。
北市场“杂巴地儿”是民间戏曲的繁兴之地。比较著名的有大观茶园(今辽宁青年剧场)、中央大戏院(今沈阳大戏院)、共益舞台(今北市剧场)等。 大观茶园最初由马洪源盖建, 1919年,由李东瀛、绳新耕、孙福臣、“御厨子”等人参股创建了大观茶园。 1922年, 何福臣、李震阳等人接手建办。 之所以称作是“茶园”而不是“茶馆”, 是因为大观茶园性质更偏向于剧场, 以演出“奉天落子戏”为主。 中央大戏院和共益舞台始建于1928年, 都是北市场有名的剧场, 主要以演出京剧和评戏为主, 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金少山、谭富英、李金顺、筱桂花等名家都曾在此演出过。
北市场“杂巴地儿”是五行八作汇集的地区。北市场南倚马车铁道,东靠火车站,交通便捷,辽宁总站建成后,更是吸引了各行各业聚集于此。截止到1927年,北市场已有“包括商业、饮食、服务、修理业等40个行业,1 369户,总资本为奉洋352万元。其中主要有:大中型京洋杂货商号67户;当铺2户;金店2户;钱庄10户;医院诊所、药房25户;钟表行17户;下杂货业121户;米面铺44户;酒店油坊17户;肉菜铺72户;澡堂5户,戏院茶社10户;其他行业977户”[12]。北市场也成为了行业比较齐全的商业服务娱乐中心,充分体现了“杂巴地儿”的平民性、娱乐性、多元性特点。
相比而言,北市场与西门脸二者的“杂巴地儿”虽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较大差异:①形成背景上,西门脸是沈阳本土漫长历史中自发形成的“杂巴地儿”,而北市场是在殖民背景下,适应自开商埠的建设需求开辟而成,更具有政治性意图。②地理位置上,北市场位于自开商埠地的北正界,是政府大力扶持发展的区域,发展更为有利。③区域空间上,北市场总面积约为0.47平方千米,更具发展潜力,是西门脸顺城街道所不能比拟的。④功能构建上,由于北市场西靠奉天满铁附属地,受日本等国外因素的影响,其发展更为多元化。
三、 沈阳“杂巴地儿”与城市发展多元化
沈阳“杂巴地儿”作为城市发展的特殊载体,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作用下蓬勃发展,促进了沈阳城市的多元发展。
1.行业齐全的休闲与娱乐方式,丰富了沈阳市民的社会生活
由于“杂巴地儿”具有很强的大众性色彩,使其吸引众多中下层民众聚集于此。除了上述三大剧场,在“杂巴地儿”还有云阁电影院(今人民电影院)、奉天座(今民族电影院)和保安电影院(今群众电影院)三家电影院及众多的饭店、茶庄、浴池、妓院、金店、服装店、放款店、大小客栈、钟表店、照相馆、理发馆、当铺等商业娱乐设施。另外,“摆地摊的、算命占卦的、卖大力丸的、卖狗皮膏药的、跑马戏的、拉黄包车的、清朝遗老各色人等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13]364-365。 “杂巴地儿”成为当时沈阳的商业娱乐中心。
2.多元构建的内在容量,促进了沈阳城市功能的完善
城市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其对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功能也在逐渐形成。一座城市功能完善与否也是判断其城市化的重要标准。近代沈阳新兴的“杂巴地儿”发挥了承载城市功能的作用。在政治功能上,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利用北市场“杂巴地儿”鱼龙混杂的地理环境,将新成立的中共满洲省委藏匿于此,刘少奇也曾出任中共第五任满洲省委书记,在此展开各项革命活动[14]。1930年3月10日,阎宝航在小河沿曾经带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将查剿日本非法商人的386包海洛因聚众烧毁,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罪恶活动[15]。在经济功能上,“杂巴地儿”不仅形成了店铺林立的商业市场,1920年6月,北市场还成立了当时东北最大的棉纺织企业----奉天纺纱厂,这也是“具有现代工业意义的民族棉纺工业,推动了东北现代纺织业的发展”[13]255。在文化功能上,茶馆与剧院成为曲艺的主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店铺外面,聚集了很多评书、戏法、二人转、落子戏、木偶戏、皮影戏和拉洋片的各色艺人,极大丰富了城市文化艺术形式。
3.大批移民的不断涌入,加速了沈阳城市化的进程
衡量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主要依据两个指标,其中包括物质结构方面的空间规模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市区人口规模。现有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移民的不断涌入,形成了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两个主要途径。近代沈阳开发商埠地,造成了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动因也属于被动性。“大批移民的涌入,特别是大量高密度、异质性的青壮年移民的到来,为东北城市的现代产业及各种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多层次人力资源,使城市各项产业的发展条件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移民的不间断流入,造成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化,使城市呈现出更加开放活跃的态势,这是城市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16]138。尤其是北市场的“杂巴地儿”,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的特殊属性,更吸引了大量外来逃荒移民和中下层市民生活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扩充了沈阳城市人口规模,有效促进了沈阳城市化进程。
4.国外先进文明的不断传入,推动了沈阳城市近代化运动
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是两个彼此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城市社会学概念。“如果说城市化是城镇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量变动态过程,那么,城市近代化就是城市发展的质变过程”[16]1。近代沈阳的商埠地坐拥奉天满铁附属地,北市场的“杂巴地儿”较早接触了国外文明。建筑风格上,中央大戏院、大观茶园等建筑,在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外建筑文化的特色,形成了中外结合的建筑风格。在城市建设中,1923年5月3日,市政公所筹备处成立,同年8月4日,正式成立了奉天市政公所。在市政公所的主持协调下,借鉴国外的城市建设经验,对奉天省城进行了大量近代化的城建工作。其中修缮了和扩建了商埠地的道路系统和商业建筑,完善了各城区公共卫生事业[17]。此举也使沈阳“杂巴地儿”的交通和卫生条件大为改观,促使其向近代化的商业娱乐中心转化。在市民的心路历程上,由于深受国外文明影响,市民开始认同西方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得到不同程度的思想解放,这主要体现在追求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观念。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Geertz)所认为的“社会现象的意义是由参与社会活动的大众赋予的”[18]一样,以上这些因素,均为沈阳城市近代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诚然,“杂巴地儿”“杂”的性质,也使其成为城市藏污纳垢的重要场所。“张作霖还准许商人在北市场修建妓馆,这些妓馆大多云集在平康里、宜春里、永宜里等胡同内,约140多家。北市场的妓院以宜春里为中心,妓女最多时达1 000多人”[13]364。另外,大烟馆、赌局等也一应俱全。这些无疑破坏了城市的社会风气。此外,“杂巴地儿”还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首者称为“寨主”,出谋划策者称为“军师”,组织成员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流氓组织的存在威胁着当地的社会治安管理。这些都是“杂巴地儿”的不和谐因素。
综上,“杂巴地儿”是当时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一区域概念虽不是沈阳地区特有,但沈阳地区的“杂巴地儿”在自主建设与殖民营造背景下,融入了传统与异国元素,见证了近代沈阳由传统向近代城市发展的多元历程。因而最具市井风情,最具时代特色。
[1]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卷八十七,建置一·城堡·沈阳县[M].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3:1963.
[2] 袁亚非. 一代盛京[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35.
[3] 西园. 旧沈阳的杂巴地:从西门脸到第一商场[M]∥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 1984.
[4] 沈阳市沈河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沈河区志[M]. 沈阳:沈河区地方志办公室, 1989:344.
[5] 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53-54.
[6] 李德周,吴香椿. 东北铁路大观[Z]. 天津:北宁铁路运输处计核课庶务股, 1920:121.
[7] 满史会.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M]. 王文石,译.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257.
[8]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5352-5355.
[9] 奉天省城店户总计数[N]. 盛京时报, 1907-02-20(3).
[10] 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A]. JC10-4766卷.
[11] 孙鸿金. 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898—1945)[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142.
[12]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沈阳市志:第9卷(商业)[M]. 沈阳:沈阳出版社, 1999:33.
[13] 辽宁省档案馆. 奉天纪事[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14] 张璐. 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研究[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7.
[15] 胡存宇. 小河沿拒毒焚烟始末[J]. 兰台世界, 2001(11).
[16] 曲晓范. 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7] 赵欣. 近代沈阳城市建设的历史变迁[J]. 东北史地, 2012(1).
[18]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7.
ResearchofZaba-DierinModernShenyang
ZhangJinch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aba-Diers in modern Shenyang are analyzed. The Zaba-Diers of the old town have long histories and localized features, and those in the self-owned commercial area especially have unique history and temporal variety. The Zaba-Diers are microcosms which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enyang, their emergence and prosperity greatly propelled the variety of Shenyang City.
modern times; Shenyang; Zaba-Dier
2017-04-27
张金春(1991-),男,辽宁凌源人,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2095-5464(2017)05-0642-05
K 291/297
A
【责任编辑王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