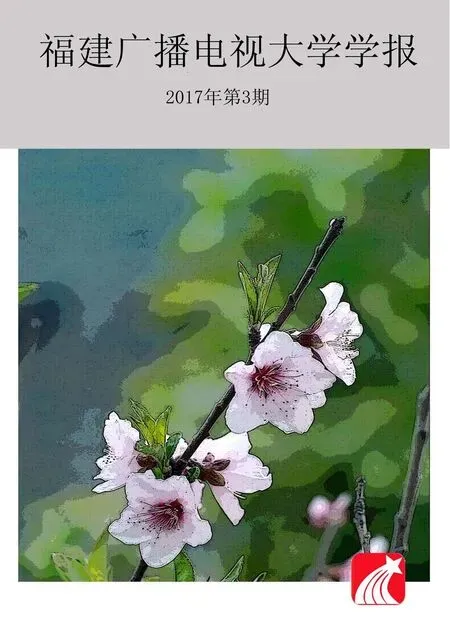论网络视域下方言词进入共同语(普通话)的过程
王 玮
论网络视域下方言词进入共同语(普通话)的过程
王 玮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建福州,350013)
根据方言与共同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特点,解析方言词在互联网中的使用、传播、分化直至最后被共同语吸收的过程。借助互联网技术所提供的方言词的传播路径,探寻在网络媒介的影响下,共同语吸收方言词的一般规律。认为语言必然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而加速变化,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应依据现行法规审慎吸纳方言词。
共同语;网络语言;羊群效应;马太效应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本文讨论的方言指地域方言。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密切。在共同语未形成之前,方言是共同语的基础,在共同语形成之后,方言是共同语的分支。方言从共同语中吸收成分,增强方言的活力;方言成分也会进入共同语,丰富共同语的表达,二者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现代汉语的共同语是普通话,地域方言包括北方、吴、湘、赣、闽、粤、客家七大方言。
追本溯源,汉语共同语吸收方言词的历史悠久。当共同语缺乏意义相当的词的时候,方言词成为重要的补充,如“槟榔、荔枝、龙眼、橄榄”等。有些意义相同但表达更生动的方言词也会被共同语吸收,如“歹毒、瘪三、窝囊、扯皮”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较快地区产生的新词、新义也会被共同语吸收,如“创意、直销、瓶颈、入围”等。在互联网技术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语言为普通话贡献了许多新词,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来自地域方言。《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与第五版之间仅相隔七年,新增方言词、方言义项就高达125条,其中不少来源于网络语言。
寻幽探径,早期的方言词进入共同语的路径已不可考,但是随着信息数字化存储、传播技术的日益强大,方言词在互联网上的使用、传播、分化与被普通话吸收的过程早已有迹可循,有理可辨。为了写作方便,笔者将在互联网上流行的方言词统称为网络方言词。
一、陌生化激发网络方言词的使用
知名学者刁晏斌指出,“网络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陌生化,即采取了新鲜,甚至是怪异的表达形式,这是网络语言得以流行的最主要原因”。[1]这也是网络方言词得以在互联网被广泛使用的最主要原因。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1916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艺术的特征,即它是专为使感受摆脱机械性而创造的……‘艺术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使感受在其身上延长,以尽可能达到高度的力量和长度……‘诗歌语言’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实际上诗语也常常是陌生的。”[2]陌生化理论指出,由于反复使用,语言有一种时时趋向固化的倾向,而陌生化的言语或表达形式,能给文学语言注入全新生机,获得更愉悦的体验。方言词无论在文学语言、日常语言,还是在网络语言中,都表现出了与普通话的巨大差异,拥有神奇的陌生化效果。
“截止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3]全国各地的网民汹涌而来时,裹挟着各自方言区的语音、词汇、语法、语气、语感……具有强烈陌生化特征的网络方言词为网络语言增添了许多新奇的言语色彩。网络方言词的陌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语音的变形、词义的异化和借词。
(一)语音的变形
语音的变形指词语由于受到方言方音的影响,词语的构词成分被其他谐音字替代,形成该词全新的书面形式。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没有声母zh、ch、sh,来自这些地区的网民经常把zh、ch、sh读成z、c、s,如网络方言词中的“色友(摄友)、女汉纸(女汉子)、桑心(伤心)”等。来自闽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北方方言之西南次方言地区的网民,总是混淆“n、l”的发音,因此产生网络方言词“菇凉(姑娘)、伦家(人家)、内牛满面(泪流满面)”等。闽方言、湘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的“f、h”不分的情况也十分普遍,网络方言词“灰常(非常)、灰机(飞机)、稀饭(喜欢)”等就受此影响。
除了受到声母系统的不同影响产生的网络方言词,还有一些受到韵母系统不同的影响而产生的。如南方诸方言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不分,产生的“盆友(朋友)、先森(先生)”等,再如“好”在粤方言中读“猴”,因此产生了猴年最流行的两个网络方言词“猴开心”“猴赛雷”。
七大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差异,以语音的差异最显著。但是网络方言词对普通话语词的读音改变不大,在通过上下文理解其涵义的同时又延长了认知过程,产生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二)词义的异化
词义的异化指词语在已有本义、常用义的基础上,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派生出新的义项,为表达增添了新的意义。如:“雷”的常用义是“云层放电时发出的响声”,而在吴方言中有“使人震惊”的意义,因此才有了“被雷倒了”这样网络流行语。“雷”的派生义是由“雷声”这一意义产生的比喻用法“仿佛被雷击中一样惊讶”而来。方言词义与普通话词义之间存在着关联,能够迅速联想,理解该词的意义。
类似这样的词语还有:“山寨”、“恐龙”、“青蛙”等。“山寨”的常用义是“1.在山林中设有防守栅栏的地方,2.有寨子的山区村庄”,在粤方言中的派生义是“仿造的,非主流的”。“恐龙”的常用义是“古代爬行动物”,“青蛙”的常用义是“蛙的一种”,在台湾地区的派生义是“丑男丑女”。这些网络方言词的形式上是旧的,但是意义都是新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也能产生陌生化效果。
(三)借词
著名语言学家陈原曾说:“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它不怕同别的语音接触,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本来所没有,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非用不可的语汇……”[4]在网络语言中,从方言词中借词十分普遍。如:北方方言之华北次方言的“忽悠”,在网络传播中大有取代“欺骗”之势,后因赵本山的小品《卖拐》,该词从网上流行到网下。再如:“给力”来源于北方方言之华北次方言,除了流行于网络,也曾多次登上各大传统权威纸媒头条,还被用在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与演讲中。这类网络方言词与普通话在语音和构词成分上都有着较大不同,产生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再借助权威媒体、权威人士的运用,为其内涵附加了更多感性意义。
类似这样的词语还有:来自闽方言的“大咖(大人物)”,粤方言的“靓女(美女)”,台湾地区的“菜鸟(新人)”等等。借词的出现,体现了不同方言区的人与人的频繁交往。普通话与七大方言的互相渗透也应证了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方言词从方言区域到互联网,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这就是网络方言词的陌生化手法。无论是语音的变形、词义的异化还是借词,经历陌生化处理的言语,其最大的特点是打破普通话的思维定势,产生新鲜的表达形式,激发网络方言词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二、社会心理加速网络方言词传播
陌生化的网络方言词虽然为表达提供了语言形式上的“新”,但是接受者更期待的是在形式外表下审美体验和心理感受上的“新”。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截至2016年12月,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73.7%,其中20-29年龄段网民占比最高,达30.3%”。[5]年轻网民求新、求异、求趣甚至求怪的心理需求,使得他们排斥并解构日常语言的框架与规范,网络方言词恰好符合他们的表达需要,并随着他们的心理需求被传播与放大。这种对日常语言的排斥与解构也是网民群体心理的反映,同时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一种现实状态。
(一)新奇
网络应用之初,网络方言词只需与众不同便可吸引眼球。如:“偶(我)、灰常(非常)、母鸡(不知道)、虾米(什么)、美眉(妹妹)”等带有强烈方音的词汇进入互联网,通过上下文和简单的方音辩证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方言词的意义。
随着电脑的普及,网络交际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手段之一,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层次也越来越低。更年轻的网民也更容易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而且标新立异、张扬自我的个性越发凸显。“雷人、狗血、废柴、抓狂、闷骚”等这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受港台综艺、影视作品影响的方言词开始在互联网流行。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上网成为了一件随时随地可以完成的事情。网民的年龄层次呈现向高龄和低龄两端发展,而受教育程度则继续被拉低。网民往往绞尽脑汁,不断创造和使用新奇的语言,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以至于以“屌丝”为代表的脏话粗口也成为了现象级的网络方言词。从求新求异到标新立异再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网络方言词的发展如同一面镜子一样映射着网民的结构变化,也折射出了他们心理需求的变化。
(二)幽默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4%。城镇网民占比72.6%,年增幅高达7.7%,远超农村网民的年增幅2.7%。”[6]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互联网成为网民宣泄情绪、释放压力的重要渠道。方言词在网络语境下,交际双方和交际方式的偏离,造成了语音形式、词汇形式、词义内涵的错位,突出了表达内容,产生了幽默效果。
如来自吴方言的网络方言词“伐开心”,可追溯到微博网友大咕咕咕鸡的《黄浦江与领导的故事》,接着在《龙与天子》的故事里被演绎成“伐开心,要包包”。这句话装萌扮傻的幽默风格与“‘包’治百病”消费主义观念极为贴合,随后各大商业网站、时尚媒体展开了一轮全新的“伐开心、要包包”的传播攻势,“要包包真的是因为伐开心吗”,“伐开心,要包包,最不可理喻的生物”,“伐开心就要买包包 女生的包到底有什么魔力”……这股消费主义潮流蔓延的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民的批判,涌现出了一批反潮流的段子。“伐开心,买包包,昨天一天买了104个生煎包”,“伐开心为啥要买包包啊?因为‘包’治百病啊”……网络段子将“伐开心”的传播推向了高潮。如关于《西游记》的段子:“猴子对师傅说:‘师傅,今天没打到妖怪,伐开心,要包包,要四个。’ 师傅白了猴子一眼说,‘肉包还是菜包’。” 该段子利用文学与生活、男性与女性等多重语域偏离,增强了网络方言词的幽默效果。“伐开心”在反复传播后最终跨进了2016年网络流行语的行列。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的不法行为证据材料,向地方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收取费用,这种行为构成违法,但是,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敲诈勒索犯罪的客观表现是对行为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恐惧不敢抗拒。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掌握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的违法犯罪证据材料,迫使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支付费用,以便帮助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消除影响,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而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试图花钱消灾,向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支付有关费用,其行为构成违法,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地方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的渎职失职或者其他犯罪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力犯罪。
从“麻麻”、“彭麻麻”到“彭麻麻折服世界的十大神器”,从“山寨货”、“山寨文化”到“山寨‘伦敦塔桥’为哪般”,每一个网络方言词都可以清晰地寻找到从词语幽默走向语篇幽默的过程。“人人都是段子手”,“不搞笑就死”的网络传播现象,体现了网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批判,也是他们智慧地表达自己观点和立场的重要手段。
(三)恶搞
恶搞心理的成因与新奇、幽默并无二致,而在它诙谐、滑稽的表象下,隐藏着是虚无主义的内涵。恶搞和幽默的最大区别是无意义,如果说幽默还是为了批判、反讽、趣味,那么恶搞就是纯粹搞笑,为了消解了一切的权威、价值和意义。
如网络方言词“蓝瘦香菇”原意为“难受想哭”,来源于广西南宁小伙子因失恋发到QQ空间的视频。当“难受想哭”变成网络方言词“蓝瘦香菇”,失恋这一被众多文学艺术作品所描绘的惆怅之美就完全消解了,也正是因为这种意义的消解激发了互联网的恶搞传播。表情包、小段子、小视频、改编歌曲甚至线下注册为商标,这些常见的恶搞手法瞬间就将“蓝瘦香菇”推向微博话题榜和热搜榜。
许多网络方言词的传播都符合网民的恶搞心理,如“稀饭(喜欢)、男票女票(男朋友女朋友)”,它们与普通话语词相比,传统爱情婚姻观众那份沉重被消解了,更多的只是年轻网民之间单纯的情感表达。这些网络方言词并不会被恶搞传播,但是在消解意义之后更受年轻网民的欢迎。
“文字显示声音。声音显示心灵的体验。心灵的体验显示心灵所关涉的事情。”[7]文字表达心灵体验,心灵体验也在寻找恰当的文字去表达,网络方言词就适应了这种表达的需要,无论是张扬个性、批判现实还是宣泄苦闷,无论是曲折还是直接,网络方言词都满足了网民们心灵表达的需要。
三、传播媒介导致网络方言词的分化
从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直至今天的网络传播,每一次传播变革的浪潮中,都可以看到一批批方言词趁势进入普通话。上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发源地,吴方言中的“尴尬、弄堂、阿飞、瘪三”进入了共同语。上世纪80、90年代,港台地区的影视、综艺等节目进入大陆,“埋单、搞掂、生猛、打拼、八卦、穿帮”等来自港台地区的方言词开始进入大陆日常生活。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互联网上每天产生的方言词不可胜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方言词都能在网络上流行,网络媒介加速了它们的传播,也加速了它们的消亡,最后仅有极少部分进入社会交际层面。在网络方言词的传播行为中,羊群效应和马太效应,对其分化造成重大影响。
(一)网络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的羊群效应
网络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邮件、QQ、微信、微博、博客、贴吧、论坛、游戏等,其中微博、微信、游戏等用户基数大、传播速度快,集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传播形态为一体的传播工具为强势传播工具。如网络方言词“伐开心,买包包”最早出现在微博网友大咕咕咕鸡的故事里,再如“坑爹”最早出现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
QQ群的群主、微博、博客中的大V,贴吧和论坛中的吧主、版主或网红常常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如网络方言词“屌丝”就出自著名贴吧“李毅吧”,“内牛满面”出自魔兽论坛著名作家有时右逝的小说《如果宅》,“老炮儿”借助了电影《老炮儿》的网络营销,当众多导演明星在微博、微信上纷纷转发后,该词为更多网民所熟知。
一旦意见领袖利用强势传播工具进行传播,将获得更加惊人的传播效果。如“蓝瘦香菇”的引爆互联网主要归因于两位明星在微博上的传播。2016年10月10日林更新发微博“深夜香菇”,当天引发5445讨论、1004转发、7万点赞;同一天演员颖儿发微博“前两天突然急性肠胃炎进了医院,蓝瘦,香菇”,当天引发3938讨论、3347转发、1万点赞。“羊群效应”放大网络方言词传播的能量,推动着它们进入更广阔的传播领域。
(二)网络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源于《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原先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效应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反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网络方言词受到马太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网络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中,越流行的网络方言词越受到传播者的追捧。
网络方言词“蓝瘦香菇”进入传播高潮期之后,三只松鼠、维达、纯生啤酒、喜士多便利店、海尔洗衣机、必胜客等近二十家品牌借势营销。如:“猛然发现,今天才周一,还要上四天的班~#蓝瘦香菇#” (海尔家电微博), “#萌到深处自然醒#假期就像气球和你的笑容,明明想抓紧,却总在不经意间飘走,蓝瘦香菇。” (三只松鼠微博),“蓝瘦、香菇?至少还有它为你擦干眼泪~” (维达Vinda微博)”。追逐网络热点,是企事业、团体等机构组织在网络营销中常用的手段,而使用网络流行语是营销文案最惯常的手法之一。
在以互联网营销闻名的小米公司的微博上,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网络方言词在传播中的逐渐分化。那些已经被普通话接纳并且流行度较高的方言词出现频率最高,如“给力”85次,“山寨”15次;被普通话接纳但流行度不高的方言词出现频率较低,如“忽悠”出现1次,“死磕”1次;而没有被普通话接纳虽然流行度较高但是出现频率也很低,如“猴赛雷”1次,“蓝瘦香菇”0次,“伐开心”0次。类似“蓝瘦香菇”这样流行度很高,甚至成为2016年现象级的网络词语,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
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可以看到今年最热的网络方言词“给力”,不仅进入了普通话语汇系统而且有从一般词走向基本词的趋势。在人民网网站内搜索,一共有60864篇有关“给力”的页面;在新华社网站内搜索,一共有1360000篇相关页面,“给力”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在人民网网站上,“给力”还分布在从财经到文化,从国际到地方共50个频道上。其中游戏频道出现次数最多,共8921次;最少的江西频道也出现了36次,“给力”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作为形容词的“给力”可以被大多数的副词修饰,如“不给力,更给力,共同给力,十分给力”等;它也经常修饰名词并作为谓语出现,如“模式给力,技术给力,队伍给力” 等,“给力”与其他词语搭配使用的能力越来越强。从使用频率、使用范围、语法功能这三个维度来考量,“给力”进入普通话基本词的条件已经基本符合,所欠缺的只是时间。
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这是方言词在互联网上传播并扩大影响力的必由之路。其中意见领袖和强势传播工具对网络方言词的传播起到了推手作用,而组织和大众媒体在其中的追逐热点,推波助澜使得网络方言词中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获得传统媒体网站、商业网站等权威媒体的认可,最终将打开网络方言词进入共同语层面的大门。
五、法规辞书规范网络方言词的吸收
从网络方言词的生成、传播、分化到最终进入共同语层面,进入到国家机关、传统媒体、学校教育、法律法规的语言使用中,网络方言词就会受到共同语规范的制约,这种制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二是权威辞书。
(一)法律法规的制约
当前规范网络语言使用的地方性和行业法规较多,如《上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禁止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使使用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再如《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禁止使用“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等。”然而,这些都不是针对网络方言词的规范标准。
网络方言词在共同语层面可以依据的法规只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四条到第十六条规定了普通话和现代汉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明确了方言使用的情形,规定了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但是这部法律所调整的是社会交际行为,而不是公民个人行为。因此在社会交际行为,尤其是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应审慎使用网络方言词,而公民个人行为则不在规范之列,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网下。
(二)辞书的制约
作为我国语言规范的标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历次改版都会吸收一些方言词,其中只有小部分来源于网络方言词。辞书收录“新词、新义、新用法的增收依据的是通用性和稳定性原则。所谓通用性是指在社会上使用频率高、使用范围广,大多已被主流媒体认可的; 所谓稳定性,是指词形、词义及其用法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8]如《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收录的网络方言词“给力、山寨、雷、死磕、忽悠”等词性词义已经稳定,使用频率高、范围广,并且能被互联网以外的其他主流媒体认可。大多数的网络方言词只存在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之中,因其使用频率较低,范围较小,因此不可能被辞书收录,也不可能进入社会交际层面。
对于网络方言词的吸收和使用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无论是法律的规定还是辞书的选择都持有极为审慎的态度,即不强制立法禁止,扼杀语言的创造力,也不追随潮流,见新就收,破坏语言的稳定性。加强引导网络方言词的使用,审慎吸收,才能让网络方言词真正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
六、结语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徐通锵指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9]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语言的统一标准也随之而变。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即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着统一的标准,但其具体的内容也一直在变化中。当今互联网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着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变化着,语言的统一标准也遭受着剧烈地冲击。字母、符号、外来词甚至图形图像,当然还有地域方言都在试图影响现代汉语的传统表达方式。
[1] 网络新词一夜红 语不“雷”人死不休——今天你“雷”了吗[NB/OL].(2008 - 10 -14)[2017-04-10]. http://media.people.com.cn/GB/8167480.html.
[2] 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1.
[4] 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93.
[5][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39, 37.
[7]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商务印书馆,2005:242.
[8]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概述[J].辞书研究,2013:2.
[9]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73-191.
[责任编辑:姚青群]
H136
A
1008-7346(2017)03-0086-06
2017-04-29
王玮,女,福建福清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与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