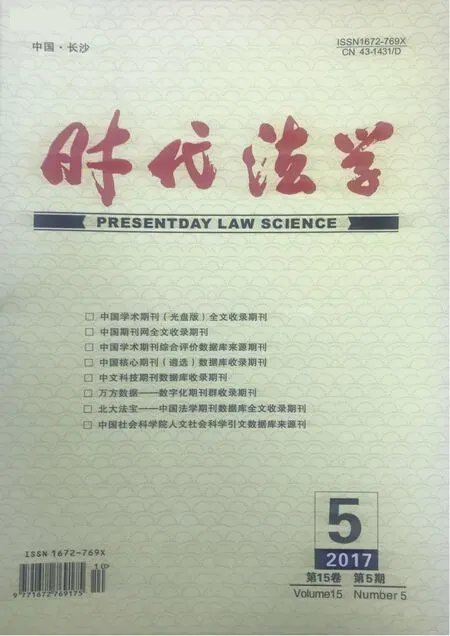“可能的语义”无法完成的任务
——论“可能的语义”维护罪刑法定原则作用的局限性及出路*
赵 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可能的语义”无法完成的任务
——论“可能的语义”维护罪刑法定原则作用的局限性及出路*
赵 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都将“可能的语义”作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工具,主张解释结论不能超越法条文字的“可能的语义”。然而,基于“语义”无法进行自我定义这一事实,“可能的语义”不仅无法独立承担重任,反而可能因解释者的主观主义而得出恣意的解释结论。从根本上看,这是源于刑法概念无法克服的不明确性。对此,应承认“可能的语义”作用的局限性,运用一种综合的约束机制以维护解释结论的正当性。
可能的语义;价值判断;罪刑法定
一、“可能的语义”承载的重任
近年来刑法学领域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成为一个热门的争议领域。对此,有学者提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已形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之势。两大阵营彼此间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构成要件的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之间的关系、刑法漏洞的弥补方式、解释方法的选择或偏好以及解释者的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的看法都存在实质分歧*劳东燕.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J].法学研究,2013,(3).。可见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纷繁复杂,两者的对立似乎尖锐而无法弥合。不同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与批评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术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张明楷.学术之盛需要学派之争[J].环球法律评论,2005,(1).,刑法学界对此争论的关注兴趣也集中在两者的分歧之上。然而,在这些争论背后,被忽视的一点是,两大阵营都将“可能的语义”作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工具,都主张解释结论不可以超越法条文字的“可能的语义”,从而使得“可能的语义”成为划分合法解释与不允许类推解释的最终判断标准。
其中,形式解释论者强调以“可能的语义”作为刑法解释的界限,认为“文义”既是一切解释的出发点,也是一切解释的终点*苏彩霞.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适用[J].中国法学,2008,(5).。“在对刑法规定进行语义解释时,如果某一行为并未被通常语义所包含,则须进一步辨别是否在语义的射程之内。只有当它被可能的语义所包含,但存在多重含义时,才需要采取其他各种方法最终确定其含义。”*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J].中国法学,2010,(4).与此同时,实质解释论者也赞同解释结论必须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认为“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在行为不能被构成要件的表述所包含(不处于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时,当然形式优于实质,即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4).
因此,尽管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对立与分歧,但二者都认为,“可能的语义”能够成为限制解释结论的有效手段。然而,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可能的语义”能否担此重任,成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最后的底线?
二、“可能的语义”的局限性
“可能的语义”尽管被赋予重任,但由于“语义”无法自我界定,使得形式解释论者的主张无法成为现实;实质解释论者则基于实现实质正义的需要对“可能的语义”进行了主观界定使得“可能的语义”的解释有主观主义的危险。究其根本,“可能的语义”作用的局限性是刑法条文中大量不明确法概念的存在导致的。
(一)局限性的表象:“语义”无法自我界定带来的危险
形式解释论者寄希望于将“可能的语义”作为禁止恣意的有力武器。他们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为形式解释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当前的刑法知识给予了理念支撑。”*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J].中国法学,2010,(4).“司法是以现行法的存在为前提的逻辑演绎,它不能质疑法律,更不能指责法律,而只能将既定的法律适用于个案。如果司法不以法律为归依,而是以司法者的意志作为处理个案的依据,定罪量刑出入于法律之外,那么刑事法治必将荡然无存。”*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但是,“可能的语义”自身能否为解释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呢?
形式性的思考倾向于将思考结论约束在一个相对明确的范围之内,那么这种形式思考必须具备的前提是,只有存在一个可以识别的具体的对象物,才有可能进行形式性思考。而实质性思考则意味着对具体事物的某种抽象和概括,侧重将其概念化、类型化。概念是一类事物的集合,而其自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抽象化*[美]威廉姆·沃克·阿特金森.逻辑十九讲[M].李奇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38.。因此,形式解释论对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的强调,其前提是,必须存在这样的可供形式思考和判断的具象,说穿了,其理论前提是:法概念必须具有明确性,只有如此,“可能的语义”才能为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对象。然而,法概念所具有的抽象性特征使其内容无法具有形式解释论所要求的明确性,也就是在“可能的语义”的标准中,“语义”无法进行自我定义。
“语义”无法自我定义这一难题,不可避免地要求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加入价值判断因素。例如形式解释论者反对将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解释为效用的丧失,认为“毁坏”仅限于财物的物理状态的破坏,这才是其可能语义范围的应有之义。但在对我国刑法中盗窃公私财物的“财物”进行解释时,关于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几乎所有的解释者——包括形式解释论者——都投了赞成票。但是,盗窃罪中的“财物”按照形式解释论者的定义,无论如何也应当是有形的财物。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可能的语义”范围?可以肯定的是,语义本身是无法承担此项重任的。形式解释论者寄希望于刑法语义本身给出限制恣意的标准,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在现实当中无法成为可能。对此,实质解释论者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由处罚必要性,也就是保护法益的正义思想来决定“可能的语义”的范围,来决定解释结论。然而,这种对于“可能的语义”的界定方法也值得商榷。
实质解释论者以保护法益为核心,强调处罚的妥当性,强调正义价值的实现。例如,实质解释论所举的两个典型例子——也是形式解释论者所强烈反对的——将他人饲养的鸟放飞解释为毁坏财物,即采取效用侵害说来解释“毁坏”;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中的“冒充”解释为“假冒”和“充当”,从而真军警抢劫也属于冒充军警抢劫。对此,实质解释论倡导者张明楷教授给出的解释根据是:“一般的效用侵害说认为,有损财物的效用的一切行为,都是毁坏……毁坏不限于从物理上变更或者消灭财物的形体,而是包括使财物的效用丧失或者减少的一切行为。”*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025-1026.“对《刑法》第275条的毁坏的理解,不能单纯以人们的日常用语含义为根据,而应注重刑法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所要保护的法益。虽然对毁坏的解释超出了日常用语含义,但只要没有超出该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又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就应当采取这种解释。”*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0.而对于将真军警抢劫解释为冒充军警抢劫,则是“对不同法条中的冒充作出不同解释,正是为了实现刑法的体系性、协调性……仅将刑法第263条中的冒充解释为假冒,就会造成不协调、不均衡的现象。”*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9.
这里,实质解释论认为“可能的语义”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义,另一部分则是没有那么普遍使用,但是仍然属于语义范围内的情况。后一部分的情况就比较可疑了。这里就将“可能的语义”置换成为了解释者所认为的,语义所包括的范围。那么,对于实质解释论者来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语义是不是“可能的”语义?显然,是由他们所认为的保护法益的正义思想所决定的。在上面的例子中,实质解释论者所反复强调的,都是出于保护法益的目的,这本来无可置疑,心中充满正义是法律人的基本素质和要求。但问题是,以“正义”(或保护法益的需要)来作为解释的最终根据,显然说理并不充分。而且最重要的是,以正义作为标准,使得“可能的语义”完全丧失了禁止裁判恣意的过滤功能。而以“法益”作为限制解释的努力,也是差强人意。虽然法益概念被公认为现代刑法的核心,但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法益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其内涵由物质向精神扩张;其范围蔓延至潮个人法益;扩展至非人本思维。法益概念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境*舒洪水,张晶.近现代法益理论的发展及其功能化解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9).。“一方面,如果坚持严格实质的、实体的法益概念,发挥法益概念的体系批判机能的同时发挥其体系内在的机能,那么就无法在法益的框架内把握而必须准备更大的框架(例如,加之以规范妥当性,行为伦理等框架)……因此就需要承认在刑法法规领域中法益关联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弃严格实质的、实体的法益概念,满足进发挥法益概念的方法论的、目的论的机能或体系内的机能,那么法益概念的内容就会非常的一般化、抽象化,因此就强烈具有保护普遍法益、中间法益的倾向。”*[日]关哲夫.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A].王充译.赵秉志.刑法论丛(第1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58-359.简言之,对于实质解释论者来说,他们并没有采取“可能的语义”作为解释的限制标准。解释的结论实际上是被解释者内心的正义情感即法感情所决定的。但是对于这种“正义感”的具体内容实质解释论并没有进行详细说明,也没有给出这种正义感作为裁判根据的正当性依据。可以说,这种解释路径中,法感情缺乏法规范的有力制约,很可能得出虽然满足裁判者主观正义,但造成主观主义恣意的裁判后果。
可见,基于“语义”无法进行自我定义这一事实使得“可能的语义”的作用效力大为减弱,形式解释论回避了这一问题,而实质解释论则通过处罚必要性的引入使得“可能的语义”的界定具有使解释结论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这是“可能的语义”局限性的表象,从根本上来说,其局限性源于不明确的法概念。
(二)局限性的本质:刑法中不明确法概念的大量充斥
德国学者恩吉施根据概念的明确性程度,将刑法中的概念分成了四组:(1)数字性的因此属于绝对确定的概念;(2)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以在整个社会中广泛一致的应用为基础的分类性概念;(3)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功能性概念,它并非通过相同的含义展示,而是通过物质的相同的社会性功能而被构建;(4)纯粹的价值概念(通常称为“概括性条款”)*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形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其中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和纯粹的价值概念都被认为是不确定的概念,而它们占据了刑法典中相当大的比重。此外,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也并非那么“明确”。例如对于故意杀人罪中的“人”该如何理解就产生了争议。关于出生的标准存在阵痛说、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独立呼吸说。而关于死亡也存在综合标准说和脑死亡说等*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47.。因此,对于描述性构成要件来说,它也不能对自身进行定义,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根据德国学者律特斯(Rüthers),当一个构成要件或一个法律原则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根据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予以规定时,就属于一般条款。在方法论上,这种情况被标示为一种法律的内部漏洞,因为在穷尽了所有解释工具之后,法律价值的目标仍然保持着开放性,这时法官必须将判决导向一个法律本身并没有规定的一个价值标准。并非所有不明确的法律概念都意味着一个一般条款,但是所有一般条款中都必然包含着不明确的法概念*Zwei Zitate,von Erick Gatgens, Ermessen und Willkür im Straf-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Verlag Lang,Frankfurt am Main, 2007, S153-154.。而立法者之所以设置这样的对法安全构成危险的一般条款,是为了使规范能够包含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使法律后果无漏洞地或适应性强地使用在相关事实上。规范适应能力的强调,是为了致力于个案正义,也就是它是与正确裁判相关联的。一般条款的适应能力赋予法官以特殊的授权,导致了司法机关地位的强化*Vgl. Erick Gatgens, Ermessen und Willkür im Straf-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Verlag Lang,Frankfurt am Main, 2007, S155-156.。德国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德国,法实证论已经走向了末日,各式各样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例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概念大举入侵法律生活的各个层面*[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M].苏慧婕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02-103.。
围绕概念的不确定性,德国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阐释模型。根据Heck的看法,概念在通常情况下都不是绝对的、稳定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特征。一个概念的内涵是围绕着概念的核心含义的。而根据耶实(Jesch)的观点,概念的辐射范围是非常广阔和弥散的,但其核心含义却相对来说特别地小。概念的核心含义和边缘含义的区分界限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而法秩序是通过概念的核心含义予以建构的。概念的核心含义保障了法秩序的稳定性,防止了法律混乱。但有问题的是,概念的核心和边缘并不总是容易区分的。依照耶里内克(Jellinek)的观点,如果没有界限,概念也就不称其为概念了。但是确定的概念具有单一的界限,对于一个现象从属或不从属于这个概念可以进行明确的判断;不确定概念也可以就一个现象是否从属于自身进行判断,然而其获得的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判断(存疑的判断),不确定的概念也存在自身的界限,只不过这个界限是不明确的*Zwei Zitate,von Erick Gatgens, Ermessen und Willkür im Straf-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2007, S179-180.。对此,加特根斯(Gatgens)指出,不确定法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为了减少其模糊性而对它进行的精确的说明,不能通过语义解释的方式达成。对不确定法概念的解释困难在于,它属于一种中性的领域,语义学对它的阐释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它是“存疑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不确定概念为司法者的自由裁量开启了一个空间。法律适用者必须找到语义解释以外的其他方式来探明不确定概念的内涵,这就因此介入了法律以外的大量因素*Vgl. Erick Gatgens, Ermessen und Willkür im Straf-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2007, S181-182.。
美国学者指出,法律语言从来就不准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法律语言变得完全准确。而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语言的意义不仅在法律界之内交流,而且还超越法律界——直到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一交流的范围越广,法律语言准确性的可能就越少。一些聪明的人也许可以运用最精密的工具——例如数理逻辑,来分析法律问题。但是法律最终必须与普通人交流。因此法律的语言就不可能精确般的完美,因为一个词的完美的抽象概念会引起人们的不解和怀疑*[美]大卫·梅林科夫.法律的语言[M].廖美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451-460.。
综上所述,“可能的语义”无法承担防止恣意的裁判、维护罪刑法定的重任,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刑法中大量的不明确概念的存在,使得概念的语义无法明确呈现出来,而必须附加其他的判断因素,而这些因素的介入,不仅不会实现控制法官恣意的效果,反而会使法官获得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学者们之所以对“可能的语义”在禁止恣意上发挥作用寄予了很大希望,很大程度上也是诉诸了一种“感觉”因素,因为所谓的“可能的”含义,无外乎就是当某种解释结果符合我们头脑中的“预期”时,就认为它在“可能的语义”范围之内;而当某个解释结论超出我们的预料,使人很惊讶时,就认为超出了“可能的语义”范围。这种对“可能的语义”的直觉式的理解,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对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定作用。但是直觉式的理解终究无法提供一个客观的控制标准,这种理解本身就说明,“可能的语义”究竟是怎样的语义,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因素。
三、出路:“可能的语义”基础上,一种综合判断方法的提倡
尽管“可能的语义”仍旧无法做到纯然的客观性和形式性,以单独实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重任,但是“可能的语义”这一标准仍然是不可放弃的。“可能的语义”为解释结论的可能射程提供了一个大致框架和基本范围,它对于解释结论的正当性具有一种“预判”功能,一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解释结论无论如何被巧妙地解释进“可能的语义”范围之内,它终归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解释结论。与其说“可能的语义”是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终标准,不如说它是一个判断的起点。有学者主张,如果某种解释结论明显使得社会一般公众感觉突兀,超出了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那么这样的解释结论就属于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付立庆.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J].中国法学,2013,(4).。但是,以一般公众对于解释结论的直觉作为判断解释结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标准仍然存在主观主义之嫌。在是否属于“可能的语义”范围无法清晰得出结论之时,需要一种综合的判断方法。
拉伦茨在其著作中介绍了最早由菲韦格所提出的一种“类观点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讨论程序”,这种思考方式围绕着问题本身所划定的范围进行讨论,其中涉及的法律观点则是指用以解决法律问题的,并且预期可能获得普遍认可的论据。这种方法主要可以适用于合议庭的法官进行评议。在法律讨论中,某些观点被提出和审查,然后被扬弃或保留*[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5-26.。这也许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进行理解。根据其“交往理论”的法律商谈理论认为,“法的合法性不在于孤独的主体性,而在于交往中多视角地主体间性,法律合法性最终依赖于一种交往的安排,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法律同伴必须有可能考察一有争议的规范是否得到或有无可能得到所有相关者的同意。”*孙桂林.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意义[J].法学杂志,2010,(3).他认为,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商谈性的共识。例如,在对话中,当有人提出“P”是真的时,如果其他参与对话者也相信陈述“P”对于客体“X”是正确的,那么“P”就具有了真理的内涵。也就是,真理是多个主体之间通过商谈而达成的共识。这样,对于真理的认识就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单向关系——主体凭借自己的先验和经验对客体的认识*陆玉胜.商谈、法律和社会公正——哈贝马斯法哲学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85-86.。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商谈不能像德沃金所设计的在逻辑语义向度的封闭领域之内,而是应当在语用的向度内,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进行多主体多角度的进行*孙桂林.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意义[J].法学杂志,2010,(3).。在“类观点学”的指引下,裁判者在法规范的诠释中的主观因素或许可能通过其他人的主观因素予以制约,从而实现禁止裁判恣意的目的。由此,在观点的交流当中,例如某人提出某种解释观点,他必须对他解释和判断的理由作出说明和展示,在获得其他主体的赞同时,他的观点就得到了“客观化”,也就是,这种交谈的过程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主观任意和不确定的,只不过,这种对于“客观化”的追求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唯一正确”般的确定性*张志铭.法律解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1.。
总之,一种综合制约机制有利于制约解释者的主观主义,也就是使用综合控制手段方式能够避免恣意的裁判。而这种综合控制手段,应当围绕着裁判理由的可交流性进行展开。在实体控制上,目前为刑法学者广泛肯定的“语义的可能性”,事实上也是要求解释结论能够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德国学者指出,文义解释应答具有相对优位性,即“如果一个个案很清楚地不能被包摄到法条之下,这个法条就不能直接适用于此案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目的解释仍然将其包摄在法条之下,那只能属于应当禁止的类推解释*[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M].蔡圣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0-83.。而在程序控制上,已经有学者主张建立判例式的案例指导制度、推进司法文书的改革,实行判决公开,尤其是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判决理由*王彬.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8.。在法官自律上,要求法官对解释法律的过程是否合宪进行审查。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解释结论不被解释者的主观主义所操纵,从而保证裁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AnImpossibleTask:DiscussionontheLimitedFunctionofthe“PossibleSemantic”asMaintainingthePrincipleofLegality
ZHAO Xi
(InstituteofLaw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20,China)
Both formal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substantive theory take the agreement that the “Possible Semantic” is the crucial instrument in Maintaining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That is,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articles should not beyond the “Possible Semantic”. However, basing on the fact that the legal text could not define itself, the “Possible Semantic” is unable to undertake such task independently. Sometimes even the “Possible Semantic” could cause the intolerable flexible interpretations. Basically, this is due to the uncertainty nature of the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 To this issue, we should admit the limitation function of the “Possible Semantic”,and utilize various of restricted condit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result.
possible semantic; value judgment;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2017-05-25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7年9月21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资助编号:2016M601212)。
赵希,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教义学。
DF61
A
1672-769X(2017)05-0031-05
DOI.10.19510/j.cnki.43-1431/d.2017092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