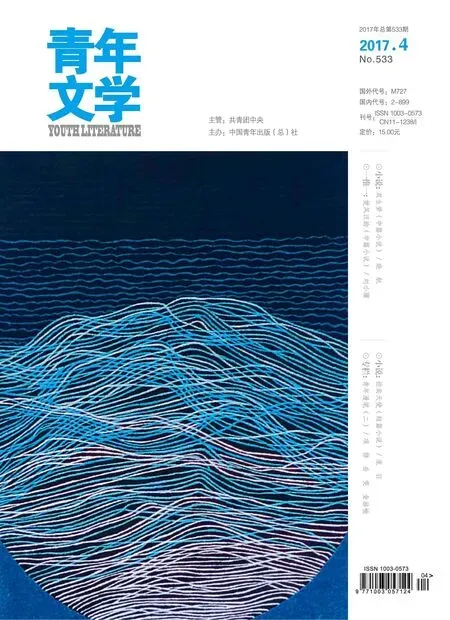青天歌
⊙ 文 / 马卫巍
青天歌
⊙ 文 / 马卫巍
马卫巍:一九八二年生于山东阳信。作品散见于《散文》《山花》《时代文学》《小说选刊》等刊。业余习字画画儿。曾被评为第二届“齐鲁文化之星”。
方四斤是个能围着桌子转一圈的人。这是句行话,大锣、小锣、板鼓、二胡、坠琴……这些响器每一样在他手里都能玩出个花样来。用王二瘸的话说:“这家伙就是他娘的有能耐,玩吗吗会,玩吗吗精!”王二瘸是个提大锣的,提大锣就提大锣吧,可他娘的连个大锣也提不好。有回杨家村一位老先生去世,专门请了王二瘸提大锣。人家给的钱多,弄得王二瘸像打了鸡血似的把锣敲了个窟窿,气得主家的几个亲戚差点半途抽签儿,他也被行里人嘲笑成洒狗血的主儿,为此灰头土脸好些日子。但这些响器到方四斤手里就变成活得了,马上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到处都透露着生机。每逢有人家办红事或办白事,只要武场上有方四斤,准能博个满堂彩。
方四斤这个本事是与生俱来的。方木伽活着的时候早就在四邻八乡说了无数遍了,他领着方四斤穿梭于各种红白喜事之间,在文武场中打转转,逢人便说:“我这儿子天生是干这行的料,大家伙儿以后多照顾着点儿。”说罢还会拱手作揖。方四斤真没给方木伽丢脸,无论什么响器准能弄得有板有眼,颇有大家范儿。方木伽打心里高兴,脸上笑得拧成了一朵花。他的两只眼睛本来就睁不开,这一笑就把眼睛给拧没了。他摸摸索索地搂起方四斤,摸着他粉嘟嘟的脸蛋说:“我的亲儿子哎……”
方木伽捡到方四斤时,这小子已经离着断气不远了。那天他听到刘庄有户人家办白事,一大早就背了二胡拿了拐棍出门。皑皑白雪覆盖大地,把成片的麦苗都盖起来了,整个世间就成了苍茫一片。寒风凛冽,把日头吹进了云朵,把雪粒儿吹进脖领子里,冻得人直哆嗦。这种鬼天气没人愿意出门,都待在家里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呢。方木伽不行,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光杆一人待在家里,摸着空空如也的饭盆子,他的牙花子都咂得生疼。他最盼着就是别人家办红白事,这样就能光明正大地坐在四方桌前拉一曲《青天歌》或《喜临门》,讨几杯热酒弄几口小菜,临了还能盛回些残羹剩饭。若是碰上好主家,赏点小钱也未尝不可。他们这种人往往不请自到,都是伸长了鼻子寻着味来的,主家也客气,想把事情办得体面些,谁会在乎一桌子饭菜呢?
刘庄死了人要办一场白事,这真是个好消息。只要天上不下刀子,方木伽就是冻死在半道上都乐意。在三尺多厚的雪地里摸索前行,他的步伐踉跄,弄得整个人像在茫茫原野里跳舞似的,十分滑稽可笑。雪已经把道路封上了,村庄与村庄、道路与田野连在了一起。有的地方雪厚一些,有的地方薄一些,偶尔来一串脚印也是老鼠或者兔子的。方木伽看不见这种景象,心里却能感受得到。他心里敞亮着呢!他身体里升腾起一团火苗,仿佛闻到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酒菜正冲着他摆手。那个香啊!
方木伽快走到刘庄的时候,需要穿过一个草场。草场上堆着一个个柴火垛,落满了雪,像白色的坟头。他看不见,但手里的棍子碰到柴火秸后,雪花扑簌簌掉下来荡起一阵微尘。方木伽跌跌撞撞走了一段路,浑身上下透了热气。他想歇一歇继续赶路,便摸摸索索地靠着一个柴火垛坐下来。他屁股刚着地,耳朵里听到一阵细微的啼哭,惊得又腾地站了起来,扑通摔在雪地里。
“见鬼,见鬼!”方木伽心里说道。他连忙起身把身上的雪粒拍打干净。但啼哭声似乎越来越亮,弄得心里一惊一乍的。他蹲下来,循着声音摸索起来。他耳朵好使,依声寻源并不难,这一摸,就把方四斤给摸出来了。
“哎呀,这是个孩子。”方木伽小声嘟囔了一句,慢慢把孩子抱了起来。“这是谁家的?”他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心下便释然了。“唉,这是个私生子,真他娘的作孽呀。”孩子裹着一床小褥子,但不足以抵御严寒。方木伽摸了摸孩子的脸蛋,冰凉冰凉的,又慢慢顺着褥子摸下去。
“是个带把儿的……”方木伽叹了口气说,“可怜的娃,他们怎么就那么狠心呢?可是你遇到我,我也养活不了你。我一个瞎子自己吃饭都是问题,再加上你岂不要饿死一对儿……应该有个好人家寻到你才是。”他把褥子裹了裹,又把孩子放回原处。
方木伽寻到棍子继续前行。草场不大,不一会儿他就走了出来。有风吹来,他的脖领中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冷不丁打了个冷战。孩子的哭声虚弱得很,像针一样扎人。方木伽站了一会儿又返回来,他解开棉袄把孩子裹在里面,然后用腰带勒住。方木伽说:“这大冷的天,没人会来……”
这孩子很奇怪,方木伽把他揽在怀里的时候,竟然睡着了。
方木伽到刘庄时,其他拉二胡的、吹笙吹唢呐的、打鼓敲锣的人都来了。他一进门就鞠躬抱拳道:“节哀顺变,节哀顺变……愿亡故人早登极乐……”然后走到白事方桌前拱手:“对不住各位,来晚了。”能在这场合坐在一块的都是苦命人,寒暄几句便抄起家伙奏起了哀事乐。一曲作罢,孩子也醒了。方木伽拿起一块儿点心嚼碎了塞到他嘴里。同行人摇着头说:“方瞎子,你这是自找苦吃啊,你一个人的嘴都是他娘的无底洞,又来一口,以后可怎么活?”方木伽叹口气说:“听天由命吧。”
方四斤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只有他自己知道。方木伽家徒四壁,袋中无粮,要想喂活孩子,有一半靠的是运气。白天尚且好说,到了晚上却是十分难熬。方四斤饿得直哭,上气不接下气,好几次都哭得背过气去。但哭也没有办法,即便哭下天来,方木伽也变不出粮食。实在没办法了,方木伽就喂他唾沫,吐一口喂一口,方四斤吃得津津有味,竟然止住了哭声。方四斤对于唾沫的依赖,一直等到他八九岁那年。有时候饿了,方四斤就说:“爹,我饿了。”方木伽回道:“儿,我也饿了。”两个人默默无语,然后一前一后开始拼命地咽唾沫,咕咚,咕咚,便都昏昏沉沉睡着了。
方四斤一鸣惊人是在张王庄张乡约的结婚典礼上,那年他十二岁。他跟着方木伽来此混饭吃,其间艺人们喝茶休息,唱小曲的小彩凤拿他开玩笑:“四斤,你这么大了还跟着你爹混饭,羞不羞,再说,我们可是凭手艺吃饭的……”小彩凤拿腔作调,兰花指跷起来,活脱一个假娘们。方四斤脸上觉得发烧,又不好意思反驳,便拿起方木伽的二胡独自拉了起来。他拉的是《喜临门》,轻快、俏皮,弓法指法极其复杂。只见他的手上下翻飞,好像激荡起来的水花儿,他闭目摇头,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忙活喜事的人围过来,都忘了给道喜的人端茶递水,一时间迷在那里。一曲作罢,张乡约带头喊了一声好,众人跟着喝彩。方木伽连忙说:“小孩子不懂事,惊扰大家了,在下赔罪,赔罪。”张乡约却说:“赔什么罪,我看这孩子手头上利索着呢。来来来,再来一曲《百鸟朝凤》,我特喜欢这曲子。”方四斤也不推辞,顺手拿了小云雀的唢呐张嘴就来。他干脆站到椅子上,鼓起腮帮子铆足气力,把这曲儿吹得滴水不漏,干净利落,圈里圈外皆都喊好。完事之后,小彩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这孩子算接上你爹的班了。可惜,咱这行也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情,看人眼色,听人使唤,难着哩。”
再难,也得吃饭。这回张乡约赏了他们爷俩双份的钱。
方四斤十八岁那年,方木伽死了。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木,只好用一张草席子裹起来下葬。方木伽这人活着的时候人缘好,死后街坊四邻都过来张罗丧事,以前的老伙计也过来吹吹打打送了他一程。方四斤哭着给众人磕头,自己无以为报,也只有磕头答谢了。
谁承想,方四斤从事红白事这个活路一干就是七十年。七十年来多少人在他的唢呐声中结婚生子,又有多少人在他的唢呐声中下葬入土,连他自己都记不起来。现在,他变成了一只蜗牛了,头几乎拱地,鼻涕滴下来,拉成一条浑浊的长丝。他的腰已经弯成了一只虾米,或者说像一座拱桥,在长廊上缓缓移动。王寡妇拄着拐棍从他身边走过,像没了劲道的发条。方四斤听得出她的声音,像风儿的声音柔得很,吹到心里,就能感到一阵温热。他缓缓停下来对王寡妇说:“你身体不好,应该多躺躺。”王寡妇像回答他又像自言自语:“都没几天活头了,还不如走走看看。”方四斤不敢看王寡妇的脸,在他心里不管王寡妇有没有衰老,他都觉得王寡妇的脸就像一朵牡丹花,开得正浓,光鲜得晃人眼睛。方四斤当年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这张脸就烙在心里了,烫烫的、刺刺的,无时无刻不在心里盛开着。
王寡妇叹着气说:“上个月老李头走了,老刘头走了,这个月张桂兰也走了……”
“该走的走,该来的来,这地方就是个临时的窝。”方四斤说着,慢慢地寻着长廊上的椅子坐下来。阳光透过窗子照到他稀稀拉拉的头发上,晃起一团稀疏的野草,野草也枯萎了。王寡妇没有停留,继续缓步向前。
方四斤沉落在这个下午的时光中,他又开始掰着手指头算账了。
账本装在心里,有什么可算计的呢?但方四斤喜欢扒拉这个账本,这些都是人情账,不算不行,再不算就来不及了。他心里明白,透亮透亮的。他这个人好面子,村子里有什么红白事,他参与归参与,拿赏钱归拿赏钱,但上个份子钱是必须的。当年王二瘸就笑话过他:“像咱们这样注定打一辈子光棍的人,人情份子该不随就不随,随了也屁用没有。”王二瘸有他的算盘,心里也明亮得很。其实王二瘸说得也有道理,到时候两只眼睛一闭,两条腿儿一蹬,身前事随风散,身后事谁又能料得到呢?人情账就变成河里的水,成了天上的云,没有人会还回来。王二瘸说:“老方,你他娘纯粹是傻球一个,放着钱不买酒不吃肉,随礼打了水漂,真没意思。”方四斤说:“我挣钱我愿意,打水漂我也愿意,你这叫扯闲淡瞎操心。”两个人在红白场上混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嘴仗,也算莫逆之交。王二瘸他爹死时,方四斤张罗大家演奏《青天歌》,演了一场白事会,不仅没要他的赏钱,还随了两块钱的人情。圈里有圈里的规矩,帮忙是帮忙,但赏钱该赏还得赏。王二瘸心里明白,两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在那个年头够人一个月的口粮。

⊙ 李瑶瑶·沉默的犀牛
方四斤的人情份子仅限在周围几个村子,这些村子他都熟悉,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见了面好说话。他们这行,大家见面说话时也有蔑视的意味,开个玩笑都话里带着话,让人很不自在。红事会的头一天晚上叫响门,这是艺人们最卖力的时刻。先吹一阵引人,再吹一阵要个彩头,围观的人聚得多了,喝彩声叫得响了,主家才会赏下喜糖、烟卷和喜钱来。圈里能要下彩头来的没有几个人,方四斤无疑是最放彩的。唢呐到嘴,吹得响亮干脆,胡琴到手,拉得轻快自然,提上大锣,敲得惊天动地。这里面方四斤最拿手的还是唢呐,这响器虽小却包罗万象,能耍高难度的技巧,吹来的曲子让人如醉如痴。碰上大方的主家,不光赏点钱赏点喜糖,还会赏下块红花花的手巾来。方四斤喜欢这种手巾,上面或是绣着荷花鸳鸯,或是绣着牡丹喜鹊,看着人心里痒痒的。主家在对待红事会上明白着呢,方四斤只要卖力他们自然不会亏待,就会心地往手巾里包盒点心。
红白事上最喜欢看他们演出的当然是小媳妇们。她们就像树林子里的红嘴雀,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冷不丁大家笑成一团,就像炸了锅。女人们最喜欢对着艺人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弄得方四斤很不好意思。王二瘸就凑过来说:“有个小娘们看上你了,说你长得像她家男人。”王二瘸说完咧开嘴,露出了漆黑的牙槽。方四斤听力好,女人们喳喳的声音早就只字不落地掉进心里去了。她听见一个小娘们压低声音说:“这人像我家那口子,像倒是像,不知道裤裆里那东西长得像不像……”另一个小娘们就凑到她跟前说:“男人那东西都一个鸟样……”说完大家就笑,像噼里啪啦放了一串炮仗。
方四斤不敢站起来,他的身上着火,裤子上已经顶起伞盖儿,生怕站起来露馅。他还没近身过女人呢,能感受到她们身上飘出来的那股味道,味道是甜的,味道是香的,味道也是骚的。骚得人心里发慌。只要有女人和方四斤说话,他心里就慢慢爬上一条毛毛虫,浑身上下痒得很,弄得很不自在。这种不自在有时候会到梦里去,她们向他招手,把他的手放到身上,她们软绵绵得像一团棉花,方四斤就能在梦里得到一次解脱。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方四斤随了份子,人家就对他多了几分客气。晚上住下的时候,就单独把他安排在一间屋子里。艺人们明早还要起来跟着娶亲,脚程远的自然要住下。主家的街坊四邻一般主动腾出间屋子供这些人暂住一晚。屋子也没有好屋,要么是闲置的老屋,要么是偏房,实在没地方就和骡马牲口住在一起,反正凑合凑合也就过去了。方四斤的待遇有所不同,他是随了份子的人,相比之下就变成了主家的客人。虽说还要把这趟活儿完整地干下来,但心里也算有了点底气。方四斤这人不矫情,该推就推该让就让。“您客气,我们哥几个凑合住一晚就行,又能说话又能解闷,就不添乱了。”主家还有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也不再虚让。屋子不大,炕也不大,几个人挤在一起翻个身都困难。几个人闲得蛋疼,拉呱也是荤的素的全有。王二瘸说:“今天刚进门的这小媳妇生得娇俏,脸蛋是脸蛋,奶子是奶子,真他娘的看着过瘾。”王二瘸也只能看看,最多在脑子里想想。小媳妇进的是别人家的门,没进他王二瘸的门,他看也是白看。但看了又不白看。王二瘸也是光杆司令一个,他的腿就是偷看别人家小媳妇洗澡被发现后打断的,断了腿应该长记性,但狗改不了吃屎,他到现在还是这副德行。张喜凤就说:“我看她的腿漂亮,虽穿着红棉裤,但绷得紧站得稳,屁股蛋子也结实,到了床上定是个好角。”张喜凤家里有个婆娘,但他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每次见了别人家的媳妇两只眼睛就直了,笙也吹得走调,一口唾沫含在嘴里使劲咽下去,砸得肚子咕咚乱响。说来说去,几个人就开始翻身、咳嗽,喘气都急促起来。方四斤虽不说话,但身体里也着了一团火,火烧火燎的,弄得自己很不自在。不自在也没办法,心里想,身上也想,手上就不老实。待大家都平静下来,方四斤就说:“别说了,快睡!”王二瘸就嘿嘿笑,他说:“我就纳闷,你怎么就满世界随红白份子呢?”方四斤有些着急,他呼啦背过身去赌气似的说:“我就是愿意!”
方四斤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随份子,真的就是愿意,这事天王老子也管不着,这事谁也说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又有什么办法呢?方四斤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把脑子都想成一锅糨糊了,也没想出个一二三四,干脆就不去想了,该随还得随,随了心里痛快。
方四斤不是没碰过女人,他和王寡妇好过。王寡妇不是真正的寡妇,这么说吧,她有男人,并且她男人还活得好好的。她跟了他男人六年,肚子里连个肉蛋都没怀上。母鸡不下蛋早就被扔到锅里炖熟下酒了,人要是不下蛋,这就成了大问题。到后来,她男人干脆和邻村一个真寡妇相好私奔了,从此杳无音信。有人说在上海看到过她男人领着三个孩子趴在街头讨饭,他和那个真寡妇倒替轮班,成了专业乞讨人。这也是说说而已,她男人具体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王寡妇等了三年,每天站在村头等,抄着手迈着碎步,从村这头晃到村那头,连个丈夫的影子都没等到。她男人就这么人间蒸发了,像锅里的水,熬着熬着就干了。王寡妇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请了方四斤等艺人班给她男人办了场葬礼。她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装进棺材里埋掉,然后一个人守着空家过日子。方四斤路远,晚上只能住下。王寡妇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之后,单独给方四斤炒了几道菜烫了壶酒,陪他小酌。
方四斤本想劝劝她,但又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只好闷头喝酒。王寡妇一边喝一边说:“兄弟,你说这事我做得对不对?我不给他办葬礼,他还在我心里活着,我给他办了这场葬礼,他就彻底死了。死了好,死了我就省心哪。”方四斤抬头看着她,她真像一枝花。“你做得在理,埋得好,埋了心里就舒坦了。”方四斤这么说,心里就有些动情,这女人也不容易。王寡妇给他斟酒,她的手很白,有些耀眼,耀得方四斤有些发慌。王寡妇也给自己倒满,然后一口气干了,酒下到肚子里,就涌上一股热气,弄得她脸色绯红。王寡妇说:“我不能养活孩子不要紧,可他连个言语也没有留下就走了,这事做得让人伤心。”王寡妇的眼圈发红,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砸到酒盅里,溅起一摊酒花。“我不怨他,我只怨自个儿命不济……”说着,王寡妇双手捂住脸呜呜哭了。方四斤不知所措,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好掏出块手帕递给她,说:“你莫哭,你莫哭,这是命里早就安排好的……”王寡妇接过手巾,顺手又把方四斤的手给抓住了,她把这双手捂在胸口。
两个人醉了,这感觉真好。
他俩最终没成一家人。这其中原因说不清楚,王寡妇男人家兄弟三个,自从王寡妇造了座空坟后就把眼睛盯到她这三间屋子上了,冷嘲热讽的,巴不得她早日出门。王寡妇心里透亮,她开始给自己发狠。女人发起狠来,老天爷都得害怕,话又说回来,不到迫不得已谁会发自己的狠呢?发狠不过是为了面子,为了争口气。王寡妇也真给自己争了一口气,她不嫁方四斤,也不坐山招夫,而是一口气在这三间屋子里住了六十多年。要不是政府安置孤寡老人,收了她的房子把她送到养老院,她将会老死在这里。她男人那两个兄弟,早已经死了多年了。
方四斤这账算得清楚,理得明白,所以,他就想把这些份子钱要回来。可要回来又有什么用呢?他住在养老院里,政府管吃管喝,把钱存多了也没个用处。可他不这么想,这事就像当初随红白份子时一个理儿,他图的就是“愿意”两个字。况且,这事在他心里谋划了很久,他见过太多的红白事,不老也变作狐狸,都成精了。下定决心之后,他慢悠悠地去找院长。在这座养老院中,方四斤最能说上话的就是院长。院长的爹娘结婚时他给吹的《百鸟朝凤》,他爷爷奶奶死的时候他给吹的《青天歌》。院长结婚时虽请了摇滚乐队和杂耍剧团,可那些都压不住阵脚,到最后还是他用唢呐把新媳妇迎进了门。这里面的渊源深着呢。
方四斤对院长说:“我要办一场葬礼,我自己的葬礼。”院长有些惊讶,脸上凝成了一个疙瘩。他以为自己听错了,腾地站起来走到方四斤身边,给他倒了杯茶。院长疑惑地说:“方四爷,你发烧了还是糊涂了?你活得好好的,怎么能给自己办葬礼呢?”方四斤头也不抬,而是伸出十个手指头当着院长的面算起了那个账本,他说:“我好好的,脑子也不糊涂。你看看,我心里有本账呢,这本账清不了我死也闭不上眼,来,我给你掰扯掰扯。”说着,方四斤就从几十年前的第一笔账开始算,二五一十,五五二十五,他比谁都明白。院长揉着太阳穴说:“方四爷你别算了,这事我也想见识见识,你想办就办,爱咋办咋办。可咱得把话说头里,你这葬礼我不出面敬老院也不能出面。你要想办,那好,你自个儿办去。”方四斤倒背着双手慢慢走出院长办公室,他心里说:“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话虽这样说,真正办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事得有跑腿的,得有内外柜房,也得有张罗布置打零杂的。但这难不倒方四斤,人活一辈子,谁没三两个交心的朋友?方四斤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人老就不中用,不中用就办不了事。他懂得放权这理儿,自己只负责思路,具体事还得依靠别人。这年头只要掏得起钱什么事都好说,所以方四斤老早就放出话请人了。
方四斤从来没想过死。人活一辈子到头来都得死,一死百了,死了清静。自从搬进敬老院,方四斤见过很多人的死亡,昨个老刘死了,今天老王死了,明天说不定是谁死。人生荣辱事,最终化青烟。方四斤觉得自己离着死期也不远了,那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得过来,阎王爷的账本清楚着呢。
方四斤找到查半仙给看了日子选定时辰,这才把自己的送死衣服找了出来。这套衣服还是当年王寡妇给自己买的,他舍不得穿,就留着死后用。方四斤嘟囔道:“死也得体体面面的……”他的墓穴选在方木伽坟的右手侧,取了个“携子抱孙”之意。方木伽携子尚可,要是再能抱孙,除非他从坟窝子里爬出来。两个老光棍,活鬼骗死鬼,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方四斤没想到王二瘸领着几个老伙计前来给自己吹奏白事,这家伙也老了,牙都掉光了,头上一根毛也不剩,乌亮乌亮的耀人眼睛。他努着四下漏风含混不清的嘴巴说:“老方啊,你这事办得敞亮。我们哥几个都闻到信了,趁着腿脚还能动前来送你一程。看你这老棒子骨头还算结实,阎王爷保准再留你个十年八年的。”方四斤抓住王二瘸的手使劲攥了攥,然后有些感伤地说:“老家伙,我以为你死了呢。”几个老伙计哈哈大笑。方四斤抱拳道:“辛苦各位了,我在这儿给您几个磕头了。”说着,方四斤扑通跪下来,实实地磕了一个响头。王二瘸冲着几个老伙计说:“老家伙们,趁着有劲咱们再风光一回,啊,敲打起来!”
方四斤的葬礼在哀乐中缓缓拉开了帷幕。
四邻八乡的人都来了,差点把方家祖坟给踩平。方四斤端坐在灵棚里像一尊雕像,接受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的三鞠躬。柜上有人就高声念:“刘金成奠金五十元!张金爱奠金三十元!刘大海奠金一百元……”他们念一个,方四斤就在心里画掉一个。当年方四斤不过随个五角一块,现在都几十倍的翻番还回来了。这事也随着物价走呢。不过也有人没还回来,这事全凭自愿。有的人来看热闹,顺手也随了个三十五十的。方四斤看着密麻麻的人群心里欣慰了许多。“乡长死了也就这个场面吧,不过这场面可比他们热闹多了。这事办得值!”他冲着人们抱拳,人们就哈哈笑开了。有人说:“方四爷,您这事在咱这儿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您老体面啊。”也有人说:“方四爷,您收了这份子礼,是不是留着给自己寻个老伴用啊?”小媳妇们也笑着说:“方四爷人老心不老,心里还想那事呢!”
王二瘸几个人把哀乐差点吹跑了调,更惹得人们大笑。王二瘸就嘬着牙花子说:“老方,《青天歌》还得你自己来,我们都没你吹得好。”方四斤说了一声好,顺手接过唢呐鼓起腮帮子吹了起来。唢呐是老唢呐,人也是老人,各自都存着感情呢。方四斤的《青天歌》悲壮、苍凉、哀婉,就像三月里的春雨洒在身上,让人听着就想掉泪。人群安静下来,无不沉浸在这首唢呐曲子里,就连方四斤本人,也几乎沉醉在其中。方四斤吹奏的时候,额头上的青筋鼓得老高,整个脸憋得通红,后背上都下了汗。人老不中用,平日轻而易举的曲子,这时吹奏起来已经有些气力不济。这首曲子自己给别人吹了无数遍,自己给自己吹还是头一回。两行浊泪顺着方四斤的脸颊流下来滴到尘土里,打起一团土花。小媳妇们轻轻抹着眼角,通过《青天歌》她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暮年。
一曲《青天歌》吹罢,到了该入土的时辰了。方四斤走到墓穴旁坐下来,象征性地举办了仪式。办事的人拿了纸钱纸车纸马和早就糊好的童男童女,各自在墓穴前烧了。王二瘸扯着嗓子喊:“老方,到了那边你就不寂寞了,有钱使劲花,争取早天找个媳妇。”方四斤慢慢从怀里掏出块用白纸包着的砖头,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墓穴里。光棍汉独坟不好,好在他早有准备。别人一般找一张女明星挂历包块砖头代表“媳妇”,可方四斤没这样做,他在砖头上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这名字早就烂在心里了。
葬礼结束后柜上过来交账,方四斤共收奠金一万六千四百三十块钱,抛去所有开销结余一万一千二百块钱,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值。方四斤几乎是捧着这些钱的,他知道,一切烟云就这么散去了,自个儿一辈子的人情就这么要到手里来了。这哪是钱,这是混了大半生的脸啊。他有些激动,跪下来给所有在场的人磕头。
方四斤用了最古朴的仪式还礼。
没想到回到敬老院,就得知王寡妇中风了,人不能自理。院长派人守护,也找来医生给输上了点滴。王寡妇仿佛变成了一把干柴,再多的点滴也浇灌不进去。时光在点滴中慢慢消失,也在慢慢地抽干她。院长交代,输点葡萄糖生理盐水什么的也算院里关怀,真到生命攸关的时候,院里也没办法。方四斤看到王寡妇时,她已不认得他,也不能说话了。但王寡妇的眼睛还是圆润的,里面充盈着两团水花儿,清灵得很。
“这双眼睛还是这么漂亮,光看着就让人欢喜。”方四斤抓了王寡妇的手,像抓着一把稻草。方四斤说:“你得好好活着……”话没说完,人就哽咽起来。他担心的就是这个。他老了,王寡妇也老了。这一个担心压在他心头很久了。他担心他心目中的牡丹花就要凋谢了。
方四斤摸了摸王寡妇的脸,有些凉,便来回摩挲了几下。王寡妇两行清泪滚下,让方四斤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方四斤掏出一个包,包里是他的一万多块钱。他递给医生说:“再用点别的药吧,能用多少用多少,用完这些钱就算。”方四斤很坚决地把钱塞到医生手里,“我能做的就是这点事了。”
医生说:“您自个儿不留着防老?”
方四斤摆摆手慢慢出了门,他的脚步很轻,像踩在云朵里一样,浑身上下都轻飘飘的。
方四斤觉得,他一下子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