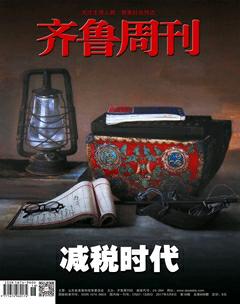当无数人犯下平庸之恶,依然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王毅
恶距离我们并不远。人类历史上几乎最大规模的恶,也只过去了几十年。当种族屠杀成为纳粹的最终目标,数百万犹太人成为亟待处理的“问题”,身为普通人,又能做到什么?同情、悲悯、反抗,这是我们能从纪实作品《动物园长的夫人》中所读到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举国倾巢,战舰、飞机、坦克、炮兵、机械化部队同时上阵,以求一击成功,这种后来所称的“闪电战”让华沙变成一片火海。人们看到了《圣经》中描述的末日,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动物园里的生灵纷纷出逃,涌上华沙的街道,海豹沿着维斯瓦河摇摇摆摆地急走,骆驼和无峰驼钻进了小巷,鸵鸟、羚羊与狐、狼并肩奔跑,食蚁兽一边跑一边不忘在砖缝间觅食舔舐……
看到这一切,想起黎明时的万道晨曦透过菩提树林,自己拉开动物园中白色小楼二楼卧室的窗纱,听到由长臂猿吹响晨号而开始的百兽争鸣,气势磅礴,那么熟悉,那么动听,园长夫人安托尼娜真是恍若隔世。
美国女作家黛安娜·阿克曼曾荣获布洛斯自然奖和美国学院诗人勒文奖,她这部新作《动物园长的夫人》是独特的纪实,厚实丰满,动物、植物和中欧原野上的生态系统,古老的华沙城和市民生活,尤其是战争蹂躏之前和蹂躏之中的那座美妙的华沙动物园,对这一切的鲜活描绘,在这个背景中对园长一家以及其他人物的传神刻画,真可谓将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融为一体了。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前,生物学就是西方世界的一门显学,它所探究的生物奥秘和可能性,带来了包括华沙动物园在内的欧洲都市动物园的建设与壮观,也让一些浅薄而偏执的妄者臆生了狂想。在动物(包括人)中划出等级,消灭“低等”,由血统高贵者来掌控世界,纳粹德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生物学疯狂”,它的病态和暴行建立在生物学和医学意识形态之上。纳粹统治波兰的总督汉斯·弗兰克有言:“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它通过接触而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对于雅利安种族的治愈而言,治疗的方法就是杀掉所有的犹太人。
一方面是希姆莱说的“走遍田野,将不想要的植物剔除出去”,另一方面,则是要控制进化过程,在生物学上复原被视为物种与血统纯粹之原力的远古动物,如欧洲野马、欧洲原牛和欧洲野牛。于是,华沙动物园中普氏野马被掠到慕尼黑动物园,野牛、山猫和斑马去了柏林,幼象去了柯尼斯堡……
对于一辈子钟爱动物、理解动物的园长夫妇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然而,利用纳粹对珍稀动物的痴迷心理,利用现已进入纳粹行列的德国动物园长的同行关系,他们将动物园先后改成养猪场、公共菜园和毛皮兽养殖场,以此加入了华沙城的地下反抗和拯救生命。
从隔离区逃出来的犹太人,反抗纳粹占领的波兰人,那些弱者、病者、饱受折磨者、精疲力竭者、被追捕者,一拨又一拨地来到了这个动物王国,与园长夫妇一家同住,躲在阁楼上或地窖里,藏在园中各处兽舍中,前后约有三百人,在维斯瓦河畔这条拯救生命的诺亚方舟上避难暂歇,然后继续他/她们的逃亡或战斗。
“他们选择了让善永恒,即使身处地狱。”这其实并不容易,决不轻松,并非单纯的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观念就能支撑下来,要靠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靠人性本能在一刹那间的随机反应。安托尼娜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与应对。动物园内德军仓库方向燃起了大火,一个德国兵来到小楼怒吼:“你们放的这火!这里有谁住着?”园长夫人微微一笑:“那两间小公寓,住的是我们以前的雇员,都是规矩人。再说,他们干嘛要冒杀头危险去烧一个啥都不是的干草堆?”“可是,起火总有原因吧?又没打雷闪电,肯定是人为的。”早已忘记的德语词从园长夫人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她用友好的语气说:“你们的士兵经常把女朋友往那边带。很可能哪对小情侣今天又去了那里,他們抽烟,扔下一个烟蒂……接下来的事不用我说了吧?”德国兵听得哈哈大笑。接下来德国警察的到来和盖世太保的电话追查,都以这个结论而化险。避难者们一个个从“洞穴”中爬出来,拥抱她,称赞她的勇敢。
园长丈夫雅安是波兰流亡政府“救国军”的中尉,主要精力放在地下抵抗的工作中,无暇多顾这条方舟不被巨浪和暗礁倾覆,他对此事有独特的看法:妻子小时候就跟很多动物生活在一起,获得了一种罕见的观察理解动物的方式。“无论是对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动物,她不会产生‘害怕这种自然反应,也不会传播‘害怕情绪。这可以化解对方的攻击意图,无论对方是人还是动物。”其实,又岂能不害怕呢?战后他告诉采访的记者,妻子“她也害怕可能的后果,她怕极了,她怕纳粹报复我们,报复我们年幼的儿子,她怕死。但是她把恐惧藏着,一个人忍受着。”
身处一个杀气腾腾的、疯狂和无常的世界中,人们有着多个层面的生存与抵抗。园长夫妇的朋友沃尔特夫妇开一家发廊,向无数犹太人教授过“美容”课程——染发、化妆、改变举止细节,不让街上的纳粹警察发觉是犹太人。凡是来过这家发廊的人,都躲过了灾难,于是大家传说这里有神奇的巫术。这当然有偶然因素,而沃尔特太太解释说,这个巫术很简单,就是同情和悲悯:“苦难像魔咒一样占据我的全部身心,让我从此消除了分别心,无论朋友还是陌生人,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在园中贮藏肥料状炸药的丈夫,认为这个环境中的生存离不开策略和诡计,而安托尼娜坚信生命必须快乐,以精神受损为代价求得身体的苟活,这不是她信奉的生命之道。如同许多人一样,夫妇二人随身携带如遇不测就随时结束自己生命的氰化物,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条飘摇于惊涛骇浪之中的方舟内创造和鼓励着幽默和音乐,以及尽力弄来食物的欢宴。书中一处细节很有趣:战时的动物园有大群乌鸦盘旋落树,德国兵以射杀为乐。安托尼娜一只只拾回来,洗净煮烂,做成腌肉酱。避难者吃得津津有味,以为是波兰名菜野鸡肉酱。安托尼娜暗笑:“何必败她们胃口呢?对动物的命名没必要过于较真。”
战时记忆自有独特的存档系统,在无数悲剧场景的夹缝之中,也给浪漫留下了存储的特别空间。安托尼娜让动物园中自己住的这座小楼充满让人忘我、忘忧的生灵——麝鼠、公鸡、野兔、狗、鹰、仓鼠、猫和幼狐,它们诱导人类进入那个永恒的自然世界——这里既有人类习惯的自然,也有让人惊异的自然。全身心地融入小洋楼这种独特的生态系统和日常生活之中,自我就消失在了不同物种的需求与节奏的交响之中,心灵得到了休憩。如同尽一切努力为避难者找来食物和取暖燃料一样,这种由生命的色香味声调制出来的精神滋养,在严酷的环境中也极为珍贵。
“春夜把华沙包裹在一件黑大衣里……一支舞蹈乐队在表演,其中有狼、有豺、有鬣狗、有澳大利亚野犬。被吵醒的一头狮子发出一声怒吼,附近的猴群闻之胆寒,水塘中受惊的众鸟虚张声势……隐居于原生态的世界角落,我们思考着自然母亲的法则,想象着她秘而不宣的天机。我们生活在动物中间,它们是我们在尘世的伴侣。”写过童书《小山猫》的园长夫人,能够潜入各类角色的身心来看世界——无论是动物角色还是人类角色,以爱和生命来看待,她这样的信念从未泯灭。
书中一位曾生活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教拉比兼作家赫谢尔,有句名言意味深长:“石碑已碎,碑文依旧活着。”的确,斯人已逝,园非旧园,但靠着大量的一手材料和实地查访,包括对园长夫妇留下来的那些老照片的凝视沉思,作者鲜活地还原了那个环境、那段生活和这些有趣而又不凡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