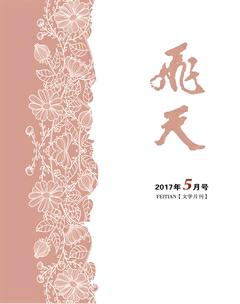圆与十字架
孙妍涛
一、道德与中庸之“圆”——中国
古典悲剧
1.实用主义与道德满足
相比于青睐“命运悲剧”的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对于命运这一命题是比较冷淡的。
中国人没有特定的、集体的宗教信仰,诸多外来宗教的影响使得中国人的信仰在千百年间变得很混乱。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本土的道教都有广泛的信徒。但中国人普遍相信,上辈子如果做了坏事,这辈子就要受到惩罚(而西方人认为一切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一观点是以佛教的“轮回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于是“轮回”就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命运”,此生遭遇的不幸,都是因为前世的缘故,于是一切都是可合乎情理的,可解释的,不需要去演绎、深究,于是悲剧中的“宿命感”在中国古典戏剧中似乎成为了一件多余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典戏剧中并不存在“命运无常”的情节,而是在这里,“命运”被更多的具体化,隐藏在封建思想、阶级隔阂以及邪恶势力背后,因而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也失去了主体地位。
道教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更加深远,道教膜拜的对象是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上人间的统治者,并且有一套同俗世对应的官僚系统,中国人在自己的宗教思想上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和现实性体现得淋漓精致。
从古典的中国哲学而言,《论语》中有如下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不知生焉知死?”由此看,孔子对死亡的态度是审慎的、实用的,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对于生死的看法。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更加超脱、豁达,然而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占据长期的统治地位,道家对待命运与生死的宽容思想没有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留下太多的痕迹。
多种因素都将中国人的哲学引向了实用主义,中国古典戏剧中处处暴露着这一点。古典四大悲剧的版本不一,但不外乎是《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窦娥冤》《赵氏孤儿》《桃花扇》等作品。这些古典悲剧,大多数都写才子佳人、名誉和爱情,或者说是欲望。从作者的创作心理角度分析,如果说艺术想像和虚构是为补偿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难以满足的欲望和理想,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多数悲剧的创作都是一个普通青年在幻想另一个普通青年逆袭成功、金榜题名的同时与佳人喜结良缘。于是悲剧表现的对象不再是多变的宿命,而是俗世中阶级的鸿沟。事实似乎确实如此,以《西厢记》为例,当张生通过科举成功进入士大夫阶层后,横亘在他与崔莺莺之间的反对力量似乎就消失了。
但是之后的事情就没有人关心了,这也许是古希腊悲剧和古典中国悲剧的本质区别。伊阿宋获得了金羊毛,并且抱得美人归,在中国人眼中是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而具有怀疑和思考精神的古希腊剧作家却描绘了伊阿宋移情别恋、出于悲愤、美狄亚杀死亲生儿子的悲惨故事,对于中国剧作家和中国观众而言,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个始乱终弃的张生和一个怨妇般疯狂的崔莺莺,这些非道德的因素,注定和古典戏剧无缘。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非悲剧性的因素也许不如《西厢记》中的剧情反转那么剧烈从而改变剧作的情感基调,但反映出了主导着中国人的悲剧创作和审美的实用主义和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和社会功用长期主宰着中国文人的思想和创作,这一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发现了文艺对人的教化作用,尤其强调事君事父的作用。南北朝人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就将原道放到了第一章,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到了宋代,古文运动将文学与道德的附属关系发扬光大,“文以载道”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要义。
道德被视为文艺的最公用和主要目的,戏剧作为文艺的一種,自然也未能免俗。中国古典戏剧源于宋杂剧和金院本,发展、兴盛于元代。下面以《窦娥冤》《赵氏孤儿》为例阐释这一点。
关汉卿所著的《窦娥冤》,是笔者童年时代接触的第一部古典中国悲剧,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窦娥命途多舛,三岁丧母,七岁被父亲卖给债主,十七岁丧夫,最后蒙冤而死。主人公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是关汉卿在结局的安排上与道德意识“妥协”:窦娥的父亲在京城当了官,回来给窦娥复仇;张驴儿和贪污的太守桃杌被绳之以法,窦父将蔡婆接到家中安享晚年。如果说简略的复仇环节大大削弱了剧本的悲情因素,那么试将这一部分去掉,看看剧本是否符合悲剧的要求?很明显,失去了这一部分的《窦娥冤》,没有了情节的完整性,结构上也很难自圆其说,读者很难看出作者的意图,这个时候,剧本甚至由于其不完整性而很难称之为剧本,更不必说属性问题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戏剧《窦娥冤》的表现重点并不是窦娥的悲剧命运,而是最后为窦娥沉冤昭雪的过程和结果?窦娥的悲剧命运,只是这个故事的漫长铺垫?如果真是这样,作者的意图又在哪里呢?在《窦娥冤》的结尾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窦天章云)我便是窦天章。适才的鬼魂,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儿端云。你这一行人,听我下断:张驴儿毒杀亲爷,谋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升任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赛卢医不合赖钱,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药,致伤人命,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蔡婆婆我家收养。窦娥罪改正明白。(词云)莫道我念亡女与他又罪消愆,也只可怜见楚州郡大旱三年。昔于公曾表白东海孝妇,果然是感召得灵雨如泉。岂可便推诿道天灾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应通天。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方显的王家法不使民冤。[1]
《窦娥冤》的结尾道德目的性非常明显,使得它看上去似乎是一部元代的制作精良的普法栏目剧,人们难以体会到深层次的审美快感。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悲剧结构时,就说一般人都喜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但是这种趣味实在很低下,看到惩报公平所生的快感实在不是美感。[2]
《赵氏孤儿》应该是中国古典戏剧中将道德感与悲剧的崇高完美结合的一部作品。王国维评价:“……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故事讲述春秋时期晋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程婴忍辱负重将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在最后的复仇行为上,而在于程婴的义举——他为了兑现保护赵氏孤儿的诺言,向屠岸贾交出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剧情是很有代表性的,换一个文化环境和时代环境,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一个人会为了保护他人的儿子将自己的孩子置于险境,但在重视“义”与“礼”的传统儒家观念中,这一举动具有极强的道德感与悲壮感,也完全能体现出人在悲剧命运面前的抗争精神,正是这种抗争,使人物变得丰满而有力量。正如斯马特先生所言:“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就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只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4]对程婴而言,他完成了自我的突破,谁也想不到一个民间医生在悲剧命运面前竟有如此的挣扎和勇敢,他的行为传递出极强的生命力感,人们通过同感和移情,感受到了同样的挣扎和勇气,于是人性中崇高的光辉在观众心中萌发,产生“卡塔西斯”的效果。程婴的举动,在戏剧中承担了巨大的悲剧意味,告诉我们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不能摧毁人的伟大崇高[5]。这大概也是《赵氏孤儿》所以被称为悲剧的原因。
《赵氏孤儿》中的这种伟大和崇高,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程婴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这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在强调道德感的传统中国社会,悲剧中的牺牲很常见: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企图带出宫,被守门将军韩厥搜出,没料到韩厥也深明大义,他指挥程婴把婴儿带了出去,自己拔剑自刎;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以年迈之躯代替程婴承担隐藏赵氏孤儿的罪名,然后撞阶而死。在结局表现上,屠岸贾并不是由赵孤亲手杀死的,而是受到王的惩治。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从周秦一直到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输入,文艺都被视为道德的附庸。[6]
中国悲剧中的结局是勉强的,又是必然的,从传播学和接受学的角度来说,剧作者必须迎合中国式的心理期待。这种思想是国民性的表现。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和道德感作为一种文学成规,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凝聚着中国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对中国古典悲剧的表现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种狭隘的倾向从某种角度上说阻碍了文艺的发展和多样性,但是艺术家创作的真诚态度和真挚情感是不容抹杀的。
2.圆满思想下的悲剧结尾
就结局来看,中国古典悲剧中,能够真正被称为悲剧的为数并不多,除过《桃花扇》《长生殿》这样少数跳脱出大团圆套路的作品,中国戏剧的结局在悲剧面前都是有所保留的,作者会通过情节的“峰回路转”来酌情改善作品的悲剧基调,但这样的结局显然使得悲剧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前文所提到的《赵氏孤儿》《窦娥冤》《西厢记》,以及《牡丹亭》等,基本上都拥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受到了各种势力的阻挠,结局却不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最终以阴差阳错的悲剧收场,而是张生如愿金榜题名,与崔莺莺结为夫妇。虽然金圣叹在点评《西厢记》时认为,《西厢记》在第四本最后一折《哭宴》就该结束,之后的剧情应当由读者结合对作品的理解来猜想,剧本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悲剧。然而,古典的剧作家们和观众,并非都有金圣叹那极具现代性的文艺思想。
“圆满”意识在中国已经算得上一种迷信了,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高鹗在续写《红楼梦》时,甚至不顾原作者曹雪芹已经铺设好的悲剧收梢,执意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凄凉结尾,改成了相对圆满的“贾府沐皇恩、延世泽”,红学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斥之为“一条光明的尾巴”,这似乎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意识中向来缺乏悲剧精神。
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样是爱情悲剧,过程中也是充满了难以避免的宿命性的误解与矛盾冲突,相似的有情人不能够终成眷属的悲剧结尾,中国的作者在悲剧结尾面前似乎觉得太过悲哀了,于是在梁祝死后,加上“化蝶”这样美好梦幻的结局,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亡则成为了无可挽回的结局。
中国人追求“中庸”、“圆满”的思想就从这里体现,而西方文化的放射性和极端性,使得西方悲剧作家拒绝在悲情面前有所妥协。于是我们在西方悲剧中,看到依包利特惨死于海上,费德尔随之含恨自尽;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伊阿宋家破人亡;善良纯洁的考迪莉娅死于非命,李尔王精神失常,诸如此类的悲伤结局,毋需一一列举。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的戏剧乃至文艺就不受道德的制约,但是至少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西方戏剧艺术要比中国古典戏剧艺术更加独立于“文以载道”的体系之外。下面我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道德观念与其他
诸种理念下的西方戏剧
1.古希腊命运悲剧
同东方一样,西方艺术也面临着道德的制约。柏拉图对于文艺、戏剧很不屑一顾,以至于他客客气气地将诗人们赶出了理想国,他说,“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克勾和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荷马尽管伟大,还比不上这些人”;“建立一个城邦比创作一部悲剧要美得多”。他轻视文艺的根本原因,是他的哲学理念,他认为真理是理式(idea),现实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对理式的模仿,而一切文艺包括戏剧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从而同真理相去甚远。柏拉图还认为戏剧、文艺都是导致人受到感性精神控制、走向堕落的元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还是因为戏剧中的一些非道德情节,柏拉图攻击荷马和悲剧家们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把神写得和人一样坏。
柏拉图在文艺思想方面,应该同韩愈引为知己,他的观点基本可以概括为,文艺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对民众要有教化作用,否则就应当被剔除。
和中国有所区别的一点是,认为文艺应当服务于政治,应该充满道德感的人,都是擅长指指点点的哲学家,而不是真正从事创作的诗人和剧作家,于是西方戏剧在这一时期看似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除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应屋大维之命写成的《爱涅阿斯记》有为屋大维歌功颂德的嫌疑,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剧作都有着自由的文艺精神和探索方向,我们依然看到了《美狄亚》《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等作品。
命运悲剧是古希腊戏剧最为重要的一个题材,希腊戏剧家热衷于对命运和人性的探索。西方戏剧中的“命运”,不同于东方,不是所谓转世轮回说的延伸,而是现世中的人们在此生的经历。索福克勒斯在戏剧《俄狄浦斯王》中,描写了俄狄浦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杀父娶母,不管在何种文化语境、时代环境下,显然都是不符合道德和世俗眼光的,但是索福克勒斯却大胆地将它写进了这个故事,使它成为主人公无法逃避的罪孽。
不仅仅是在古希腊时代,之后的文学史中,西方悲剧也甚少受到“道德绑架”。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法国古典主义运动时期的《麦克白》《费德尔》等剧,也有非道德情节的展现,但正是这些非道德性的情节,让我们意识到人的主体精神和独立性,我们从中洞察人性,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关照自身。下面以《俄狄浦斯王》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俄狄浦斯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他去国离乡,因为恐惧杀父娶母的结局;当瘟疫降临,俄狄浦斯获神谕要找出杀害前任国王的凶手,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他自己的时候,他依然选择继续追查下去,百姓爱戴这样的国王,称他为“最高贵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
《俄狄浦斯王》是一出典型的希腊戏剧,按照古代希腊人的理解,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因此,俄狄浦斯无论怎样挣扎,只能在命运的罗网中越陷越深,他试图竭尽全力与命运作斗争,而最终却依然被命运所吞噬。在这出悲剧中,命运被描述为无形的、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始终伴随着俄狄浦斯。然而,索福克勒斯并非要单纯地揭示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绝望感,相反,通过主角与命运抗争的行为,观众体会到的是一个人在命运的无情碾压之下,将会迸发出怎样的生命力。俄狄浦斯是悲壮的,因为他无辜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同时他又是高贵的,因为他面对不可逆的命运仍然奋起抗争,这恰恰体现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崇高。他的罪恶丝毫没有影响到人们的道德感,或者引起任何道德感的不适,反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审视自身。
这出悲剧表达了古代希腊思想中注重对人的本身的探索。对人本身的认识和思考,不但体现在主人公俄狄浦斯与命运抗争和最终陨落的过程中,也体现在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上,“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人生各个阶段的形态特征,在本剧的具体语境中,向观众揭示出“认识自我”这一深刻谜底的形而上意义和价值。[7]
2.文艺复兴思潮中的悲剧创作
十四世纪,欧洲历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此后的三个世纪里,一场深刻改变人与世界关系、催生了近代科学文化的运动逐渐发展,蔓延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出现改变了西方文艺的走向,它催生了之后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源泉,也是西方文艺思想和中国文艺思想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在中国,直到近代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式的思潮,中国的文艺思想也没能走出“文以载道”的基本框架。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学开始反抗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苦修精神和禁欲精神,所谓的“复兴”,是重新发现人的崇高价值,认识到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无限的潜能,这一觉醒使人们摆脱了中世纪封建主义和教会的精神桎梏,迎来了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确证。在这一时期,悲剧创作更加不受道德满足感和社会功用的限制,对人物心理和人性的挖掘、对悲剧命运的表现也趋于深入和多样化。
这一时期的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几部作品,如《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哈姆雷特》等等,题材广泛,从爱情到历史,几乎无所不包,不仅仅深刻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也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
悲剧《麦克白》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最为杰出的悲剧创作,也是主题最为阴暗、最为深沉的一部,氛围阴郁沉重,充满超自然气息。剧中,似乎是女巫的出现和妻子不断的怂恿使得麦克白最终误入歧途,但是实际上,女巫或许只是麦克白野心的化身而已,他对权力的渴望早就已经植根在心底。女巫的预言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诱惑的外因,是不是受引诱在于麦克白自己。贺祥麟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对比了麦克白和班柯这两个人物。面对三个女巫,班柯只是对他们奇异的外表感到有趣, 对他们所说的话却充耳不闻。而麦克白对女巫虚假的许诺却认了真。因此,正是麦克白自己心中的罪惡使他堕落成一个魔鬼[8]。
从个人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来解读,女巫三姊妹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命运。麦克白的悲剧说明了命运的难以捉摸——它引诱你,激起你的希望和欲望,却又欺骗你,最终抛弃并毁灭你。麦克白依照女巫的预言采取行动,顺利地坐上了王座,而等待着他的并不是一劳永逸,他失去了心灵的安宁,终日处于良心谴责之下,并且看着自己的罪恶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在欲望和生存的驱使下,他又必须苦苦挣扎。
女巫告诉他没有一个女人所生的孩子能够征服他,却向他隐瞒了麦克德夫是剖腹产的事实;而英格兰军队砍下树枝作掩护,使勃南树林似乎在移动。麦克白从始至终都被命运的大网所捕获,他的挣扎与痛苦,最终成为了舞台上一点微弱的回音。麦克白最终所经历到的幻灭感,使《麦克白》的悲剧有了某种普遍意义。观众在麦克白陨落的姿态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容,在麦克白的悲剧命运中瞥见了自身命运的一点残影。麦克白追求的幻灭,是人的追求的悲剧;麦克白的悲剧, 是人存在的悲剧。麦克白从他的追求中得的只是一种悲剧性的意识——人生的无意义。这表现在他那段著名的独白中: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的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 却找不到一点意义。[9]
没有人像莎士比亚这样把人的存在表现得如此具有悲剧性。直到上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人生的无意义与存在的虚无感才成为小说家笔下主要的表现主题,足见《麦克白》思想内涵的先锋性和深远影响。现代主义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品《喧哗与骚动》的书名便是来源于此。
文艺复兴之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欧洲大陆先后兴起,戏剧也在此消彼长的文学思潮中渐渐衰亡,小说作为新兴文体取代了戏剧和诗歌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文艺之美的价值、对文学作品的目的和追求也有了新的认识,东西方的审美体系也渐渐完善。
结 语
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10]文藝所追求的美,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个体,究竟不能够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而东西方戏剧艺术对于创作与审美的不同定义和追求,也使得东西方戏剧展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带给观众不同的审美快感,在不同的文化与时代中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辉。
参考书目:
[1]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五年七月版,P103.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102.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206.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209.
[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五年七月版,P98.
[7]王立新主编《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P32.
[8]贺祥麟《莎士比亚研究文集》,[C]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24.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评论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