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形象的坍塌与重建:解读《母亲的岛》
朱 阳
新人话语
母亲形象的坍塌与重建:解读《母亲的岛》
朱 阳
壮族作家陶丽群在《母亲的岛》里讲述了一个有别于以往经验的故事:常年逆来顺受的母亲突然在某一天选择结束这种生活,她逃离了父亲和子女的压迫,独自搬到了附近的一座岛上生活,并且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回来,而这一举动也改变了“我”和父亲的生活,大家纷纷为母亲的举动感到不安,担心,但是却无能为力。在这篇小说里,母亲的形象和以往我们所熟知的母亲有所不同,她是一个被拐卖到外地的女人形象。我们在文学作品里看到的母亲形象,往往是慈爱、温暖、端庄的,而在《母亲的岛》里,则是神秘、沉默、唯唯诺诺的。在这位母亲身上,地位、尊严、自由这些东西是统统看不到的。因为害怕她逃跑,父亲像犯人一样常年盯着她,在家中也肆意打骂,就连子女也可以对其乱发脾气。在作品里,作者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作者的家乡,买来外地妇女作为生育工具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所以这里的小孩对母亲大多都非常倨傲。母亲这个角色对于尊严和地位的缺失,注定了她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
故事开始于母亲的逃离。母亲一声不响的离去改变了很多人。最为明显的就是父亲。小说里的父亲是一个暴君的形象。他自大、傲慢、暴躁,是这个家中唯一的独裁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所有者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母亲是他花钱买来的一件货物,于是父亲拥有了无条件的支配权与使用权。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母亲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她要面对丈夫的压迫与侮辱,子女的轻视,无休止的家务和劳累。《母亲的岛》里的母亲是非常坚韧不拔的。尽管她深知自己的地位无法改变,但是她默默的忍受着责骂与苦痛,从来没有扭曲到报复他人,对子女也尽量保持着母亲特有的温情慈爱形象,尽管比不上普通的母亲,但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母亲选择了出走。而反应最激烈的就是父亲。母亲的出走逼迫父亲展开了一项艰难的思考:到底自己和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母亲出走以前,毫无疑问,父亲是把母亲当货物,当奴隶和佣人来对待的。因为男权意识,因为买卖关系,所以父亲的这种思维拥有貌似天然的合法权。但是母亲走了,而且走得非常巧妙,让父亲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四面环水,多少买卖过来的媳妇走投无路,最后渐渐成为丈夫的附庸。但是母亲很聪明的选择了住在附近的一座小岛上,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向所有人宣告父亲和子女的暴行与欺压。母亲的行为像是抽去了这个家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当父亲得知了母亲的出走,他变得非常生气,狂怒,就像是一件私有财产被人夺去的感觉。母亲的出走是对父亲男权至上的一种无声挑战,并且,母亲用行动证明,自己离开了这个家族,同样可以活得很好。母女在岛上种地、养鸭,甚至还可以卖菜赚钱,又把钱给几位子女,这都是对父亲权威的一种挑战。她越是活得好,越是证明父亲的无能与可笑。自古以来,“男权至上”在中国社会文化观念里都是主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有受到压迫的女性敢于勇敢的站出来对抗男权。尤其像母亲这种“祥林嫂”式被压迫惯了的女性,想要彻底与过去的身份决裂,更是艰难无比。在母亲心里,出走意味着面临多重的煎熬。首先是对于传统夫唱妇随,三从四德观念的颠覆。其次是对于自身作为买卖物品的自主权的缺失。所以当母亲说出那句“我要出去住一阵子”时,短短几个字,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
母亲走了,父亲态度的转变,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发现父亲晚上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江边张望,眺望母亲所居住的那间孤独的木屋。这个时候,父亲已经理智了许多,他的内心也是非常复杂的,他不仅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甚至要求我去看看母亲“是死是活”。此时的父亲是希望母亲回来的。他渴望回到过去那种已经建立好的“家庭秩序”里,重新站在独裁者的位子上对每个人发号施令。所以此时父亲对于母亲“是死是活”的疑问既有好奇的成分,也是怀着一种自私的目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希望母亲回来,这个人就是玉姑。和母亲的身份相同,玉姑也是被买来的媳妇,在家中也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两个人同病相怜。但是玉姑是一个彻底的服从者,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奴役生活,并且默认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母亲的出走对玉姑来说有多重意味。首先,母亲完成了玉姑不敢想象的事,几乎是一项壮举,所以玉姑内心为母亲迈出的这一步感到激动,甚至希望她的出走能够成功。玉姑的心愿就寄托在了母亲身上。其次,玉姑又是矛盾的,在漫长的囚徒般的岁月里,只有母亲是她唯一可以倾诉心声的人,母亲的出走意味着孤独的开始,所以玉姑又希望母亲能够再回来。
“我”与母亲出走后的第一次“交锋”,是“我”前去岛上与母亲进行交谈。“我”是几名子女当中与母亲最亲近的人,所以理所当然的希望母亲能够回来,但是这种愿景也是复杂的。首先,“我”对于母亲的敬爱里,也有着轻视的成分。母亲毕竟是买来的,这件事所有人心照不宣,尽管作为亲生子女,也依然受到了这种买卖关系的影响,“我”从没有想过为何会轻视母亲,也没有想过她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仍然忍不住会对她产生偏见。所以,当“我”请求母亲回来时,那态度分明不是在请,而是强硬的催促,当母亲的答案是拒绝的,“我”变得生气了,因为一向柔弱的母亲居然也学会了反抗。此时的“我”无疑是父亲一部分的化身,是人性中阴暗自私的一面。此外,我希望母亲能够回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母亲的出走,让我成为了她的“替身”,做饭、家务变成了我的责任,于是我希望母亲能够回来,只有那样,一切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母亲的态度是沉默的否定,无声的拒绝,默默的坚持。由于过去的压迫,她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该具有的种种权利,已经渐渐快要成为玉姑那样的“货物”,所以母亲的出走绝不是一时兴起,空穴来风。这种不痛不痒的反应让“我”愤怒万分,甚至明白了为何父亲会那样愤怒,因为母亲这件沉默的“货物”,已经变成了一头倔强的驴子,不再接受主人肆意的控制指挥。“我”的吼叫和谩骂,就像拳头砸在了沙堆里,毫无作用,于是“我”只好悻悻然地离开。“我”与母亲的第一次交锋,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说第一次交锋只是“我”对于母亲出走后顽固态
度的愤怒,那么第二次交锋,则是全家人对于母亲身份的重新认识。一个人的身份一旦确立,或者说思维一旦定型,想要再发生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就像鲁迅和成年后的闰土相遇,尽管鲁迅竭力回忆着儿时的种种美好,渴望能够再看到那个小英雄般的闰土,但是闰土已经褪去了稚气,被打磨成“社会化”的成年人,脑海中有了尊卑贵贱意识,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同样,母亲也是如此。她以货物的身份卖给他人做妻,所有人(包括子女)都轻视她,这种身份是难以转变的,尤其对于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弱势女性来说。但是母亲却以一种另类的方式,让她的丈夫和子女开始重新审视这种身份。和母亲的第二次交锋发生在一个雨夜,狂风暴雨让全家人担心独自居住在岛上的母亲的安危。其中最为担心的人,就是父亲。当江水翻滚,暴雨倾泻而下的时候,父亲再一次暴怒了。不过这次的暴怒不是对母亲,而是对他的子女们。他的愤怒来自于子女们如自己一般的冷漠。他希望子女们能够呼唤母亲,也希望母亲能够在暴雨之中安然无恙。当“我”将母亲的出走的根由归结于父亲,并对他破口大骂时,父亲居然意外的沉默了。最后,母亲的小屋里终于燃起了灯,父亲悬着的心才放了下去,并破天荒地给我们做了饭。这是小说里最激烈,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幕。父亲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首先,母亲的生死安危激发了父亲内心的担忧,而这种担忧绝非主人对于“货物”或者“牛马”的那种简单的担忧,而是对于生命中重要人物即将离去的深深的忧患。虽然过去父亲一直使唤母亲,并且没有给她应得的尊严地位,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勤劳善良的母亲也给了父亲一种无法替代的踏实感——如果没有母亲,这个家庭将不会有今天的和睦与团结。其次,母亲和父亲一定是有感情的,这是所有人类都具有的特性,长期共处,相濡以沫。只不过这种感情一直被父亲压抑着,从来不曾表达。那么父亲为何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原因也是很复杂的。首先,母亲确实是如假包换被卖到这个小山村的,在这里,没有哪一家人会对这种买来的媳妇格外的好,所以父亲也不能免俗,如果对母亲太好,就会遭到其他人看不起,这是表面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人的私欲在作祟。当权利在握,我们都希望能行使这种权利,哪怕凌驾与他人之上,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行使这种权利罢了。种种原因,让父亲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地压迫着母亲,就连亲生子女,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影响,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亲情观。所以母亲的形象就在这种不健康的、病态的环境里一天天坍塌下去。直到出走后,才发生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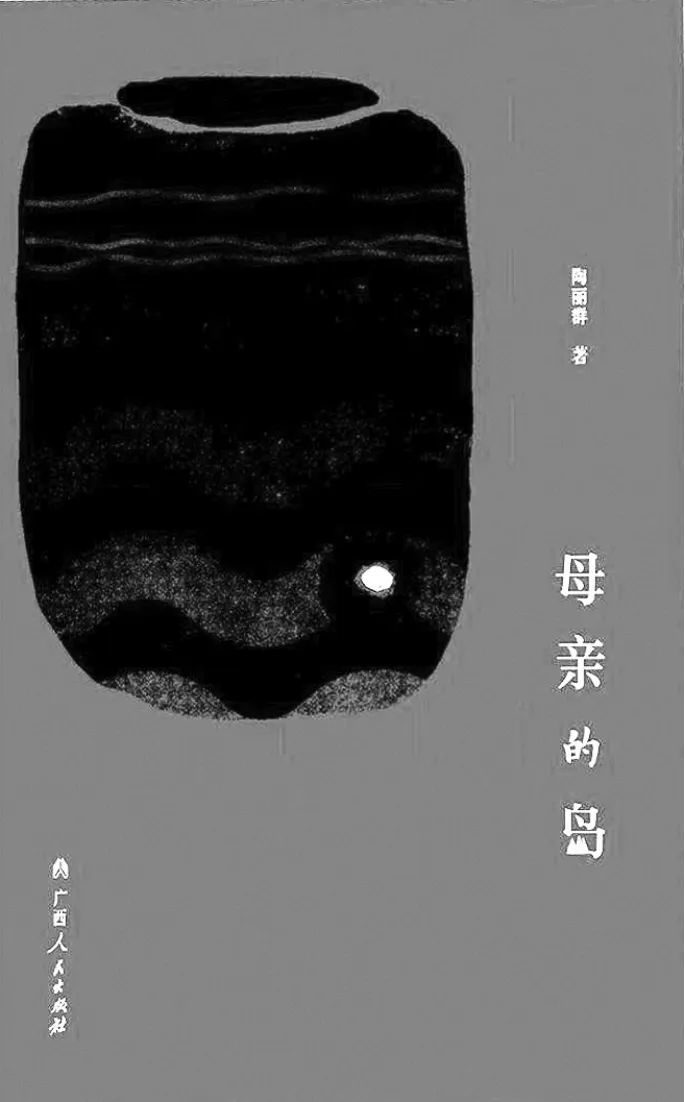
《母亲的岛》
母亲的出走为她迎来了转机,但是我相信母亲出走的动机一定只是单纯地想要逃离。当自然灾害降临,母亲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大家开始不由自主地担心了,甚至没有人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平时被肆意打骂,毫不关心的人,现在却变得如此重要?“我”和兄弟姐妹以及父亲,都热切地盼望母亲回来,然而母亲已经铁了心要离开。这个时候,全家人开始重新想象母亲的形象。“我”希望母亲能回来,希望能消除和她之前的种种隔阂。父亲也希望母亲能回来,虽然小说里没有直接描写父亲的心理活动,但是父亲的态度显然已经表明了:他会洗心革面迎接母亲的归来。于是,母亲的形象在众人的想象里就这样逐渐被重建了。过去那个任人使唤,稍不顺意就随意打骂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婉善良,勤劳肯干,家庭支柱式的妈妈形象。大家热切地盼望这样一个母亲归来,这些都要拜母亲的离去所赐。
但是母亲是不会回来的。这也让所有人没有预料到。在“我”和父亲眼中,母亲之所以要离去,只是因为家庭没有给予其一个正常母亲的身份。具体来说,即母亲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地位和自由。现在“我”和父亲愿意将这些一一还给母亲,但是母亲却依然选择了孤独地居住在小岛上。那么母亲到底是恨父亲,还是恨“我们”?其实都不是。母亲相反还为她的子女们做了很多。她将卖鸭子的钱无私地给了子女们,仿佛过去那些都没有发生过。当“我们”问及母亲何时归来,母亲却再一次一声不吭地离开了这个地方,而且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小说的结尾也是耐人寻味的,那个暴躁的父亲搬到了母亲居住过的小岛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下去。母亲就像《边城》里的傩送一样,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
我想把这篇《母亲的岛》和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小说《河的第三条岸》作为比较讨论,因为这两篇小说实在有太多异曲同工之处。在《河的第三条岸》中,作者描绘了一个离去的父亲形象。和母亲相似的是,这个父亲也是沉默寡言的,他在家中也没有获得过应有的地位,于是沉默的出走。但是这篇小说与《母亲的岛》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出走的父亲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般飘荡在河流上,“我们”无法和他取得联系,甚至获得只言片语的交流,只能任其在风雨中飘摇。而且,这个离去的父亲无疑是一个梦魇,日日夜夜折磨着他的家人。当暴风雨来袭,全家人都担忧着他的安危,父亲却始终不肯露面,这种反复的精神折磨几乎将全家人逼疯。最后,“我”希望能够接替父亲,让他回到岸上过正常人的生活。当“我”与父亲面对的一刹那,我却惊恐得仓皇而逃。可以说《母亲的岛》和《河的第三条岸》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是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在《母亲的岛》中,母亲彻底地离开了村子,由父亲接替她继续守在小岛上。母亲的离去代表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她选择到外面的世界,开始全新的生活。离开家搬到毛竹岛去锄地、养鸭,继而又离开了毛竹岛的母亲究竟去了哪里?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显然,乡土习惯所具有的“可怕的力量”,被陋习潜移默化之后无意识地将其内化为习以为常的规则的乡土社会以及家人的“漠然态度”是促使母亲离家出走的深层原因。但不同于其他一些“底层叙事”作家的是,在揭示出这些原因之后,具有高度文学自觉的陶丽群又以温暖的笔触为出走的母亲留下了一条回归的路,小说结尾写到,父亲“想待在岛上等母亲”,他“从此再也没离开过毛竹岛”,“每年梅雨季节过后,他总是把母亲的衣物翻出来晾晒,仿佛母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父亲最后住在了母亲的岛上,这不仅有等候和眷念的含义,更有“赎罪”的意味。是“我”和父亲将母亲一步步逼到如今的地步,而父亲无疑才是“主谋”,作者在结尾安排父亲留在母亲的岛上,是希望父亲能够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体会母亲那种艰苦绝伦的心路。虽然母亲走了,或许不会再回来,但这无疑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结局。
《母亲的岛》不仅是一个颇具深意的现实故事,更像是一则内蕴丰富的寓言,其中折射了在男权社会压迫下女性的选择和出路。对于那些丧失尊严和地位的底层妇女,如何重建其应有的母亲身份和女性话语权,作者陶丽群在这篇小说里给出了她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