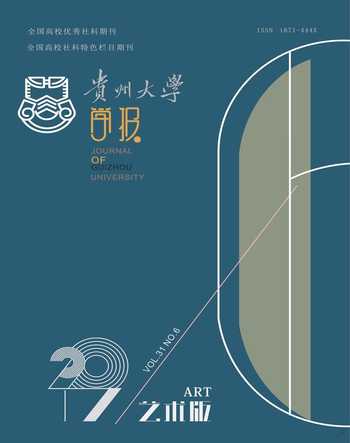再谈华语电影
龚艳 鲁晓鹏
学术主持人语:
“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在国内电影界引起的波澜前后延续了十来年,《当代电影》《上海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都曾做过专题或访谈,在国内的几次大型学术会议上国内外学者也就这一话题进行过交锋,各自亮明过观点。此次再做专题,既不想落人后,又很难出人意表,所以我们决定这一期的作者全部邀请海外华裔学者,希望提供更多阐释角度。另外,除了第一篇访谈是对“华语电影”焦点人物鲁晓鹏教授的访谈之外,另外两篇是对“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展开或者说是案例。香港电影是两岸三地电影中最有特色的,它曾经的殖民地身份,后九七身份,以及商业和政治话语、西方和东方文化的交织都让它呈现出不同于大陆和台湾以及其他华语区域的特色。可以说华语电影成为了我们讨论这些电影的通约数。匹兹堡大学钱坤副教授的论文《从悲剧英雄到黑帮罪犯:香港黑帮电影及其城市寓言》从类型的角度进入,兼顾和审视了香港身份问题,将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中的影像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之所以会讨论香港问题,而不是讨论一个北京电影或者沈阳电影,是因为香港电影在“华语电影”这个框架内是有效的。纽约州立大学珀契斯分校电影与媒体研究系助理教授张泠的《火山与矿山之歌:19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南洋”想象/意象》以“华侨”“南洋”“故乡”“异乡”“他乡”这些概念建构起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那些在中国本土之外的人、情、景。当作者将左翼和南洋连接起来,那个乡土和他者,革命和远方的投射变得更有趣。至少,“华语电影”是一个更有效的概念,能让我们进入到那些差异化的又互相连接的华语区域电影的讨论中。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6-0001-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6.001
时 间: 2017年4月1日
地 点: 美国匹兹堡大学
受访人: 鲁晓鹏教授(以下简称鲁)
采访人: 龚艳(以下简称龚)
觉得这个问题提出来有助于我们再去审视一些历史的概念,其实它的外延和内涵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词“旅行”,还在不断的扩展、变化。我自己做邵氏的研究,我记得当时邵逸夫好像在新加坡建国的时候拍宣传片的,这个关系就是很微妙的,他帮一个新兴的脱殖的国家政府拍了个宣传片,他又在新加坡、马来亚这些地方做了大量的电影工厂,他的片场就在那里,拍大量的华语电影。你说怎么界定他?至少“华语”这个词能突破国家、边界等概念,可以涵盖更多,有效性至今也是有的。
鲁: 对。像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先生,是华人但他不会说汉语,他说英语,他在英国的制度下长大。后来他自己学华语,又鼓励大家学华语。我在新加坡住几天,打开电视发现,我要不看屏幕,以为是在中国。播音员的国语跟北京话差不多呀,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是挺复杂。国族、语言、电影不能直接地划等号,关系不对称。有些同事写东西自家人说自家话,但是如果大家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场所看问题,就可能有新发现。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我批评北京同事,也无所谓。假如你屁股坐在北京,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得这么说话。各种压力下,你只能这样写,你换个方法和视角写,可能还惹麻烦。中国非常大,比如上海各种人都有吧,有些上海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与北京学者不太一样。我碰到福建的学者,他们说,我们离中心很远,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并不反对北京的同事,我本人在北京长大,我不会说任何方言,只会说北京话,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的母籍是广东番禺,我得自我批评。福建人说,我们这么远,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看法,隔海就是台湾呀,我们说闽南方言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语言政治非常微妙。
前两天我还问你万玛才旦的片子。他的情况很有意思,他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机部分。但是他拍的藏语片,有极其个人化的东西。前两年有一部藏语大片:《西藏天空》。虽然是藏语片,讲藏人故事,但那是官方主导的一种拍摄方法。万马才旦的片子《塔洛》就不一样啊, 很个人化。
龚: 是的。
鲁: 电影刚开始,一个藏人背诵毛主席语录,这给你无穷的想象和解读。藏人跟中国政治的关系、那代人的经历,非常有意思。
龚: 对。我当时和万玛才旦谈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看过他以前的一些片子,不知道您看過没有?我们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交往,他最早的短片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放的,在一个学生电影节上,叫《草原》,很短又是藏语拍的,完全超越我们对少数民族电影的理解,他讲的完全是他们那个宗教的逻辑,就是一个老太太要送上山去献祭的牦牛丢了,村长就说我要帮你去找,然后锁定了两个嫌犯就去找这两个人,他就让这两个男孩绕着嘛呢石转,然后发誓说自己没有拿,这个老太太最后说我不需要再去追查任何事情,因为如果你要惩罚人就有悖于我去做(祭神)这件事情。所以推动故事的构成或者说逻辑,不是汉族的逻辑了。但这就是我们希望或期待的东西。
鲁: 就是呀。
龚: 我们当时觉得很不一样,当时他年纪比我们大些,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写小说写诗歌了,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艺青年,然后拍了电影。后来他就一直拍,为什么那天我约了他要谈这个片子,因为我觉得《塔洛》里面有点急,有点很明确的那个意思。您知道那个片子讲身份证丢了吗?
鲁: 少数民族身份,对不对?
龚: 是,而且这个片子一直没有正式地放过,我在独立电影节看的。我就问他,以前看你拍片子用心平气和来形容,就很像他那个世界,或者说我们想象的那个藏族世界。他自己后来说有美化的成分在里面,他说我现在要拍这样的你们看起来很用力的片子,我内心也在变化。因为他人特别温和,非常谦和,说话声音很小,汉语说得很好的一个人,但他写作是用藏语。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复合性,他自己一定是藏族精英,而且他深受汉文化教育。少数民族精英势必要经过汉化这个过程,汉化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矛盾在里面的,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他说对,他说我是有意识地告诉自己虽然我是接受了汉族的教育,我也很向往汉族的文学、艺术,但是我的身份是一个矛盾体。而且他拍的电影里对民族的表达反而是看不到他自己说的他受伤痕文学的影响,他读书的时候正好是1980年代,他说他是非常爱看那个时期的文学的,他也很活跃。他这个身份多复杂!
鲁: 对。我觉得像这种个人化的电影或是少数民族电影挺重要,因为我们平常看不到。看到的多是有宏大叙事的从上到下主导性的电影,就像十七年的少数民族电影。
龚: 那就不叫少数民族电影了。
鲁: 叫少數民族题材电影,是吧?我们对少数民族了解很少,我没去过那些地方,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呢?我的知识是从看电影来的,而且都是从一种特殊的角度看电影。现在有一部电视剧《新丝绸之路》,国内主要电视频道播放。故事怎么开始呢?我不看都知道。开始一定是解放军解放新疆,以前的统治阶级跟国民党勾结,解放军来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少数民族题材的这个大的历史模式不能变。刚才我说关于西藏题材的电影也有这个问题。那部大片也是从解放农奴着手。大的话语没变。 1950年前后,解放军进藏、进疆,这个根基是叙述底线。而万玛才旦的电影其实我们挺需要看的,但平常看不到,电影院也不公映吧。
龚: 2014年他在香港做过一个完整的放映。您说的这个“华语”,我记得您之前访谈里提到,他其实是多语种的,不是简单的普通话。这里面肯定会有人觉得能不能涵盖到他的范畴。
鲁: 这个学术问题我也在思考,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我知道国内学者也做了一些努力。“中国电影”属于“国族电影”的范畴,中国境内拍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后来华语电影的概念出现以后,国内学者又搞出一个“母语电影”,比如蒙语电影、藏语电影。后来有人觉得这个概念说起来也不太上口。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华语不是个语言学的概念吧?在中国大陆,人们说“汉语电影”“汉语字典”。能不能华语电影也包括中国其他语言的电影呢?我想可以把万玛才旦拍的片子也算作华语电影,我个人觉得可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怎么归类和划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东西。华语电影、母语电影有些人赞同,有些人不赞同。华语电影包括各种方言,能不能不光是汉语方言,能不能包括其他民族的方言,少数民族语种?我持开放态度。
龚: 他们会不会纠结在“华”这个字上?
鲁: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宪法里说,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这样一来,“中华”就包括中国境内各种语言和民族。“华语”是否可以包括这些语言?大家需要反复研讨。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叫“中华民族”,但是在美国就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说“美国民族”,说起来人家笑话。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国家。“中华民族”你怎么翻译成英文?“美国人民”怎么翻译成中文?有时候两个不同的文化语境转变还是挺困难的。
龚: 是不是还是因为汉文化太过强势和历史的书写作为主题?
鲁: 有可能,这里有个历史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都成问题。那时别人就开中国玩笑,包括从葡萄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说你看,这个国家没有一贯名字,它叫“明”,或叫“清”,这是朝代名字,不是国家名字。 那时大家讨论,这个国家应当怎么称呼?可以叫“华”,可以叫“中华”“华夏”等等,最后选择“中国”。“中国”这个字当然几千年前就出现了,但是在近代,中国经历了重新构建的过程,新的国家取名“中华民国”。
现在小学生都知道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中华民族”,但这个概念也是近代构建的,清末民初吧。辛亥革命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他们要推翻满族统治。后来成功了,满族被推翻了,他们一看,不行啊,这是个多民族国家,你不能驱除这些民族。随后,又出现新的概念,“五族”:满、汉、蒙、藏、回,做了五色旗。中华民族不断地自我构建。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的经验,识别它的民族。前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中国识别了56个民族,到今天这个数也不能变,只可以学术讨论。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荣”,到56个民族,国族的话语一直演变。电影研究也有类似现象,所谓“华语电影”“母语电影”都是有益的尝试和话语的构建。
美国是另外一套说法。它有数不清的族裔,西班牙裔、越南裔、日裔、华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等等。它的官方话语是“多元文化”。它是另外一种国家构建。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历史演变比较复杂。前一阵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兆光写了本书讲中国历史,他提到周成王时代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宅兹中国”。那时候就出现了“中国”这个字,起码有三千年了。这里“中国”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是否一样?它可以证明“中国”的悠久,但是随着历史变迁,中国的概念不断变化和扩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古老国度旺盛的生命力,就像《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那时候周朝已经八百年了。中国是个老的国家,同时焕发新的生命,需要我们不断地构建、阐释、研讨。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华语?什么是华语电影?身份认同问题,国族构建问题,诸如此类问题,需要大家不断讨论。
龚: 那回归话题,比如说华语、普通话电影,戏曲电影中的黄梅调电影,因为戏曲电影曲目很多,但是黄梅调电影是特例,就是它流传到东南亚比较盛行,邵氏当时那一批黄梅调电影风靡东南亚,包括北美也有。我想借华语电影这个语境来讨论这个问题。黄梅调更倾向于普通话,我觉得这个是它流传的一个因素。它在东南亚、台湾地区非常盛行,这个和华语或者和普通话是否有联系?
鲁: 以方言为主的戏剧强调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丰富性,比如昆曲电影《十五贯》,越剧电影,甚至像谢晋的《舞台姐妹》。当初周恩来总理想把中国各地的戏剧拍成电影,这是强调中国的民族性。香港的方言喜剧电影,也能产生一种民族向心力,同时也娱乐港人。
龚: 对。身份的一个强调。看上去是去政治化,其实我觉得是强调身份的。
鲁: 但是在电影工业运作的层面,比如邵氏公司,就有商业考量了。他要赚钱,希望扩展不同层次的华语电影观众,而在地理层次,让公司的电影广为流传,波及东南亚。
龚: 但是黄梅调毕竟有点像普通话,那普通话本身就是有一点想要统摄民族,或者想要民族有个建构有个共同语言,所以他并不是所有曲种都拍,他选了黄梅调来拍,实际上在海外散居了各种籍贯的人,但是类似于普通话的黄梅调他是不是有这种建构的意思在?
鲁: 也可以这么讲。中国大陆的方言电影很多,比如贾樟柯的电影有山西方言。但贾樟柯讲的是中国的故事,他用方言是伪装。越有方言,中国性越强。从《小武》到《天注定》,他的片子使用中国各地方言,增强电影的真实感和戏剧感,内容上涉及中國各地的普通百姓。“十七年”也拍了一些所谓的方言电影,比如《抓壮丁》,那是通过方言讲述宏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故事。香港的粤语片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商业运作,以娱乐为中心,自成体系。现在香港电影经历所谓的大陆化、中国化的过程,为了赚钱而跟大陆合作。影片的观众是中国大陆的庞大人口,这也慢慢地改变香港电影的模式和特色。香港几百万人口,原来南洋是非常大的市场。冷战时期,南洋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观众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跟13亿人的大陆市场比,还是不行。陈可辛说,他不期待欧美市场,中国大陆市场足够了。他拍《中国合伙人》,就是瞄着中国大陆。原来南洋市场很大,现在是个零头。这样做,港片也有点变味吧。片子都是双语配音吧,针对大陆。
龚: 好像连续剪辑了几个版本,我记得《无间道》就剪了几个版本,大陆放的版本是不一样了。当然版本不一样在1950、1960年代就有,当时邵逸夫和香港其他公司发给南洋就有不一样的,他们有考量。您说香港的粤语片挺有意思的,本来香港没有那么多大陆人,在1940年代初大陆进去的那么多,他本土的人还是以粤语为主,当大量大陆人进去,普通话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民族或者身份的标志,其实主要是方便沟通。
鲁: 还有台湾的市场吧。
龚: 对。他还是有市场考虑。但是到1970年代,香港本土化的意识起来了,所以1970年代到1990年代又是粤语特别兴盛的时候,然后到了合拍片时代更复杂了。
鲁: 台湾的情况挺特殊。国民党去了以后,他们的话语是革命话语,很像中国大陆的话语。蒋介石到死都说革命。那个时候就是拍国语片,虽然闽南话或者说台语片也有。
龚: 台语片有。
鲁: 地位比较低。
龚: 对。那跟粤语残片的状况差不多了。
鲁: 现在台湾电影工业已经七零八落了,很可惜。原来以国民党为主体的电影,辉煌一时。
龚: 有官方的电影厂。
鲁: 很可惜,台湾的电影工业生存艰难。
龚: 这两年又起来一点,魏德胜拍了《海角七号》。但还是很狭窄,他还是只能到大陆来。
鲁: 原来有国家主导的中影挺辉煌,他们的电影也送到香港和南洋,反过来说,台湾也是邵逸夫的香港电影的市场。台湾、香港、南洋这几个地方互动。解禁以后,后蒋经国时代,台湾的电影受到商业化冲击。
龚: 但后来政府也鼓励他们拍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又完全被香港电影吞没。其实台湾一度有很好的商业类型,比如琼瑶电影。
鲁: 对。可是现在,它的电影产业微乎其微。
龚: 对,就断了。现在又有一点但很零星,他们本土市场可能支撑一下,但都不够。
鲁: 前一阵子我还看一个叶月瑜的访谈,关于亚洲电影工业。她说,她写完她的那本书以后,亚洲电影工业这个概念就不适用了,因为各方都来和中国大陆合作,没有所谓亚洲电影工业。日本、韩国、香港、台湾都和中国拍合拍片,看重大陆市场。
龚: 以前是多极的。
鲁: 这是商业考虑。
龚: 对。当然也有政治。
鲁: 也有,以后香港电影可能就没有原汁原味的香港的东西了,它的产业跟大陆连在一起了。冷战时期它跟大陆是分开的,是两回事,它主要开拓南洋、台湾,甚至韩国市场。我遇到一位韩国学者,他说他从小在韩国看吴宇森、周润发的电影,比如《英雄本色》,是他们的粉丝。
龚: 对。那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前看过马来西亚一个人拍的电影,他肯定是看香港电视剧长大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人拍武侠电影,他看得太多了。
鲁: 是。韩国那时候也是台湾和香港电影的市场。他说他上中学时候看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对周润发印象很深,特别喜欢周润发。港片的传统市场包括日本、东亚、东南亚的观众,而现在主要是中国大陆观众,大陆的中产阶级兴起,构成庞大的消费群体。
龚: 但是我自己在大陆倒是感觉这几年其实好多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大陆本身生产的质量看上去很多很糟糕,但是钱又很多,钱很多的时候有的人就愿意投艺术片了。就是当商业都不好的时候,艺术就更糟了。现在艺术电影也还出来,虽然大的市场里也很糟糕,国片很差,但是很多像毕赣、万玛才旦也还是出来了。
鲁: 一般人不愿意看这些缓慢枯燥的“艺术片”。《塔洛》开头,光读老三篇《愚公移山》就读了三分钟,谁有耐心看?一般老百姓看一会就不行了。贾樟柯的片子都看的烦。好莱坞大片闹点科幻电影,娱乐目的达到就行了。年轻人看郭敬明的片子,放松一个半小时换换脑子就行了,不需要深刻思考社会问题。
龚: 所以他们其实很难,尤其是这种独立电影导演。
鲁: 拍了又不能流行。两年前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开会,看到一本新书:《蒙古族影视研究》。文集内容包括中国大陆内蒙古拍的电影,也有蒙古国的电影。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蒙古国是独立的国家,而中国大陆有蒙古族。
龚: 但书强调蒙古族,所以还可以用蒙古语来概括,和我们讲华语电影还不一样,跨边界的。
鲁: 对。内蒙古是中国的事。
龚: 我们讨论华语电影是讨论内蒙古这个部分。
鲁: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不知道以后怎么解决。“国家”这个概念也不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就说,以后国家要消亡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帝国的概念,没有边境。草原上你的马来吃草,我的马也来吃草,没有说弄个铁丝网划边界。原来都是部落,今天我臣服清朝,明年我臣服蒙古,都无所谓,但是部落一直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现在是民族国家时代,你要划界限,立界碑。目前人类历史就是这个阶段,咱们死以后谁知道什么样呢。
龚: 他需要这样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就像柏林墙。
鲁: 原来清朝是大帝国,控制很多部落。如果整个部落归顺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一大块土地随之都是清朝的。过了一百年,部落跟着英国跑,跟着俄罗斯跑,那块地又不是中国的地方了,但他们没有划一个边界。
龚: 現在的研究也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历史背景之下进行。
鲁: 对。我们不能跳出这个背景。我们看事情需要开阔眼界。咱们通过学术,说一些平常人们不愿意说的话,比如国家消亡,这话说了不犯错,是马克思说的,毛泽东也说过,共产主义以后国家要消亡,政党要消亡。政党怎么消亡我搞不清,一个社会总要有组织嘛。
龚: 连国民党现在都成这样了。
鲁: 真是希望有一天国家消亡。约翰·列侬最震撼的一首歌就是《想象》(Imagine),想象有一天国家不存在了。每年新年到来之际,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就放这首歌。歌曲想象哪天没有地狱、没有宗教。那完全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充满反战情绪。几十年过去,这首歌还是最动听的一首。新年来临之刻,歌词传递出一种和平的信息给全世界。
龚: 文化完全不一样。
鲁: 昨天我说到美国从小学就教育一个孩子成为美国人。孩子不愿意同学们听见自己说外文,比如中文、俄文、意大利文。他们要认同英语。美国是非常爱国的国家,这个超级大国有特别强的民族意识,民众非常喜欢批评自己的国家,而这样的自我批评也是一种姿态,一种高姿态,自豪感。我们敢于批评自己。美国人越批评自己的国家,越显得爱国。你看,我们的国家可以随便自由地批评!但外人批评自己的国家就不行,就不容易接受。我想每个国家都一样,尤其这种超级大国,民众意识特别强。
龚: 我们能不能从学术上谈一下中美差异的问题,因为我基本是在国内受的教育。您作为海外的学者,您自己感受中国大陆学术研究比较大的问题或者优势是什么?
鲁: 我不敢多说。几年前我接受李焕征访谈时,说了一些话,后来整理出来,似乎我说了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有一种零碎的感觉,需要整合一下。我现在回忆,好像当初我没那么说。中国大陆资金特别雄厚,人员多,机构多,成果多,华语电影研究是最繁荣的,其他地方没法相比。我原话这么说的,好话一大堆。但是有些人还不能满足,太敏感了。
我个人觉得个人独立思考比较重要,而不是一个新话题出现后,大家一窝蜂上的造势。但这也不容易,电影不像研究唐诗宋词,它的共时性非常强,你不能关上门研究。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反复思考研究了三年,想通了一件事,然后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给大家看。但什么东西传到国内马上就不新了,一百个人来谈这个事,而且不加引用。一个人好不容易琢磨出来的观点,一到国内,哗的就完全被人接受了,炒作太厉害。
龚: 其实大家没有心平气和来做自己独立的研究。
鲁: 国内信息传播特别快。两年前我和国内同行在复旦大学有个华语电影讨论会。有学者说:怎么一亮底牌都是海外人的底牌呢?“华语电影”“文化中国”这些话语怎么都是海外人的底牌呢?中国自己的底牌在哪?
龚: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国内的学者一直在试图去寻找,为什么李道新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他其实是要寻找一条所谓的中国自己的路,他们喜欢提民族。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不能说这就是最好的,我们也希望提供其他的路径。
鲁: 我是比较文学出身的。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有这种说法:我们要创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你看中国更大的官方话语,我觉得也很好,不是不赞同。几个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等等,这也说明问题。但是,也不能动不动批评别人是西方理论框架或西方中心主义。你要总是这种态度,就很少有原创性,就不敢有些新的东西。
龚: 交流可能不是特别顺畅。
鲁: 对,杜维明先生一个很著名的论点就是“文化中国”“边缘是中心”。他长期在台湾和美国。也有人说这个概念也不是他提出的,是南洋华侨最先提出来的。现在大陆接受他的观点,还任命他为北京大学高级研究院院长。他又娶了中国大陆太太。“文化中国”“华语电影”这一系列概念从外边传过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性起源,写出四卷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多么厉害。但是他借鉴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京都学派的思想,说宋朝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中国的原创性自然重要,但要营造一个好的氛围,产生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这方面大陆可能要注重一些吧。
龚: 有没有你们觉得大陆学者完全不同于海外的角度?当然不说特别极端、意识形态想要妥协的一部分。可能海外的学者就不会这样想,他们还是挺有特别的角度。
鲁: 对,他们做东西很扎实。他们研究上海电影史、南京电影史,我们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上次咱们在南京艺术学院开会,我在一个小组里,坐在旁边的一位国内学者说得很有意思,他说海外学者跟大陆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海外学者先有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往里面塞细节,大陆学者先有细节。
龚: 先有材料是不是?
鲁: 好像是,他说的也有道理。这两种学术方法,就好似哲学思维的两种不同方法:归纳(induction)和推演(deduction)。一个是从经验到理念,从特殊到普遍;另一种是从理念到现象,从普遍到特殊。近代欧洲哲学史上,曾有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之分别。理论框架在海外学术比较重要,跟训练有关,我们在海外教学生也是如此。就像在中国教语文,你写一篇文章,一定要有中心思想。在美国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论构架一定要有。一篇论文不能弄成一个流水账,要搭构一个理论平台。这是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呢?我觉得也没必要扯到那里。学者都在努力搭建自己的理论框架,说明一个问题。作为学术,不能死板地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要不然你做不出新的成果。我是比较文学出身,严格意义上我不是搞电影的。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我们在综合大学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训练和工作,思维方式也是综合的,而技术方面不那么敏感。大卫 波德威尔谈电影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分析。我的训练是比较文学,偏重理念,就像你有哲学背景。我不是电影学科班出身,电影工业、产业研究不多,而偏重思想吧。大陆学界现在更多元化。在电影学界里,好像有几个机构培养了不少人才,比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它们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自己的圈子。不少人擅长史学。我觉得电影史很重要,让人看到整体而不只是片段。有搞史学的,注重资料和考据;有搞电影批评的,比如北京大学的戴锦华老师。
龚: 她确实是在电影的圈子里有众多的粉丝。她的研究会给人很多启迪,我入门其实也是最开始看了戴老师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包括她讲“第四代”“第五代”,可能电影史书都没她讲得明确。做电影史有个问题,资源占有的不均衡。
鲁: 有些负面的电影,比如李香兰演的电影,大家也可以看看,作为反面教材,可以研究嘛。观众是有头脑的,能够分辨是非,了解历史真相。
龚: 那个没问题,我们上课要讲的。
鲁: 但你不能放李香兰的东西是不是?
龚: 我们没有资料,不是不能放。
鲁: 对啊,在海外你去买就可以,上亚马逊网去买。中国买不到李香兰的电影。
龚: 如果和香港与台湾电影资料馆相比,中国电影资料馆对资源的共享程度还有待提高。
鲁: 大家应当呼吁资料公开。
龚: 好的,再次感谢鲁教授接受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从“华语电影”开始,结束于对电影资源共享的呼吁,希望给更多热爱电影、研究电影的人以更便捷和公平的平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