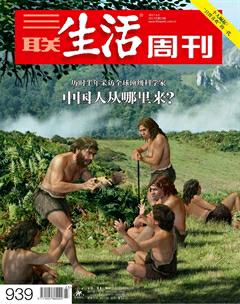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4)
朱伟
《米》写仇恨导致恶的滋养,还是一个因果故事。五龙坐在运煤的火车上,从枫杨树逃荒到城里。如果不是因为饿,他就不会遇上码头上的恶霸阿保,不会因阿保留下耻辱的仇恨。同样,如果不是因为饿,他就不会跟着拉米的板车来到鸿记米店,不会因为两姐妹对他的侮辱,更萌芽了仇恨的种子。这部长篇的故事其实不复杂。假如冯老板与他两个女儿有一点怜悯心,五龙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他本是靠力气吃饭的本分人,尽管他有本能的欲望。偏偏这一家人视他为狗,大女儿织云被六爷抛弃,又怀了阿保的种,冯老板便使圈套将她甩给了五龙,又花钱给船匪要他的命,偏偏又少给了银元,以致只卖了他的一根脚趾。五龙是一点点感觉到,“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成了米店一家的猎物”,于是开始一连串的报复。他先借六爷的手把阿保的生殖器割了下来,又视织云为性奴。冯老板中风死后,他占有了织云的妹妹绮云,成了米店实际的老板,又策划了对六爷的复仇,先炸了他的公馆,又策划了对他的谋杀。除掉六爷后,他就成了码头兄弟会的头子,成了与当年阿保和六爷一样的恶霸。成了恶的代表,他就该承担因果报应了——先是染上了梅毒,兄弟会鸟兽散后,他成了孤家寡人。随后是,他的第一个儿媳成了妓女,第二个儿媳被日本兵刺死,两个儿子都成了光棍。最后是织云与阿保的私生子抱玉在他身上施酷刑,实施报复,完成了自作自受。小说结尾是,这个垂死的五龙包了一个车皮,装了一车皮的米还枫杨树乡。他临死前对二儿子柴生说,我的脚趾是不全的,两只眼睛是瞎的,曾令以骄傲的生殖器烂掉了,胸腹都掏空了,最后就剩下一口金牙。柴生就将他最后剩下的金牙都拔了下来。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这小说,因为这小说里写人性溃烂,凝结着太多的残暴之恶痂。苏童其实不是莫言,他对城市其实没有恶毒之心,却非要通过五龙咒骂“狗娘养的下流罪恶的城市”,在“我身上到处都留下伤痕”。小说里最畸形的是五龙在米堆上性虐的嗜好,他一次次将米塞进织云、绮云,以及妓女们的阴道。这部小说黄建中将它改编成了电影,一直没审查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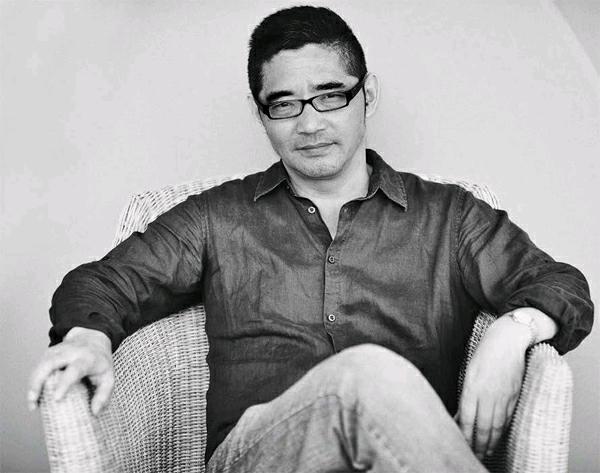
苏童2004、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城北地带》与《我的帝王生涯》
随后是《我的帝王生涯》。那段时间苏童英气勃发,写得天马行空,很顺。《我的帝王生涯》的构思杂糅了很多戏剧化的模板,苏童像飞鸟般洒脱俯视着掠过,结构上只用三章,就才华横溢地写完了。前两章写“我”父亲驾崩后,祖母皇甫夫人伪造了遗诏,扶植“我”成为假燮王,垂怜听政。“我”在帝王生涯中学会了专权,学会了残暴。第二章的结尾,皇甫夫人死后,已经掌握了兵权、羽翼丰满的真燮王端文,带着老燮王亡灵在他额上留下的金光闪闪的刺字杀回了京师。端文“像真正的兄长一样”摸了摸“我”的脸说,从宫墙上爬出去吧,去做一个庶民。于是第三章他就开始了奴才燕郎陪伴的庶民生活。这小说的真正价值其实在第三章——苏童让打劫者抢光他们的钱财,真的变成一无所有,然后从庶民的起点,开始流浪生涯,自己组成杂耍班子。我从中依稀能见到德国作家伯尔《小丑之见》的影子。这部长篇的前两章,在我看,失在那些表面看踌躇满志的漂亮而自信的叙述,因为情节太多已被他人打磨过,帝王生涯中太少“我”自己的切肤之痛,叙述就如一件华丽的衣服。衣服越华丽,就越显出肢体干瘪。
第三章好在相对出脱了窠臼。小说中写得好的是燕郎这个人物,论类型,他其实不新鲜,但苏童写了一种质朴又锐敏的奴性——“陛下去走索,奴才就去踏木”,“我能聞到陛下身上的每一种气息”,没有狡黠,除了伺候,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是这小说中的温润所在。另一个类型化人物蕙妃,好在第三章被苏童安排进了凤娇楼,戏剧化地成为帝王流浪之路上的风月相会。苏童让曾经的帝王责怪她:“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让这位曾经的宠妃回答他:“到这里来等陛下再度宠幸。”干脆将戏剧化推至极限,能产生极致的效果。
我不明白,在构思上,苏童最后为何没让这个前燮王组成的杂耍班子进京城,在燮宫后草地上,面对旧日臣相官吏皇亲国戚,完成那场“终极”走索仪式,完成前燮王与现燮王的生死戏剧化面对,却让杂耍班流产于彭国士兵的屠杀,燕郎轻易被杀死了,现燮王也轻易就被烧死了。本来一个在戏剧化中寻找趣味的文本,却回避了最应着力表达的戏剧化结尾。苏童最后安排的结尾是,蕙妃在旧货街上兜售“我”的风月笺,“我”逃出了“伤心之城”,到了少年时代老师觉空的苦竹山,白天走索,晚上读《论语》。《论语》是小说里最空洞的一个道具。
这篇《我的帝王生涯》,鼓荡了张艺谋拍武则天的欲望。张艺谋想拍武则天,由来已久,拍《红高粱》时,就念念不忘了。他期望苏童能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则天,却不理解,苏童其实既不擅长写剑拔弩张,更不擅长通过尘封的历史,塑造出一个油彩丰厚的形象。他声称,那段时间他泡在故纸堆里苦不堪言——命题作文,捆绑了他的天马行空。而张艺谋,大约也因担心他不能胜任而想出了邀赵玫、须兰、北村等一齐竞技这一题材的主意,那时他已有足够的实力了,但竞技对作家们意味着什么?苏童说他“完全被蒙在鼓里。到知道了,觉得很没意思,这小说就草草收场了”。
我倒觉得,这段时间他真正写得好的是《城北地带》。其中的环境是“文革”中期。“文革”开始时苏童才4岁,这是他以童年视角,看化工厂那三个大烟囱有毒烟雾笼罩下,香椿树街上那些芸芸人事。横跨街面的晾衣竿上的水滴、临河木窗上映出的水光、闪出鱼鳞波却又是浑浊肮脏的河水,以及飘着夜饭花甜香的深巷,回到承载他童年的城北,一切都有了切肤感。
我以为,苏童是以美国作家安德森《小城畸人》的方法,夸张了一个少年眼中的小街人事。《小城畸人》是那时我们讨论过很多的一本小说集。苏童学了安德森,以一种感伤的态度,来嗟叹香椿树街上那些轻薄卑贱的生命,他们轻薄得就像一页页随时都可撕毁的纸——18岁的红旗因突发的冲动,就强奸了14岁的美琪,被判了刑。美琪面对不了投注给她的目光,就带着她剪的蜡纸红心投河成了鬼魂。叙德进洗瓶厂当学徒,被风流的金兰勾引后,没想到父子搞了同一个女人。金兰生了孩子,引导叙德私奔了,叙德的父亲却羞于面对贞洁的妻子,剪了自己的生殖器。小说中的主角达生,最后为了香椿树街的面子,只身一人去赴群架,被打死在煤堆上。那年代这样的群殴很多。这小说的后半部相对前半部,显得有点匆忙,但苏童笔下这些被本能欲望、本能所要维护的自尊损毁的一个个小人物真是写得太好了。他用一个闹钟作道具,就写透了辛酸——小说开头,达生的父亲李修业在闹钟声中匆忙要去上班,因自行车被儿子偷走,他借了辆没刹把的车,轻易就被撞死了。小说结尾,带了闹钟去赴约的达生,临死前嘱咐“猪头”要把闹钟带回给他母亲,因为她上班要用的。“猪头”在逃逸中忘了,以致他母亲打着雨伞,到处问这个闹钟。苏童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写残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