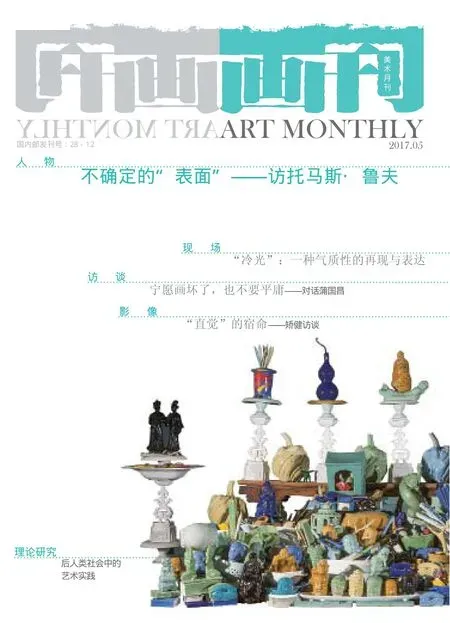“直觉”的宿命
——矫健访谈
本 刊
影像 PHOTOGRAPHY&VIDEO
“直觉”的宿命
——矫健访谈
本 刊
编者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美院读书的时候,矫健的绘画里就显现出一种受自相机影响的精确和冷静。在他后来的摄影创作中,这种冷静和精确,又与一种直觉性的表达相结合,形成一种具有内敛气质的影像语言,即在看似理性的图像之中,流露出对诗意和唯美的探求。在《填补空白》《午山村》《1/24》等作品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气质的存在。经年累月的创作,不仅让矫健越发熟稔相机的脾气、相纸的差异以及各种胶片的特性,更让他对材料生发出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情感。他在访谈中这样说道:“偶然的机会,我找到过期三十多年的相纸,我让它曝光来完成它的宿命”,“我能够感受到光线射到纸上,让银盐乳剂形成潜影的快感”,这些听来略微有些玄虚的表述,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矫健摄影艺术非常感性的一面,并呼应了弥散在他作品的细腻影纹中那种无可言状的情绪。如果如矫健所说,他以曝光完成了相纸的宿命,那么将他的艺术直觉定格在相纸上显影成像,或许也是他的一种宿命。

《赝品》 矫健 行为、装置、摄影 2003年
《画刊》:你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就有绘画作品参展,也画了很多年的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地投入到摄影上来的?
矫健:什么时候开始我也说不清,因为那是渐渐地发生转换的。可能是各种原因,时间越来越少,画画需要消耗的时间更多一些,拍照又是相对快一些。还因为个人的关系,我对手工的、机械的东西,对这种物和直接的接触感兴趣,这里面的美学和语言的特质跟我们以前用手工进行绘画有相似的地方,总体上,我还是保留着一种绘画式的方式,我不是纯粹从基于记录影像的思路来做摄影创作的。
《画刊》: 我想到你把这种基于记录的摄影称为应用类摄影,你说摄影除了可以因记录和传播的价值得到广泛应用以外,还有一种强大的能力是独特的方式介入,沉浸体验用反观的可能性的方式。
矫健: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我要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要参与到我的认知过程,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过程中,两者是交织着的。我的艺术不是说我种了一个花、弄了一个产品,而是跟我是一起成长的,所以它参与我的思考,成为我的思考方式和工具,在这过程中不断地给我提示。我喜欢那种艺术,我的摄影也是这样,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不完全依赖我的存在。比如偶然的机会我寻找到过期30多年的相纸,我让它曝光来完成它的宿命。这种体验确实有不同,它不是仅仅把对象搬到图像上去,而是一种自然的生长,同时又能完成我心里对某一个东西的理解。我能感受到光线射到纸上,让银盐乳剂形成潜影的快感——卤化银颗粒放肆地尖叫着拥抱每一粒到达的光子的纵情一刻。在很多作品里面,我感觉到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在跟我对谈,所以我的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依附于一种观念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经常会看着自己的作品看很久,有一种跟熟人在聊天的感觉,并且这样的过程不断给我提示。在我,摄影是一种伴随着我的思想的基础性的存在。
《画刊》:《填补空白》这个系列你做了四五年。怎么想起来做这样一件作品的?
矫健:当时一个意大利策展人叫莫妮卡,我们都是蛮好的朋友,突发奇想要做一个关于“我”的展览,叫做“It is I”,邀请艺术家们自拍,不限定是否影像艺术家,因为所有的艺术家都会自拍,对于“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跟我讲的时候,我接受做这样的“命题创作”,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困难的命题,意味着要思考“我”而不是记录我的表象。我怎么来看我自己?我是谁?怎么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关于我自己对“我”的认识?再或者说什么是“我”?是一个视觉上的直观的我,还是一个身体里的我,还是一个活在这个时间段里的我,还是意念里的我?到底什么叫做“我”,我没法确定,有一种陷入的感觉。在这种纠缠中突围的方式就是直觉。我认为我在从小到大这个时间段里面我比较清晰地知道我的存在的价值,可能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而是整个环境赋予的:你必须是一个对公众有贡献的人,你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大家能一起过得更好,我们个体的存在价值是以对其整体的贡献程度来加以判断的,这是我成长的那个时候受的教育。
“填补空白”这个词在我们那个时候隔两天就能看得见,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几乎所有的能够“填补空白”的成果都被看做成就,因此,这是一个混合了理想与政治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褒义的词汇。能够为整体利益作出贡献,必定是引以为荣的,从小受的教育是这样,我认为这种使命感是我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状态,而且我也愿意把这个叫做“我”。所以在作品中我很艰难地适应现实的空洞,作为一种象征,让我的身体完成了一个使命,获得存在感,这样的方式似乎也让我的精神得到了一种归宿感。
《画刊》:我觉得《午山村》有一种比你的其他作品都更为理性的东西,同时又是最诗意的一套作品。
矫健:这个系列也拍了40多幅。午山村在我们学院附近,我几乎天天路过,看到一点点被拆除的农村别墅废墟,我感觉到的并不是表面的沧桑。后来偶然的一次走进去,才发现里面赶工装修的地方甚至有一些还没有干,但所有的东西都碎了,里面仿佛是那么新鲜、娇嫩的伤口,在空空如也的室内从窗口看出去又完全是静谧唯美的田园风光,这两者的结合打击了我的知觉系统,让我印象很深。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拆迁是按照楼层与装修算补贴的,所以是为了拆而盖,自然就会有这种结果。在拍摄的时候,实际上技术上有难度,要达到我预想的效果,得考虑景深与光比,把现场的光比调整得非常好,室内和室外要接近,以及权衡景深的先决条件,窗口要像镜框镶嵌的一幅画挂在墙上的感觉。我把室内的光比和室外的光比保持一致是要让它显得没有那么突兀,也弱化甚至排除那种时间/地点的现实感,让它沉浸在一种表面上平坦柔和的氛围里面,让那种张力在观看者心里慢慢发生作用。总体上来说,对这种视觉呈现的要求,还是我个人的趣味和欣赏习惯在起作用,里面还是隐藏一种唯美的视觉性。我没有要肩负着揭露或者记录现实的使命感,我也不想一下子把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时代的变革导致城市向外扩张,建好的农民房子如何拆迁,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那些东西在我的作品里面意义并不大,对我来说那样太简单了。我要把这个事情从当时的环境里面抽离出来,相对要含蓄和复杂一些,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视觉的方式。
《画刊》:2002年你做了《表面》系列,之后2003年又做了《赝品》,这两个作品在观念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矫健:《表面》和《赝品》差不多是一个时间段的作品。当时很纳闷人们为什么会有许多奇怪的行为,比如很多地方把老房子拆了,造一个新的老房子也是这种类型的,毁掉那样的形象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真实的形象被一个虚拟的形象代替,这种一系列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感受。同时,并非亲历的甚至是虚拟的事物是怎样作用于我们的认知,让我们坚信它是实际存在的呢?当时觉得这个点有趣,所以做了几个系列作品,这两个相对有代表性。

《表面·杭州旅行者的酒吧》 矫健 2003年
《表面》指向的问题是:我们不断在表面修饰的掩盖下面从来碰不到一个真实的表面,明明知道这是一堵墙,但是我们用现实的各种伪装来修正它,来伪造我们意念当中的一个真实。所以在《表面》这个系列里,我翻拍了墙面和地面,再把照片又贴回去,这是用表面来掩盖表面,用虚拟来代替真实,这何尝不是另类的真实,但是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吗?就像我的面孔对应于我的身份证照片。《赝品》是一件行为摄影作品,它是模仿自己的赝品。我记录了土豆的所有表面数据,从空间形态到表皮的具体位置,然后把它变成土豆泥,作为建材来重塑自己原来的形象。现在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困扰:一个同样的土豆放在那里,或是全新的土豆摆放在那里呢?是土豆或是具有土豆外观的别的东西?

《1×24》 矫健 摄影 60cm×50cm 2009年
《画刊》:《100 DINOSAURS》这张作品,属于你拍的一个日常状态的室内景象。这一系列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矫健:这个系列是我10多年前拍的一些学生,那个年龄段的人大部分时间还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蒙蒙眬眬的状态里,自然而然在闲着的时候,显现出不是很明确的、中间的状态。在我的作品里,这个人是谁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只是凝神在某一个时刻,对应在心里面存在的某种情结或者是意境。这样的作品,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包括在技术上怎么样让它保持一种跟现实的距离。这件作品是我对唯美的一种致敬,我认为这是最诗意和唯美的样子。
《画刊》为什么名字叫《100 DINOSAURS》?
矫健:这幅作品是8英寸x10英寸大画幅底片拍摄的,图像的清晰度非常高,在把相片放大的时候,会呈现大量的细节,于是我看到了床头那本书的名字,就用这个无意义或中性的名字命名这幅照片,也是在暗示一种打开方式:局部的细节将要作为重要的参考,参与到对这幅照片的品味里。
《画刊》:我了解到你1995年的时候开始信佛。学佛的经历给你的艺术和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矫健:就是获得定力,很多东西不要究竟,不要那么想直接究竟,在对某一事物本质东西进行追问的同时,也要保持对既定的逻辑与方法的怀疑,甚至对追问本身的怀疑。另外就是不执著于一件事情,很多东西看得淡了是因为了解了起心的原委。所以我的艺术作品难以归类,字面上模棱两可,需要心相印。相对来说我的作品是较向内的,或许有禅意,是我理解世界的思考方式和过程,可能学佛之后这种体验的东西更多一些。
《画刊》: 《1x24》这件作品就用摄影记录了你24小时打坐的过程。
矫健: 24小时不是为了修行而打坐,也不是简单为了拍照片,只是相当长时间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这是出于一种好奇,像达摩面壁10年,这个长期打坐的过程当中,究竟他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我想要试一下才知道,就好像弘一法师年轻的时候尝试辟谷三天也是因为好奇。我知道24小时打坐是很艰苦的一件事情,我选择用相机把我想坐在那里的状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记录下来。是为了可以通过图像,重新以第三者的立场去回看当时的感受。事实上我的准备工作包括考虑各种循环:24小时的地日关系与昼夜循环、趺坐的坐姿本身、我和相机的对照、背后安放的镜子反射我面向的室外、时钟指针做的圆周运动以及镜中逆时针走动等等。24张照片每张都有一个小时的曝光时间,它的虚实变化,记录了我忍耐和晃动的过程,这些打坐期间的不稳定,被相机记录下来,神奇地把作为对象的“物”抽象化了,并且,这一连串图像中表现出一种闪烁不定的超出视觉的东西,这是一种意外;在漫长的过程中,我真实体验到了很多难以表述的感受,时而极致细微时而恍惚纠缠,虽不能了然但能生无名快意,算是又一个意外。
《画刊》:在你拍摄作品的时候,你首先考虑的是视觉呈现的效果吗?
矫健:对我来说,视觉效果作为一种基础审美修养,总是在作品里悄悄地起作用的,而观念是视觉下面的骨头。观念如果缺少视觉效果也即合适的方式,就脱离艺术了,艺术纯粹的观念价值没有那么大。同样,如果没有观念做支撑,纯粹的视觉效果只能是苍白的图式,这一点上,摄影尤其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这个过程谁先谁后,真的不好说。但是不可能突然有一个观念就完成创作了,我一定要在某个瞬间找到观念和技术的契合点,我经常做一些笔记、做一些创作方案,但不一定马上实现它,因为我还没有找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要留待某种机缘,而且接下来做的事情花的工作比如技术上、呈现上等等细节无一不会导致偏向,这种需要持续把控的东西比想象的还要多,最终怎么达到我之前一闪念的瞬间灵感和具有持久的效果,这个最费心思。

《100 DINOSAURS》 矫健 摄影 60cmx50cm 2008年
《画刊》:你的摄影作品几乎都是用最传统的古典银盐工艺制作完成的。对你来说,传统银盐摄影是数码摄影不可替代的吗?
矫健:从技术上说,手工放出来的照片和数码喷绘输出的照片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传统银盐工艺在大画幅或超大画幅领域仍旧具有视觉品质上的不可替代性。即便是银盐方式存在的“缺陷”比如不确定性和颗粒性等,也都带有特定的表情和语言特质,姑且说是一种气质吧。但关于我为什么选择银盐或者说胶片的方式,就不是仅仅基于简单的视觉品质的问题了。大约2014年,捷克的摄影家简·索德克(Jan Saudek)在上海办展览期间有一个小型见面会,索德克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黑白照片上着色变成彩色的图像,而显然比彩色照片有趣味。因为想知道他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时就问他:“你费力地把原本黑白照片都着色成彩色的,为什么不直接拍彩色的呢?”索德克回答说:“我当然试过,但是,Magic has gone.”我觉得他回答得很精彩,非常贴切。索德克认为就他的艺术而言,用了彩色摄影的方式,他的灵感就会不见了,他的艺术作品的魔力也没有了。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传统银盐摄影是我最早接触摄影的一种方式,就像我的母语,摄影近30年来,我习惯这样的方式,也喜欢这样的方式,用新的技术方式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没了,它还不仅仅是操作的手感或者是仪式感,也不是细微的影调的变化,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东西影响着我的行为和我的思维的方式,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填补空白》之一 矫健 摄影 60cm×50cm 2005年
《画刊》: 如果有一天胶片消失了,你会放弃摄影吗?
矫健:不会。我现在做的很多实验的方式,也有不需要胶片的。我现在用的相纸直接拍摄,也可以手工涂布乳剂,或更多非银盐工艺,都不需要胶片或相纸,就影像创作而言不是非要胶片来完成。数码影像也很好,即便拿手机我也做了一些创作,对于胶片我很执著,是因为喜爱,包括喜爱那些精美绝伦的机器设计和它们的工作过程,又没有那么执著,因为胶片摄影并不总是适用于特定创作,这个是看具体的创作需要。只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是我本能的和最熟练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