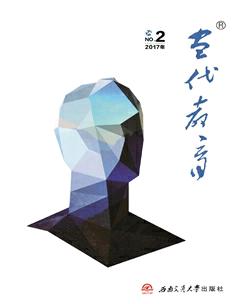90后诗歌:寒冬的野火之光
全球在变暖,而我们的文化却深陷寒冬。在忧心文化寒冬之时,波兹曼警告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波兹曼《娱乐至死》)。如果说这预言切中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十之八九,那波兹曼一定没有想到,赫胥黎式文化寒冬在“中国式”奥威尔之后又光顾了当下的中国诗歌,大众文化的娱乐戏谑出现在了严肃文学的诗歌中。
■寒冬与野火之光
如今自媒体、民刊、官刊、官媒等平台涌现出大量90后诗歌,去除掺杂其中的歌词押韵、无病呻吟、造作象征等未入门习作,我们着重评鉴已经进入语言诗意通道的作品。在这些获得诗歌通行证的作品中,年轻的诗人们幸运邂逅了现代语境中的缪斯,他们摒弃稚嫩空泛的抒情,学会克制的情绪和语言,创造张力之中的扭曲,慢慢拥有了时空中裂变的场域,甚至少数人已经具备轻飞于灵犀诗意之间的语言功力。这似乎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特有的诗歌生态中孕育出来的写作景象:诗人们年纪轻轻就可以轻易地涉猎古今中外各门各派文学艺术,诗人作家、天才庸人,大家小丑都能纳入观览视界,大家无需多少能力就可以在审判和摹仿前人的作品之中悟得一二自我笔法,天赋和勤奋兼具的学徒们,手艺精进的神速更是令人感到丝丝惊喜。
不过,这种别致的景象也导致了写作的混乱和人格的脆弱,青年才俊的出现和消损也让人惊讶不已:前年还在南京烧烤摊纵情朗诵的诗人今天可能已是千杯不醉的公务员了,手捧诸种诗歌奖的校园诗人毕业就搁笔沉寂了。诗歌天赋上表现聪慧的年轻人,正在这个“赫胥黎式”的狂欢气候中乖巧地转变成庸碌的小市民。无论是同语言之乡的背离,还是陷入玩味语言的游戏,都可能是这一代诗人“入门”即会感染的“病征”。
细读90后诗歌的诸多文本之后,不难发现其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鬼魅——以语言艺术为诗歌本质的诗学观。这种诗学观源自20世纪前期的形式主义文论,在后来跟着大行其道的新批评滑入了极端的语言形式诗潮,经历后现代解构主义洗劫之后,众多崇高的诗歌理想、诗学信念更加不堪一击,倒是这种语言艺术的“工匠精神”为大多数诗人躲避现实冲击和中年衰退充当了挡箭牌,众多优秀的诗人无心形而上学的沉思,整日醉心于生活的拈花数草,饮鸩止口般玩耍诸种语言游戏。在这种诗学观的诱导下,无数杂耍的后生也深受追捧,在各种刊物平台上演各式各样的滑稽戏。从上海到广州、武汉到四川、河南到北京,各有来头的年轻人跟着各路仙风道骨的大师学习包装,师承当代诗人教授的诗出有名,师承国外仙逝大家则诗出无名,大多千篇一律,都在语言游戏和琐屑生活里绕圈子。诸多内行的年轻人被特朗斯特罗姆的玄妙语言吸引,但瑞士老头古典的节制,十年铸一剑的品质却没有什么人愿意效仿。大家都在飘飘大雪中摸爬滚打,今天拜师这家镖局,下一个酒桌就投靠另一个山头,一个诗歌奖可以号召几千人奋笔疾书。张爱玲和特朗斯特罗姆都想学,但谁都学不像。
没有坚硬的内核抵御世俗对诗歌的侵蚀,许多诗人“伤仲永”也是情理之中,对语言穷兵黩武,与诗意渐行渐远是这些“新锐”的常见归宿。你可以看到很多操此诗观的诗人教授们在高校里洋洋洒洒的写着不痛不痒的宴酒歌,发情般语焉不详的烟花式诗丛,一两日就能更新一条与友人对唱的微博。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一旦停下对于语言的暴政和意淫,其自身便变得一无是处。只有那些在语言之上,在每个鲜活的时代之中,超越自身而直视人类生命困境的诗人,才能在历史洪流和喧哗中核爆自己的光热,才能登临次神的圣殿。
大浪淘沙,在这个语言滑稽戏的寒冬里,左安军的诗歌无疑是野火般的存在。他的自印詩集《第三人称的我》(第一版2014年印制于成都,修订版2016年印制于北京),收录诗歌九十首,涉及黑暗、死亡、爱情、语言身份、种族以及欲望等诸多人类永恒的命题,淋漓诗意的语言与深沉的求索相生相融是其艺术最高妙的地方,这本诗集也是90后诗人中罕见的庄重美学存在。限于篇幅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第三人称的我》诗歌的文本解读,重点探寻左安军诗歌中显著的特质——凭附和抵御的语言、原型意象以及黑暗主题三个部分。希望既能抛砖引玉,打开左安军诗歌的密码空间,又能以管窥豹,再现当下90 后诗歌在萧瑟寒冬之中另一种持久炙热的野火之光。
■言说的困境:凭附和抵御的语言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言说困境是人类思想在符号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难题。在这个大难题之下,中国诗歌的言说困境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围困。新诗萌芽之初,在古典语言的压制之下,“言文合一”的白话文革命发端就处于传统的围困中,既没有言说的典范引领,也没有接受的听众支援,诗人开口就意味着言说之物合法性脆弱至极;其二是衰退的困境。中国新诗不得不面对青年热血写作的“前车之鉴”,新诗一百年而来,最负盛名的诗作出自青年之手已经屡见不鲜,郭沫若、顾城、海子、韩东等诗人都是典型。诗人们虽然不至于“江郎才尽”,但是却感受到了无情的暗示,热血之后的写作将陷入难以超越的困境,转型的“中年写作”或者“零度写作”都面对巨大的挑战;其三是语言血脉的侵略性。最为深刻又典型的语言侵略就是德国大诗人保罗·策兰受到的德语侵略,策兰的母亲鼓励策兰学习使用德语,但是德语民族却屠杀了策兰的双亲。诗人在写作时心里充满对这种语言系统的敌意和仇恨,但又不得不凭附此种语言符号以及之上的整个文化系统,于是在写作实践时就会形成言说本身的困境——对言说自身以及对诗歌能指、所指进行嘲弄批判,甚至复仇般毁坏。策兰后期的作品在德国专业的文学读者看来都艰奥晦涩,其实他就是在切断德语本身的意义通道,和语言进行较量。说得悲壮一点就是“一个人对德语的战争”。语言血脉的侵略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策兰式的重度创伤,具体而言,彝族诗人的汉语写作开始是具有被侵略意味的,只是大多是怀旧感叹文化的弱势,并且也因为在其汉语诗界的特殊地位受到了恩惠,所以引发的语言深思自然没有策兰深刻的地步了。不过这种类似言说的困境始终存在于非汉语民族的汉语写作者身上。
尽管“穿青人”在法律上已经作为少数民族来对待,且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图腾和信仰,但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因为很多对“穿青人”一知半解的话语权者在遇到“穿青人”问题时常常会采取保守主义,故意绕开这个艰难的课题。因此“穿青人”作为一个“未识别待定”的少数民族被置身于边缘地带,总会遇到某些无形的阻力,尽管如此,从左安军在其诗集《第三人称的我》扉页简介中赫然写着的——“左安军,穿青人”,可见他对“穿青人”民族认同感的强烈程度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就是对抗话语权威最强有力的武器,它否定一切权威,建立另一种新的秩序——平等。
在这种鲜明的民族意识确立民族存在的同时,也将生成强烈的个体语言心理,即洞察外族语言的入侵,甚至可能产生“策兰式”的叛逆毁坏。左安军诗集的题目“第三人称的我”就直接实现了这种毁坏,“第三人称的我”,不仅悖论般表现主体的我被弃之为“第三人称”的客体,还从汉语语法上戏耍了原本的汉语逻辑。惯用的语言陌生化分析都不足以道出其内在分裂,这个悖论真正来源于穿青人整个民族被压缩在56个民族之中的语境,来源于穿青人族群的失语。还有诗歌《沉默在说话》,“她来了/如你所愿/穿过人从/在拐角处消失”[1],其中沉默和说话的悖论是在经过“人丛之后”发生,“人丛”的命令和欲望言说之后,不得不以沉默不语消失的背影来完成说话,仿佛一种无声的挽歌,进行着源自言说自身的抵御和毁坏。在诗集第三辑“语言之都”,诗人既在具象的生活中找到归宿,又在形而上重视语言的维度。《一封短信》《长途电话》《上吊的二爷》深情又伤痛地回到了诗人本土的记忆中,凭借汉语语言重新表现了诗人原生的性格,诸如“我们有一种目睹亲人死去却无能无力的本领”,希冀“山不垮,路不断”,面对多年的远行,“你却突然站在我面前欲言又止”等等具象的人与物成为诗人的语言寄居之所,在这些抒写中诗人虽然消除不了抵御汉语的潜意识,但欣慰的是诗人凭附着汉语完成了对于语言之乡回归的想象。在更高意义上的“语言之都”,“非汉语语言之都”回归,还是《从语言开始》中,诗人对于“语言重生”的企图拥有着强烈的欲望,“我要让你变成处女/并从我的精囊中诞生/我要你像洪水一样淫荡/要你唱歌给我听”[2],一种重回贞洁,重新洗牌的欲念从诗歌中扑面而来,这欲念正是长久以来汉语民族的语言压制之下潜意识的爆发,是渴望“从语言开始”的毁坏和重造。而《飞翔是它唯一的天赋》则是引入一种对诗人自身反讽式的神秘隐喻来表现这种语言述求,诗歌讴歌了一只向大地言说但是被抓捕囚禁于牢笼的白鸽,但是诗歌最后却哀叹“一只鸽子怎么会忘记,飞翔是它唯一的天赋”[3],其中飞翔的“天赋”具有非常微妙的阐释意味,这个“天赋”所指的飞翔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飞翔”不是指向大地演说的自觉,而是指一种民族与生俱来的言说血脉,一种民族的灵性,“当成群的鸽子为早晨的谷粒喋喋不休”[4]之时,唯一的“白鸽”无助地陷入了言说的困境,陷入了灵性的消失和血脉的衰退,“它发现,自己已不能开口说话”,所以当诗人写出这样的咏叹时,不禁让很多深陷汉语围困的少数民族诗人感慨不已。对于现实的诗人而言,这莫不是一种自身的反讽,忘不了天赋却不得不陷入其中。在《关于雪的记忆》《答谢辞》《我小心翼翼将你打开》《老鼓手》《飞翔是它唯一的天赋》《复调》等作品中,诗人都表现了对于某种语言存在的向往,对于笔下的语言的某种超脱和逾越。
左安军穿青人的身份所引发的对汉语的警惕,一直是他诗歌写作的棱镜,诸多写作主题都要经过这个棱镜到达文本。这面棱镜可能是他发散想象无法逾越的场域,也可能是其语言魅力的持久又醒人的来源之一。他在序言里谈及诗歌时候说道,“它取消了语言差异,取消民族之分,取消国籍,进入每一个有可能成为她主人的生活”,他对于这种原生的语言差异,民族分别有着先天的敏感,而当他以逾越界限时候又能创造重新认识语言的快感。
■边民的耳朵:声音的原型意象
左安军对于诗歌意象有着特殊的沉迷,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对他诗歌意象解读我比较倾向于原型批评的理解,虽然原型批评已经老套滥觞,但是左安军是从贵州偏远山村走出的90后诗人,他对于大地和世界的认识与诸多诗人看到的现代浮躁、迅捷的世界大不相同。他的诗歌意象既有80年代以来的严肃象征性,也有边民敏锐的独特性,所以我坚持经典性看待他的诗歌意象。来源于集体无意识学说的原型批评认为,原型意象是“根植于某一特定社会的神话体系及时地留下了该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幻想和语言经验的遗产,因而,神话体系有助于创造一种文化史”(叶舒宪编《批评的解剖》),这其中的“神话体系”更多指示一种经过提炼的人类经验,其实原型意象就是高度凝聚了早期人类共同经验的象征物,这些经验被不断遗传保存,在人的特殊的情境中触发时就会被召唤,引发个体厚重久远又难以名状的感受体验。
在左安军的诗歌中,大地、河流、母亲等等都是鲜明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比较正统庄重,也在原型意象中能够找到对应的解释,所以不在此赘述。我要着重分析左安军诗歌隐秘的原型意象——回响的声音。“回响的声音”应该是来源早期人类对于洞穴回音的认知记忆,在这种回音中,人类能够重听自我的声音,发现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在不断遗传记忆之后,这个意象核心“重听自己的声音”的内涵就被保存下来。左安军的很多诗歌中就有这种“回响的声音”,一些明显,一些隐蔽。《在黄蜂死亡的季节》中,黄蜂这个意象引发的一种潜在的翅膀振动声音,一直潜伏在诗歌中,连续细小微妙的回响作为一种潜在的声音背景,在最后蝴蝶乱飞黄蜂死亡的时候,“你就在我身边而我们离得越来越远”[5],这个动作伴随振翅的“嗡嗡嗡嗡”回响,突然将“我从我众多的身体里掏出同一个人”的认知全部裹挟,以至于读者只在一种黄蜂振翅的回响中听到众多无法认识的自我之声,即他们越走越远。在《地下乡愁蓝调》中,有一只鸽子扮演了回响的墙壁,“鸽子飞落其中,它旋转着/旋转着咕咕叫”[6],它象征着一种不断沉思往返的认知思维活动,暗示着诗人与诗歌之间的某种反复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听者》使用了最明显的排比式句法,直接造成一种客体的回声听觉,既有能指上的语音效果,又有所指上反复认知的潜在回响,不断地加深听众的理解,放大听众的背影,表现一种努力向世界发声但是无法获得回响的遗憾。认知回响并不只是经过一种单纯形式上的重复,有时也是理解经历了主体化的回响,在《穿过河流》中便出現了这种主体间的回响,“我们喘着气,在对方那里吹奏自己”[7],两种不同质地的声音在流淌之中,彼此交融理解,最后回到“古老的习俗”,重新认识自己的“河流之源”。原型的声音回响甚至会经历碰撞,在破碎中引发反弹的效果,在《盛满经血的杯子》中,回响的声音便是“声音”与“杯子”碰撞发生的,“饮破碎的声音/杯子——杯子”[8],破碎的声音碎片与象征处女般纯粹之痛的经血共振于杯中,“一饮而尽,而声音中止杯子存在”,最原初的纯粹之痛消失之后,声音就成为了终止事物存在的命令,应该说这种声音就是面对纯粹之痛的绝对音响,是人进入纯粹创伤之时产生的神秘回声。
通过解开隐蔽的原型声音,我们可以发现左安军诗歌中许多地方闪耀着着形而上的光辉,诸多地方散发着哲学诗人般深沉庄重的诗学气质。当大量的90后诗歌一味地表现琐碎的自我生活,沉溺于锻造语言的游戏中时,左安军的诗歌无疑成为了90后诗歌中珍贵的存在。独特的边民听觉,淋漓智性的抒情语言,浓厚的理想大地气息,神秘的直觉修辞等等,你仿佛可以看到了当年昌耀的影子——与诗坛主流瓜葛甚少,诗歌自成一体,赤诚灵锐。
■野火之光:通往黑暗
“通往黑暗”是《第三人称的我》第二辑的题目,直截了当地彰显了左安军正视黑暗命题的主体立场。黑暗,这一主题在古今中外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学中常常使用“黑夜”“夜晚”等等更加具象的含义来代替“黑暗”的抽象表达。中国古代神话中有盘古开天辟地中的“混沌”,西方文学典籍《圣经》里神创造世界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都有人类对于世界黑暗的想象(张厚刚,王洪月《黑暗意象丛:海子诗歌的意象主题》)。人类第一次自觉抵抗黑暗是在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之中,人类第一次在神话中表达了对火之光明的渴望,也反应了对于黑暗的某种恐惧和趋避。在现代文学中,英国大诗人狄兰·托马斯的名作《不要温顺的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直接显示了人处于时空之时和无边黑暗的对峙。中国新诗史上的杰出诗人海子更是写下诸多冥想黑暗的名作,最为著名的诗句就有“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历经千年,太阳西沉之后黑夜笼罩大地的规律从未被改变,诗人们对于光明消失之后的黑暗大地,黑暗本身,以及黑暗带来的所有感受体验一直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表现。“黑暗”的降临意味着取消認知事物的可能性,人类在光明之下获得的经验在黑暗降临时都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同时,黑暗以熄灭万物的魔力施加给人类巨大的恐惧和颤栗,人类在黑暗中无处可逃,不自觉地寻求最为直接的依靠,正如近乎所有婴儿、小孩在夜晚来临之时紧紧地抱住任何一只怀中的手臂。
虽然黑暗在人类记忆中是一种灾难式的记忆,但是在现代诗人们复杂的思考中,黑暗却成更多地成为了他们步入神秘境界的必经之地。黑暗巨大的魔力在诗人思考之时也会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神性”,这种神性来源于一种可能——当黑暗熄灭万物,诗人置身并正视黑暗就会具有与某种超然存在并肩的可能,诸如在黑暗中时间不会流逝的幻觉会使诗人感到永恒之感;在黑暗中的一切事物、规律束缚被无条件的清空,诗人的思绪可以走向绝少束缚的地带;黑暗席卷了万物,诗人便有了独自对最纯粹“自在之物”冥想的条件,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表象;黑暗也将笼罩其他人类,唯独“自我”清楚的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这种绝境般的“独处”将使诗人在无尽的思索和沉默之后爆发出巨大的言说冲动等等。黑暗主题在诗歌中多重的表现是人类极为重要的精神探险,兼具美学和哲学的诗作就更显珍贵。左安军的诗歌正是在这样的探险中达到了90后诗歌罕见的高度。
在“通往黑暗”的一辑中,左安军以不同角色从各个方向突入了黑暗,《入冬》《风景》里的勇士,《颤栗》里的浪子,《时间之唇》里枯坐的病人,《告别》的路人,《为了》里的大地精灵,《运动》里夜行人,《重逢》的失眠患者等等,都表现深处黑暗所引发的形而上的思考。此辑开篇之作《我们》中的“星星”和“阳光”就是在依赖“你”的世界里消退破败的去势,“你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碗里的阳光碎了”,“那些喋喋不休的星星啊/什么也不说”[9],诗中“我们”彼此依赖,因为回忆而陷入沉默的黑暗,“一任往事酌满杯子”,“我们”之间有一种和黑暗相似沉默,一切无法言说一切又都被洞察,“为了看清彼此,我们什么也不说”,仿佛经历了黑暗的清空。“黑暗”意象与另外的意象附着在一起之时也会展现其裹挟降临的特点,《入冬》里冬天的寒冷加深了黑暗的属性,而在寒冷中走向茫茫黑暗则渲染了壮怀的气氛,诗人发出祈祷般的请求,“夜晚啊——你为何还不降临/为何一再将我引向深渊/只有黑暗才能看清肉体的颜色”[10],也因为黑暗取消所有现象,取消阶级使得诗人最后发出狂欢般的演讲——“入冬以前,我骑着你的玫瑰之躯整夜奔流/入冬以前,我们的两位帝王不同姓氏,选票投进垃圾箱/入冬以前,无人统治我们”[11]。当然黑暗的吞噬性也会发生在诗人身上,在《风景》中,“我”从唯美外界,“雪”“花瓣”“清凉之水”走进自我,最后却在黑暗里被降解为人类集体意义上的他人,“黑暗中你我融为一体/血液的拱门划亮道路/我们不是自己,而是他人”[12],这其中“血液的拱门”更是暗示了黑暗中认识自我的残酷性,黑暗既有提供独处的契机,也具有将一切客体化的毁坏力。
左安军的诗歌还有另外一种特质,那便是诗人的使命感。他常常在黑暗的能指中思考诗歌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仿佛黑暗给他提供一种全新的语言认知背景。比如《歌声之外》,他指出了黑暗里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不可言说之物,“在黑暗中闪光在我未说的部分/必有不能言说的歌声汹涌而出”[13],在《时间之唇》中,语言在黑暗中面临着时间无限延长的命运,“夜游人已坠入漆黑的枯井/啊,没有年轻儿子的老泪纵横/就没有语言破土而出”[14],年轻的抒写者也不得不慨叹捅破遮蔽需要耗尽年华。《目的地》《二维》则是将诗歌视作时间维度里被“夜色”囚禁的“真理”,是自我难以在光线之下难以认知的“目的地”,只有置身黑暗之中,我们才能领悟“沉默”,才能“说出一切”。具有艺术宣言的《为了》和《时间之书》以“鲁迅式”的勇士精神在黑暗面前昭告诗人的理想:
所有的风都在路上
所有的种籽都吹向天空
自然的力与美
在病态的平衡中接近自己[15]
当障碍遍布,根系无望之时,“我”仍然以负隅顽抗的姿态接近艺术——自然的力与美的平衡,“我是被艺术的力雇佣的孩子”,“我”在黑暗面前永远年幼渺小,甚至只有“那被黑暗催熟的孩子的心”,“我”不得不承受黑暗对语言和心灵的冶炼。这些凝重又坚定的宣告极富感染力,其真挚的浪漫精神和昭告的宿命编织于一体,释放出了神圣的理想情感。
■结语
当一个时代醉心于私人游戏之时,当大众和诗人们合力拆解神明之时,我看到黑暗中燃烧的野火之光,这寒冬中心最后的红热火焰。左安军的写作在90后诗歌中踽踽独行,他用淋漓诗性的语言保存的理想和肃穆将是我们这一代难能可贵的风景。如果说要忧虑,那我们应该忧虑的是起点如此之高的他未来如何超越《第三人称的我》惊人的表现。在资本和权力双重夹击的时代,谁能抵制谄媚阿谀?谁能高耸诗人最后的头颅?谁守住最后的神殿?我们不敢太多期待,我们也不能没有期待,至少,《第三人称的我》给了我们期待的可能。
注:未标注的均摘自左安军自印诗集《第三人称的我》(修订版,2016)。
作者简介:何敏,男,笔名何牧天,青年诗人,译者。1993年生于四川三台。河北大学文学院2016级文艺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