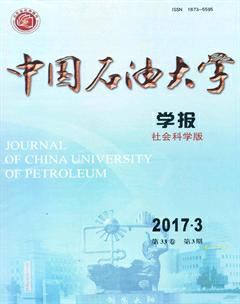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仪式”问题研究
刘伟兵
摘要:仪式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致性,使得仪式可以成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形式变革。仪式自身的中介性和情境创设等都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内在契合。传统仪式的消解和现代仪式的尚未确立,使得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仪式缺失的现象。象征系統、仪式感和情感互动等作用机理的存在使得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社会安全阀和合法性赋予者的功能。通过对传统仪式的基础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和注重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实践方式,实现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回应。
关键词:仪式;意识形态认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3-0036-08
仪式,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其做了深入的探讨。关于仪式的概念,学界的理解并不统一,本文采用薛艺兵的观点,即“从仪式的行为、仪式的情境、仪式的意义、仪式的功能四个方面加以阐释”[1]。仪式是超常态行为、是虚拟的世界、是象征的体系、是社会的表象。仪式缺失现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将仪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结合,既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拓展学科外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横向发展的内在要求。仪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性在于仪式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仪式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研究时,会面临着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仪式这两个概念的辨析。至少,在注重意识形态教育这个共同语境和目标情况下,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仪式是一体两面的概念。仪式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侧重仪式主体和强调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则强调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仪式。因此,当探讨仪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仪式的意识形态功能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仪式都聚焦在意识形态教育。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仪式理论视角,而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则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一、仪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只有30多年,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却早已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仪式的内在价值维度的统一点,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对意识形态的维护也是仪式的主要目的和内核。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对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仪式彰显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受教育者,是社会的、现实的人。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简单地主客二分,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情况。“自笛卡儿提出二元论以来,二元对立的观点便深深扎根于现代性哲学的内在逻辑里。而二元对立首先表现在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有利于对象性思维的确立。”[2]但是,将受教育者客体化的结果就是忽视了人的人本属性和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对人学的呼唤,便是要呼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关注人的主体性,尊重每一个人。“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认为,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和相关律是内在统一、相互协调的,构成了以实践客体为中介而联结起来的多级主体的主体—客体—主体的模式。”[3]交往实践观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主体。交往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从而达到主体共性的发展,还强调主体通过对客体的实践来达到对主体的交往实践活动。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因此在强调施教与受教双方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是摒弃了以往人对物的主客二分,从而使得受教育者脱离了客体化,摆脱了客体性。这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具有很大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否认主体对客体的客观实践活动,使得社会实践活动成为了主体间的精神交往活动。因此,人与人的交往实践既有精神层面的交往,也有物质层面的实践。但是,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客体实践,使得游荡于精神层面的交往就显得愈是幻想了。因此,对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观点要进行批判的吸收。
其次,在交往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仪式充当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纽带。仪式是人们的一种实践活动,体现了主体对客体、主体对主体的实践统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35仪式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人们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也是人们确证自我存在的他者在场。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的人类活动都是实践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理解。”[4]133仪式作为一种时空的场域,成为了人与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场所。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仪式可以划分为世俗与神圣两个领域。如果人们把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一些动作、一些象征物的实践活动看做是主体对客体的世俗领域层面的实践活动,那么,这些世俗的客观实践活动,便使得主体完成了一次无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一次意识形态教育。宗教对人的精神世界异化就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仪式进行的。“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4]59“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两大机制就是意识形态质询与主体的询唤和镜像复制与自动臣服。”[5]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表象系统,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是一种无意识结构。在仪式中,人们通过仪式的规范化或者非程序化的行为,发挥着意识形态两大机制的作用,从而使得仪式主体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进行确认和认同。阿尔都塞将这一过程归纳为“1.把‘个人传唤为主体;2.他们对主体的臣服;3.主体与主体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承认;4.绝对保证一切都确实是这样,只要主体承认自己的身份并作出相应的行为,一切都会顺利。”[6]例如,升国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国歌、对国旗行注目礼等主体对客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询唤了国旗和国歌这两样象征符号所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一次次的镜像复制,而对国家意识形态自动臣服。在这一共同的意识形态仪式中,每个人都是仪式的主体,而仪式的象征符号则作为客体,实现了主—客—主的交往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完整模式。因此,在主体对客体的仪式实践活动中,仪式主体会自然获得对其自身的主体确认和意识形态的确认,实现主体对主体的精神交往。“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4]59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实践观的视域下,仪式是个人与集体的纽带。
再次,仪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时的思想信息内容及思想政治教育方式。”[7]238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维度出发,儀式就具有了中介性。仪式的中介性特征,有利于仪式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同领域的结合。仪式的关联性、传导性和互动性,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所必需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仪式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产生关联,并通过仪式的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行为传递着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通过仪式的一系列活动进行着互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指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7]392将仪式看做载体,意味着是以工具主义视角看待仪式。介体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强调仪式作为载体,就是强调仪式的形式和工具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主要是由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组成。活动形式就是仪式形式,物质实体就是仪式的象征符号。通过仪式的形式选择或者建构以及象征符号的运用,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者们传递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例如,开全体会议,所有人出席是一种仪式形式,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活动形式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是可选择的。因此,全体会议可以是表彰大会,也可以是批评示范会议。再比如,当举办喜庆的婚礼等典礼时,红色成为了具有喜庆意义的象征符号。但是,当运用在警告牌等警示物上时,红色就成了鲜明的警示象征符号。仪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强调仪式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属性。以往人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弱的原因在于内容的滞后、不贴近生活,但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与时俱进和日益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不再远离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而施教者固定化、刻板化、形式化的施教模式成为了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大障碍。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建构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仪式载体,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最后,仪式创设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体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是指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对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7]240将仪式看做思想政治教育的环体,就说明仪式具有环体的多样性、多维性、开放性和历史性的特征。(1)仪式是多样的。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有着不同的具体对应的仪式。喜庆的仪式,形式是生动活泼的;悲伤的仪式,形式则是庄严肃穆的。针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建构起具有针对性的具体仪式形式。(2)仪式是多维的。仪式横跨着时空两个维度,在时空境遇情况下,仪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此外,仪式还由各种条件和因素综合形成。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场域、时空场域。在仪式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实践统一。此外,人们通过仪式的时空场域,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实现了对过去的意识形态的询唤和对当前的意识形态的赋予。仪式的文化场域更是通过一系列文化象征系统,构建起人们外在的感性客观的文化环境,并通过文化人的方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3)仪式是开放的。仪式代表着保守的力量,在历史中一直维持着自身的形式和固定模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积极健康”的仪式必然会吸收外界合理的因素进行自我改造,从而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这也是由仪式其自身形式的工具性和内核的意识形态性所决定的。(4)仪式是历史的。仪式的历史性不是强调仪式的固定性,而是指仪式总能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发展自身,更新自己的形式。在为了传输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维护意识形态这一目的下,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是发展的、可变化的。此外,环体的情境创设与仪式的情感共鸣具有内在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教育者可以利用情境把教育内容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在情境中,受教育者之间互相影响可以共同内化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7]321把仪式放在情境视角下,使得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化、生活化、社会化。柯林斯在研究仪式时,认为情境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尤其关注仪式的情感能量和文化符号。因此,仪式其本身作为情境,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们更有利于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和感性的认知。意识形态的最初产生就是人对社会环境的感知。“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4]161因此,仪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环体和情境,更应该被及早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进行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建构,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仪式缺失现象
3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客观上也存在着目标与效果之间的矛盾。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缺失更是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组织(工作)环境、社区环境、同辈群体环境。”[8]正是由于不同的微观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同,而相对应的微观环境内思想政治教育仪式建构的缺失使得仪式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7]261因此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缺失,也主要是这四方面内容的缺失。
首先,家庭教育中仪式的缺失。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个人一生所处时间最久的微观环境。在家庭环境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由家庭仪式建构,并进行家庭仪式的意识形态教育。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的家庭仪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成员上,“实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出现了大量的4-2-1家庭”[9]。在居住上,人们受经济的影响,出现了比以往更大的流动性。加上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与多样化,传统家庭仪式开始消解。“家庭仪式传播主要包括了民间节日传播、人生礼仪传播和其他种种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传播。”[10]在节日方面,许多节日内涵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假日意识和旅游、美食意识。被人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国家法定假日的节日,是有独特食物或者可以旅游的节日,节日自身的内涵和节日仪式逐渐被淡化。因此,如今许多人觉得年味不浓,传统节日变为旅游节、休假日。在人生仪式方面,人的生老病死,在传统文化中都被仪式化,并作为人一生中重要的节点。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们逐渐将传统文化的繁琐礼仪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化、快速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家庭孝文化仪式的消失。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渐渐抛弃了以往对长辈的问候礼仪和餐桌上的礼仪。飞速发展的几十年快速消解了中国的传统家庭仪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感受到仪式感的缺失。
其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仪式的缺失。学校作为人们最重要的学习场所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其思想政治教育中仪式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在学校仪式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了目的性、导向性明显的特点,内容上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特点。由于学校自身需要承担教学任务,以及学校是依据学生的成绩进行考核,因此,学校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形式化、边缘化的趋向。升旗仪式简化为一周一次,入党入团仪式被简化,缩减步骤,甚至略过宣誓。上下课的师生礼仪也因为时间原因被忽略。在成绩这一可量化的标准驱使下,所有学校都压缩甚至取消了其他无关成绩的仪式。学生的成人礼仪、颁奖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庆等仪式自身的意识形态内核被简化、淡化,只留下一些形式,造成学校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缺失。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其实效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再次,社会生活中传统仪式的失落。一方面是职业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缺失。传统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其自身的仪式和规矩。在中国古代,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也有自己的行业神,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将这些视为封建迷信因素而彻底抛弃。“迷信的衰落被置于多重语境之中:这是科学的天然对立物,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其自身合法性的场所,也是各式各样的被论述对象周旋于改造者、群体利益以及各自生存境遇与内心体验的社会空间。”[11]当行业仪式抽离了宗教因素后,现代社会却并没有注入現代文明的新内核。文化的传承认同礼仪也因为其祭祀的宗教形式而被抛弃了。打碎了行业的宗教形式的仪式,抛弃的不仅只是迷信,还有行业的文化认同和核心凝聚力。从事商业的人们不再有道德上的畏惧,技术行业的人们对师道传承也不再予以重视。行业的祛魅使得行业自身的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处于一个支离破碎的状态。这就使得飞速发展的行业,在资本的逻辑下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业的道德约束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仪式的缺失。传统中国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以乡村为单位的集合模式。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乡村这一聚落单位受到极大的冲击。很多乡村成员迁徙到了城镇里,一方面是解构了乡村的仪式,另一方面是在城镇里以社区为单位重新聚居。但是城镇的社区单位聚居形式并没有建构出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传统中国的乡村思想政治教育仪式,以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和宗教色彩。求雨仪式、祭祖仪式、丧葬仪式以及乡村内依靠族内长辈来维持秩序等,都是基于血缘的远近和宗法的规矩来维护宗法的上下尊卑的意识形态。“而社区成员的参与者,往往是自觉、自愿的,不需要人为发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约束力。”[12]社区的仪式建构并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在地缘关系和新环境中,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的“远亲不如近邻”这一最优模式。这一仪式虽有仪式的形式,但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内核建构并没有完成,与主流意识形态也仅仅处于自发联系状态。因此,社区仪式思想政治教育依旧缺失。这使得现代许多社区出现了社区文化淡薄、社区凝聚力较差的现象。
最后,同辈群体交往中仪式的缺失。同辈群体在现代社会的宏观语境下,更多的是以年代划分,如80后、90后等等。因此,同辈群体是指出生和成长生活在同一时间段的人群。正是由于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以10年为一代的人们拥有着自身年代的特性。因此,以年代划分同龄人的说法也在最近几年中日益流行。微观的同辈群体,是以自我为核心、周边同龄人为集合单位的群体。他们不仅有着时代特质,也有着地方特质和更多的共同经历。因此,同辈群体的仪式,更多的是以集体记忆为核心而出现的仪式模型。“集体记忆并非‘客观地回忆往事,更确切地说是在实践的沟通中集体回忆发生在过去的回忆(欧里克语)。与此相应,每个时代都依据一定的社会现实、社会框架、社会理念和社会需求进行历史与往事的集体筛选和现实诠释。”[13]因此,不同年代的同辈群体们拥有着自己的集体记忆,有着自己的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这些构成了自己同辈群体的仪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同辈认同。这种同辈群体仪式认同也是一种自发的认同,并不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有关,其自身的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处于自发的状态。因此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同辈群体的仪式思想政治教育依旧处于缺失状态。
总之,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日益更新,不仅仅解构了以往中国传统社会的仪式,还将仪式文化当做封建文化和迷信消解了。然而,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仪式并没有建构完成,或者一些仪式依旧处于自发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重视,加强仪式的意识形态内核建构,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并提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仪式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机理
人们对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认识早已有之。但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早期更多的是对仪式加强宗教信仰作用的感性认识,后期开始关注到了仪式对政治认同、对意识形态认同甚至是对个体认同的作用。以往对仪式的研究,更多的是宗教学和人类学的范畴,仪式的理论体系和建构也是基于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的理论而建立的。因此需要重新梳理和建构仪式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机理,从而更好地推动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仪式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基本形式
第一,象征符号是发挥仪式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首要元素。研究仪式的诸多学派中,特纳等为代表的象征文化学派,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仪式的象征符号上。“从象征的社会表述向象征的文化意义转移,文化作为意义、价值观和情感的主要层面,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组织,文化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与社会层面交汇,相互作用,构成一整体。”[14]无论是以往的宗教意识形态还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能被直接感知到的,只是作为抽象的存在,对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因此,一个能被感知的客观的意识形态的象征便成为了关键。通过象征,使得那些不可感知、不可触摸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能够感受得到的象征符号。“仪式象征符号使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信仰、观念、价值、精神和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感觉极上的‘实体化不仅使对纠纷、矛盾、冲突进行仪式化、戏剧化处理成为可能,同时预示仪式化、场景化解纷的必要甚至特定情形下的必然。”[15]因此,象征符号是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内在关键。例如,国家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存在,我们只能通过国旗、政府办公楼、国家元首等象征符号来感知国家的存在。“象征为人们理解政治过程提供了方法,因为政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象征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16]7现代性哲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技术理性取代了政治理性。科学对世界的祛魅,使得人们从匐拜上帝到崇拜科学。科学理性要求人们要理性地认知世界,要求对事物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这就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感性认知不重视,对象征符号的感性认知不重视。因此,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忽视人们的感性认知和对象征符号的感性认知的同时,忽视了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