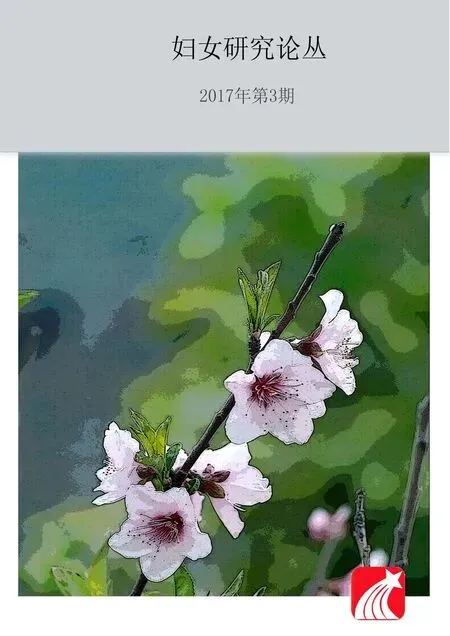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GSS2012数据的分析
徐兰兰
(汕头大学 法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GSS2012数据的分析
徐兰兰
(汕头大学 法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社团参与;性别隔离;社会资本
基于对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本文检验了中国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及其影响因素。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社团参与中的纵向性别隔离和横向性别隔离在中国的确存在,它们受到社会人口特征、文化、非正式社交网络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用。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会加剧两性在社会资本类型和社会资本存量上的差别,维系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现状。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加强公共政策领域的顶层设计,改进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引导男女两性跨越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社团参与类型;另一方面,推动传统社团的组织改革和制度创新,促成更为开放、包容、公益、平等和自主的社团组织。这些举措将拓宽桥梁社会资本的构建空间,从而有利于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平等的实现。
一、引言
在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社团参与是极受关注的议题之一。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基于对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比较研究提出,北部的地方政府民主运作较好,缘于当地存在着邻里组织、体育俱乐部、农业合作社、慈善团体等众多密切横向互动的社团,市民对社团参与的热衷促进了社会信任[1](PP 213-215)。在分析公民参与网络的作用时,帕特南将社会网络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其中正式的社会网络主要表现为社团参与。社团参与被认为不仅会带来诸如职业机会和支持网络等对个人的报偿,还会通过培育公民合作解决本地问题的能力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社区公共品[2](P 73)。
既然社团参与能够带来诸多好处,那么整个社会中的社团成员资格是否是平等分布的?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最先注意到社团参与上的性别差距问题。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通过对全球70多个国家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社团参与数量上的性别差异在农业社会中最大,而在后工业化国家中最小;最为显著的性别差异不是表现在社团参与的数量差异(“纵向隔离”),而是表现在社团参与的类型区别(“横向隔离”)。在绝大多数国家,男性依然主导着政治政党、运动俱乐部、和平运动、职业团体、工会和社区行动组织,女性则更多地停留在各种弱势群体志愿帮扶、教育文化团体、宗教组织以及妇女组织等符合传统妇女角色定位的社团组织中[2](P 74)。
中国的社团发展情况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数量上来看,中国的社团以行业和职业协会类为主,教育、研究类社团次之,文娱、社会服务和校友会等联谊性社团所占比重相对较低;经济中介功能社团居多,公益性和服务型社团相对薄弱[3](PP 59-60)。市民社会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在中国尚未成为主流,大部分主要社团仍处于党或政府的管理领导之下,其中有些还承担部分行政职能,半官半民色彩较为浓厚。与此同时,尽管国内有关社会团体相关研究著述颇多,但社团参与本身却非研究热点。在大多数提及社团参与概念的学术文献中,社团参与仅是被作为测量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状况的维度之一而存在。在有限的社团参与专题文献中,有关大学生群体的社团参与和就业相关研究占据绝对多数,剩余少数文献涉及社团参与与居民信任或社会治理等议题。
由此看来,国内没有学者对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现象进行过专题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笔者经文献检索后发现,胡荣教授曾对福建省农村居民社团参与[4](PP 27-29)和厦门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状况[5](P 101)进行过抽样调查研究,部分内容涉及性别与社团参与相关性的检验,而其结果并未验证社团参与的横向或纵向性别隔离的存在。那么,中国的社团参与是否并不存在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描述的性别隔离现象?本文认为,基于对更大抽样覆盖范围和概率抽样方法获得的调查数据的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对上述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采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意在回答三个问题:中国的社团参与中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隔离?如果存在的话,影响中国社团参与性别隔离的因素是什么?为何我们需要关注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就发现,男性通常会参加核心经济组织,后者为他们提供可能的工作和商业机会的信息,以及职业发展的机会;而女性则参与聚焦家庭和社区事务的组织,后者为她们带来家庭领域内的关系网络[6](PP 883-904)。尽管研究者们预测,随着社会发展为男女两性生活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在社团参与上的性别差异在最近几十年间会逐渐消失,但梅丽莎·库尔撒德(Melissa Coulthard)等人对英国2000年综合住户统计调查(GHS)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男女两性对各类社会和社区活动的性别偏好差异依然存在;男性更喜欢参与运动和娱乐活动,女性在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领域更为活跃[7](P 111)。皮帕和罗纳德对2001年的全球价值调查(WVS)数据的分析结论是: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社团参与都存在着显著的横向性别隔离;在社团参与数量上的性别差距虽相对较小但仍具有统计显著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2](P 9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和假设2:中国的社团参与存在着性别隔离,既有横向隔离(H1)也有纵向隔离(H2)。
至于导致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现象的原因,国内外研究文献中提及的影响因素可以被归类为结构解释、文化解释和非正式交往网络三种。结构解释认为,人们在社团参与的数量和类型上的性别差异与其社会阶级、年龄、种族有关,与男女两性在时间、金钱、知识和技能上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也有着密切关系[2](P 78)。时间通常被视为影响社团参与的关键因素之一,日程安排的灵活性被认为有助于参与活动;但处于婚姻中的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或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要么面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要么需将主要精力花费在照顾家庭上,这些都阻止了女性更多的公民参与[8](PP 250-251)。还有一系列研究表明,正式教育以及认知、技能对人们的社团参与,尤其是政治社团活动的参与产生影响[5](PP 101-102)。简言之,结构解释强调,基于教育资质、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基础上的社会人口特征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在技能、知识、信息、经历、时间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会导致某些人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参与到正式的社会交往网络中去。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性别、年龄、教育、有酬劳动、社会等级、婚姻/同居状况等社会人口特征,与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相关性(H3)。
相较于结构解释,文化解释更关注的是促使人们参与社团活动的态度和观念。政治效能感等态度因素,被认为与政治参与中的性别差异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9](PP 15-16)。女性往往表现出对自己在政治领域行动能力的信心不足,对通过大众媒体追踪新闻和公共事务的兴趣也较低[10](PP 30-31)。此外,有西方研究认为,社会性别意识对打破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具有积极作用:越具有性别平等观念的女性,越有可能参加不符合传统妇女角色定位的社团组织,例如足球俱乐部、贸易团体或政党组织;而越具有性别平权意识的男性,也会对加入过去通常由妇女主导的社团表现出更大的兴趣[2](P 88)。社会贡献意识作为公民社会意识的组成要素,也被视为公民社会参与的心理基础和内生动力之一[11](PP 46-47)。宗教信仰也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影响因素。有西方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在宗教参与上的性别差异由来已久:相较于男性,女性定期参与宗教活动和隶属于宗教组织的比例明显更高,但在宗教组织层次结构中男性更容易拥有专业权威的位置[2](PP 185-189)。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宗教信仰、政治效能感、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贡献意识等文化因素,对于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具有影响作用(H4)。
非正式交往网络因素关注的是与家人、朋友、同事等之间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对社团参与的影响。有研究分析了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将人们“拉入”到社团生活中去;而那些隔绝或切断与亲朋、同事之间非正式交往网络的人,就不太可能与社区团体等组织发展出正式的联络关系[12](PP 311-320)。由此,本文提出假设5:非正式社会交往越丰富的居民,就越有可能拥有更大规模的正式交往网络,成为更多社团组织的成员(H5)。
此外,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文专门提出假设6:媒体使用和社交频率这两个生活方式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到居民的社团参与数量与类型倾向(H6)。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CGSS2012,选择该年份数据的原因在于其基本涵盖了本文所需要的主要研究变量。CGSS采取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调查范围基本覆盖中国大陆各省和直辖市。2012年版共有11765份有效个案,其中涉及本文所需各变量问题的样本量为5810份。在剔除在本文所需变量相关问题上作出“拒绝回答”“不知道”和“不适用”回答的缺失个案后,本文共获得4978份有效个案作为研究数据。
(二)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本文以横向隔离和纵向隔离两个维度来考察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状况。CGSS2012问卷中列举了9种组织类型,要求回答“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如果是,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答案分别赋值为“1=不是成员;2=是成员但基本不参与;3=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本文按男女两性在各社团参与程度的高低,将上述社团分为三种类型:男性主导型社团、性别均衡社团和女性主导型社团,并将原回答选项1和2合并,重新调整为赋值“0=不是成员;1=是成员”。“横向隔离”的测量是通过考察男女两性在上述不同类型社团中的参与程度;“纵向隔离”的测量则是通过比较男女两性参与成为社团组织成员的数量差别。
2.自变量:主要分为四类,社会人口特征、文化因素、非正式交往网络和生活方式。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特征由10个变量组成,包括重新赋值为虚拟变量的5个变量:①“性别(0=女;1=男)”。②“民族(0=少数民族;1=汉族)”。③“婚姻/同居”(0=无;1=有)。④“有酬劳动”(0=无;1=有)和⑤“居住地(0=农村;1=城市)”。3个有序变量:⑥“政治面貌”(1=群众;2=共青团员;3=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⑦“教育”(1=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私塾;……;8=研究生及以上)和⑧“社会等级”。“社会等级”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您认为自己目前在哪个(社会)等级上?”,“10分”代表最顶层级,“1分”代表最低层级。社会人口结构特征还包括2个连续变量:⑨“年龄”和⑩“未成年子女数”。
文化因素包括4个变量:宗教信仰、社会性别意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贡献意识。“宗教信仰”被赋值为虚拟变量(0=无信仰,1=有信仰)。“社会性别意识”的测量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同意以下5个说法:①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②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③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④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⑤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本文将第⑤个说法由正向“应该”表述改为负向“不应该”表述,并将回答按Likert五点量表赋值为从“1=完全同意”到“5=完全不同意”,反映社会性别意识从低到高的排列。
在CGSS2012 调查问卷中有两个问题涉及“政治效能感”的测量:一是“像我这样的人说什么对政府的作为都没什么影响”,二是“政治和政府太复杂,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回答均按Likert七点量表赋值为由低至高的“1=非常同意”到“7=非常不同意”。“社会贡献意识”测量的是被调查者是否同意“我想对社会做贡献”,回答按Likert七点量表赋值为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非正式社会交往网络的测量询问的是被调查者在“一天里与多少个不住在一起的家人或亲戚有联系”的“亲属交往网络”,以及“除家人和亲戚以外,一天里与多少个人有联系”的“非亲属交往网络”。回答按照联系个数从“0”至“100个及更多”被分别赋值为从“1”到“7”的七个等级。
在生活方式变量组中,“媒体使用”的测量是通过询问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的使用情况;“社交频率”是询问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进行社交。两个问题的回答均按Likert五点量表赋值为从“1=从不”到“5=非常频繁”。
(三)综合因子量表的数据检验
本文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本文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来衡量社会性别意识、政治效能感和媒体使用3个变量的测量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结果显示各变量的α系数在0.645-0.668之间,说明3个量表的内在信度基本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上述3个量表各项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6,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均高于50%,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适宜进行综合因子分析。
四、假设检验及结果
(一)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基本特征
本文首先对在社团参与上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隔离进行了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了男性和女性在社团参与程度上的显著性差异(如表1所示):女性和男性在政治团体、工会及类似劳动者组织、校友会、职业协会/专业学会及行业协会,以及宗教组织的参与度T检验t值依次分别为-9.936(p<0.001)、-5.908(p<0.001)、-3.974(p<0.001)、-3.370(p<0.01)、2.155(p<0.05)。这表明男女两性在上述五类社团的参与程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对群众运动/消费者权益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娱乐休闲团体、社区组织四种类型社团的两性参与度检验结果是,t值的概率p值均大于0.05,说明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与前述西方学者关于男性更多参与社区行动和娱乐活动、女性更活跃于社会公益服务和消费活动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相符。从表1均值比较结果来看,男性主导型社团包括政治团体、工会及类似劳动者组织、校友会、职业协会/专业学会及行业协会四个组织,性别均衡社团包括群众运动/消费者权益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娱乐休闲团体和社区组织四个组织,女性主导型社团仅有一个宗教组织。整体而言,在社团参与的类型上(“横向隔离”),女性和男性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假设H1基本得到验证。
对于男女两性在社团参与上的数量差异(“纵向隔离”),本文通过考察不同性别被调查者拥有各类社团成员资格的数量来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对九种类型的社团组织的成员参与中,女性社团成员的均值为0.35,而男性这一比例则为0.50,t值为-5.860(p<0.001),这说明在社团参与的数量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社团参与数量明显少于男性,假设H2得以验证(见表1)。

表1 男女两性社团参与程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
注:*p<0.05, **p<0.01,***p<0.001,以下皆同。
CGSS2012还询问了被调查者在“在上述组织中,您过去12个月参与最积极的是哪一个”,以及这个“组织的成员关系”和“成员看问题、做事情方式差别大吗?”,这三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社团组织成员关系的平等性和成员异质性情况。成员关系平等性问题的回答被赋值为从“1=上下级之间等级分明”到“4=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4个等级;成员异质性问题的回答赋值为“1=绝大多数成员没差异”到“4=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四个等级。
如表2所示,单因素ANOVA方差检验发现,三类社团在成员关系平等性和成员异质性上的组间比较相伴概率Sig.(P值)均小于0.000,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成员关系平等性方面,男性主导社团、性别参与均衡社团和女性主导社团的均值平均差分别为-0.582和-0.766,且所有的相伴概率Sig.(P值)均小于0.001,这说明女性主导型社团的成员关系最具平等性,性别均衡社团次之,男性主导型社团的成员关系平等性最弱;在成员异质性方面,男性主导社团与性别均衡社团、女性主导社团的均值平均差分别为0.151(p<0.05)和0.444(p<0.001),这说明在成员看问题和做事情的方式上,男性主导型社团的异质性最明显,性别均衡社团次之,女性社团的异质性最小。

表2 性别化社团的成员关系平等性和异质性
(二)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影响因素
本文设定的自变量较多,在做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进行检测。将所有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通过“输入”法将各变量强制引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介于1.066-2.726,均小于5的警戒值,可认为本文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一的因变量为“拥有各种社团成员资格的数量”,用以考察社团参与纵向性别隔离的影响因素,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的因变量分别为“是否属于至少一个男性主导社团的成员”“是否属于至少一个性别均衡社团”和“是否属于至少一个女性主导社团的成员”,用以了解社团参与横向性别隔离的影响因素。模型一的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二、三、四的因变量为虚拟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一采用“逐步法”、模型二、三、四采用“Wald法”,将各个自变量逐一引入回归模型之中,得到如表3所示的分析结果,从数据来看,四个模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3 社团参与性别隔离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首先来看性别的影响作用。从系数的显著性来看,性别因素在模型一、二、三中均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这说明:其一,男女两性在参与社团数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社团的成员资格,假设H2再度获得验证;其二,越是男性,越有可能成为男性主导社团的成员,而女性则更有可能参与成为性别平衡社团的成员,假设H1得到部分验证;其三,在模式四中性别没有呈现出显著影响作用,与女性主导型社团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的自变量只有宗教信任。考虑到本研究中女性主导型社团仅包括宗教组织,相较于其他变量,宗教信仰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具有宗教信仰与否,是决定居民是否参与宗教组织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除性别以外,其他社会人口结构特征变量也表现出程度不一的影响效应。教育和政治面貌与前三个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之间均有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和更多属于党员、民主党派或共青团员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更多数量的社团,也更有成为男性主导社团和性别平衡社团的成员。此外,从系数值和显著性来看,居民参与更多社团和男性主导社团的机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上升;汉族比少数民族更有可能参与性别平衡社团;居住在城市而非乡村的居民,成为男性主导和性别均衡社团成员的机率更高;从事有酬劳动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更多类型的社团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同居、未成年子女数和社会等级三个变量被剔除出回归模型,这说明是否处于婚姻或同居状态、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多少,以及所属社会阶层的高低,并不会显著影响个人的社团参与情况,这一结果没有验证前述西方研究文献中的某些普遍假定。总的来看,社会人口结构特征中的大多数变量与社团参与的横向或纵向性别隔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假设H3获得大部分验证。
而在文化因素变量组中,最具显著性作用的变量是社会贡献意识和宗教信仰。具体来看,越是有意愿对社会做贡献的居民,越有可能参与更多数量的社团,也越有可能参与成为男性主导社团和性别均衡社团的成员;而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更多社团,尤其是性别平衡与女性主导社团的机率更高。此外,拥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更多类型的社团组织,尤其是性别平衡社团;社会性别意识越强的居民,则越有可能参与到男性主导型社团中去。由此可见,文化因素的各变量与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显著关联性,假设H4基本得到验证。
在非正式社会交往变量组中,只有非亲属交往网络在模型一、二、三中对因变量起到了正向影响作用。这意味着,与家人和亲戚以外的其他人的交往网络规模越大,居民越有可能参加成为更多社团的成员,包括男性主导社团和性别平衡社团。亲属交往网络的大小对社团参与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假设H5只获得部分验证。
从系数来看,在生活方式变量组中,“媒体使用”对前三个模型中的因变量最具显著影响,“社交频率”次之。这说明,频繁使用各种媒体形式和经常在空闲时间进行社交,会对居民参与更多类型的社团,尤其是男性主导社团和性别均衡社团,产生积极的正面效用,假设H6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基于对CGSS2012数据的分析,本文检验了男女两性的社团参与是否存在着横向和纵向的隔离,以及对隔离现象的三类可能解释。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研究结论:
第一,研究证明了在社团参与数量和社团参与类型上的性别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即两性在社团参与中的纵向隔离和横向隔离在中国的确是存在的。当然,并非所有类型的社团组织都是由其中某一性别主导参与,在某些类型社团组织中男女两性的参与程度较为均衡,但这并不能改变社团参与在整体上的性别隔离分布。
第二,不同类型的横向性别隔离社团,其组织成员的结构特征也不相同。在成员关系的平等性方面,女性主导社团最强,性别均衡社团次之,男性主导社团最差;在成员异质性上,男性主导社团最明显,性别均衡社团次之,女性主导社团最弱。
第三,研究检验了对社团参与中性别隔离现象的四种解释假设的有效性。在影响社团参与的社会人口因素中,最有解释力的是性别、教育和政治面貌,而年龄、居住地、民族和有酬劳动与否,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社团参与的某些性别隔离特征产生了影响;在文化因素解释中,社会贡献意识和宗教信仰最具解释力,政治效能感和社会性别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社团参与的数量或类型分布;在非正式社会交往因素中,不是与家人和亲戚的社交网络,而是与非亲属的朋友、同事等的社交网络,被证明其规模大小会影响居民的社团参与情况;在生活方式因素中,媒体运用和社交频率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力。
(二)启示意义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关注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及其表现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通过社团参与等途径建构的正式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作用。诸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林南(Nan Lin)和边燕杰等知名学者,已论证了社会资本是如何有助于个体获取信息、资源、职业提升和社会支持。既然社会资本存量对个体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社会资本积累上的性别差距很可能会成为阻碍两性平等实现的一大障碍。
一方面,男女两性在社团参与上的纵向隔离意味着女性更少拥有正式社会网络,这不仅削弱了女性的个体发展机会,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民参与增长,并影响到社会信任和集体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两性在社团参与上的横向隔离会带来社会资本类型上的差别。由于在成员异质性程度上的显著区别,女性主导型社团更容易建构出具有先赋性、封闭性和内聚性特征的同质性社会资本,而男性主导型社团则容易发展出基于业缘、趣缘和利益目标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此外,对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社团的参与,更容易形成帕特南所称的“联合社会资本”(bonding capital),虽然它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之间的团结,但也有可能导致成员对外部的敌意[13](PP 11-12)。在性别隔离基础上建构的联合社会资本和同质性社会资本,将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问题。它会使女性被隔离于公领域的发展机会之外并强化其在私领域的传统作用;参与社团活动的女性,将更多地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维持与同性别和相似背景人群的接触。以宗教组织这一典型的女性主导型社团为例,琳达·伍德海德(Linda Woodhead)将女性更积极的宗教参与归因于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性别社会化结果的女性“关怀伦理”以及对物质剥夺和社会剥夺的代偿性反应;女性的宗教参与少有挑战社会性别的现状,却可以缓和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性地位[14](PP 67-84)。女性主义学者薇薇安·朗兹(Vivien Lowndes)指出,女性社会资本的配置模式,决定了它更有助于“保持现状”(getting by)而非“获得更多”(getting on)[2](P 230)。也就是说,女性可用的社会资本类型并不能带来性别不平等现状的改变。
出路究竟在哪里?普特南认为,异质性的“桥梁社会资本”(bridging capital)能够包容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员,产生出更为广泛的互惠规则[13](P 12)。女性主义也认同,更具兼容性的桥梁社会资本能够产生人际信任和增进社区联系,从而促进社会平等,包括性别平等[2](P 76)。那么,应该如何培育兼容性的、异质性的桥梁社会资本?
本文认为,打破社团参与的性别隔离,引导男女两性跨越传统性别角色限定的社团参与类型,将有助于缩小社团参与数量上的性别差距,从而促进桥梁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对于社团参与数量和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启示我们:拥有更高知识水平和体制内政治身份,生活于城市地区,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贡献意识,惯于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了解信息,更多参与社交活动,以及拥有更多非亲属社会网络的居民,更容易成为传统男性主导社团的成员。上述这些因素大多与教育背景和正式工作发展机会等后致性条件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公共政策领域的顶层设计,改进社会资源的性别分配现状,提供女性更多教育和正式就业的机会,必然会带来女性在知识、技能、态度、观念的变化,缩小我国女性在劳动力城市迁移和业缘关系等方面与男性的传统差距。这些都会增加女性突破社团参与横向隔离的可能性。表3的统计结果表明,从事有酬劳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参与更多社团类型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支持了女性主义学者对普特南观点的批判,后者曾声称“近年来社团参与的减少主要集中于女性群体”,坚称因经济需要而全职工作的女性造成了公民参与最大限度的下降[13](PP 231-233)。英国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揭示,在雇佣劳动大军中女性比例的上升,会导致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性别角色的变化,最终带来女性参与社团活动的增加[15](PP 417-461)。
此外,传统社团组织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加速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有研究显示,性别社会化结果导致女性更倾向于社群主义,具有友好、可亲和合作氛围的团体更能吸引女性的主动参与;反之,不平等或疏离的成员关系更容易引发女性对团体的距离感和消极参与[16](PP 65-68)。尽管中国大多社团并不存在形式上的性别隔离机制,但社团参与中的性别隔离现象确实存在。一些男性主导社团的行政化色彩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像消费和公益服务组织这类在西方国家通常女性参与更为活跃的社团,在本研究中却没有显示出女性主导的特征。而作为女性主导社团的宗教组织,尽管在西方国家是民间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也是普特南所称的美国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17](PP 37-38);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里,宗教参与更多产生的是人们对宗教团体的忠诚度和小团体内部信任的积聚,以及跨团体社会的潜在分裂[18](P 104)。为解决传统宗教参与造成的社会资本的封闭性问题,以政策扶持去引导我国宗教团体积极发展慈善公益活动,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从而改造和发挥宗教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已成为业界和政府的共识[19](P 76)。西方经验研究表明,广泛的宗教慈善公益活动对女性突破照顾者的传统性别角色,发展出与公民参与相关的技能、规范和兴趣具有积极影响[2](PP 192-208)。曾有女性主义学者对美国历史的回顾研究发现,随着社会进步和妇女地位的提升,具有隔离或排斥等封闭性特征的传统社团在成员数量上急剧萎缩,成为美国的社会资本在20世纪后半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2](PP 18-39)。殷鉴不远,推动中国各类主要社团组织的组织改革和制度创新,促使社团向更为开放、包容、公益、平等和自主的方向转变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利于吸引更多社会公众的参与,增加社会资本的整体存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拓宽桥梁社会资本的构建空间,增加基于普遍信任的社会资本的规模,从而推动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平等的实现。
[1][英]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B.O’Neill and E.Gidengil ed.GenderandSocialCapital[M].New York: Routledge,2006.
[3]邓国胜.中国社会团体的贡献及国际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06,(3).
[4]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2).
[5]胡荣、胡康.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6]Miller McPherson and Lynn Smith-Lovin.Women and Weak Ties: Differences Sex in the Siz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82,87(4).
[7]Melissa Coulthard,Alison Walker,Antony Morgan.People’sPerceptionsofTheirNeighborhoodandCommunityInvolvement:Resultsfromthe2000Survey[M].London: The Stationary Office,2002.
[8]Sue Falter Mennino and April Brayfield.Job-Family Trade-Offs: The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of Gender[J].WorkandOccupation,2002,(2).
[9]鲁晓、张汉.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性别鸿沟: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14,(4).
[10]杨荣军.女性政治效能感实证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6,(4).
[11]伍华军.公民意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促进与形塑[J].法学评论,2014,(4).
[12]Steven J.Rosens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Mobilization,ParticipationandDemocracyinAmerica[M].New York: Macmillan,1995.
[13][美]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祝乃娟等译.独自去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Linda Woodhead.Femin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Region: From Gender-blindness to Gendered Difference.InTheBlackwellCompaniontoSociologyofReligion[M].edited by Richard K.Fen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2001.
[15]Peter A.Hall.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J].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1999,(28).
[16]Christopher F.Karpowitz and Tali Mendelberg.TheSilentSex:Gender,DeliberationandInstitution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17]刘澎.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J].美国研究,2005,(1).
[18]苗月霞.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J].浙江社会科学,2006,(6).
[19]龚万达、刘祖云.从衰熄到兴盛:当代宗教慈善与社会资本积聚[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8).
责任编辑:玉静
The Study of Sex Segmentation of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CGSS2012
XU Lan-lan
(Law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 515063,Guangdong Province,China)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sex segmentation;social capital
Upon analyzing the CGSS2012 data,this article examines sex segmentation of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ndeed are vertical segmentation and horizontal segmentation of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which are highly influenced by social demography,cultural practice,informal social network and life style.Sex segmentation of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 will exacerbate the difference in types and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between men and women,a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of in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public policies are to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so as to guide men and women to engage in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memberships that help overcom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Efforts are also needed to promote reforms in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o as to make these organizations more open,inclusive,public-benefit,equal and autonomous.All these efforts will widen the space in which to build bridges and social capital in favour of social equality,including gender equality.
徐兰兰(1977-),女,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
本文为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WYM11058)和汕头大学文科科研基金项目(编号:SR13001)的研究成果。
C912.2
A
1004-2563(2017)03-009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