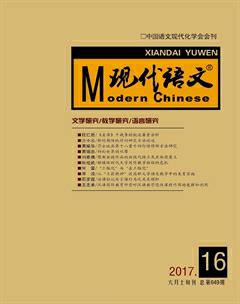论北村《安慰书》中的创伤书写
摘 要:作家北村在时隔近十年后推出长篇新作《安慰书》,依旧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隐痛。但和《施洗的河》《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以往的写作相比,北村的书写呈现一个明显的转变,作家不再花笔墨书写主人公受到上帝感召得到精神的救赎。这是否是北村写作中有意识的转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北村对个体精神困境出路的追寻是否有新的思考?《安慰书》中的人物身上留有时代烙下的精神创伤,而且创伤还以代际传递的方式留存到下一代。
关键词:北村 创伤 代际 幽灵
北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名先锋作家,他在1992年皈依基督教,之后开始在创作中引入基督教的维度,陆续创作了《施洗的河》《卓玛的爱情》《周渔的喊叫》《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作品。所以看北村的创作,一方面在于他的基督徒身份。他以自己对《圣经》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于基督教忏悔和赎罪意识的灵性感悟,使他区别于非基督徒的宗教文学写作。另一方面,他在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中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神性视角,窥入人的心灵,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2016年,这位曾经的先锋文学作家在告别文坛近十年后以长篇新作《安慰书》宣告回归,“这十年可谓蹉跎,忙于生活,所幸没有停止阅读,放下体验,在北京这个急剧变动的城市,看到了急速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狄更斯笔下最好的时代或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深刻变化的时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好和坏的变化,以及其中非常复杂的精神图景。”[1]
北村依旧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隐痛。《安慰书》以一桩杀人案件引开,副市长的儿子陈瞳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孕妇,在杀人案表象的背后,北村慢慢揭开十二年前花乡霍童村高铁拆迁案背后两代人的纠葛,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扭曲,法律与道德的悖逆。在北村犀利的人性剖析下,我们看到当代人在近三十年来的泪与痛,“小说家只关心灵魂战争的秘密。我不写历史,只写历史对人类人性和精神的影响。”[2]但是在《安慰书》中,和《施洗的河》《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以往的写作相比,北村的书写呈现一个明显的转变,作家不再花笔墨书写主人公陈瞳、刘智慧、李江受到上帝感召得到精神的救赎。这是否是北村有意识的转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北村对个体精神困境出路的追寻是否有新的思考?《安慰书》中的人物身上都留有时代烙下的精神创伤,而且创伤还以代际传递的方式留存到下一代。
一、创伤理论与北村的小说
创伤无时不在。从语源学意义上来说,创伤源于希腊文,英文为trauma,“本意是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3]但直到近年来创伤理论才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运用到文学领域。“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首次正式收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词条,此后对心理、文化、历史、种族等创伤的文化书写、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创伤一跃成为左右西方公共政治话语、人文批判关怀乃至历史文化认知的流行范式。”[4]1993年,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凭借创伤小说《宠儿》及其他几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在近百年来受到无数的战争创伤、文化创伤,但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作家有意识地关注创伤的书写与精神救赎。笔者不知道北村是否了解创伤理论,但北村似乎意识到了创伤书写,他笔下的主人公刘浪、陈步森、刘智慧、李江都曾遭遇过严重的心理创伤。
由于北村的信仰背景,他笔下的主人公获得内心安宁的途径均是走近信仰。在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当人的心灵处于枯寂、困顿之际,而又找不到情绪发泄的场所,宗教总是很容易找到这一类人群。而无一例外,这些底层的民众或是童年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伤,或是成年后受到时代发展带来的都市创伤。北村意识到心理创伤给个体精神带来的挣扎。北村以文学家的方式关注着现实。他在《安慰书》中延续了关注底层群氓,开掘人性深处的爱与痛的写法。他依旧在关注沉默的大多数。进化论时间进步逻辑给时代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也有一些个体的生存尊严受到践踏。花乡霍童村高铁拆迁为霍童村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代价却是刘青山等人的身体遭到现代性进程无情的规训与惩罚,被推土机压残。随之而来的是潜藏在两代人之间的创伤与梦靥,血腥的场景不断在当事人及其后代的梦中闪回。创伤通过代际传递在李义与李江,陈先汉与陈瞳,刘青山、刘种田与刘智慧两代人之间继续存在,并引发人性的诸种悖论。
二、幽灵的代际传递
北村在处理《安慰书》中创伤的跨代传递时称为“策划已久的复仇。”[5]但是安妮·怀特海德认为,“当是一件可耻的、因此不可言说的经历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或被保密的时候,症状就会从这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创伤无需被说出即可交流,作为一种沉默的在场或幽灵,留存在下一代之中。”[6]刘智慧、李江是无辜的第二代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在拆迁案中犯下罪行,他们是跨代创伤的承受者。刘智慧亲眼目睹了父亲刘青山和母亲身体被毁灭的惨状,“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悲惨的午夜我抱起刘智慧时她睁开的眸子里的恐惧,就像个深渊!” [7]“当我赶到医院时,水沟里流淌的血水把我吓坏了,更让我魂飞魄散的是:我看到幼小的刘智慧正和大人们一起,用毛巾和热水清洗尸体!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仔细地清洁母亲的遗容(后来证实没有死亡,只是脑死)。” [8]一个孩子在目睹父母亲遭受的惨状后竟有如此冷静的表现,笔者不知道北村是不是延续了先锋小說的写法,笔锋冷酷不带感情。从心理科学来看,刘智慧作为儿童在目睹父母身体被毁坏的惨状这一事件后,“创伤后的结果是极易出现应激障碍的,这一障碍通常来说的反映会是抑郁或焦虑、解离症状、转换障碍并伴有明显的生理或躯体症状。”[9]在刘智慧后来的讲述中,她曾一度丧失对生活意义的追寻,患上抑郁症。在心理上,她经常梦见父亲和母亲惨遭推土机碾压的梦靥。在生理上她经常呕吐,却查不出病因。这是典型的心理创伤的重度反应。“DSM-IV进一步强调,创伤不只是通过直接经历或目睹此类事件造成,还可以通过得知家人或其他亲属的意想不到的暴力性死亡或严重伤害,或者由死亡或伤害的威胁所造成。”[10]刘智慧承受了上一代遗留的创伤。但是在刘智慧成长的过程中,她的存在感逐渐苏醒。她大学时热衷于公益事业,并且与仇人的后代李江、陈瞳保持暧昧的关系。当读者以为刘智慧宽恕了仇人,内心获得安宁时,真相却被刘智慧说出,“我是个病人了,而且这病永远也治不好了,我已经是一团复仇的火焰……它让我觉得生活重新获得了意义。”[11]原来刘智慧和陈瞳、李江亲近是因为心理创伤无法发泄,转换成为复仇的情绪。仇恨转化成为她的存在感与价值感。副市长陈先汉当年下令轧死刘青山,但是他的儿子陈瞳也成为了代际幽灵的牺牲品。陈瞳是悲哀的,他虽然生活在官宦人家,但童年是不幸的,“打他记事以来,他和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12]“亲眼看见过几次父亲和女人鬼混。”[13]这对于一个童年时期的孩子来说无疑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家庭并未给他带来精神的庇护。在他后来和刘智慧的接触中,他了解了父亲当年下令轧死人的举动,父亲这一形象在他心中早已崩塌。陈瞳开始具有审父的眼光。他将引导自己做义工的刘智慧视为圣母,并且对她含有“一种复杂的对恋人和恩人混合体的崇拜。”[14]人性的隐微与复杂在北村的笔下逐渐显现。最终刘智慧揭开了多年来亲近陈瞳的真相——复仇。人性善恶两极的转换如此迅速。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北村的信仰背景对他理解人性提供了独特的角度。人类的善行中也包含罪性的成分。于是陈瞳被彻底地抽空了存在的价值。父亲形象在他心中早已是罪恶的化身,而一直以来被他当作心灵慰藉对象的刘智慧竟然将他当成复仇的对象!陈瞳将如何面对价值感的崩塌和精神的虚空!于是陈瞳做梦般地杀死了一位孕妇,将多年来遭受的心理创伤转换成为外在暴力行为。北村在这里没有像在《施洗的河》《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中进行类似的叙事安排,让入狱后的陈瞳和刘浪、李百义和陈步森般受到上帝的感召,接受信仰以获得内心的安宁。陈瞳直到面临死亡时才恢复爱的知觉。北村以文学表现的方式呈现这些创伤个体身上的爱与痛。
三、创伤的治愈
跨代的幽灵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会代代传递。“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重新审视自己的反应以及事件本身,而不去逃避,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能力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其实我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15]北村在199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基督教中,告解是一项重要的仪式。信徒在神职人员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以求得天主宽恕,并得到神职人员的信仰辅导和生活道理。北村应该熟悉基督教中这一仪式。在《安慰书》中,刘智慧经常到临终医院看她当年被烧成植物人的母亲,并且将她当成倾诉的对象。倾述是治愈心理创伤的重要方式。“创伤的倾听者成为创伤性事件的参与者和共同拥有者。”[16]刘智慧通过倾述,将自己多年来的恐惧和梦靥讲述给一位不能作出回应的植物人听,将内心的隐痛释放出来。但是她母亲只是一位倾听者,却不能回应问题症结以解决她心理的创伤。她并未在倾听者那里获得治愈的心理治疗以及存在的价值感。仇恨依旧占据在她的内心。另一位受到代际幽灵困扰的主人公李江,他的倾诉对象是酒吧的孙小梅。在孙小梅那里,他获得爱情的滋润和肉欲的狂欢,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内心的创伤。但是和刘智慧一样,他的仇恨情结一直萦绕在心。小说中类似告解的宗教行为并没有治愈两人的创伤。小说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没能做到宽恕。或许这是北村对于时代病症的思考,也是他对文学书写治愈创伤的不确定感。在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文学家充当书记员的角色记录下时代的爱欲与痛楚,但是作家对现实的透视使得他不能够用文学手法提出或怀疑治愈创伤的方法。信仰是否也变得无力?精神的救赎该往何方?这是北村以文学的方式抛给读者的追问。小说的最后陈瞳被执行死刑,刘智慧到非洲成为一名修女,而李江成为花乡集团总经理。小说似乎成为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笔者以为这是北村《安慰书》的局限所在。作者处理的过于草率。在文本中,刘智慧此前没有接触信仰的信息,北村设计了她的结尾,其实却削弱了小说探索人的精神救赎和存在局限性的向度。或许在北村看来,成为修女是刘智慧摆脱梦靥,治愈心理创伤的方式。而李江,这位复仇者,他又将如何面对间接害死陈瞳的良心不安,他的心理创伤如何治愈,精神如何得到救赎?作者并没有在此深入探讨。
并且,官逼民反、父仇子报的古典文学思维依旧存留在《安慰书》中,封闭传统空间中的落后、蒙昧生存等前现代思维通过代际传承依旧深深镌刻在民族心理中。作为受过启蒙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需要对此警惕以及对此思想资源进行清理。某种意义上,代际幽灵不仅是隔代传递,甚至会如幽灵般一直缠绕固结于民族心理中。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将“国民性批判”视野置于文学实践中,在铁屋子中呐喊。这是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治愈民族创伤提出的文学治疗方法。
四、结语
北村的复出之作《安慰书》并没有带给读者太大的惊喜,就像余华的《第七天》,市场有时对读者的阅读期待造成误导。2016年中国很多作家依旧在关注底层现实,像贾平凹的《极花》、陈应松的《还魂记》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要支点。‘五四之后,底层民众被认为是构成民族国家的主体,于是,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就成了知识分子获取合法身份的重要渠道。”[17]当下中国的现实给作家提供无尽的宝藏。北村以他独特的开掘人性善恶两极的笔触讲述社会热点拆迁事件。小说中陈先汉秉持的价值观是改革就会有牺牲,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前进。这一进化论时间进步逻辑所带出的现代性观念成为当前社会许多人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一些存在个体的精神隐痛被忽视,存在的尊严受到践踏,生命受到漠视,对于存在的个体而言,物质的补偿并不能治愈时代带出的精神创伤。刘青山、刘种田虽然获得了巨额的物质补偿,但是留存在他们以及他们下一代心灵的创伤该如何解决?甚至,代际创伤的幽灵如果得不到治愈,将会通过代际传递下去。这无疑是民族的灾难。20世纪中国社会遭受了太多的历史灾难,战争创伤和文革创伤的幽灵至今镌刻在民族心理中。文学家能够观察到时代的创伤和隐痛。对当下中国的权力而言,如果能够充分尊重个体的生存和生命权利,让他们存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并且完善合理告解与述说的途径,那么冲突也将会减少。
注释:
[1][2]北村:《安慰书·后记》,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3][4]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5][7][8][11][12][13][14]北村:《安慰书》,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70页,第223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24页。
[6][16]李敏译,[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第40页。
[9]王文胜:《“十七年”时期的创伤叙事——以<红岩>为例》,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
[10][15]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第2页。
[17]王宇:《国族、乡土与性别》,中国社会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参考文献:
[1]北村.安慰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2]徐凯文等译,[美]John Briere&Catherine Scott.心理创伤的治疗与指南[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3]李敏译,[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4]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5]王宇.国族、乡土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王文胜.“十七年”时期的创伤叙事——以<红岩>为例[J].小说评论,2009,(6).
[7]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
(吴泰松 江苏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