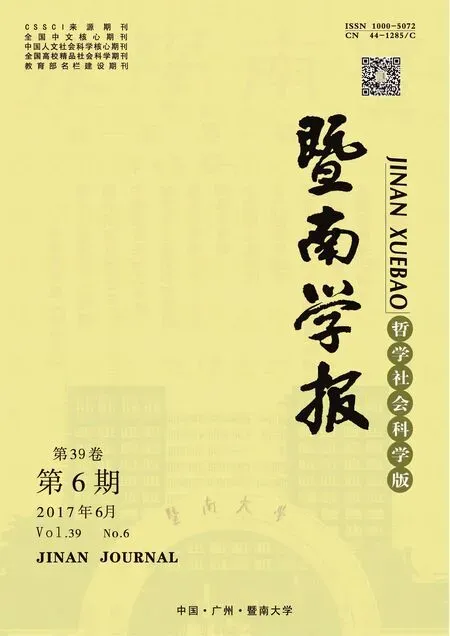民国戏班价银的约定与收取
——以香港、日本藏粤剧戏班经营文书为中心
陈志勇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近代史研究】
民国戏班价银的约定与收取——以香港、日本藏粤剧戏班经营文书为中心
陈志勇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日本东京大学、香港文化博物馆和香港“中央”图书馆藏有一批民国时期广州太安公司下辖戏班的定戏契约及相关经营文书。这批文书直现了戏班(卖戏公司)与买戏主会之间对本价戏银和附加银价(中宵银、利市银、折合银等)的议定,戏班关于度量衡标准、主会克扣拖欠戏金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对戏金收取的风险规避。围绕戏金的约定和收取,戏班(卖戏公司)与买戏主会、行会组织、信息中介人、政府权力部门甚至盗匪、军队之间相互交缠的利益关系得以清晰呈现。这批文书是了解民国时期粤剧戏班(卖戏公司)生存境遇和岭南墟镇演剧市场变迁的原始史料。
粤剧; 契约文书; 戏价; 戏班; 吉庆公所; 戏曲市场
价银也称戏价、戏金,多指职业戏班商业演出的经济收入。戏价的生成与给付,贯穿于戏曲演出的全过程,关涉到戏金周边的多方利益人群,是窥悉戏班经营活动和伶人生存状态的重要角度。1924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了《明清戏价》的读书杂记,表现出对明清时期戏价问题的浓厚兴趣;近年也有学者从戏价角度观察明清戏曲发展的轨迹,但由于缺乏更为翔实的文献,对戏班经营情况尚停留在概观介绍的层面,戏价相关问题的研究难以推进。
近蒙黄仕忠教授赠阅一批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民国时期(1914—1934)粤剧太安公司经营文书影印件。这批经营文书包括41份订戏合同、7份执照、20种23份戏班横头单,以及78份信函及封套、6份香港华民政务司签发的许可证。后又由容世诚、关瑾华等学者的论文知晓,日本东京大学所藏这批粤剧戏班经营文书,实际与香港文化博物馆所藏26张戏班合同、香港“中央”图书馆所藏源氏太平戏院经营文书同出一源。这批数量庞大的经营文书直现了民国时期广州太安公司下辖祝太平、颂太平、詠太平、一统太平、永康年、太平剧团等戏班在粤属诸县墟镇的演出面貌。尤值得称道的是,其中67份订戏契约对当时戏价的议定、组成、给付和扣减等事项有翔实的规定,是窥探近代粤剧戏班经营情况的重要史料。
一、本价戏银与附加银价的议定
戏班进行商业性演出,首先需要戏班接戏先生和聘戏的主会代表议定戏价。在不少地方把买卖双方议定戏价、戏目、日期的环节谓为“写戏”,而在广府地区则有专门负责买卖戏的中介机构吉庆公所为粤剧交易提供洽商的平台。吉庆公所里常年悬挂着戏班名号的“班牌”和写有戏班阵容的“水牌”,供前来买戏者挑选;挂牌戏班还会派出接戏先生常驻吉庆公所,为聘戏者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对于挂牌戏班的接戏,吉庆公所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和惩处制度,规避聘戏过程中各种徇私舞弊和戏班间的恶性竞争行为。
聘戏的主会代表确定演出戏班,需要买卖双方签订合同。从日本东京大学和香港文化博物馆藏吉庆公所及其分支机构藉福公所签订的67张聘戏契约来看,合同围绕戏价周详地规定买卖双方的权责和违约的风险。为确保契约的有效生成和戏价的最终兑付,制定有“初下定银”和“再下定银”流程与保障条款。
初下定银。签订合同的当场即要预付定银,定银的数额,根据现有合同来看并无一定之规,也看不出与议定的戏价有直接的关联。如民国三年(1914)10月11日顺德龙山官田乡订到颂太平班京戏三本,戏价银980元,当日交定银141元8毫5仙;民国七年(1918)顺德东马宁水口坊订咏太平班三本戏,戏价银1 380元,当日交定银261元6毫。这是比较多的情况,少的不到10元,如民国七年(1918)增城久裕乡订祝太平班4本,戏价银1 130元,就日交定银9元6毫。初下定银只是对在吉庆公所签订合同的初步确认,主会代表还需将合同带回与其他主事商议,对戏价、演出戏目、演出时间、班中名角等相关事宜予以确认。对已签合同需再下定银以示确认,否则视为无效。
再下定银。在戏班尚未到埠演出前的规定期限内,主会代表会再下数额较大的定银,表示愿意履行已签合同各项条款,戏班也开始档期演出的准备工作。1914年11月7日增城张何沙头乡订颂太平班的合同中写道:“是感凡城乡市镇及各埠戏院过爱,不可听信戏禡惑言,务要亲到本所定允,写立合同,任班酌量,应推约于××日主会亲到本所听班回话。如不合式(适),任班恭辞主会另买别班。如肯应允,依期赴演。”回话时再下定银明显比初下定银要多,如民国六年(1917)6月7日东莞大享乡定祝太平班4本戏,戏价银1 150元,初下定银是20元,在戏班正式下乡开台的前两天,主会亲到吉庆公所再下定银230元,虽然与合同约定的300元有所减少,但也明显比初下定银数额要大很多。因为再下定银是关系到定戏合同能否最终确立的关键一环,为表达买戏方的诚意,其数额基本上占到全部戏价银的10%~20%。在初下、再下定银之后,戏班还会于演出过程中,陆续向主会催缴一定数额的预付定银,而戏班的管账先生会在合同的天头记录下这些定银的数额;当全部演出结束时,定银会从戏价银中予以扣减。定银的陆续支付,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买戏方的履约行为,为戏班的自身利益和演出活动提供了保障。
戏班是伶人、乐师以及其他管理者、杂勤人员组成的共同体,民国时期大型的粤剧红船班社都在140-160人之间,小班也有数十人,如此庞大团体的衣食住行都是不小的开支。为保证戏班在演出前、中、后不同阶段的资金充足,合同对各个细节的支出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以期最大限度保障戏班和伶人的各项权益。折合为银价和实物的戏班权益,都可视为戏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过去多被学者所忽略,而在太安公司粤剧戏班合同中却有很好的呈现。
首先是中宵银。中宵又称“中消”,是主会供应给戏班的伙食。伙食所需物品的清单会在订戏合同上详细开列。以民国三年(1914)11月7日颂太平班到增城张何沙头乡庆贺共和万岁演戏为例,合同写明:
每日中宵白米二石六斗,要官斗,鲜鱼一十三斤,豆腐十斤,青菜三十斤,姜盐糖各二斤,生油七斤,干柴百斤。
不仅如此,还会就赴演途中戏班的伙食开支,也一并在合同的格式条款或附加要求中写明。颂太平班在沙头乡庆贺共和万岁演戏合同还写道:
上馆居住,上下马中宵多一日,水夫二名,床铺板凳柴水足用。过驳盘船,每日白米二石六斗,官斗生油七斤,鱼菜折银二大元。干柴足用,原应有中宵,毋得包办,如违照罚。
戏班到乡下演出,人生地不熟,加之交通不便,为使艺人在生活上有良好保障,他们很少将柴米油菜及生活必需品折合成银两,而是直接在合同中列出实物数量,这种惯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1929年“寰球乐”班主何浩泉借口改善艺人生活,首倡取消“中宵”,除油盐糖茶仍供应实物外,其余统由主会每日折合现银38元发放,自此成为新的通例。中宵折银,虽给主会减少了麻烦,却为班主通过掌控伙食盘剥和控制中下层艺人提供了便利,是粤剧戏班管理历史上的转折点。
次之是利市银。利市银分为开台利市和开箱利市两种。粤俗,戏班到新的台基演出,第一晚都会破台、祭台,演出《祭白虎》、《收妖》等例戏。粤剧破台仪式中由关公及其部将周仓、关平来煞鬼,若破台不成功,恶鬼还会来作祟,破台的演员也要招灾,故而大破台后,当晚不演出,顾主或会首照付戏金,还会给扮演神鬼的演员赏钱。开台利市在太安公司下辖戏班订戏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如民国初年,一般“开台利市银八大元”,参加开台的“脚色银五毫正”,另由于开台要使用公鸡的血祭台,则有“现交挂红鸡银一毫五仙”。开箱利市银既可以实物形式缴纳,也可折合为银元支付,“每日开箱利市,戏桥纸、打面油,颜色,溪纸,脚香、茶叶,共银八毫正。”开台利市和开箱利市是南粤地区民俗文化的产物,为祈愿戏班演出的吉利安泰和台基民众的福祉,这类利市银尽管未归于总的戏价本银中,但主会都不会无故拒绝支付。
与各种祭台收妖例戏收取赏金不同的是,诸如《碧天贺寿》、《六国大封相》、《跳加官》、《天姬送子》、《状元进宝》等吉祥戏,因为会给主会带来好的彩头,演出的艺人或戏班往往会获得丰厚的赏金。在有些合同中,明确规定“如演落地《八仙贺寿》、《加官》、《送子》,每次利市银四大员(元)”。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观念的改变,加之各地主会首脑对戏班收取开台银颇有微词,20世纪20年代吉庆公所经过公议,发表启事,“废去开台银”。删减利市银名目与支出,目的是为了迎合各地主会尽量压低戏价的苛刻要求。
再次是各类折合银,此项戏价银属于杂项,有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附加性,如遇到主会大摆宴席,艺人由于要上台演戏,不能及时吃到主会的酒席,以银折算更为实际,因此“每逢起庆摆席,每日折席金银四大元”,至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项折合银涨至八元。再如,有的戏班与主会议定,会有点心银、茶水银等杂项,至民国十五年(1926)后还增加了“剧员整容费”,即今天的化妆费用。民国十八年(1929)4月8日新纪元班到四会白蚬步演出,在合同天头上记有点心银1元,槟榔银1元的字样,这说明有些折合银是戏班临时与主会商议而获得的,并非合同规定的折合价银,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附加戏价银的组成部分。
综合民国吉庆公所定戏合同条款,民国时期粤剧戏班的戏价银其实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演出本戏所获得的,它是整个戏价银的大头,另一部分是附加戏金,他们零零碎碎,名目繁杂,且具有相当的灵活度,有还是无,多还是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戏班与主会的协商,但它们也是戏价银的重要补充。另外,赏银曾是明清时期戏金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在岭南地区的粤剧演出市场中,都归于利市一类,并在合同中写清楚。这种在合同中直接写明赏金(利市)的做法使得主会易于操作,也是岭南人崇尚简洁务实作风的集中体现。
二、戏银收取的不利因素与风险规避
戏价议定以后,戏班就开始陆续收取报酬。从首笔定银开始,到演出结束时最后一笔尾款的收讫,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出现拖欠,更是难以预期。令戏班同样头痛的是,部分主会以各种理由克扣戏价,在申演、赴演、演出和离埠的过程中遭遇不可抗拒的因素,也会导致戏价银的减除。可以说,戏价银议定数额,很多时候与最终收取的数额是不相吻合的,甚至相差甚远。这其中的影响因素蕴含着民国时期戏班与主会及各种地方势力的交缠关系,也是当时戏班艰难生存状态的历史写照。
(一)戏价给付的度量衡问题
戏金的给付包括银元和实物两类,如果主会交纳的银元成色不好,实物又缺斤短两,将直接损减价银的实际到账价值。民国初年,广东币值混乱,虽经整治,但仍有多种货币流通,通行的除光绪十三年(1887)广东银元局铸造的龙洋,还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香港银元、日本银元等数种。民国三年(1914)国家铸造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每枚7钱2分,成为当时通用的主币,但仍有不法商家以劣充好,把成色不足、分量不够的银元用来流通。正因如此,所有的太安公司的订戏合同都明确规定了银元的收取标准:“近因百物腾贵,集行公议,由民国三年七月起,各班戏价及杂项每元均收七贰,以擞毫计,免用平兑,并不折不扣。倘有固执历年向章,将戏价银元七壹折交及低扣等情,作欠戏金追收。”有的合同不仅在正式条款甚至在补充条款中也写入“每元均收七贰”,表示着重强调。“每元均收七贰”即指银元标准为库平0.72两,是当时通行的大银元。
由于民国初年度量衡不统一,也存在戏价兑付不公的情况,因此对于量化白米的容器,合同中多规定要官斗。官斗较省斗大五合,而一合为4两,也就是说,官斗每斗要比省斗多1斤4两。如按当时合同规定,每个戏班“每日中宵白米二石六斗”,那么,用官斗量取将要比省斗多出32斤8两白米。称重的秤,在吉庆公所的合同中也明确规定为“司马秤”。这种秤又名司秤,以16两8钱为1斤,民国时期存在多种衡制的秤,有的甚至以10两为一斤,显然在定戏合同中将度量衡规定清楚,让戏班在收取实物戏价时不致吃亏,保障戏班和伶人正当权益的足额兑现。
(二)主会克扣拖欠戏金问题
主会不按合同兑付戏价,找各种理由克扣拖欠戏金,对于已完成演出义务的戏班而言无疑是最为头痛的事情。粤剧戏班在县邑演出,时长基本固定,中午12时至晚6时为日场,晚7时至12时为夜场,然不同戏出搬演时长各异,日戏正本或夜戏出头太长都会影响夜场正本戏艺人的按时上场,苛刻的主会则借口扣减戏金。鉴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吉庆公所的合同中都会加上这样的新条款以规避风险:“凡是日戏本太长,或是晚出头太长,为原有钟点时间所限至(制),该剧员不能出台唱演,无论各处戏院及乡村墟镇,均不得藉端短扣戏金。”即便行会组织绞尽脑汁预料到多种可能导致戏价受损的“假设”情况,但现实中的风险总是层出不穷,难以一一防备。民国六年(1917)9月咏太平班到南海堤田乡贺天后千秋演剧,议定戏价1 460元,但在结算尾款时还是出现了克扣戏价的事情。戏班代理给位于广州黄沙太安公司总部的信函写道:
咏太平班在堤田乡唱演,该处主会万分野蛮,强迫点《卖胭脂》出头,否则不找数,不落箱。本班无奈,迫得哑忍,勉强演《卖胭脂》一出。及至找数时,主会又云:“文仔演《卖胭脂》不跴步”,要强罚扣戏金。经弟多方理论,无奈主会恃蛮,硬减扣戏金94.55元。
主会找岔子来减扣戏金,对于下埠跑乡的戏班而言是常见之事,强点《卖胭脂》之类的淫戏、指责艺员表演差池都是惯用手法。这类事情属于戏班演出过程中的联络事务和经济纠纷,主要是靠戏班主事(“坐舱”)和聘戏主会之间沟通协调。
现藏香港“中央”图书馆的太安公司《历年乡镇拖欠戏金账目》(共7页),涵盖了太安公司下辖戏班颂太平、咏太平、祝太平、一统太平、新纪元、花影女班,从1914年至1932年,在顺德、台山、增城、南海、新会、东莞、番禺、香山(中山)、花县、鹤山、新安、开平以及梧州等邑乡镇墟市演出时,各地主会历年所欠戏价72宗。从年份分布来看,1914年最少,仅为1项;1917、1918、1919三个年份最多,分别为11、9、10宗,其余年份2~5宗不等。就所欠金额情况来看,以台山为例,共13宗,总欠10 249元,其中多的欠4 400元,少的也有几十元,多数皆欠数百元不等。这种情况与东京大学藏1932年太安号整理的两张记账单(编号85800-75、85800-67)对于拖欠戏金账目记录完全吻合。以上数据表明当时墟镇演剧拖欠戏价极为普遍,已然成为戏班正常回收价银最大的障碍。这份欠账单开出的时间为1934年,也就是说最长的一笔颂太平班在增城张何沙头乡拖欠戏金20年,已成呆账死账。若将这些欠款视为坏账,减除这部分账单,原契约所订戏价总额将大打折扣。例如民国五年(1916)咏太平班到顺德马滘乡为天后元君酬神演出,合同戏价为3本400元,每本才130元,比当时墟镇演剧戏价均价300元要低一半,即便如此低的戏价,主会仍欠戏金188.4元。笔者猜测最终所欠戏价中可能包含附加价银,但普遍存在的拖欠戏价现象为戏班的正常经营带来不少烦恼和压力,也说明当时粤剧交易处于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戏班在交易过程中居于弱势地位。
讨要所拖欠戏价势必是太安公司及其所属戏班的重要工作,它需要粤剧八和会馆、吉庆公所协调行会组织的集体力量予以整肃和追讨。如上文所及1917年詠太平班遭到南海堤田乡被当地主会刁难后,戏班主事及时向公司总部及吉庆公所报告事情经过,寻求总会的声援。在吉庆公所签订的合同,当按时足数缴纳登记银(也称“义号银”、“叙号银”),即视为愿意接受行业组织的监督和帮助,故而主会“对一个戏班的违约实际上是对八和所属演艺界的违约,吉庆公所可以强制所属戏班实施禁演”。对于拖欠戏金,八和会馆和吉庆公所一般采取两种措施。一是以行会集体意志,在行会的订戏格式合同中,明确规定前欠不结、新戏不订的条款,迫使欠钱地方结清欠款。粤剧实力最好的三十六班都会在吉庆公所挂牌,各地主会要想聘请到最优之戏班,必须到公所买戏;正因如此,清末民初的吉庆公所对粤剧市场具有相当大的操控能力。有些主会拖欠戏金,但又想聘到上等粤班,于是“改换地名,瞒定别班”,吉庆公所发现后将这一问题专门写入合同:
凡该地拖欠戏金,必要该地方填还清楚,方得再到本总处买戏,倘或改换地方、瞒定别班,一经发觉,该班亦不到唱演,所交大小再定及保证费各项经费,一概无追,此合同视为故纸。
吉庆公所利用契约的“诚信原则”和法律效力,杜绝拖欠前欠戏金的地方主会“改换地方、瞒定别班”的不诚实行为,否则会承担所付定金“无追”的代价。
二是将拒不缴纳拖欠戏价的地方列入黑名单,发动所有粤剧班社在接戏之前,先催缴所欠戏金,否则不落乡开演新戏,且定银不退。在太安公司的经营文书中偶尔能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六年(1917)6月7日,东莞大享乡定到祝太平戏班合同的天头有吉庆公所的红印启事:“主会应允,如系在小响、梁下地段唱演,主会要填还旧欠国丰年班戏金。如不清还,本班不到唱演;所交定银及叙号经费银两一概不得退回,此合同视为故纸,毋得执拗。”既然是刻印好内容的红泥印章,则说明吉庆公所的这通启事并不仅仅是达知祝太平班,应该是告知所有粤剧班社凡到莞邑小响、梁下地段演出,都有责任和义务替国丰年班追缴当地主会欠银。整合所有粤剧班社的集体力量参与追缴拖欠戏金问题,充分显示出八和会馆等行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事实上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民国十四年(1925)4月颂太平班到台山潮境乡演出就收到吉庆公所的函件,要求该班为地方主会前欠顺太平班20元、富康年班25元“讨追代收”。这类的尾欠数额并不大,主会或存侥幸心理,以各种理由搪塞不予结清,当被八和会馆和吉庆公所列入前欠黑名单时,反而在新合同的议定中由于理亏而陷入被动。当然,先催交前欠、再落箱演戏的规则在现实中并未完全落实,行会的这条指导性意见对戏班而言不产生强制性作用,这也就可理解太平公司到歇业的1938年为何手中会有7页的戏价欠账明细了。
(三)各类不确定因素对戏金收取的影响
戏金正常兑付的前提是戏班能提供合乎合同规定和主会要求的戏曲产品,而当演出环节出现不确定因素时则会妨碍产品的“按期交付”。一般而言,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戏班不能按期演出;第二类是名角因故不能登台演出。以上两类突发情况对于戏班主事而言,都是难以预料和掌控的,但它们的不期而至会影响到戏金的足额回收。一般而言,戏班对于不确定因素的具体情况会分别对待和处置,首先在合同中会规定不可抗力因素所导致的演出误期的免责条款。如民国三年(1914)11月颂太平班与增邑张河沙乡签订的订戏合同中就写定:
倘班遇官府传唤及班意外之事,以及霎时散班,不能赴演,只将原定及义号银送回,并无加倍。
如班到步(埠),官绅禁演,及因一切意外,不能演唱,其戏金亦要如数找足,毋得少欠。
这两项条款的预设,虽然都因为强力作用而导致戏班不能履约,但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前者因为官府的禁演,对于卖戏与买戏方都无法改变,故而合约解除,退回定银,两不相欠;后者因为是主会无法摆平地方官绅的干预,属于对方能力欠缺,故要向戏班足数给付合同中所约定戏价。
影响合同演出的不可抗拒因素还有恶劣天气、自然灾害以及禁演政令等等,如民国十八年(1929)8月一统太平班到中山小杬酬神演出,且因“风雨阻滞,前订之日期取消”,改期再演,“戏价套数照旧”。改期很大程度会影响到主会的筹办工作,这次一统太平班的戏价未因此大打折扣,并将新达成的改期约定作为补充事项写入合同末尾空白处,说明戏班与主会之间的协商获得一致性。半年后一统太平班在四会沙富乡演出就没有这么幸运,因遇到新历3月13日孙总理忌辰,停演一套,被买戏方“减扣戏金347元”,但戏班主事给吉庆公所的信函中则明确表示要“作欠数计”。最终也不得而知一统太平班是否把这笔“欠账”讨要回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缺演,在是否按照合同兑现戏金问题上买戏与卖戏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不难发现,在合同中诸如“意外之事”、“官绅禁演”含义的理解与执行上,主会和戏班总是各执一词,难以统一。
可以说,地方势力的每一次禁演都会给戏班收取议定戏金带来麻烦,民国三年(1914)9月颂太平班到顺德龙山官田乡演出,“现本坊军队禁演”,只得“即往别处”,“日后定银,两不追”。由于戏场开赌为官府所禁,戏班往往在合同中就写明“倘戏场有违禁开赌情事,立即停演下箱,解舟别往,其戏金仍要照戏价找足。”这则启事是宣统三年(1911)3月1日吉庆公所订立,但一直以红泥印章的形式存续于民国初年每张粤剧订戏合同的天头。晚清在南海任知县的杜凤治就曾因为该县澳边乡演戏开赌,而强行“饬差督勇往拆台,并谕吉庆公所将戏班叫回”。官府强行拆台中止开赌的戏演,致使戏班在地方政权与乡绅势力的斗争中损失惨重,既扰乱了台档排期,也影响了戏金的正常回收。所以说在现实中,戏价的实际兑付远比我们在合同上看到的各种“假设”情况要复杂得多,这也是从民国三年(1914)继后近二十年间太安公司粤剧戏班合同条款不断变化更新,但每份合同中都会反复强调一旦出现意外因素影响正常演出予以免责的根本原因。
对于名角不能到演而影响戏曲观演效果,戏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能预料艺人缺演的,双方一般会在合同条款中写明不予减扣,主会不能再借口短减戏价;无法预料的艺人缺演,则需要临时与主会协商扣减戏金的具体数额。民国七年(1918)8月祝太平班到增邑久裕乡演戏,名小生细杞不能到演,只得“减戏价银七元正”;民国八年(1919)4月7日,咏太平班到四会白庙乡演出,班中花旦缺演一晚,“主会扣银一百二十大元”;民国十二年(1923)5月9日颂太平班在顺德吉佑乡演出,因为小生新奕不到场,戏班“肯愿扣戏金银四百大元,扣在行下情银八元”;民国十三年(1924)元月4日郑拂臣不到演,“减价银200元”。名角的缺场肯定会引起主会和观众的不满,买戏方和卖戏方相互博弈,最终会根据角儿的知名度以及缺席对整台戏演出效果的影响程度,扣减数元到数百元不等的戏金。对于主会因名角缺场而扣减戏价,戏班往往隐忍认同。就戏班内部管理来看,班东或坐舱除扣减缺场艺人的酬金外,会另按聘用合同中实施其他惩戒措施,如1935年太平戏院在雇佣谭兰卿的合约第八条写道:“开身之后,无论何处聘请,必须依期到演,毋得借口乡居僻壤,地方不靖,或受种种摆弄,推不到演”;即便“遇意外事或身体有恙”,也要提前征得班东或坐舱允肯,并就此规定了一系列赔偿和惩处措施。在长期流动于圩镇的戏班与误期伶人之间,吉庆公所扮演了居中调停的角色,我们看到民国十年(1921)以后的行会合同中都明确写道:“凡班中各伴,间有适遇别故不能出台演唱,只许在其人身上一年之工银多少,按日伸除,不得藉端多扣,至伤和气”。吉庆公所在订戏合同中特意加入这则格式条款,看似是行业总会以此申告戏班和艺员各守本分,关注戏班和谐平稳地运营,实不妨视为是对名角的特别爱护,毕竟多数情况下缺演的是那些同时要赶场子的名角,而不少名角同时还兼任行业总会的管理职务。
据上可见,民间戏班从订立合同到演出完成、尾款结清,才意味着一次商业活动的圆满完成。然而现实中,完成一次商业演出活动,隐含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影响戏班的履约。这些风险,一部分可以根据从业经验提前评估,所以吉庆公所合同中会出现很多“假设”事件规避条款,但有相当一部分风险完全无法预计,它们的不期而遇会给戏价银的兑付带来不利。可以说,民国时期戏价银的收取,是戏班(卖戏公司)与中介组织、主会、地方各类势力之间复杂博弈和角力的过程。角力的结果,直接表现为戏价银收取的额度、速度和难易程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就不难理解吉庆公所拟定的格式合同中,为什么会在多种可能性“预设”之外增列诸项附加条款,为什么会协定很多戏班的权益,却很少见到戏班违约赔偿的条款。因为对于下乡演出的戏班和伶人而言,他们是弱势群体。
三、戏银的各方博弈与再分配
通常来讲,经济利益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多重利益链条;同样,戏金收入的背后也牵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人群。当戏曲作为商品进入演出市场,戏班经营活动的周围就开始出现相关利益组织、团体和人群活跃的身影。这些人包括三类:一是商品的购买者,即聘戏的主会;二是中介组织,如吉庆公所、藉福公所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场信息介绍人;三是地方权力机构,如警察局、乡公所,甚至是地方军事力量。这三类人群围绕戏银,与戏班(卖戏公司)展开博弈,对价银的正常收取制造各种障碍,或直接利用特权强行参与价银的再分配。
首先是戏班(卖戏公司)与中介组织围绕戏银的博弈。大约成立于咸丰七年(1858)的吉庆公所,其渊源可追溯至乾隆年间的外江梨园会馆。梨园会馆为将戏曲买卖都集中在行会手中,规定提供戏曲商品的戏班“不许私自上门揽戏”,并且“各班招牌俱入会馆”,从而导致聘戏的主会只能到梨园会馆买戏,“总以先后为主,价钱高者可做”。梨园会馆戏班挂牌、聘戏主会直接上会馆洽谈订戏的传统得到吉庆公所的承继,吉庆公所掌控了广府周边地区相当大份额的定戏话语权,成为“珠江三角洲粤剧市场的买卖交易平台,是整个‘红船机制’的营运核心”。掌控买卖市场的吉庆公所,利用其管理权限开始向订戏双方收取合同登记银等费用,以便在粤剧交易中获利。
粤剧行业组织吉庆公所向签订聘戏合同的戏班和主会收取的中介费、管理费,俗称义号登记银。由于清末民初珠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订戏交易掌控在吉庆公所手中,公所按合同份数收取登记银。“初期,每张合约,由买戏的各乡主会及班主各付二三两银子,到了20年代,改为每张合约,主会及班主共同支付28元左右。”据太安公司下属戏班签订的合同来看,民国初年吉庆公所根据合同签约情况,每本戏提取1元的登记银。一般而言,粤剧演出的一台戏是三日四晚,演出3~4本戏,这样的话一份合同,吉庆公所收取的登记银也就是几元钱。由于广府地区活跃着数百戏班,每年签约数相当可观,吉庆公所借此收取的登记银总数自是惊人。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前后,吉庆公所为聚敛更多财富,将登记银改为合同保证费:
昨年敝会同人大会议决,每套戏现收主会合同保证费银贰元,现收班柬班号费四毫。无论内结外结,一律照收。但在江门藉福馆,写立合同者,除该馆原有担定费外,亦每套照收主会合同保证费贰元,照收班柬班号费四毫,以贴划一而符议案。 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吉庆介绍总处谨启
合同保证费收取标准发生改变,由原来按“本”改为按“套”收取。粤俗,日场演出的为本戏,而套戏则是根据日场、夜场各个演出单位时间计算,包括例戏、出头和戏尾。一台三日四晚的戏,按“本”算只有3或4本,但按“套”算则有7套。这样,吉庆公所征收的合同保证费数额就从原来的几元上升为十数元甚至二三十元不等。吉庆公所利用自身行会组织的权威性敛财,导致戏班的收入被强行切分和蚕食。
吉庆公所对戏价银的盘剥,更大程度体现在占取和侵吞合同定银。据粤剧老艺人刘国兴介绍,民国时期主会在吉庆公所签订合同后,都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订金,吉庆公所代班方收取的定金一般不得少于五十元。这笔钱被吉庆公所掌握在手中,只有当戏班需款使用时,才向他们支定(俗称“拆定”),然手续繁琐,支取不易。由于每年签订合同时主会缴纳的定金数额巨大,吉庆公所利用这笔款项投资金融业获得不菲的利息,时间一长就视为私产甚至挪作他用。戏班为求生存往往多不敢就这笔钱提出异议,客观上助长了吉庆公所对戏价银的吞噬。
进入民国后,民族资本涌入粤剧演出市场,先后有宝昌、怡和、华昌、耀兴、兴和、宝兴、宏信、太安、宜安、联和、怡顺、一乐、兴利、汉昌等数家戏班公司成立。戏班公司按照公司运作模式积极对接市场,多途径占据粤剧演出市场份额,逐渐消解吉庆公所对戏班、戏价银的掌控力。以太安号为例,为最便捷获取珠三角地区粤剧市场的最新买卖信息,1914年源杏翘(1865—1935)在靠近吉庆公所的广州黄沙海旁街开办太安公司(即太安号),这是活跃于20世纪10-30年代初的一家粤剧“戏班公司”(又称“卖戏公司”)。太安公司不仅派专门的接戏先生常驻吉庆公所卖戏,而且主动出动上门找主会接戏,“吉庆公所的职权逐渐为他们所取代,这些公司还发展了吉庆公所前所未有的业务活动。它们接到所有的主会的上演合约之后,纵观全年上演的‘台期’和地点,如发现某些地区没有订戏班前往演出,就随即派出卖戏人员前往这些地方上门卖戏,这对戏班的营业是要有利得多的。因此,各个戏班就逐渐由依靠吉庆公所而转为依附公司而生存了”。1932年太安号下辖戏班永寿班主事高远文给公司老板源詹勋的信函中讲到墟镇戏曲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四邑地区同时有觉先声、定乾坤、人寿年、碧云天及永寿年五班活动,“现四邑内地连本班共有五名班,恐有僧多粥小之叹,但视乎卖戏者之手腕如何”。依附于卖戏公司的卖戏者究竟使用了哪些“手腕”,借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台期订单,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戏班积极笼络中介人,获得更及时准确的演剧需求信息却是必不可少的。
公司主动上门卖戏,很多时候需要中介人提供交易信息,这样就存在中介人对戏价银的盘剥,即在私底下收取“在行银”。在行银作为各个戏馆、戏班之间相互介绍生意而收取对方的介绍费,逐步演化为戏班在总戏价中支出的一个重要科目。戏馆成员间互相介绍生意并索要“在行银”,大约是在1919年前后从四会的“藉福馆”开始,后来蔓延至吉庆公所。“在行银”逐步在行业内部被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粤剧同业组织吉庆公所、藉福公所对演出市场的掌控能力有所减弱,以往介绍戏路、提供服务的戏馆悄然演变为盈利的中介组织。太安公司下辖戏班的订戏合同和往来文书记录了一些中介收取介绍费的情况,见下表。

时间戏班演出地戏价银在行下情银1919年4月7日咏太平班四会白庙乡1050元16元1920年9月11日颂太平班番禺石溪乡990元12元1922年11月28日咏太平班顺德古朗乡1580元14元1923年5月9日颂太平班顺德吉佑乡1600元8元1924年1月4日颂太平班顺德水籐岑屯乡1980元14元1929年4月8日新纪元班四会白蚬步乡2400元17元1929年4月21日新纪元班四会八堡乡2300元11元1929年5月12日新纪元班四会外海乡1400元10元1930年6月17日一统太平班广州太平戏院2640元14元
在这张表格中,在行下情银(介绍费)支出基本维持在10元左右,未完全按照戏价的高低而作相应浮动,也难以看出是按比例抽成,但戏价高的在行银也确实会提取多一些。现存的合同及相关文书还显示,1919年前由广州吉庆公所认证的订戏合同,基本上不存在支付“在行银”的情况,但此后随着吉庆公所凝聚力和掌控力的下降,戏班各显神通广找门路接戏,向介绍人支付“在行银”已成惯例。吃“回扣”的主会代表和拿“在行银”的介绍人,他们以掮客的身份参与到戏价银的再分配环节,不仅加重了戏班的负担,更是扰乱了民间戏班演出市场和生态环境;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存在正是卖戏公司破除吉庆公所、藉福公所等中介组织对粤剧交易市场垄断地位的产物。
即便如此,在戏班公司和吉庆公所对于戏价银分取的博弈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合同登记银的保留和维持。从现存1914年至1934年太安号订戏合同看,太安公司即便主动上门订得主会的演出台期,但仍然和主会到吉庆公所签订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合同登记银或保证费。这一举动显示,吉庆公所作为行业组织仍有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但戏班公司对定银上缴的抵制,又可视为是公司和公所二者在戏价银分割上存在相互妥协、相互利用的博弈状态。第二个问题是,戏班公司制的出现消解了吉庆公所的权威性存在,但时过境迁,乡村演剧市场的凋敝也让戏班公司退缩至省港城市之中。诚如上文所述,民国初年,公司制被引入粤剧演出市场,很大程度将有限的市场资源垄断到少数如宝昌、怡和、华昌、太安等公司手中,促进了公司、戏班、戏院(演出地)的一体化经营;然而大约在1924年至1934年之间的十年,乡村演剧市场急剧凋零萧条,对戏班公司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墟镇粤剧市场衰落的原因错综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端:一是由于“近日四乡兵燹频频,乡绅鲜作演戏之举”,改变了原来“惟落乡居多”的局面。从伶人角度而言,老艺人刘国兴回忆,“民国八年起,各乡河道已极不靖,艺人屡遭洗劫”,“班中子弟,以畏匪故,多不肯落乡开演”。二是省府对赌戏的禁绝。以戏聚众开赌,以赌抽资助戏,形成了乡村演剧市场的独特风貌。政府对乡村赌博戏的禁令是截断戏价的一个重要来源,乡村演剧凋敝与此不无关系。三是世界经济的整体下行,“农村破产,醮坛景色大逊从前”,影响到墟镇演出市场。容世诚先生甚至注意到因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北美洲华侨向国内汇款急剧下跌的情况,以此证明农村经济凋敝给珠三角地区墟镇演剧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约在1934年(岁次甲戌)农历七月到八月之间,香港太平戏院院主源杏翘接到来自广州太安公司“侄孙”源授湖的三份书函,报告太安号已经三年未有起班演戏,业务停顿之余,只能依赖乡镇过往欠下的旧戏金,勉强维持日常开支,建议及早关闭公司,随后太安公司也黯然退出了珠三角地区粤剧墟镇演出市场。如果说1914年太安公司的成立是对吉庆公所等中介行会组织掌控戏班和盘剥价银的反制,那么二十年后1934年太安公司淡出珠三角粤剧演剧市场,则不如说是另一种话语权的没落。戏曲市场总是随时势而动,任何经营方式都只能适应某一时段的市场需求,吉庆公所和太安公司的没落就是最好的注脚。
各类苛捐杂税对价银的榨取,也是戏金流失的重要原因。戏班尽管开支巨大,但每年戏价的账面数目也极为可观,自然成为当局课税的重点对象。戏班面对的诸种捐税,大头是戏捐。民国时期各地戏捐名目繁杂,征收的办法各异。在城市多根据戏园戏院营业规模、票房收入进行征收;而对于墟镇戏班,则多按演出台数或按戏价多寡分为等次予以抽取。在广东地区,县邑墟镇多是酬神赛会演剧,戏班的价银一般不会被主会勒捐,但当遇到党团及政府部门所举办的演出活动,很有可能会被索捐。合同显示,民国十五年(1926)8月25日颂太平班参加台山城国民党党日庆祝获得,“自愿”地“捐助党部银一百元整,此款在戏金扣除”。民国十九年(1930)2月一统太平班到四会沙富乡演出,除缴纳4元警费外,还上交灯捐费(戒烟专款)10元;继后一统太平班在台山新昌埠为福田医院开幕演出,“被”助捐250元。助捐,能让戏班赢取募捐活动主办方的好感,为以后获得较多的演出机会奠定基础,但事实上每次助捐对于戏班而言就是戏价“被”强行蚕食的厄运。
警费是戏班需要缴纳的另一种杂税。警局名义上要对演剧过程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若因为对戏班演出服务而收取一定数额的警费完全是正当的,但事实上是只收取而不作为,警费也成为警局创收的上好来源。东京大学和香港文化博物馆藏有多张太安公司下辖戏班向南海县警察长(财政局)、番禺县兼警察长申请演戏执照的批准文书,每套戏缴纳警费2元5毫,一般是七套戏缴费17元5毫。除戏捐、警费,还有学捐、保护费、清乡团练军费等各项,只要是地方强权机构和势力都可以向戏班张口,参与戏价银的瓜分。
关于这些杂税,民国九年(1920)吉庆公所的订戏合同的天头上都有红印启事:“贵客光顾,无论戏院乡镇就地戏捐、学费、警费、戏船湾泊保护费、清乡团练军队各费,一律归买戏人支理,概与戏班无涉。先此声明,以免后论。”那么这些保护费、警费是否真如订戏合同上所写明“一律归买戏人支理,概与戏班无涉”呢?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地方主会并不乐意缴纳这笔款项,戏班为求自保,只能代交;缴纳后再找主会追讨,是否能成功,难以预料。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8日,永寿年班到开平大岗乡演出,合同天头上就注明交保护费五元,警费二元。向到乡戏班收取保护费的都是当地黑恶势力,一旦不能及时缴纳费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戏班往来文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本班前廿二日二点半钟,经船至大江四处,埗头阻止不得湾泊,迫得将船退开。与主会谈判求情,无效。候至夜深,主会着班放出公益上搭火车,一点半钟女步上馆,开演正本。……另强入车费银55.8元。
即便在订戏合同中都有规定聘戏主会负责戏班人员安全和顺利上馆“落箱”,但当地黑恶势力不让戏班红船靠岸的情形也并不鲜见。这通文书中,戏班收到阻扰不能泊船上岸,反而要舍近绕道,转乘火车,又被“强入车费银”数十元。戏班不能顺利上岸演出,按照合同条款是主会的责任,但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戏班,往往忍辱吞声,难以维权。再说,因不能顺利上馆“落箱”导致唱演的取消,则会给戏班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即便是延期也会与紧接的台期产生冲突,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戏班不愿见到的。所以,当遇到主会不愿缴纳保护费的情况,戏班也只好代交了事。
综上所论,民国时期太安公司下辖戏班订戏合同及其周边经营文书,完整呈现出当时戏价生成的原始过程和戏价在实际收取、兑付环节中所遇到的不利因素及其规避的措施、效果等情况。透过这批史料还看到在粤剧戏价银的周围隐藏着纷杂的利益群体,它们以戏班(或卖戏公司)为中心,生发出戏班与行业组织吉庆公所(藉福公所)、戏班与戏路介绍人、戏班与政府权力部门,甚至戏班与盗匪、军队、士绅等人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层次利益关系。吉庆公所订戏契约及其周边文书反映出民国时期粤剧戏价生成、兑付、收取、再分配的多维面相,对探视民国粤剧戏班(卖戏公司)的生存状态和岭南墟镇演剧市场的真实生态环境意义重大,值得作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6-10-22
陈志勇(1975—),男,湖北嘉鱼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加坡藏“外江戏”剧本的搜集与研究》(批准号:14AZW009); 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批准号:16wkjc12)。
K258
A
1000-5072(2017)06-006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