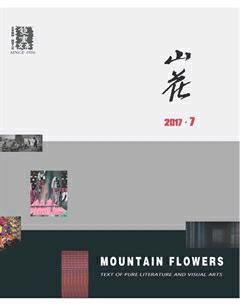从社会档案到社会方案
鲍栋
在《淹没》中,李一凡克制着自己的造型冲动,在拍摄中只有记录而没有介入,作者几乎是隐形的,在后期剪辑中也是如此,最终观众在成片中看到的重庆奉节永安镇在三峡工程移民搬迁中发生的事情,远远没有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富有揭露感及爆料性。对于李一凡来说,他的工作首先是据实记录,而不是摆出“地下”、“独立”的姿态。纪录片的批判力量源于客体的真实而不是导演的主观倾向,因此据实记录的《淹没》肯定不同于主流影像中欢天喜地搬新家的移民安置故事,它注定具有一种异在的批判力。李一凡不愿意把现实处理成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他要尊重现实的原质本身,这种态度最终确立了他档案性质的工作方式。
在《乡村档案》中,不仅名称,就连影片本身也具有档案的体例,它以农历节气为单元交替呈现一个中国内地乡村的生产及公共生活场景,列表似地呈现着当下乡村中的日常生活、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淹没》相比,《乡村档案》有着明显的抽样调查性,因而更需要全景式的记录,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当下乡村现实的档案标本。
在李一凡的纪录片中,影像显然要高于任何話语,他的镜头并没有试图形成一个个明确的话语表达序列,相反,它们大多数只能被注视,而不能被解读。这样一种影像语言是非表达性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影像获得了自足的地位。但在纪录片中,这种影像的本体性直指见证了现实的不透明性的,而不透明的现实才真实。
像李一凡这样的被称为“89一代”的人一贯有着强烈的知识份子热情,但在纪录片工作中,他一直有意压制着这种既是动力也是局限的人文热情,这种压制的用意在于——用他自己的话说——“力图对那种以猎奇为目的的解读方式,以简单的文本解构显摆精英阶层的高明的解读方式进行反拨和批判”。在他那里,纪录片必须要遵循现实第一性的原则,这样才能获得社会标本,即档案的实质。
李一凡的“档案”工作出发点可以概括为:借助事物自身的力量去批判既定的诸种话语,在这个层面上,他其他类型的作品,包括图片、影像 、装置和行为艺术,与他的纪录片是一致的。但如果说他的纪录片更多的是呈现现象的话,那么他的当代艺术实践则更集中地展现了对现象中所隐含问题的发现、思考,以及思考的方向和路径。简单地说,纪录片属于调查,而后者属于研究。
他思考的首要问题是中国主流社会与底层社会(农民、民工、都市贫民)之间的裂缝与这种裂缝可能引发的危险,以及如何弥合这一裂缝——通过他的纪录片,我们已经对这一巨大的社会裂缝感同身受。
首先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担忧,他曾提到他自己像一个既得利益者在危险来临时向其他既得利益者发出信号,他说,“当然我更希望我的信号能避免一场鱼死网破的危险,社会能尽早地建立起码的公平”,而在一个潜藏的层面上,令他恐惧的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关怀姿态与底层现实之间已然形成的错位,因此底层可能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反而会强化既定的社会区隔,甚至“底层”可能只是一种符号秩序内部的产物,其功能恰恰是用来压抑并遗忘所谓的底层现实,把它彻底排除到意识之外。对此,李一凡亦有着自己的判断——“我渐渐明白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社会把牺牲底层社会的利益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理所当然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