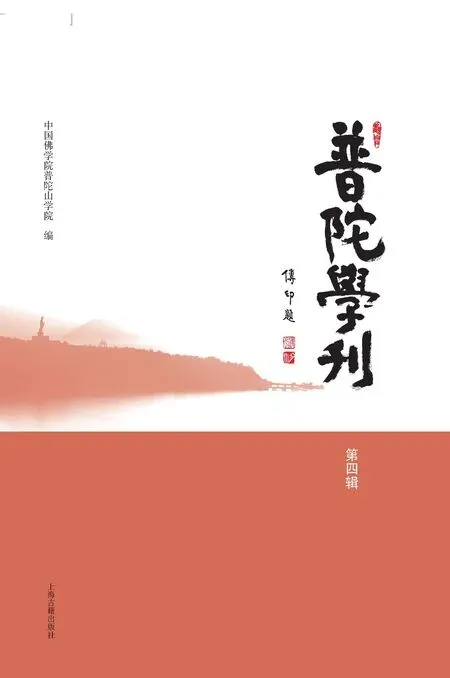近代韩国佛教的形而上学受容与真如缘起论的作用
金永晋
(韩国东国大学庆州校区佛教系)
一、 西方哲学的传入与佛教哲学的出现
“哲学”一词是对于“Philosophy”的汉文翻译,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在他的《百一新论》中首先使用的。哲学概念虽然基本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逐渐与像佛教这样的东亚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了一起。这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历史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日本明治思想史专家船山信一在《明治哲学史研究》中,将明治哲学史分为如下五个时期。*船山信一:《明治哲学史研究》,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1959,第3—34页。第一期,实证主义的移植;第二期,观念论与唯物论的分化;第三期,日本式观念论的确立;第四期,哲学启蒙家;第五期,日本式观念论的大成。属于第一期的代表人物是西周与津田真道,他们主要致力于将密尔的功利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介绍和传播到了日本。而且这二人还在日本倡导了启蒙主义,即他们试图用英法哲学来启蒙日本。在第二时期当中,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是井上圆了,他主要是接受了德国观念论,并以此来对抗实证主义和唯物论,并认为这种对抗是日本思想界对于西方化的一种反省。
井上圆了的哲学在中国与韩国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梁启超就明显受到了他的思想影响。梁启超曾访问过井上圆了设立的哲学馆,并在那里查阅了“四圣祠典”。井上圆了推崇释迦、孔子、苏格拉底、康德等四名圣人,因此而设立了四圣祠典。梁启超在访问哲学馆的时候,首次接触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之后他以《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为标题,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关于康德的内容。而梁启超在写作的时候,还参考了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翻译的《理学沿革史》。梁启超翻译了《理学沿革史》中关于康德部分的内容,并且还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中江兆民翻译的《理学沿革史》,是法国人Alfred Jules Émile Fouillée(1838—1912)所写的L’Hlstrire de la philosophie(1875)。详细内容请参照井田进也:《〈理学沿革史〉解题》,《中江兆民全集》6,东京,岩波书店,1984。而在这里梁启超使用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唯识学理论。

1910年代的后半叶,韩国佛教界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更加深入了,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并接受近代教育的僧人们开始主导韩国佛教界。例如,在1918年出版的《朝鲜佛教总报》第9号、第12号、第13号就像是“佛教哲学”特辑,其中连篇登载了《佛教伦理学》(李智光)、《佛教心理学》(李混性)、《佛教与哲学》(李钟天)等论文。*李混性与李钟天曾留学于日本东京的曹洞宗大学(今驹泽大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的话,那就是缺少了《佛教逻辑学》方面的论文。李钟天在他的文章中说道:“广义的哲学应该是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的总称。”翌年,即1919年的时候金喆宇(1888—?)写作了《佛教哲学概论》,书中介绍了哲学的定义。
柏拉图认为,哲学的任务是研究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所谓哲学的心就是热爱永恒不变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哲学是研究宇宙的太初及其原因的学问,又是研究本体的学问。康德则认为,哲学是出于人类理性的需要而阐明一切知识之关系的学问。黑格尔则认为,哲学一般是指关于对象的思维,又是研究绝对的学问。*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6号,第36页。[以下所引韩国近代佛教杂志均来自《韩国近现代佛教资料全集》(首尔,民族社,1996)]
金喆宇所说的哲学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近代佛教哲学的发展方向可能就是相当于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所定义的哲学内涵。因为这两人均认为,哲学就是思考宇宙的根源或是思维绝对的东西。试图建构近代佛教哲学的人们认为,如果佛教想要成为一门哲学,那么上述的问题意识与志向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佛教借用的是欧洲式的问题意识,而且实际上问题本身也是进口的。当然也有拒绝这种问题意识的情况,近代中国佛教思想家欧阳竟无(1871—1943),于1921年10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研究会上做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为主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明了佛教之所以不是哲学的理由:“哲学家唯一之要求,在求真理,所谓真理者,执定必有一个什么东西,为一切事物之究竟本质,及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者是也。”*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6页。欧阳竟无所说的哲学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而这也是日本和韩国所设想的佛教哲学的方向。*在近代佛教的哲学化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了真理,因而欧阳竟无似乎发现了某种别的意思。所以他意味深长地说道:“真如决不以一真理范围一切事物,亦不以众多事物奔赴于一真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同上书,第7页。他认为佛教肯定不是哲学,而他站在唯识学的立场上批判《大乘起信论》的真如概念,可能也是源于这种认识。欧阳竟无认为佛教不可能谈论“所从来”,即佛教不可能谈论所谓的根本原因。但是,近代的佛教哲学的发展方向则与此完全相反。
金喆宇在《佛教哲学概论》中这样说道:“哲学阐明的是宇宙的根本原因,而且以满足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为其核心。”*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7号,第28页。而且,他认为至少在佛教当中哲学与宗教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哲学的思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能认知宇宙万物的认识原理,而且还可以知晓宇宙万物的真性、实相、作用及其显现的过程等,并且还可以知晓让这种哲理自动进行有意义的活动的道理”。*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5号,第37页。即,通过对宇宙哲理的把握,我们可以谋求有价值的生活。而这样的思考方式其实并不需要分清楚到底是属于宗教还是属于哲学。
那么,这样的哲学该怎么做呢?如前所述,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片面的哲学是无法论及宇宙真理的。因此,这样的学问不可能成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需要的是更加包容、更加根源的东西。李钟天认为,佛教哲学是“狭义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是一种纯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学问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对其进行了体系化,并且他将形而上学定义为研究存在之第一原理的学问。所以,一般也将形而上学称之为第一哲学。井上圆了在《哲学一夕话》(1885)序文中则是这样定义的:“纯正哲学是哲学当中的‘纯理’的学问,是研究真理的原则与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学问。”*井上圆了:《哲学一夕话》,东洋大学创立100周年纪念论文编纂委员会编,《井上圆了选集》第1卷,(东京,东洋大学,1987)第34页。在这里,“纯理”指的是最纯正的真理。
白性郁曾经在德国留学,他于1924年的时候发表了《佛教纯全哲学》,内容是他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提要。他在此文中说道,由于西方人将佛教的阿毗达磨翻译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a),而他又将其翻译为了“纯全哲学”。他认为“佛教纯全哲学是阐明全宇宙真理的学问”(《佛教》第7号,24),即对他而言佛教哲学还担负着探寻“宇宙真理”的任务。
如果说佛教哲学是在探寻宇宙的真理,那么就没有必要与宗教进行争论,最需要与其争论的反而应该是科学。而且随着佛教的哲学化,实际上与佛教哲学进行竞争的恰恰也是科学。且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不断地在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主张相较而言形而上学更加优越。例如,在近代日本将物理学这样的纯粹科学翻译为了“理学”,从此也可以看出科学不得不与哲学进行一番竞争。甚至philosophy曾经也一度翻译为“理”。井上圆了在《纯正哲学讲义》(1891)中,将所有的学问区分为“理学[有形质(物质)的‘学’]与哲学(无形质的‘学’)”。*井上圆了:《纯正哲学讲义》,《井上圆了选集》第1卷,第246页。即,将学问分为了科学与哲学。那么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应该是研究的领域不同。
金喆宇在《佛教哲学概论》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大体上科学的原则具有相对价值,但是不具有绝对价值。但是,哲学则有确定的原理,进而也具有绝对的价值。即,科学研究的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哲学研究的是全部的宇宙现象。(中略)正因如此,将哲学称之为研究宇宙万物之绝对根源的学问”。*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6号,第39页。如果按照这种看法,那么研究宇宙的本质及绝对原理的就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井上圆了在《纯正哲学讲义》中将哲学分为“有象哲学”与“无象哲学”。同时又将哲学分为“纯正哲学”与“实验哲学”。纯正哲学研究的是物·心·理的本体,而实验哲学研究的则是其形象,其中实验哲学指的是实证主义。李钟天在《佛教与哲学》当中则照搬了这样的议论方式。因为纯正哲学探求的是事物的本质或者是宇宙的本质,所以对构成世界的根本原质具有极大的兴趣。根据是否有“本体”,他将哲学分为“有元论”与“无元论”。其中将“无元论”定义为“虚无论”,而将“有元论”再细分为“一元论”与“多元论”(二元、三元、多元)。而且将“一元论”进一步细分为了唯物论、唯心论与唯理论。井上圆了在《哲学要领后编》中,将一元论分为“相对的一元论”与“绝对的一元论”,并认为唯物论·唯心论属于相对的一元论,而唯神论·唯理论则属于绝对的一元论。*井上圆了:《哲学要领后编》,《井上圆了选集》第1卷,第151页。
在近代谈论佛教哲学的时候,之所以大部分的议论都陷入到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当中,可能也是由于上述这样的思想脉络所引起的。李智光在《佛教伦理学》*李智光:《佛教伦理学》,《朝鲜佛教总报》第9号,第23页。当中,将佛教的心理分为“物心二元论”与“唯心一元论”。俱舍学是主观的物心一元论,唯识学是相对的唯心一元论,华严学与天台学则是绝对的唯心一元论。而李钟天也采用了相类似的分类方法,他将佛教分为了“宗教门”与“哲学门”。而在“哲学门”中,他将俱舍学、法相学与天台学一一对应于小乘教、权大乘教与实大乘教,并且又各自命名为法体哲学、识体哲学与理体哲学。可以说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教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探究世界根源的西方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之后所产生的格义佛教。
二、 对世界的形而上学认识与对绝对真理的追求
(一) 一种陌生的形式“现象与实在”
形而上学在韩国被称之为“纯正哲学”,那么其基本的思考方式是什么呢?其模式很可能就是“现象与实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Metaphsica)的开头部分写道“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如果说我们知道了某个事物(什么),那么这与“为什么存在、是什么”是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金珍成(音)译注(解说):《形而上学》,首尔,EJB,2007,第17页。他将形而上学命名为“第一哲学”,并将其定义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按其本性来说属于存在的属性的学问”。李钟天则认为,因为佛教“解释心的各种现象,进而试图解释其本体”,所以是一种形而上学。*李钟天:《佛教与哲学》,《朝鲜佛教总报》第9号,第29—30页。金喆宇在《佛教哲学概论》第二篇的第一章《宇宙论》中,是这样论述的。
大抵宇宙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现象界是怎么产生的,而且还需要解释实在的镜像是什么,而且还需要解释现象与实在的关系。换句话说,需要解释的是宇宙的一切存在是怎么产生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本体即实在又是什么?如果说现象是由“实在”所显现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在说明宇宙论的时候,主要是从现象论、实在论及现象与实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7号,第32—33页。
金喆宇所说的宇宙论其实相当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中国哲学史》(1930年)中将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及知识论。然后又将宇宙论分为了两个部分。“宇宙论可有两部:一、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二、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第2—3页。而在1910年代与1920年代的时候,在韩国佛教界所说的佛教哲学基本都是从形而上学的主题出发的。1924年7月登载于《佛教》创刊号的《佛教研究》当中,也是以“为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开始的。香山外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就不能说是自己认识自己,因此这种人一辈子只是在吃饭、睡觉而已,就像行尸走肉一样”。*香山外人:《佛教研究》,《佛教》第1号,第27页。
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说的话就是“抛弃了知识,那么就是抛弃了作为‘人’的资格”,那么怎么将这个与佛教结合在一起呢?其中的关键就是“实相论”与“缘起论”。“实相论解释了‘是什么’的问题,而缘起论解释的是‘为什么’的问题”。*香山外人:《佛教研究》,《佛教》第1号,第28页。这种模式在现今的佛教界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金东华的《佛教学概论》(1947年脱稿,1954年刊行)是韩国解放之后最初的也是最为大众化的佛教学概论方面的书籍,而此书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金东华认为实相论、缘起论、达观论各自对应于本体论、现象论、认识论。在佛教哲学当中,使用了各种缘起论解释了佛教,例如业感缘起论、赖耶缘起论、真如缘起论等等。从“现象与实在”的模式来看的话,前面的这些“缘起论”各自将业、阿赖耶识和真如看作是现象的实在。
在近代佛教界当中,则使用了“万法”与“真如”及“事”与“理”的概念,替代了“现象与实在”这样的西方哲学术语。李钟天认为“哲学的问题就是从现象出发研究其本体,也可以说是认识‘万法’与‘真如’的关系,而且其动机就在于自然界当中。其中,真如的‘真’是真实、‘如’是如常的意思,即指的是本体的状态。”*李钟天:《佛教与哲学》,《朝鲜佛教总报》第13号,第59页。但是,在佛教哲学当中之所以重视这个真如概念,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中所包含的双重含义。《大乘起信论》中说道,真如具有“随缘”与“不变”的两面性。根据这样的定义真如是一种不变的实在,但是根据不同的状况又可以产生各种现象。李钟天认为,“‘事’是现象,所以是有限的、相对的、有差别的世界;而‘理’是本体,所以是无限的、绝对的、平等的”。*同上书,第60页。即,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当中仅仅存在着现象与本体(实在)两种领域。
在近代佛教界当中,对于“现象与实在”并没有使用柏拉图的二元论式的解释方式,而是更倾向于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用明治佛教哲学的概念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现象即实在论”。在这个时期,人们在研究“现象与实在”或者是“万法与真如”关系的时候,一般强调的是“现象即实在”或“万法即真如”。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当中是明确区分现象与实在的,但是在近代研究“现象与实在”的问题时,则不像柏拉图那样在现象的背后另设一个观念(理念)。即,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现象即实在”。船山信一在说明“现象即实在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在明治时期的唯心论·观念论当中,主张的并不是与“客观”对立的“主观”或是与“现实”对立的“理想”,而是认为“主观”即是“客观”、“理想”即是“现实”。所以“客观”之外并不存在“主观”,“现实”之外也不存在“理想”。*船山信一,《明治哲学史研究》,第77页。
井上圆了在《哲学要领》中认为,“佛教当中的‘万法即真如、真如即万法’与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即无常、无常即现象’的观点是相一致的。而《起信论》中所说的‘一心’分为‘二门’的观点,又与谢林所提出的‘绝对’分为‘相对’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里‘真如’与斯宾诺莎的本质、谢林的绝对及黑格尔的理想(精神)是比较相似的”。*井上圆了:《哲学要领 前编》,同上书,第104页。末木文美士认为,“井上圆了将‘真如论’与斯宾诺莎、谢林及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而井上圆了对于佛教的解释则受到了黑格尔的很大的影响”。*末木文美士:《明治思想史论》,(东京,TRANSView,2004),第48页。可能他是在井上圆了的佛教理论当中看到了某种“绝对性”的概念。而这种将“绝对性”与佛教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的倾向也传入到了韩国佛教界。金喆宇在阐明佛教是什么样的宗教的时候,提出了“万有神教”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与“现象即实在论”是相关联的。
佛教应该属于哪一类呢?佛教应该属于万有神教。宇宙万有是现象,而“实在”是真如、实相、一如。而“现象即实在论”是佛教的极致,不发达的宗教会严格区分“实在”与“现象”,所以在其他宗教当中无法说明“实在”与人类的关系。因此佛教作为一种进步的“文明宗教”,很好地说明了“现象”与“实在”的“合一”,并且提倡“现象即实在论”认为一切万物都具备有“真如”的“实在”。因此真如是“实在”,而宇宙万物是“现象”。*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6号,第53页。
如果在佛教人士看来“万有神教”这个名称可能不是很舒服,而金喆宇则认为如果将佛教看作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它就属于“万有神教”,而且金喆宇好像一点都不反感使用这样的用语。这里的“神”比较类似于本质或是根源。*井上圆了在《哲学一夕话》的第二篇《神の本體を論ず》当中,考察“物心”的起源之时假设了一个“原体”,他将这个称之为“神”。金喆宇所使用的“万有神教”概念可以说是一种泛神论,而泛神论一般是指“神的实在”内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当中。如果与佛教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就是,真如作为一种‘实在’内在于千差万别的万物之中,因此超越了现象的差别,所以作为本质的真如是无差别的、绝对平等的。在1927年的时候,金敬注在《华严哲学的内容》当中使用了“现象与实在”的结构模式说明了华严学的“四法界说”。*金敬注:《华严哲学的内容》,《佛教》第40号,第4页。即,使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说明“理”与“事”。接着他将华严哲学定义为了一种唯心论(观念论),并将西方哲学史当中的唯心论分为了客观唯心论、主观唯心论和先验唯心论。而且,他认为华严哲学的本质就是指向绝对唯心论。
(二) 真理主观与真理客观的宇宙论
在研究1920年代的佛教哲学化过程时,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是白性郁(1897—1981)。他曾在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学习过哲学,并于1924年在《佛教》杂志上连载了《佛教纯全哲学》。他说“佛教纯全哲学”用梵语来说的话就是“阿毗达磨”。白性郁在写作时使用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这样的比较传统的文章格式。他在序言中说道,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均没有关于“佛教哲学的主观”方面的著作,所以他才会以“佛教纯全哲学”为主题写了学位论文。*白性郁(白峻):《佛教纯全哲学》,《佛教》第7号,第19页。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他所提到的“佛教哲学的主观”这句话,从现今的语言习惯来说,这句话是比较奇怪的一种表现形式。
“主观”与“客观”是指我们在认识某种事物时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主观”自然是具备感官而进行认识行为的主体,那么在“佛教哲学的主观”当中,其主体指的是佛教哲学本身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考虑到他所说的佛教哲学是“纯全哲学”即指的是形而上学,那么他所说的“佛教哲学的主观”很可能是指,站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观立场上研究佛教的意思。换句话说,差不多就是“佛教哲学中的主观问题”的意思。实际上在《佛教纯全哲学》的正文当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意思。
在白性郁的文章当中,相当于正文部分的正宗分由第一章“Buddha”与第二章“Dharma”构成。这种模式本身其实不是非常特别,这两章的内容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当中的佛法内容。但是,这两者被白性郁定义为“宇宙真理的主观”与“宇宙真理的客观”。如前所述,他将“佛教纯全哲学”定义为了“研究全宇宙真理的问题”。如果将这种全宇宙的真理分为“主观”与“客观”的话,那么这相当于“佛陀(Buddha)”与“达磨(Dharma)”。他将“佛陀”与“达磨”看作是“内在于真理的主观”与“内在于真理的客观”。这种观点带有一种唯理论的形式。也就是说将这个世界看作是真理的全部,即全世界就是完整的一个真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道:“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真理,而近代佛教哲学的建构者们则频繁地使用了“真理”这个单词。其实这个真理(truth)是比较近代的命名方式,如果用佛教本身的术语来说的话应该相当于“谛(ariyasacca)”,其意思可以理解为是“由圣人所教导的”。初期佛教当中提出了四种真理,即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及道圣谛。这个不是对于世界的理解,而是关于“痛苦和克服痛苦”这种极其个人式的问题的回答。所以,这种问题对于人类个人来说是非常切实的问题。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形式与白性郁所说的宇宙真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佛教哲学中的问题意识发生了某种转变,即白性郁转换了“达磨”的内涵,而他所要建立的一种佛教形而上学。
“达磨”是这个“宇宙真理本体”的代名词,如果将佛陀命名为“宇宙真理本体”的“主观”,那么“达磨”就应该是“宇宙真理本体”的“客观(对象)”。*白性郁:《佛教纯全哲学》,《佛教》第10号,第14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道:“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全大浩(音)·太璟燮(音)译,《HEGEL》附录,《精神现象学·序言》,首尔,EJB,2000,第991页。黑格尔正是想通过“主体”概念来实现“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即这个世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而且虽然一直处于不停生成的过程当中,但是又不是无序的。白性郁认为“佛教纯全哲学的概念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迁流的判定’。这是由于佛教的哲人们认为,万象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迁流的过程(与现今的学者们的观点一样)。由此可知,一切存在都是‘迁流的判定’当中的一部分。即,这是一种进化的过程”。*白性郁:《佛教纯全哲学》,《佛教》第11号,第13页。虽然可以将森罗万象的变化看作是“诸行无常”,但是不一定非要将其理解为是进化论式的。因为我们不能对于单纯的变化赋予一种价值,在进化论当中变化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正确的价值前提。白性郁认为“宇宙真理”当中的确存在着“主观”,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世界的形成。通过梵语语源的分析,他认为“Buddha”有着“觉者”与“智慧”的两重含义。
佛教哲人们所理解的“Buddha”是宇宙真理的“自体”,所以与dharma(达磨、法、客观)形成相对概念的时候,“佛陀”就成了一种“主观”。根据“无边虚空、觉所现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佛陀在一切众生心中”等这样的引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佛陀”这个词的含义的确是从事物的名称转变成了人的名称。这是由于“佛陀”这个词本来就暗藏着这种能力。*白性郁:《佛教纯全哲学》,《佛教》第8号,第16页。
在这里,白性郁强调了“Buddha”这个单词原来的意思是一种“物称”,他又认为这个单词从“物称”变成了一种“人称”,那么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可能白性郁认为,如果佛陀只是一个人名,那么佛陀只能是一个单个的人,他为了克服这一点才强调了“佛陀”本来是一种物称。为了将佛陀的概念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将其上升为宇宙论的层面,他将“佛陀(buddha)”这个单词所包含着的“人格”部分剥离了出去。从而他将“佛陀”与“作为真理的达磨”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一种宇宙真理的“佛陀”,如果要显现整个世界的话依然过于“主体”了。
在白性郁首次引用的《圆觉经》的句子当中也很好地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意图。在那里,他说无边无际的虚空是佛陀所显现的。稍不留神的话可能会将这段话当成是创造宇宙,但是他在之前就已经说过佛陀是宇宙真理本身,而显现的世界当中也囊括了宇宙真理的“主观”与“客观”,即这些都包容在一个真理当中。他将“达磨”看作是“宇宙真理本体”,不是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观念,而是试图将其看作是具体的世界。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他才使用了“达磨—虚空—自然”的模式来试图说明“达磨”等同于“自然”。
“善男子,一切众生无不从达磨(法界)流出,无不复归于此达磨(法界)。(中略)与其说是达磨创造了这个宇宙,不如说是宇宙是由达磨生成的。另一方面,此宇宙又是由达磨所整顿的。如果人类由‘虚幻’进入‘真理’的话,那么这些‘万象’即是‘达磨’”。*白性郁:《佛教纯全哲学》,《佛教》第10号,第14页。这个宇宙是虚空的一部分,如果假设虚空是由佛陀而出,那么无疑这个世界也是建立在佛陀之上的。*白性郁:《佛教纯全哲学》,《佛教》第13号,第21页。
白性郁所说的“达磨”其实是对于“佛性”或“法界”的一种翻译,而他是站在佛性论的立场上,将其范畴扩张到了宇宙论的层面。并且,白性郁还借用了华严的理论,认为这个世界是从“达磨”流出的,又是由“达磨”来整顿(秩序)的。《大乘起信论》中这样说道,“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白性郁认为,虽然这个世界是有差别的,也是无法直接进行肯定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属于虚空的一部分,那么也是可以对其进行肯定的。因为虚空正是由佛陀所生成的,所以这个世界也是由佛陀所生成的,因此世界的成立也获得了肯定。
三、 真如缘起论的登场及其意识形态性质
(一) 赖耶缘起论与真如缘起论的差异
在近代佛教的哲学化过程中,佛教哲学的建设者们总是纠缠于“现象”与“实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体又是什么呢?如前所述,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宇宙论的原因也在于此。白性郁为了说明这样的宇宙论,引用了《大乘起信论》的“九相次第说”。“九相次第说”指的是从“无明业相”开始的“三细”与“六粗”。*白性郁在这里试图做一个重要的转换,他将《起信论》中所说的三种细微的意识活动中的第一个“无明业相”命名为了“业相”。他认为这个“业相”不是无明(avidy),而是明(vidy)。虽然将九相都解释为了“无明”,但是其出发点则不是“无明”而是“明”。结果就是假的世界也包括在真理当中。白性郁虽然曾经留学过德国,但是在这一点上与留学过日本的人们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1924年的时候,香山外人在《佛教研究》当中将佛教的缘起论分为业感缘起论、赖耶缘起论、真如缘起论、法界缘起论和六大缘起论。*这种方式被明治时期的佛教学者们所定型化了,从韩国佛教的立场上来看的话,这种分类方式是比较陌生的。特别是其中的六大缘起论是根据密教的理论,而与日本不同,密教在韩国佛教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仅对业感缘起论、赖耶缘起论和真如缘起论进行了说明。并且香山外人将这三种缘起论各自对应于小乘教、大乘权教和大乘实教。而李钟天在《佛教与哲学》当中,说明了赖耶缘起论的性质和界限。
(法相宗认为)追求“万法”可以到达“第八识”,而其本体则是真如。即在说明“真如”和“万法”的关系时认为,真如与现象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万法世界”则是依存于第八识。所以,法相宗认为“真如凝然、不作诸法”。即法相宗的宗旨是,虽然世界的成立是以真如为根本,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从真如流出的。*李钟天:《佛教与哲学》,《朝鲜佛教总报》第13号,第59页。
在这里,法相宗所说的真如并不与“万法”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真如缘起论的立场上来看的话,这种“真如凝然、不作诸法”的法相宗式的真如概念是不可接受的。这里的“凝然”指的是超安静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绝对不动”,用传统的佛教术语来说的话则相当于“平等”。为了生成这个世界,这种安静的状态需要自我崩溃并产生某种造作。但是就唯识学中所说的真如概念来说的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唯识学中的“真如概念”与真如缘起论中生成这个世界的“真如概念”是互相冲突的。
在近代中国佛教界当中,围绕真如概念与《大乘起信论》也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现象。对于《起信论》坚持批判态度的是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吕徵、王恩洋等人,与此相反,以太虚为代表的武昌佛学院的人们则坚决拥护传统的《大乘起信论》的权威。欧阳竟无在1922年的《唯识抉择谈》中认为“真如是所缘,正智是能缘”。*欧阳竟无:《唯识决择谈》,《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第39页。用白性郁的方式来说的话则是,真如是客观,正智是主观。即,真如的自体是不主动发生作用的。欧阳竟无认为真如仅仅是“遮诠”而已。在《中论》当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使用了“遮诠”的方式表示了“空”,即指出了真如不具有任何特别的内容。欧阳竟无认为“佛法但是破执,一无所执便是佛也”。*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同上书,第6页。这句话不由让人想起来《金刚经》当中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在这里,欧阳竟无强调了唯识学是立足于“空思想”的,中国学者周贵华用两句话整理了欧阳竟无与支那内学院关于“真如”和“如来藏”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批判其心性、真如、如来藏为一的观念,否定其本体论含义;第二、批判其体用论与缘起论(宇宙论或发生论)的合一”。*周贵华:《唯识心性与如来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232页。根据周贵华的分析,欧阳竟无与支那内学院是反对将真如看作是“本体论”或“宇宙论”的。所以他们与坚守《起信论》传统权威的以太虚为代表的武昌佛学院进行了论争,而且与试图建立中国式本体论的熊十力也进行了论争。
在唯识学当中,并不是通过真如,而是通过阿赖耶识才能生成现象。“赖耶缘起”指的是阿赖耶识的“识转变”。但是在《摄大乘论》这样的印度唯识学文献当中,阿赖耶识基本上属于一种“妄识”,而唯识学中所说的“真如”是一种“空性”,因此其所显现的世界并不是一种肯定的对象。“以阿赖耶识为出发点的唯识学当中,阿赖耶识虽然是众生本来的状态,但并不是应该的状态,因此觉悟的前提就是自我变革和自我否定阿赖耶识,而这就是所谓的‘转依’。”*高崎直道:《唯识入门》,东京,春秋社,1992,第225页。简单来说的话,“转依”指的是对于人类意识的根据进行革命性的转换。从“转识得智”当中也可以知道,阿赖耶识仅仅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拥护的对象。而通过这种革命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就是诸法皆空的真实。唯识学中所说的真如就是这样的,而我们也理解了“真如凝然,不作诸法”的含义。但是近代佛教哲学所指向的是,探求作为世界根源的实在或作为真理的实在,因此唯识学中所说的阿赖耶识概念并不适合其要求。所以,建构佛教哲学的人们将“赖耶缘起论”看作是一种不完全的缘起论。而通过下面的一段内容可以看出,缘起论并不只是单纯地仅停留于佛教学内部的一种理论。
这个“赖耶缘起论”的特征是,改造了小乘的“心物二元论”并将其统一为“唯心一元论”。这不仅是单纯的“一元论”,也是个人的唯心一元论。根据这种逻辑,在百姓眼里这个国家和社会是为了百姓而建立的,而在官吏们的眼里这个国家和社会是为了官吏们而建立的。因此,世界万物并不是梵天或上帝所创造的,而是作为阿赖耶识主人的自己本来所具有的。*香山外人:《佛教研究》,《佛教》第4号,第28页。
如前所述,香山外人将“赖耶缘起论”命名为个人的“唯心一元论”。而金东华则是与“绝对唯心论”进行了对比之后认为,赖耶缘起论是“相对唯心论”。他说“因为他人的阿赖耶识所转变的诸法,并不是自己所转变的,因此在这里‘唯识无境’是不成立的”。*金东华:《佛教学概论》,首尔,宝莲阁,1954;1984,第194—195页。如果根据这两人对于赖耶缘起论的理解来看的话,这个世界是为个人所包容的。因为阿赖耶识的主人公是个别的“有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克服“个别”的限制,而且这个“世界”的数量也要与个人的数量一样多才行。
我们可以看出,在上述引文当中为了说明“赖耶缘起论”而所举的例子是非常近代的,其中列举了个人与共同体、特殊与全体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结果是相比于“共同体”或“全体”而言,赖耶缘起论更接近于“个人”或“特殊”。即在这里使用了个人与共同体(国家、社会)的关系对赖耶缘起论进行了说明,并认为赖耶缘起论是只能选择“个人”一方的哲学体系。如果仅从韩国的理论发展情况来说的话,可能不容易理解这一点。人们一般认为近代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确立”。
而在明治初期所进行的日本近代启蒙运动,也可以通过从上述的思想脉络进行把握。一般从近代意义上来说话,应该更加关注个人的成长,或者是更应该积极地推进赖耶缘起说才是。但是,“明治哲学史”的第二期“观念论”当中,则是极力反对这种个人的“确立”,并且其思想也是在与上述思想之间的对抗当中所形成的。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日本的这种思想脉络后来发展为了集团主义、国权主义及日本主义等等。在日本试图建立佛教哲学的井上圆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后来的西田哲学则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可见日本的佛教哲学,甚至是日本的近代哲学的主题就是“克服个别”。而1910年之后这种思想则又传到了韩国佛教界。
(二) 绝对平等与全体性
在日本的明治哲学史当中,可以说井上圆了“使用近代思想重构了佛教理论”,而且“井上圆了充分认识到了当时的日本所处的状况,因此他并不是仅从佛教内部看佛教,而是通过与近代的欧洲思想、基督教、儒教等思想之间的对话之后,试图重新认识佛教的传统”。*立川武藏:《井上圆了の佛教思想》,《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9卷第1号,2001.12,第12页。在这个时候,最受人关注的是佛教的真如概念。在上面的引文当中所使用的那样,“绝对平等”是对于真如的修饰语,而李钟天在《佛教与哲学》当中认为“真如所指向的是全体宇宙世界本体的一种平等”。*李钟天:《佛教与哲学》,《朝鲜佛教总报》第12号,第36页。真如与法身概念也联系在了一起,金喆宇在《佛教哲学概论》当中认为“法身可以命名为‘真如理性’,是一种本来就绝对、无差别、平等的实在”。*金喆宇:《佛教哲学概论》,《朝鲜佛教总报》第16号,第54页。可见,很早就开始普遍使用了真如是“绝对平等”的观念。而香山外人在《佛教研究》当中是这样认为的。
《起信论》主张的是真如缘起论。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现象世界当中。如果观察这个现象世界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不仅存在着生灭变易的相对性的差别,同时又存在着不生不灭与不变易的绝对的平等。《起信论》当中将前者称之为“生灭门”,将后者称之为“真如门”。因为这个真如是宇宙万象的本体,不管是生物还是无生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这个真如中发生和显现的,而这就是真如缘起论所主张的内容。*香山外人:《佛教研究》,《佛教》第6号,第37页。
在这里所说的真如,不像赖耶缘起论中所说的阿赖耶识那样局限于个别的“人”当中,而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存在着的一种“普遍存在”。因此从每个“个别”都各自构成世界的模式当中解放了出来,而这个世界最终也可以成为一个“一”。如果说赖耶缘起论是个人式的唯心论,那么真如则是“世界性的唯心一元论”。《起信论》中所说的“一心”或“一法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至少从上面的引文内容看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平台。即不管是生灭的差别还是不生不灭的平等,都可以说是在这个当中所发生的“风暴”或是“寂静”,而且不管是生物还是无生物,也都是这个巨大而又温暖的世界之中生灭着。
末木文美士认为,近代的日本思想界担负着“个体与超越个体”这样一个巨大的课题。*末木文美士:《明治思想史论》,第10页。“个体”与“超越个体”的问题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在这里个体的超越指的是打破主观与客观的框架。根据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赖耶缘起说并未能克服“主观”的拘束。金东华认为真如缘起说正是克服了赖耶缘起说的这种局限性,并“设定了普遍的‘唯心体’,然后从这个‘唯心体’当中发展出了‘主观界’与‘客观界’的一切万有的诸法”。*金东华:《佛教学概论》,第194—195页。而这个“普遍体”存在于客观与主观、存在与非存在的背后。李钟天下面的一段论述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使用了现实当中的政治体制比喻说明了缘起论。
如果与国家组织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小乘就像75位臣子各自形成一个领域而管理这个国家的秩序一样;而法相宗就像总理大臣式的政治模式,尊贵的天皇住在九重宫阙的深处,因此不直接管理行政,而是由大臣来管理行政。真如就像天皇,只是需要通过大臣下命令而已。但是“实大乘”则不然,真如直接就是天皇,亲自担任各种政务,这就像真如统摄万法。*李钟天:《佛教与哲学》,《朝鲜佛教总报》第13号,第59页。
在上述引文当中,使用了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的方法说明了缘起论的三种形式。这种观点与前面所提到过的赖耶缘起论的说明方式处于同一个脉络当中。即,在这里将天皇安置于真如的位置,他认为超越个别的真如与超越个人的天皇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是以“差别”的形式存在着的“万法”并不与平等的世界相分离,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都是由无差别的平等真如所产生出来的。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像绝对真理、绝对平等、绝对唯心等这样的关于“绝对者”的描述非常频繁地出现在“佛教哲学”相关的各类著述当中。这种“绝对性”像“神性”一样是超越时空的,因此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巨大的真理或者是全宇宙真理这样的概念。而且这样的思维模式也非常容易地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在了一起。著名的哲学史家科普尔斯顿(Frederick C.Copleston)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这样说道:“哲学的主题是‘绝对者’,但是绝对者是总体的、全体的实在性的宇宙。”*Frederick C. Coplest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7, 1994, 170页。黑格尔试图通过“绝对精神”来克服个别与普遍、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化,将宇宙统合为一个总体。在近代,推进佛教哲学化的佛教人士们看来,华严学与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契合的。
一般在华严学当中将宇宙看作是“一大精神”的显现,因此将其称之为“一心法界”或“万有总核心”。这里的“心”并不是有限的、有差别的心,而是绝对无限的心。万象只是这个“一心”中显现的映像而已,这就像平静的大海会毫无保留地将森罗万象照出来一样。*金敬注:《华严哲学的内容》,《佛教》,第40号,第3页。
金敬注将华严学看作是研究绝对精神的哲学。他在解释华严学的“圆融无碍”时认为“在全一(Allone)的世界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在这里,“全一”是一种总体性(全体性)的概念,所以金敬注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其实将全体性、总体性、有机体这样的概念与华严学进行关联的倾向由来已久。因为这些概念的确有助于理解“华严”这样的比较难以理解的哲学。虽然不能否认华严学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但是金敬注所说的华严当中也存在着一些特别的地方。他通过华严的“法界缘起”概念不仅烘托了世界的全体性,而且还赋予了“主体”的概念。
金敬注将华严学中的“一心法界”的术语分为“一心”与“法界”,然后将主观与客观各自对应于“一心”与“法界”。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一心”是指绝对无限的心,指的是超越了现象世界的主观与客观的一种“主观”,可以说并非是相对的“主观”,而是一种绝对的“主观”。这种观点与前面所提到过的白性郁的“宇宙真理的主观”有些类似。而且金敬注还直接引用了黑格尔,他说:“西方哲学家当中将‘一’与‘多’的问题解释得最好的是黑格尔,黑格尔说道“真理不在于‘一’,也不在于‘多’,而是包括这两者的一种统一’。”如果考虑到黑格尔是用全体性设定了真理,那么金敬注的上述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黑格尔说过这样一段话:
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按照它的本性,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全大浩(音)·太璟燮(音)译,《HEGEL》附录,《精神现象学·序言》,首尔,EJB,2000,第991—995。
在上述引文当中,说明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它(绝对精神)本质上是个结果”,而金敬注也说道,“实在”总是以结果的形式显现。而且作为存在者的起源是不可能被遗忘的,所以绝对精神并不是太古时期的某种东西,而是从结果上来看绝对精神就是自己。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在1943年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当中说道,“皇室是包容过去与未来的绝对现在,皇室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起点也是终点”。*西田幾多郎:《哲学论文集第四补遗》,《西田幾多郎全集》12卷,岩波书店,1996,第430页。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是,皇室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所以并不是过去或未来,而是现在。金敬注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说道“这就是‘实在’不得不恒常活动着,还得常常随缘而深入现象之中,以现象为依据,并且还得生成现象本身的原因。而这正是华严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的解释,而进入现象论的解释的重要意义所在”。*金敬注:《华严哲学的内容》,《佛教》,第40号,第8页。当然这段话的内容与黑格尔的立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总之,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于理念(Idea)这样的不动的“实在”,黑格尔所说的可以生成的“绝对精神”更加接近于他所说的“实在”。
四、 结 论
近代的韩国佛教哲学是以西方的形而上学与德国观念论为哲学的基础而形成的。而直接的渊源则可以说是日本的明治佛教。近代韩国的一些佛教知识分子们接受了“现象与实在”这样的形而上学的结构模式,并且将佛教教理的展开看作是一种观念论(唯心论)的发展史。而在佛教当中“观念论的发展史”表现为“缘起论的发展史”。他们将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的诸多教理体系分为了业感缘起论、阿赖耶缘起论与真如缘起论,并且将其中的真如缘起论看作是缘起论的集大成。虽然这是对于佛教教理的一种进化论式的解释方式,但是没有经过一定的批判过程就直接传入到了韩国佛教界。而且以绝对性为基础的真如缘起论,又成为了使用国家主义解释佛教教理一个契机。所以在殖民地时期的韩国佛教理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这样的倾向也一直持续到了解放之后。综上所述,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系谱学的方法对近代韩国佛教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一番考察,从而希望能进一步分析当时的真实状况,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试着对近代的韩国佛教进行了一番理论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