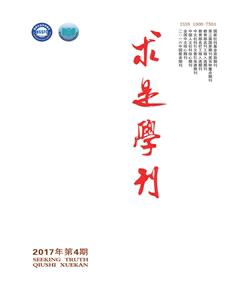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摘 要: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关键词:清代文字狱;小说禁毁;文本形态
作者简介:陈才训,男,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1CZW042;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地专项)重点项目“明清小说文本生成方式研究”,项目编号:HDJDZ201608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105-07
明清时期,小说禁毁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明清易代之后,文网更趋严密,文字狱时有发生,像著名的庄廷 明史案、戴明世《南山集》案等皆对当时的文坛造成了极大震慑作用。其后,清廷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强化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发布谕旨云:“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1](P17)于是,前人书中的“违碍字样”[1](P18)悉被删改。这一谕旨虽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但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文化政策之严厉,而这正是造成清代文字狱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频发的文字狱令文人噤若寒蝉,故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称,“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以致“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2]。清代文人的这种惧祸意识在小说创作及传播领域也得到充分反映,以至许多小说家特意声明自己“书中无违碍忌讳字句”[3](第1辑,小和山樵《红楼复梦·凡例》,P1)。换言之,作为清代政治文化生态组成部分的文字狱,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明显的惧祸心态,并由此影响到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
一、清代遭禁小说文本形态之演变
毋庸置疑,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清代官方禁毁的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会在刊行过程中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例如,刊刻于顺治十七年(1660)的《续金瓶梅》在康熙三年(1664)即因文字狱而遭到查禁,故丁耀亢《归山草·焚书》有“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4](P502)之语。丁氏《续金瓶梅》以宋金之战为历史背景来展开故事情节,其中写到金人劫掠烧杀之事,因此该书被人检举有违碍之语而遭查禁,当时刑部判结云:“经查阅该书,虽写有宋金两朝之事,但书内之言辞中仍我大清国之地名,讽喻为宁固塔、鱼皮国等。据此,理应绞决丁耀亢。但有司所查送之文内则称,丁耀亢自首属实。又于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所颁恩赦内一款曰:‘凡查拿之重犯,若有自首者,可著免罪。故此,议免丁耀亢之罪。至于所撰写之《续金瓶梅》十三卷书,拟交礼部查封焚毁。”[5]该书虽遭官方明令禁毁,但其刊本并未绝于世,只不过书坊主是将其改头换面,易名《隔帘花影》后继续刊行。当然,书坊主已对部分情节内容予以大幅删削,删除的基本都是那些容易触犯时忌的敏感内容和激越沉痛的议论,特别是像第十三回“陷中原徽钦北狩”、第十九回“宋道君隔帐琵琶”与“张邦昌御床半臂”、第二十一回“宋宗泽单骑收东京”、第五十四回“韩世忠伏兵走兀术”与“梁夫人击鼓战金山”、第五十九回“辽阳洪皓哭徽宗”等情节单元,其中有关金兵烧杀劫掠的描写文字都被淘汰净尽。即使一些涉嫌丑化金人的细节文字也被更改,如《续金瓶梅》中骗孔梅玉为妾的是金帅挞赖之子哈木儿,而《隔帘花影》却将哈木儿改为汉族将军金钰之子金坚。而且《隔帘花影》还重新拟定回目,对人物姓名加以改易,如以南宫吉替代西门庆,以楚云娘替代吴月娘,以慧哥替代孝哥,以毛橘塘替代蒋竹山,等等。晚清民初,孙静庵根据《续金瓶梅》并参照《隔帘花影》编撰《金屋梦》,恢复了《续金瓶梅》中有关宋金战争的情节内容。不过,需要明确的是,《金屋梦》文本形态的生成也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一是此时清王朝已经覆亡,再无文祸之虞;二是孙静庵本人曾于1904年参加兴中会,抱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志愿的他民族意识空前强烈。无疑,由《续金瓶梅》到《隔帘花影》再到《金屋梦》,这些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情况,已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政治生态的变化给小说文本形态带来的显著影响。
李渔《无声戏二集》中某些小说文本形态的变化也与文字狱相关。《无声戏二集》中有作品写到张缙彦事,即写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城,时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欲以死殉国而被救,由此他被赞为“不死英雄”[6](卷79《贰臣传乙》,P6624)。职是之故,先降李自成而后又归顺清廷并出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曾资助李渔刊刻《无声戏二集》。顺治十七年,张缙彦因党争而被流徙宁古塔,其中罪名之一便是指斥他欲借小说以自饰,谓其“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认为小说中有关张缙彦的描写“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等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6](卷79《贰臣传乙》,P6624)这一政治风波之后,在文禁尚不十分严厉的康熙初年,有人将《无声戏二集》文本加以改造后以《连城璧》之名重新刊行,它删除了原书中与张缙彦有关的违碍作品;重新调整原书目次,且回目由单句变为双句;又将杜濬《无声戏序》改为《连城璧序》,并对其作了改动,尽量隔离《连城壁》与李渔及其《无声戏》之间的渊源;还对原本中一些敏感之处予以删除,如《连城壁》第十一回戌集将《无声戏》原有的回后总评予以删除,因为其中有“夷狄进于中国而中国之,中国入于夷狄则夷狄之。知《春秋》褒夷狄之心,则知稗官重奴仆之意矣”[3](第1辑,李渔《无声戏》,P643)这样的语句。既然《连城璧》在《无声戏》基础上修改而来,必然会在《连城璧》文本中留下蛛丝马迹,如《连城璧》亥集总评中仍保留有这样的话语:“《无声戏》之妙,妙在回回都是说人,再不肯说神说鬼。”[3](第1辑,李渔《连城璧》,P860)这里“无声戏”字眼的出现,显然是由删改者疏忽所致,而这恰恰证明了《连城璧》与《无声戏》的渊源关系。由《无声戏二集》引发的文字狱虽未直接牵连到李渔本人,但对其创作心态却产生了不小影响,因此他主张戏曲小说要“戒諷刺”,并以《誓词》云:
稗官好为曲喻。……矧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词场,使不岑寂而已。但虑七情之内,无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认为有样之葫芦?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喑,即漏显诛,难逋阴罚。[7](第3册,《笠翁一家言文集》卷2,P7)
这里李渔反复强调自己的戏曲小说绝非“曲喻”“讽世”之作,其惧祸意识不难想见。例如,李渔《巧团圆》将拐卖妇女的清兵改为李自成起义军,便是为规避文字狱。
那些创作于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更是成为官方禁毁的主要对象,其文本形态常常会被大幅“修正”。例如,《新世鸿勋》是在遭到官方禁毁的《剿闯通俗小说》基础上改编而来,它不仅将原本中的“虏”“国朝”“皇明”之类字眼悉数删去,而且对清王朝极尽颂扬之能事。首先,《新世鸿勋》编撰者在“小引”中盛赞清朝为“否极而泰承,乱甚而治继。天应人顺,大清鼎新。迅扫豺狼,顿清海宇”,“率土倾心,普天欢忭”[3](第1辑,蓬蒿子《新世鸿勋》,P2—3)。其次,小说第一回开篇便云:“大清开国皇仁布,喜和风甘露。彩凤呈祥,灵龟献瑞,咸歌遭遇……这一首词,名为《贺圣朝》。前半篇称大清开国之盛,圣主当阳,官清吏治,万民乐业,熙熙皞皞,如际唐虞。”再次,小说正文一律尊称清为“大清”,且对清兵进犯之事多所隐晦,如在叙及李自成起兵原因时,回避了清兵犯境这一事实,而改写成南番交趾兴兵犯境。最后,小说最后一回即第二十二回再次颂圣云:“恭荷大清皇帝法驾入京,位登大宝,建号大清,改元顺治。……自此华夷一统,国正官清,太平景运,亿万斯年,天下臣民,无不庆幸。……自是江南群县,无不臣附归服。就改江南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凡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俱皆归顺,而大清万年基业,于斯定矣。诗曰……真人应运龙飞日,一统山河属大清。”此外,《新世鸿勋》对《剿闯通俗小说》的改动还有许多,如它删除了原著中吴三桂赞扬史可法的话语,因为在原著中吴三桂虽已引兵入关,但他当时仍为明臣,小说结尾还写到弘光帝对他的敕封;而《新世鸿勋》成书于清代,此时吴三桂已经降清,因此书中对他大加赞扬,但却已变成清人的立场。可见,由《剿闯通俗小说》到《新世鸿勋》,小说文本形态的演变与政治生态息息相关。
二、编刊者对小说文本形态的修正
有些小说虽然未引发文字狱,也没有遭到官方禁毁,但为避免触犯时忌,那些编刊者即书坊主或改编者在编刊过程中也往往会对其中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予以主动“修正”。例如,上海图书馆藏本《四雪草堂重订通俗隋唐演义》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该小说初刻本,其第二回对隋文帝废太子之事有着详细的描写,而重刊本即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二回却对相关情节作了最大程度的简化,尽量规避屡见于初刻本的“东宫”“太子”之类字眼。例如,初刻本第二回回目为《隋主信谗废太子,独孤逞妒杀宫妃》,“信谗废太子”这一政治色彩极强的敏感字眼未免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于是重刊本将第二回回目改为《杨广施谗谋易位,独孤逞妒杀宫妃》。不止改动回目,初刻本与重刊本第二回正文也作了相应处理,像初刻本第二回中“太子宫中有好事,不与他传闻”[8],在重刊本中变为“寻规蹈矩的事体,不与他传闻”[3](第1辑,褚人获《隋唐演义》,P29);初刻本第二回中“但只是废斥东宫,须有大罪”,在重刊本中变为“但只是废斥易位,须有大罪”;初刻本第二回中“太子要展辩不得”,变为重刊本中的“他自然展辩不得”;初刻本第二回中“这番太子不怕不废”,变为重刊本中的“这番举动不怕不废”,等等,都是将“太子”“东宫”这样的字眼删除或以其他词语替换。重刊本的改动与当时敏感的宫廷斗争有关,因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曾两废太子胤礽,其中也涉及诸皇子之间的争斗、朝臣的介入,“太子”“东宫”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字眼,所以《隋唐演义》重刻本及后来的文盛堂本、文锦堂本、同德堂本、文奎堂本等都对隋文帝废太子情节予以删节简化,以防影射时政之嫌。又如,《聊斋志异》中《张氏妇》等暴露了清统治者乱杀无辜的罪行,流露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青柯亭本便将其删去。对于由此导致的文本演变情况,有论者指出:“友人刘君北平,蒲留仙之同里人也。其先世与蒲姻亲。刘君为余言,近时所流传之《聊斋志异》与原本颇多不同处。其原本中言民族主义,及讥当时权贵之语甚多。当刊行时,其亲族畏祸,全行删改,其原本尚存其乡某君处云。余每读《聊斋》,辄怪其妍媸互见,且每多牵强处,闻刘君言,始恍然。”[9](平子《小说丛话》,P316)所谓“亲族畏祸,全行删改”虽有夸张之嫌,但因文字狱而引发的惧祸心理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再如,《野叟曝言》成书于乾隆间,最初刊于光绪七年(1881),共有一百五十二回,但该刊本缺少第一百三十二至第一百三十五回这四回,正文第一百三十二回處有注称“以下四回原稿全缺。只录卷数回目,如俟觅得完璧补梓”[3](第4辑,夏敬渠《野叟曝言》,P3617),这四回主要写文龙、文麟率军征服日本、蒙古、印度、锡兰等国及根除佛教之事,有论者认为编者是为避免文祸才将这四回删去[10](P480)。
同样缘于惧祸意识,那些创作于明代的小说作品,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其文本形态也往往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改。如《西游记》世德堂本第七回写悟空对如来道:“他(指玉帝)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3](第4辑,吴承恩《西游记》,P156)刊刻于清代的《西游真诠》与《西游证道书》都对此作了修改,改成“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1,这一改动虽大大淡化了孙悟空身上的叛逆色彩,却有助于评改者避开敏感的政治字眼。更为显著的是,明代小说中那些与满人称谓相关的字眼,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往往成为改编者或书坊主极力规避的内容。如《怡情阵》实由明代艳情小说《绣榻野史》改头换面而来,它对原作中那些比较敏感的违碍语作了修改。其中《绣榻野史》上卷姚同心给赵大里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话:“吾弟三败于金,可见南宋无弱兵矣。昔日跨崔之兴安在哉!屈首请降,垂头丧气,徽、钦之辱,亦不过是。可笑。弟即当招兵买马,卷士重来,以图恢复。毋使女真主得志,谓我南朝无人也。”赵大里的回帖中则有“直捣其巢穴而扫腥膻然后已”之类话语,它们虽为情调低俗的戏谑之语,但在文字狱频发的清代,《怡情阵》还是将“金”“女真”“腥膻”等容易触犯时忌的字眼悉数删去。又如,七十回明刊本《于少保萃忠传》多以“胡”“虏”“鞑子”等指称蒙、满北方少数民族,而四十回清刊本《于少保萃忠全传》则以“北兵”“边外”等字眼代之,像明刊本第十七回《正统蒙尘胡虏地,郕王监守镇家邦》,在清刊本中则变为 《正统蒙尘北地,于谦扶掖朝纲》。清代小说选本在选编明代小说时也以同样原则对原作文本形态予以加工改造。如清佚名辑《别本二刻拍案惊奇》有多篇作品选自陆人龙《型世言》,其中卷十九出自《型世言》第九回,它将原书中的“鞑子”改为“贼子”或“臊子”;卷十二出自《型世言》第十二回,它将原书中“鞑子”改为“倭子”。又如,《西湖拾遗》卷三十六选自《醒世恒言》卷三,编选者将原作中“金虏”“鞑子”之类有碍字眼一律改为“金人”。清代小说选本在编选明代小说时对明帝或明朝的称谓也做了相应修改。如明人周清原《西湖二集》在提及朱元璋时多用“洪武爷”或“我洪武爷”,分明是明人的叙事口气,如第一卷、二卷、四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九卷等皆是如此;而清人陈梅溪所辑《西湖拾遗》将其中一些作品收录时,则改称“太祖”,叙事主观色彩大大淡化。同理,《西湖二集》中作品一般称明朝为“我朝”,如第一卷、十二卷、十八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等;而《西湖拾遗》收录其中一些作品时则改称“明朝”。这一切都反映出时代政治文化生态的变迁给小说文本形态带来的微妙变化。
即使一些清代小说,其中那些与满人称谓相关的字眼也会随时被修改。如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六十三回写宝玉“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攥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称“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11](P1123)。作者用长达一千余字来叙述这一情节,但它却不见于程甲本,无非是因为它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程甲本刊行者恐触犯时忌,故将其删除。又如,《醒世姻缘传》大连图书馆藏辛丑本第六十二回中出现的“南倭北虏”“几千万鞑子犯边”,在同德堂本、怀德堂本等版本中则分别改作“南倭北敌”和“几千几万来犯边”。这些文本改动看似细微,却能充分表明清代文网之密及文人惧祸意识之强。
另外,因忽略避讳制度而引发文字狱的现象在清代也时有发生,如乾隆间王锡侯《字贯》案就是因为作者在书前“凡例”中没有缺笔避开康熙、雍正及乾隆帝名讳所致。正因如此,清代小说家或编刊者在涉及与帝王名字相关的字词时,往往采取避讳措施,这在小说文本形态中也得到显示。例如,为避康熙帝玄烨之名,大连图书馆藏辛丑本《醒世姻缘传》中“玄”字多缺末笔;清末书坊主将《梼杌闲评》易名为《明珠缘》刊行时,将小说中“玄”字一律改为“元”。这虽属文本形态上的一些细微变化,但它确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三、小说家的惧祸意识与文本形态
频繁发生的文字狱和官方的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明显影响,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其中最引人瞩目者,是清代小说家在惧祸意识支配下一般对本朝开国之事避而不谈。例如,吕抚《纲鉴廿一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三卷中的第三十九回《天付与大清朝升平万岁》与第四十回《混乾坤归一统海晏河清》,从回目看它们应叙写清朝开国之事,但正文中这两回仅列有回目并抄录他人诗歌以颂圣,并无任何情节内容。具体而言,第三十九回抄录唐人贾至的《早朝大明宫》:“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自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瀚侍君王。”它描写的是皇宫的豪华气派以及百官早朝时严肃隆重的场面。第四十回抄录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它描绘的是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氛围与皇帝的威仪。显然,作者精心拟定的第三十九、四十回回目及特意抄录的两首唐诗都带有浓郁的颂圣意味。其实,《纲鉴廿一史通俗演义》所呈现的独特文本形态乃是作者惧祸意识的产物,这从本书卷首“凡例”即可看出:“本朝未有实录颁行,传闻不无讹谬,并不敢以不识不知之民妄谈本朝事迹。虽另为二回,惟祝嵩呼以见本朝如日之方升,万万斯年,非野人见闻,所可妄谈。另起一卷而空其后者,以见后此而无穷也。”[3](第2辑,吕抚《廿一史通俗衍义》,P1)以上两回有目无文,并非因“本朝未有实录颁行”,因担心文字狱而不敢“妄谈本朝事迹”才是作者的真实心态。一般小说家反对他人翻刻盗版自己的小说,而吕抚恰恰相反,他在“凡例”中称“是书欲广其传,不禁翻版,第抚数载苦心,原非为利,如有易名及去名翻板,又或翻板而将本朝之事迹,得之传闻,妄意增添者,虽千里必究”[3](第2辑,吕抚《廿一史通俗衍义》,P1)。小说盗版现象在当时已司空见惯,为防止别人在盗版过程中私自增补第三十九、四十回,吕抚才有以上声明,其真实心态无非是想借此撇清责任而已。据民初《新昌县志》卷十二记载,曾屡试不第的吕抚以著述为事,成书甚多,可后来海宁査嗣庭文字狱发生,他担心受到牵连,私下毁板过半。由此不难理解吕抚何以会在小说“凡例”中有以上严正说明,何以会如此谨慎地处理第三十九、四十回。又如,道光四年(1824)啸月楼刊本《末明忠烈奇书演传》“凡例”也郑重声明:“是书叙事无伤碍语,且照末明时事实录,并不敢少涉当代旁说,只末数页将吴三桂往本朝乞师灭贼带写数言耳。”[12](P545)所谓“不敢少涉当代旁说”,意在说明小说对诸如吴三桂之类与“本朝”开国史事密切相关的敏感人物做了谨慎处理。
清代一些小说即使并不关涉本朝国事,作者在建构文本时也往往心怀顾忌。例如,因文字狱而引发的惧祸意识便影响到曹雪芹的叙事谋略,这从《红楼梦》的文本形态中即可看出。甲戌本《石头记》“凡例”云:“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此書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又云:“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13](P2—3)这里曹雪芹一再强调自己的小说写“闺中之事”而略于“外事”“不敢干涉朝廷”,实为其惧祸心态的真实写照。因此,他在小说第一回便隐晦其词,称小说“无朝代年纪可考”,告诉读者不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并再次强调“毫不干涉时世”,其中虽有“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而是“大旨谈情”。而且,曹雪芹还有意疏离了自己与《红楼梦》之间的距离。首先,在甲戌本“凡例”中作者先是声明此书乃是他“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而第一回开篇却又面向读者发问:“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如此一来就给读者造成一种该小说已先于作者而存在的印象,借此疏远了自己与小说之间的距离。其次,作者在第一回又将全书的叙述者让位于空空道人,称空空道人把石头上的文字“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作者此举仍是意在进一步拉大自己与小说之间的距离。最后,作者在第一回中又称小说原名《石头记》,继而改称《情僧录》《红楼梦》及《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衩》”,这里曹雪芹仅仅赋予自己以小说整理者的身份。以上叙事形态显系曹雪芹有意为之,目的无非是淡化乃至隐去自己的作者身份,其创作心态当与清代频发的文字狱不无关系。即使如此,宗室子弟弘旿仍云:“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违碍语也。”[14](P10)又如,李绿园虽将自己《家训谆言》“或反或正,悉数纳入”[15](P59)《歧路灯》,使小说表现出与官方文化政策完全一致的教育理念,但他仍在小说自序中强调该作乃“空中楼阁,毫无依傍,至于姓氏,或与海内贤达偶尔雷同,绝非影射。若谓有心含沙,自应坠入拔舌地狱”[3](第3辑,李绿园《歧路灯》,P35),其惧祸意识不言自明。吴敬梓也是如此,金和谓其在描写人物时“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16](《儒林外史跋》,P795),这虽有过于求深之嫌,但小说采取模糊或错乱时间的叙事策略,将故事背景设置于明成化末年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他如《续金瓶梅》故事背景为宋金易代之际,可像第二十八回、三十五回在描写金人时却出现了“蓝旗营”“旗下”之类字眼,而这样的建制直至清朝才形成;再联系第五十三回写扬州失陷时作者穿插的那首“满江红”,其中有“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之语,由此可以断定小说所写实为清代事,而作者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文本处理方式,也与其所处的文祸频发的时代环境有关。
小說作者署名属于“副文本”1,但清代小说家多用笔名、别名而很少用真实姓名,这固然与小说低微的文化地位相关,也与小说家的惧祸意识不无关联。例如,陈忱在《水浒后传》卷首附有署为“雁宕山樵”的序和署为“樵余”的《水浒后传论略》,在序中他又提及“古宋遗民”,实际上这三个别号皆为作者本人。陈忱为明遗民,入清后参加了顾炎武、归庄、吴炎等人组织的“惊隐诗社”即“逃之盟”,其中吴炎曾因受庄廷 “明史案”牵连而被杀,显然陈忱在小说中自署为“雁宕山樵”或“古宋遗民”,与其因文字狱而产生的惧祸意识息息相关,毕竟他在小说中流露了比较浓郁的遗民情绪。
种种迹象表明,清代官方为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而制造的众多文字狱,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得到充分反映。其实,在清代几乎所有小说的文本形态都可能会在传播过程中被修改,难怪余治在《得一录》之《删改淫书小说议》中有如下提议:“欲罗列各种小说,除《水浒》《金瓶》百数十种业己全数禁毁外,其余苟非通部应禁,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版片,乃可通行,所有添改之处,则必多引造作淫词及喜看淫书各种果报,使天下后世撰述小说者皆知殷鉴,不致放言无忌。”[17](第92辑,余治《得一录》卷11,P16)据此,几乎所有小说都须通过“删改”或“添改”的方式对其文本形态予以加工改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文化政策的严厉。说到底,以文字狱及小说禁毁为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清代政治文化生态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多维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李祖陶:《迈堂文略》,同治四年(1865)刻本.
[3] 《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丁耀亢:《丁耀亢全集》,张清吉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5] 安双成:《顺康年间〈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受审案》,载《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
[6] 《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28.
[7] 李渔:《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8] 褚人获:《隋唐演义》,康熙同德堂刊本.
[9]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11]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2] 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13] 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 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16] 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17]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ten occurs, and the strict official novel prohibition policy leads the novelists, compilers or bookshop owners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fear, which is finally reflected in the form of the novel text. Those novels which have been banned in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especially the current novel, have a text form often modified in printing process. Although some novels have not caused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order to avoid breaking the law, the bookshop owners will make necessary changes to the content of those sensitive and politically connected part in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The inquisition and policy therefore influence the textual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novelists.
Key words: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Qing Dynasty, novel prohibition policy, textual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