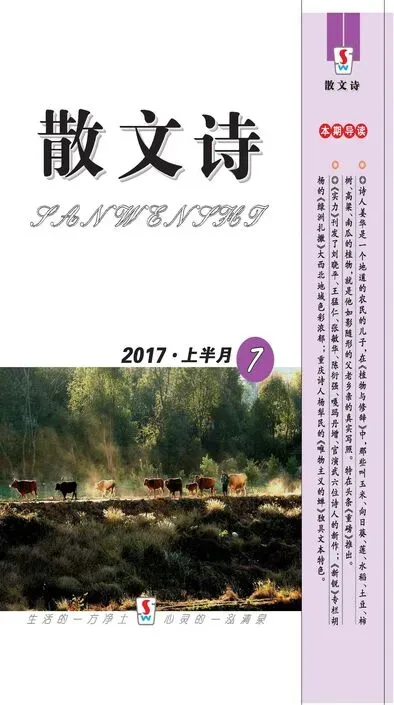奥尔丁顿的散文诗
◎董继平 译
◎耿林莽
奥尔丁顿的散文诗
◎董继平 译

理查德窑奥尔丁顿 (RichardAldington,1892-1962),英国著名意象派诗人、作家,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的一个律师家庭,童年在多佛和南方海边的乡间度过,17岁时出版第一部诗集。1912年,他参加了诗人休姆和庞德在伦敦组织的“意象派”诗人团体,并成为其最年轻的成员,并很快在这个团体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后来,他娶了美国女诗人希尔达·杜立特尔(即H·D),两人一边创作意象派诗歌,并对当时的传统诗歌进行批评,一边积极从事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翻译。奥尔丁顿是意象派的得力干将,在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阶段发挥过一定作用。
夜 景
我不眠地躺着,聆听。
在镀锌的大水箱里,水悦耳地滴下来,我身边的那只小小的手表让我的生活嘀嘀嗒嗒地逝去,圣玛丽修道院院长的钟声间或在这个区域沙哑地咆哮:叮当、叮咚!
沉寂。水更缓慢、更悦耳地滴下来,手表更轻柔地嘀嘀嗒嗒,窗帘在风中稍稍作响,一点隐约而困惑的月光悄悄溜进房间。
沉寂。我起身拉上窗帘。那迷蒙的白色月光让房舍交替变成巨大的块状和线条,变成水一般的银白色和强烈的黑色阴影。城里没有运动,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吗?一声火车的汽笛非常模糊、尖锐、清晰而又遥远地鸣响——比军号声还要清晰,声音尖锐得犹如流浪的夜鸟。一列火车正从马里波恩①或者维多利亚②驶出……
那汽笛声非常模糊、尖锐而又遥远地鸣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野鸟。这细细的、颤抖的汽笛声,突然让我那未曾得到满足的欲望、空荡荡的希望和模糊的想念,产生疼痛。
注:①②均为英国伦敦地名。
黎 明
这是夜晚,沉寂。
薄雾仍在封冻的堤坝旁边,薄雾躺在僵直的草丛上,围绕着白杨的树干。最后的星星熄灭了。鸥鸟从大海中鸣叫着飞上来,犹如一块块薄雾,犹如白布的碎片飘浮而过。它们经过之际,转动脑袋窥视。低垂的天空深深地呈现出紫色。
在远处耕耘过的土地上,一些鸻盘旋、疾飞,它们的尖叫充满悲伤、刺耳。那紫色飘上苍白的天空,变得更红。薄雾搅动。
耕马进入田野的时候,披挂在它们身上的马具铜器叮当作响。鸟儿们以散落的小群飞起来。薄雾颤抖,变得更为稀薄,升起。在冰上,那红色和金色的天空单调地闪耀。
人们越过解冻的土块叫喊,耕犁吱嘎作响,马匹在寒意中热气腾腾,那些鸻和鸥鸟消失了,麻雀啁啾。
天空金黄而蔚蓝,非常模糊而潮湿。
这是白昼。
最后的歌
最后的褐色麦束沿着被收割的田野而一路伫立,把长长的阴影投在秋天的日落中。
赫利俄斯①的马,在黎明洁白,在正午金黄,在夜里血红——这一天,一切都太短暂。
我的生活就如此,甚至如此短暂,夜晚降临,我从欢宴上起身,为生命的众神而干杯,把焚香投掷给死亡的众神,把一朵破碎的玫瑰投掷给爱神,走开。
欢迎一切!笑吧,这就是生命最后痛苦的结局。
注: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个性:诗人的生命———读《月光如箭:桂兴华散文诗新作89章》
◎耿林莽
与桂兴华相识是在1985年的哈尔滨,那次中国散文诗学会第二届年会可谓盛况空前,艾青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当时在《文学报》工作的桂兴华,在会上朗诵了他的散文诗《南京路在走》,以南京路人情世故的变迁抒写改革开放,给大家以耳目一新的冲击。
其后又是多年,桂兴华依然不断勤奋写诗,也不断听到他的各种行踪与写作成果的反响。去年春节期间,他来青岛小驻,看望朋友,也来看过我。思绪始终处于活跃状态的他不久就写出了一本新的散文诗集,转来让我写点文字,颇多感慨之余,也有了写点什么的欲望。
桂兴华的散文诗,属于昂扬的朗朗上口的风格,犹如他《南京路在走》的散文诗,朗诵效果很强,很有鼓动性,前些年他写了不少这类作品,有诗歌,也有散文诗。而在这部集子中,却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既有温柔委婉,又有思考,甚至不乏那种穿透性的锐气。
这部集子分了四辑,其中第一辑是写给他去世的爱人的,篇章中其相依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如在《月光如箭》中这样写道:“回家的路,不要太明白。”上海人的口语中“不要太如何如何”其实是肯定语,如“不要太潇洒”其实是赞美潇洒的意思。这里的“不要太明白”其实是“很明白”的意思。“今夜没有月光。/月光,会使四周更加凄凉。/原本隐蔽的,不想亮出来。/回家的路,不要太明白。”这里的“不要太明白”却透着凄凉,于是,“小区的这条道,不用这么宽了”,“我的悲伤,不用照耀”。这些都指向“最后一片温柔,已被你披走”。表达对陪伴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爱人的怀念,写得切实感人,不落俗套。这种贴近生活的写法,是桂兴华扎实的写作基点。
在这一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种凄婉的作品,可谓亲情散文诗在作者笔下写出了特点。
体现作者的思考,而且用散文诗这种形式写出其思想的是第二辑中的《被废弃的斗牛场》:
谁在出售还帶有血腥气的门票?
当初的一块红布,竟使一群群无知狂奔乱撞。
最易躁动的季节。风,也被挑唆。
可悲啊:来参观的与被废弃的,今天,踩着同一曲著名的节奏。
如果当年换成“逗”,就不会歩步见血。
那时候,习惯于你死我活,将残忍称赞为兵的矫健。
少年,最易被发动。根本没有一句嗲声嗲气的“逗”。太多的牛,也甘于被揪出来批斗啊!
这场蒙蔽,为何持续了这么久?
那块红布,充当了场外最痛心的解说。
关于“斗”与“逗”的联想与巧妙使用,“那块红布,充当了场外最痛心的解说。”于不动声色中,一句话把“带有血腥的门票”属性说明白了。在作者颇有分寸的含蓄中,我相信读者在这章散文诗中,会读出各自的体会。
在《驴:不蠢》这章散文诗中,很有臧克家《老马》的风骨,此处不仅是要给驴“翻案”,其坚韧的性格,恰恰是无声的劳动者的写照,当然最后拐到了胸前挂着相机的“驴友”身上,也是精彩的一笔。
在《嫉妒,在狠狠践踏》中,写出了明星的处境。《苦恼的长跑》写痛苦与健康的关系,即用“痛苦”换取“健康”。在《希望,已经闭眼——写在拉斯维加斯郊外免费加油站》中,作者体悟到的境况,反映了社会的一角,从独特的角度写出了赌徒的境况:在赌徒被压榨尽了最后一滴,也就是输光了最后一分钱之后,“残酷的创意”就是给你的汽车加上免费的汽油,让你离开赌场——Finalhope!(最后的希望),是多么残酷。
从上面这些作品中,一个善于从生活中攫取诗意的诗人已经可以站立在读者面前了。诗人的笔触从国外转向国内,在第三辑中有一章,可看作是具有哲学思辨性的作品。在《日全食:上海2009年7月22日的某一刻》中作者写道:
一扫半个世纪的恐惧与憎恨。
这么多人:会对黑暗,这么欢迎,这么企盼!
还在大白天,动用了满街的灯火,列队恭候!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这是光明向黑暗的一次大投降!
前所未有的妥协。
暗有暗的魅力。
这一刻:常年被否定的,偷偷在暗笑。
光明与黑暗是人们用来表达正面与反面的意象,其实就事物的本身是没有正反的,更没有对错之分,作者通过日全食五分钟的光明与黑暗的转换,透视到了事物的本质,这不仅仅是“暗有暗的魅力”,也是作者笔下散文诗的魅力。
桂兴华去年在青岛期间,与青岛的散文诗人做了散文诗写作体会的交流,其中与诗人方舟约定要相见的,不巧因故没见上,不久这位散文诗人故去了,桂兴华由是感慨,写下了《悼一位相约的青岛诗人》,“这一边的杯,还有余热。/那一边的酒,却浇灭了你的手机。/风衣里的手,不敢拨突然走远的号码。/只怪那天,海风太猛,掀翻了城角边的那条鱼……”方舟有散文诗专著《游在城市里的鱼》,作者的感情燃点,也随着“那条鱼”而点燃。
那几天,作者到那座城市的老建筑里静坐,细细体会旧城的文化与风土人情,写下了《塔楼咖啡馆》,从“打开的书,肯定有现煮的香味”里,他闻到了青岛这座城市的气息。
作者是一个感情饱满,随时都可以喷发的诗人,尤其是对历史的钩沉,像一个站在历史长河岸上的人,可随时看着每一个漩涡,每一朵浪花进行自己的思索。在《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红:1921——写在兴业里》《幸福巷19号的一盏马灯》等篇什里,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特别是《有的红,在艳丽中藏着毒》这一章,不仅是他看到的历史浪花,而且在作品中也掀起了浪花:
这一朵朵准备加工成鸦片、海洛因的罂粟花,在艳丽中藏着毒。
早些年,我并没有发现。
炫耀的袖章,就是那种红。
呼啦啦喊着口号的,也是那种红。
忙着改姓名、店名、路名,甚至改市名的,也是那种红。
最流行的疯从一块块布开始,把整叠的书扔进熊熊火堆,那么多字,在那种红中跌倒……
因此,现在当满眼晃动着红的时候:
我,不会马上激动。
这章作品同前面写日全食的那章的思想深度相同,“红”在这里有着独特的含义,也是属于作者自己的意象。从其中,读者也会体会到一些人生经历的斑点。
个性,是一个诗人的生命。桂兴华是一位个性突出的诗人,他的独特视角与写法,使散文诗得到了一定的丰富,也是他为散文诗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是一位勤奋的诗人,这些年成绩斐然,这一本散文诗集的出版,为他诸多成绩中,增添了一份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