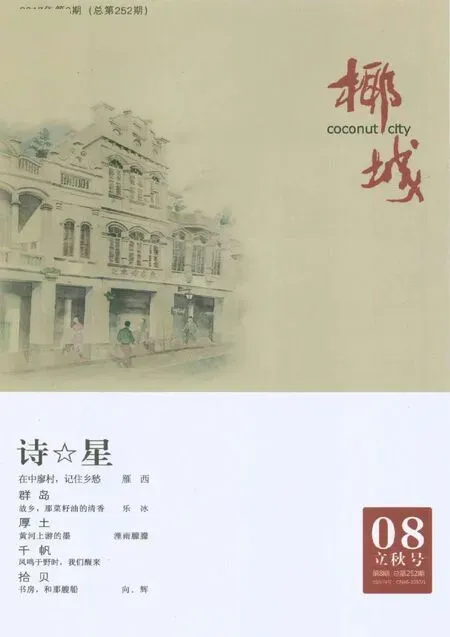燕大初期群星谱(上)
陈远
燕大初期群星谱(上)
陈远
陈远,河北武强人,历史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代表作《燕京大学 1919-1952》。
司徒雷登:一纸任命让他突然面对无数难题
191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任命打破传教士司徒雷登平静的生活。
那一年,他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从1905年来到中国传教,效果甚佳,不仅让他所隶属的南北长老会刮目相看,也让他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那一年,他已经在金陵神学院工作多年,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都得心应手,好几个计划,也正在展开。
正在此时,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的大学”。对此,司徒雷登的第一反应是“我实在不愿去”。
只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就会理解司徒雷登的这一反应。
在教会的计划里,即将成立的燕京大学由两所规模略小的教会学校联合而成。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联合,但是在其中之一的汇文大学看来,他们已经形成规模,将华北协和大学兼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华北协和大学看来,兼并不是联合。
双方都坚持新校名应该包含自己原有的校名,否则对于联合而成的新学校就不予承认。这样的争执令教会也感到莫衷一是,从1901年动议联合,到1918年两所学校校舍合并,争论竟然持续了18年!这还不算两所学校分别隶属不同的差会①,而差会之间又各有想法。
再看一看当年的校舍,据燕京大学早期的学生回忆,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的资产是这样: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室和实验室。
关于教员的情况,冰心当年的老师包贵思有这样一段记载: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里,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和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并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他会如何突围?
亨利·路斯①即亨利·温斯特·路斯 (Henry W·Luce):一场任命的博弈
好吧,如果经费充足,校址可以另改炉灶,
在南北长老会的任命下达的时候,几乎司教员可以重新选聘,司徒雷登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可惜的是,燕京大学的经费状况也是一团糟:当时领导这所联合学校的四个差会同意提供的经费只有35万美金,而在联合计划中,校园建设购置土地的费用就要花掉将近24万,剩下的11万,还不够拆除当时购置土地上的房屋,更不要说建徒雷登所有的朋友,都认为那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司徒雷登
但是司徒雷登的老朋友亨利·路斯却对他表示了支持。只是,在支持的同时,这位老朋友提醒司徒,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在明了任命无法撤回之后,司徒雷登按照老朋友的建议审查了燕大的经费,提出了接受任命的条件:他不管经费的问题。虽然这个条件最后只是一纸造新的校园。四个差会每年只提供4000美金,用来负担当时教师的薪水、差旅、房租、医疗费和休假,而在1920年,仅并入燕京大学的协和女子大学就有22名西方教师,更要命的是,包贵思说“经费常年有一半是落空的”。而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是当时美元的汇率出奇的低,这些经费在中国,只能实现一半的实用价值。
一句话,燕京当时的经费,即便用来应付日常的运转,就已经是僧多粥少,更不要提再聘用优秀的教师了。
但是,司徒雷登在日后所面对的困难,远远不止这些……空文,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对于这位老朋友,非常看重。
亨利·路斯是谁?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是说起他的儿子,不少人必然耳熟能详,那就是被称为“时代之父“的《时代周刊》创办人哈里。丘吉尔曾经说哈里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20世纪的50年代,被称为“卢斯的十年”,说的就是他。
父亲的名气虽然没有儿子大,但是同样了不起。
和司徒雷登一样,亨利·路斯也是在大学时代受到“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影响,改变了最初的志向,决定把一生贡献给传教事业。这样一个共同的经历,让路斯和司徒雷登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隔阂。
教会大学在中国的联合有一个背景,在此之前,日本的美国传教士由于差会之间的各自为战,错过了在日本建立像早稻田大学那样的机会。教会吸取了教训,决定在中国把分散的兵力联合起来,消灭差会之间的竞争。
在那场联合大潮中,亨利·路斯正是关键人物之一。早在1907年,为纪念入华传教一百周年,新教传教士们召开了“百周年纪念大会“,在那场大会上,亨利·路斯提议成立”教育总会“并获得通过。教育总会的职责,就是调查研究中国各地的教育情况,同时要求在同一地区从事教育的各个差会加强合作,建立联合大学。
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之江大学,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教会大学,正是教育总会的工作成效。
亨利·路斯和齐鲁大学的渊源尤其深厚,1897年10月13日,路斯夫妇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短短逗留之后,第一个长期驻地,就是山东的登州,任职于文会馆,也就是日后齐鲁大学的前身。《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就是在登州出生的。齐鲁大学联合建校的资金,也正是亨利·路斯募集的。
在当时,进教堂的美国人给传教士捐款已经成为习惯,但是为教会办大学捐款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让人们为一件陌生的事物捐款,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在10年之后,燕京大学创建之时,美国人已经了解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所进行的的事业,募捐依然是难度重重。
那时期的亨利·路斯,成了一个双料传教士:在中国宣传美国的宗教,在美国宣传中国。经过三年的努力,亨利·路斯为齐鲁大学募集到了充足的建校经费,之后齐鲁大学校址的选择和校舍的修建,也是亨利·路斯一手操持。1917年夏天,齐鲁大学校舍建成,亨利·路斯功成身退,从副校长的位置上挂冠而去。
一切像是安排好的,在路斯辞职后不久,他的老朋友,在金陵神学院任职的司徒雷登收到了教会邀请,出任即将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校长。老朋友特地向亨利·路斯发出邀请,让路斯陪他一起到北京看看。
一旦发现任命无法推辞,司徒雷登就发现,当初不负责经费问题的约定形同虚设。如果他不负责经费,只能接受他的想法无法实现的现实,得过且过。那既不是司徒雷登的性格,也有违教会任命的初衷。
要在需要的时间内募集到资金,司徒雷登就不得不投入战场。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老朋友路斯发出邀请,请他担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负责在美国募集资金。虽然在此之前路斯推却了众多大学副校长职位的邀约,但面对老朋友司徒雷登,他无法推辞。
路斯接受司徒雷登的邀约,老朋友的情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燕京大学是全新的系统,而不像之前的邀请,系统已经成型,他加盟之后,只能在既有的秩序里施展手脚,而燕京大学,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开创局面。
司徒雷登接受校长职位之后,校董会提名路斯作为副校长。然而,这个提名遭到了远在纽约的董事会的反对。司徒雷登给纽约回信,同时附上了一封辞呈。权力的傲慢在这时体现出来,纽约对于提名依然不准,连建议权都没有。
司徒雷登急了。
他把所有的理事都叫到北戴河,把自己和纽约的信件往来展示给所有的理事。理事会立刻给纽约方面写了一封紧急信,最后,董事会终于妥协了。
司徒雷登就是这样,对于认定了能给自己带来帮助的人,会无条件地挺下去。另一方面,这其中也包含了司徒雷登对于事权的认知:教会既然任命,就要有充分的权。在日后执掌燕大的生涯里,司徒雷登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同事们的,但吴雷川是个例外。
亨利·路斯的上任,使司徒雷登稍稍可以从令人头疼的经费问题中抽出身来,司徒雷登事后回忆说:“就在这一篇黑暗之中,亨利·路斯博士可以算得上是一丝曙光。”
吴雷川:尴尬的身份认知
20年代的一个盛夏之末,燕京大学朗润池畔,一位老者正步态沉稳地走来。
突然天降大雨,手中无伞的老者并没有惊惶奔跑,“还是和晴天一样从容庄重地向着家门走去”。这一幕,给在燕大读书的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近60年后,冰心书写《关于男人》一文时,还觉得其慈颜如在眼前。这老人,即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
不过,旁观者眼里的外在从容,与当事人的内心,未必可以划上等号。
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吴雷川,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身份认知之中,由于这种尴尬的身份认知,吴雷川在燕大任职期间,工作得并不愉快。
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回收教育权运动,是吴雷川来到燕京大学的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才能了解吴雷川何以来到燕京大学以及他的任职处境。
简要言之,非基督教运动是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知识界针对传教士使中国全面归化越来越强烈的企图所做的自觉抵制,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人都参与其中。这场运动越演越烈,最终上升到政府层面成为国家意志,演化为回收教育权运动。在北洋政府和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中,核心内容有两条:凡外国在中国所设置学校,必须遵照教育部颁发法令和规程,并向政府申请注册批准;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看一看吴雷川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吴雷川正是那一时期出任燕大校长的最佳人选: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8岁的吴雷川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
1906年,吴雷川出任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这是清廷效法西式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
1911年后,短暂出任杭州市市长一职。
1912年任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参事,主管部内秘书工作。
1915年接受圣公会的洗礼,开始积极参与基督教活动。
1926年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
翰林院编修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人群的身份标识,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是吴在教育界的资历,杭州市市长和教育部的经历暗含的是当时政府的认可,在燕京的执教经历和基督徒这一身份,则让教会接受起来不是那么困难。
一个人之前的履历,只有和之后的经历参照,才会显示出无穷的意味。
在1929年,还有比吴雷川更合适的人选吗?
对于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来说,答案是没有。
但对于吴雷川来说,只有他在进入燕园之后,才能感受到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对他的角色期待。
尽管吴雷川起初非常重视身为中国人校长的意义和重要性,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同事,校长是一个大学行政人员,但他很快认识到,校长只是一个忙于其他事务而不能密切关注校内行政的名人。
一切大权,还是在此时职务是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手上。
校务委员公开会,地点是设在司徒雷登家中;所用的语言,是吴雷川并不通晓的英语,司徒雷登并非有意排斥,但吴雷川的反应是不再出席会议。
司徒雷登和吴雷川两人对于校长这一身份的不同认知,导致了吴雷川只有一条出路:辞职。
辞去了燕大校长的吴雷川,依然留在燕园里教书。燕大校长的身份与他的期待有差距,但是燕园里的一部分依然是他的理想。冰心看到的那个形象,更符合解决了身份认知问题的吴雷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