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姜师傅
老姜师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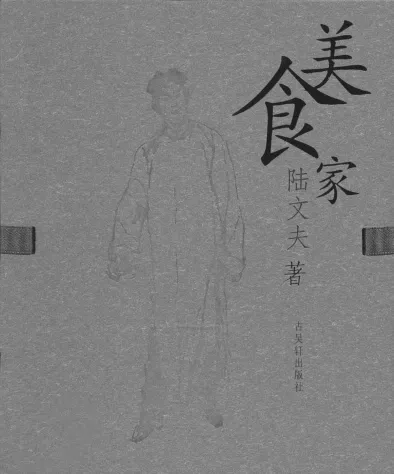
美馔的呼唤
华永根

苏州杂志社的文瑜兄约请我去他社里吃顿晚饭,应该说吃顿饭不算什么,但这次吃饭我激动不已,苏州杂志社,地处城南一条小巷内,在那里走出一位著名作家美食家陆文夫先生,他常年在那里办公,撰写出《美食家》《小贩世家》等多部著名文艺作品,直至现在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文瑜兄告诉我晚饭烹者为陆文夫先生之婿姜洁先生,他虽不是专业厨师,但尤爱烹饪,家常菜做得一流。陆文夫先生在世时常吃他做的菜点,时不时还表扬他“菜烧得好”。也就是说这次吃请烧制的均是姜洁先生定制的陆氏私房“家常菜”。当前社会,约请吃饭是件麻烦的事,吃饭得告知人家:“今天吃什么菜”“在哪地方吃”“与哪些人一起吃”,最后才能让人决定是否赴约,今文瑜兄的请吃这些都对我的路子,吃陆文夫家中“家常菜”,晚宴设青石弄小巷深处,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叶圣陶故居内,来的人有书画家、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等等,这些聚吃条件能让人不激动吗!
那日宴请客人落座后即人手一份红枣鸡头米百合汤,刚上市鸡头米飘出一股清香,洁白几瓣百合,枣红色汤里放入老法的红糖暖人心胃,两粒红枣散发着扑鼻的枣香,丝丝甜味汤口真叫人吃了欲罢不能,在座的有人戏称:吃了“宫暖”。
前菜有十只,排列有序放在桌上,上面有我最喜欢吃的盐水籽虾、糟味仔鹅、五香牛肉等,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一款熝味黄鱼,一块块蒜瓣肉,鱼肉鲜美,咸中带着黄鱼肉的清香,淡淡的熝香味让人食欲大开。另有一盆南瓜玉米,据说是陆文夫先生生前最爱,烹调上简单易之,但在食材选择上尤为重要,此品为陆先生女婿特地从无锡农村带来的,蒸熟即吃,那南瓜玉米散发阵阵热气,像是送来的农家田园清风。我吃过许多此类农家乐,但今天食之真感不一样,南瓜酥烂粉嫩,回味甜津津的,玉米的糯感又高一层次,而且在咬嚼中还有果汁绽出带着丝丝的甘甜。吃这些农家杂粮时得用手,亲力亲为,我一直感觉,凡是吃的东西能用手抓着吃的,都吃得香,有滋有味,这可能与人类吃食本能有关。
这次吃食热菜亦有数十只,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头道热菜是只糖醋排骨,此菜一直受到陆先生表扬说:“烧得好,味道到位!”那菜酱汁裹满排骨上,枣红色泽,满满一盆,我吃上一块酸甜适中,上口时酸甜味,后是肉的咸鲜味,最后咬碎骨头,其骨汁味美膏厚,味道层层递进,吃后口齿留香。轮到酱烧脚圈上桌时我是满心喜欢,那盆脚圈,红红堂堂地闪着油光,端上桌时,肉圈还在不时抖动,可知火候到位了,我挑起一块最大的脚圈放入自己盆中,迫不及待咬上一大口,肥腴油滑肉皮连同酥烂入鲜的精肉一同进口,满满一嘴巴,一时还说不出话来,邻座的文联画家吃后连声叫好。不是我贪嘴狠吃一大口,实在诱人,咽下这口后,我细细品味其味,这些脚圈烧得十分用心,火候恰到好处,肉中香料有点睛之妙。五香八角特别是还用了丁香等,猪肉如与这些香料同烧慢炖,其味悠长,味鲜不俗,回味无穷,就像肉中施了魔法一样好吃,尤其其中骨头上肉酥烂见鲜,还有旁边蹄筋,软烂鲜糯。此菜做法堪称一流。饭后姜师傅告诉我,此脚圈,他在菜场中找了好几家肉店,最后选择一家肉店,出售的是一种黑毛香猪,并特地关照在切割脚圈时大小匀落,皮与骨不能切碎。脚圈为猪爪上面一段,俗称“脚馒头”,因此要买到好脚圈才可能做出好菜来。他还说,肉中香料都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了经验,把控数量,点到为止,啥时投放,烹前、烹中、烹后都有讲究,特别是丁香,用多会刺舌反而不香造成异味,不用难出香气,故而是一种调香的手法。整盆脚圈底部还用花生垫底,焖烧中花生仁酥烂软糯,吸收脚圈中卤汁,好吃非凡。我听后真为他潜心钻研烹调技艺而感动。
这次请吃吃食数量多,盆面大,为了减少浪费,临时还叫停几样大菜。令人难忘的菜品有干蒸童鸡,原汁原味,鸡油飘荡,鸡嫩汤鲜;传统两筋页带有家常风味让人大快朵颐;那盆香炸带鱼,鲜香无比,在柠檬汁的推动下,越发诱人。在热菜中姜师傅特地做了一只他最拿手的姜母肥鸭,满满一砂锅的“硬菜”,鸭肥汤美,此乃滋补佳品也,还有的菜……那晚的主食是苏州的虾肉馄饨,那一只只馄饨细巧,味道鲜爽可口,虽然已吃饱,但还是吃了几只。
那晚宴毕,走出餐间,皓月当空,撒下满地银光,院落里凌霄花开得火红,墙角紫竹在湖石后时隐时现,那棵高大的玉兰树挺拔葱郁,满地鹅卵石泛着白光,衬托起园中的夜景。我走在回廊里,与文瑜兄诸友告别,想到刚吃的满桌美馔,我在餐桌上说的多是吃食废话,听到的都是昔时师恩、友谊、亲情之言,实在感动不已。像我这样“日图三餐,夜图一宿”的人,谈吐差距怎么这样大呀!
一人撑起的盛宴
常新

我不知道“美食家”的最早出处,以我的认知水平,这个称谓来自陆文夫中篇小说《美食家》。在陆文夫之前,所谓美食家,应该是被称之为“饕餮者”“好吃的人”“馋痨坯”等,当然也可说是“饮食鉴赏家”,但都没有“美食家”来得有文化,来得堂堂正正、雅致倜傥、言简意赅。如今社会各界倒是心态端正,朋友圈里,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自称“吃货”。
《美食家》对我的教育是多重的。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早春,《收获》杂志,灯光下父亲的话:你看看吃面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岂止是吃面,《美食家》简直就是苏州小吃和苏帮菜的词典。但是,年少的我,更关注的还是高小庭对朱自冶的斗争,可是看到最后就是不明白谁胜胜负。小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表现的主题是什么?看来都没有,但就是读得有趣,有滋有味。联想到之前看过的汪曾祺《受戒》,开始有点觉悟:原来,小说也好,文章也好,不必都像《金光大道》《闪闪的红星》一样需要有好人坏人的,需要拔高人物和升华主题的。
副作用也有,我好像不大能做对语文试卷的阅读理解题了,分析段落大意更是会掉链子。还好,我初中毕业考考得还行。
顺便提一句,刚高中毕业、准备上大学的那年夏天,我看了电影《青春祭》,张暖忻的这部片子给我的震撼和《美食家》类似,让我又有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让我对以后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有了很大的观赏心理准备。
一晃就到了今年夏天,我在苏州杂志社结识了陆文夫的贤婿姜先生。那天,姜先生从早忙到晚,包揽买汏烧,独霸红案和白案,切剁泡拌卤,炒爆煎蒸煮,挥汗如雨,热气腾腾,一人撑起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受邀的美食家们和姜先生现场切磋,印证武功,我实在插不上话,只能顾着对付眼前的佳肴,把个“馋痨坯”的角色演得十足十。
其实,我当时特别想问问姜先生,是不是陆老爷子吃了他做的菜才把女儿嫁给他的?
老姜见“老姜”
亦然
老姜是姜先生,本来应该称姜师傅的,但是老姜是一位高段位烹饪爱好者,不是职业厨师。我非此道中人,暗忖大概不好叫姜师傅。又不很熟悉,初次见面就称老姜似有不妥。现在还是称老姜只是因为冒出个有趣的现成标题,不得不冒而犯之了。
说“老姜”也颇为冒犯:晚宴上被推到首席就座的是烹饪大师华永根,市烹饪协会会长,这一行当里的“老姜”确定无疑。可是我还是觉得使用这个词没有把我心里的敬意表达得充分到位。
当老姜被拉到“老姜”旁落座的时候,菜已经上齐了。菜没上齐他执意不肯入席,如同小说没有写完定稿作家绝不愿将之示人——老姜是晚宴的掌勺大厨。
两人也不相识,但面对满桌佳肴他俩比谁都亲。
一位江湖盟主,一位绿林高手。老姜见“老姜”,两眼放毫光。
满满一桌子菜是老姜的满堂儿孙,又是见到真佛,两眼放光是自然的。“老姜”呢,难得看到业余好手,聪慧可教,自是开心。就像武林,往往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在高人眼里,看到能够传承绝技的人太不容易了。一肚子秘笈都激动起来,挡都挡不住。我等在座的吃瓜群众也是两眼放光,满桌目光刷地罩住他俩,机会难得,美食真经谁不想听几段啊。而且大家心里有谱,专业高人与业余好手的对话,定是深入浅出而又精彩生动。
老姜见“老姜”,话题个个香。“老姜”点评菜肴,一盆盆说过来,言简意赅,比如红烧脚圈的诀窍就是一块黄酱,比如干煎带鱼要紧的是得“糟”一下,而那盆老姜的创意之作黄鳝螺蛳则是鲜美有趣。连我都听得跃跃欲试,原来烹饪技艺竟然如此家常啊。
开始觉得这老姜胆儿挺大,敢跑到苏州杂志社开宴,这可是美食家陆文夫开创的地盘,就算陆老师不在了,还有陶老师把守着呀,这不是摆擂叫板吗?后来才知道老姜正是陆文夫的女婿,曾经耳提面命,深得岳父真传。于是“老姜”深情追忆,正是陆老师的名作《美食家》,才让我们这些人,还有广大吃货,有了一个能引以为骄傲的共同姓名。
老姜见“老姜”,语亲情也长啊。
我有一餐饭,足以慰风尘
苏眉

如同一个好中医可以康健一方人物,一个好的厨子足可以改善一个区域人们片刻的心情,而家中有一个善于做饭的人,则是一生之中长久的福气,像源源不断的温泉,足可以抵御整个世界的寒凉。
吃罢四季宴、花之宴、虾籽宴、白鱼宴、大师宴,陶老师说我们今年吃吃寻常人家菜,第一位,便是陆文夫先生的女婿。
当然期待,地点选在苏州杂志社,晚餐,我早早便去了,穿了一件蓝印碎花布长袍,双鱼耳环,舒服潦草打扮。吃家常菜,一种是细气女主人做出,青瓷雅盏,餐前香茶细果,甜羹清汤,精致小菜,简直要柔声浅笑,屏息静气相待的。另一种则粗盘大碗,只讲真味,可是要撸起袖子吃的,布袍子可席卷一切场合,我作了折中妥当的准备。
终究等来晚餐,陶老师还叫了几名雅士,另有美食界泰斗华老师,大家寒暄几句便落座了,凉菜已备,像极一个家常,丰衣足食味道,盐水鸭、清水毛豆、牛肉、盐水虾、凉拌黄瓜、凉拌肚片、糟鱼、千丝大虾、鸭肠胗干,皆清爽好味,落胃菜蔬,吃下去马上心身一体,像看到王羲之的字,笔笔入眼。凉菜前先有一碗甜汤,大枣百合鸡头米。
然后是热菜,大锅炖的红烧脚圈(猪蹄里最精华的一块),煎带鱼,煨了许多大蒜瓣的红烧黄鳝,糖醋排骨,大锅的煨鸡汤,油豆腐塞肉与百叶包同煮,青菜炒毛豆,猪皮炖海参,辣炒鸡块,另有一道菜肉馅儿大馄饨。
众菜之中,我尤爱那道盐水虾,一只只细心剪出,每一枚都是精心打扮的新嫁娘,鲜咸之中略加糟料,原料自然是好的,新鲜纯美之中有一种出其不意的美艳,仿佛可以看到六月里荷风清凉的湖面,采莲女含笑半拂袖,不过惊鸿一瞥,已消失在无尽的绿意中。
林文月的《饮膳札记》写得又朴素又美貌,她道:“行家多能在寻常小菜间辨识厨者之用心。”食者,良人也,烹饪为二,好料为一,其三是吃客的落定与投机。
本色
胡笑梅
立秋后的苏城,寡燥,微凉。呼朋唤友闲谈小坐,便是镇湖黄桃、同里鸡头米似的,渐多起来。
夏末,温热犹存,沿十全街林立的店铺,踱至老苏州茶酒楼,巷北向西又巷北,拐入滚绣坊青石弄。一下子,从形色现代秒回本色民国,连气场也瞬间两样了。鹅卵石铺就的小路,泛着青色的时间之光。返璞归真的粉墙黛瓦,素面朝天的回廊庭院,闹中取静。这是繁华都市中一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雅舍。耳边聒噪的各种叫卖声、游人喧闹声、汽车喇叭声戛然而止,发际间,只剩下几瓣细微的虫鸣蝉唱,还有几朵稀星流云。
是夜,月色淡淡,风儿暖暖,一切都刚刚好。同道好友,齐聚叶圣陶故居,谈天说地,把盏吃茶,品苏味儿美食,味蕾如夏花绚烂盛开。大厨是“美食家”陆文夫之婿,每一道佳肴都是陆文夫生前所钟爱的地道苏帮菜。滋味之赞自不必说,仅色彩流光,就令人神摇目夺,魂不守舍。
席前点心是红枣鸡头米,枣酡红与象牙白,西域贡果与江南水仙在一盅甜品中晕染跳脱,整桌菜都为之风情万种起来。
前菜有:碧绿生青的盐水毛豆,翡翠墨玉的醋卤黄瓜,金黄橙红的南瓜玉米,百合丝滑的白烧牛肚,金雀花黄的盐水籽虾,葡萄酒红的五香牛肉,莹白银亮的卤味黄鱼,淡黄粟面的开洋干丝,米灰浅咖的糟味仔鹅和海水鹅什。恍惚阴差阳错,我们从私人定制的深夜食堂,走进一爿彩帛锦缎铺,处处姹紫嫣红开遍,斑斓柳绿争艳,五光“食”色,神气“食”足。
热菜有:蜡黄油亮的干蒸童鸡,古粉紫红的糖醋排骨,玫瑰宝石的酱烧脚圈,柠檬赭黄的香炸带鱼,烟雨青灰的螺蛳鳝段,亚麻麦秸的面筋百叶,珍珠奶白的皮肚蹄筋,琥珀琉璃的姜母肥鸭,鲜绿滋透的青菜毛豆。这哪里是烟火家常?俨然冷暖色彩的跨年盛会,荤素食材的绝妙搭配,“食”里洋场,“食”全“食”美。
主食是虾仁馄饨,红的虾,绿的菜,红肥绿瘦,红情绿意,在青花瓷盘中厮守到地老天荒,不离不弃。
良辰美景,宾主尽欢。相遇苏帮美食,养眼;邂逅苏派文人,养心。闭上眼,把味觉交给思想,把视觉交给心灵。满桌的缤纷溢彩,艳而不俗,色香味俱全;团坐的文人画士,契阔谈宴,咀咀嚼嚼,心心念念——
本色!
家常便饭
陶文瑜
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当编辑有不少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看了别人的稿子可以有所启发,从而博采众长了,实在并不是这回事。
事情要从姜浩说起,姜浩早就认得了,只是不久之前才知道他烧了一手精致的家常菜。一般的理解,烧烧家常菜的,不过是江湖中人,似乎饭店里的厨师才是武林高手,其实未必,厨师服务的对象只是笼统的顾客,他才不会在意张三李四什么的,因为这是他养家糊口的工作吧,而家常菜是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红烧白笃,这是满怀深情的劳动啊。饭店里吃的是人情世故,家里吃的是人之常情吧。
言归正传,说起姜浩,首先要提着的就是红烧大肠。说出来不怕难为情,姜浩带了一锅刚烧好的大肠来青石弄,我竟有流口水的感觉。姜浩说,大肠洗起来麻烦,他花了两个多钟头。
我母亲生前也拿手红烧大肠,这道菜的要点是洗得干净,然后是浓油赤酱。我母亲买了大肠,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洗干净放在煤炉上,烧得差不多了就封好炉子去上班,待傍晚回来,就有一道烧好的小菜了。
家常菜其实是从前记忆和生命留痕啊。
俗话说吃啥饭当啥心,吃了姜浩的红烧大肠,我想到家常菜其实是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请姜浩来烧一桌家常菜,再听听姜浩的人生故事,不是很有意思的文章吗?更何况工作是在吃香喝辣中进行,多有意思啊。
姜浩是很兴奋地接受了我的想法,他实在是热爱这个生活吧。这与我和书法有点仿佛,我是看见毛笔就手痒,接到写字的生活,整个身体都是轻飘飘的了。所谓犯贱,大抵如此,然而在我心目中,凡这样的犯贱,光彩照人。
当然,姜浩的厨艺要比我书法功夫高明许多,这一天聚在青石弄里品尝的人,全是一副水到渠成的酒足饭饱。
百叶炒肉丝和两筋叶我吃了好多,百叶是姜浩在无锡采购的,我一向认为,无锡的工业、农业和百叶,在众多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
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骨。
说起来这道菜也是我母亲的拿手好戏,我们虽然是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但日子不至于捉襟见肘,只是我母亲是十分节俭的人,家常便饭小荤居多,这或许也是我对百叶炒肉丝亲切的原因吧。不过凡有客人来家里,我母亲会花不多工夫,信手拈来似地做出来几道小菜。而这几道小菜之中,必有糖醋小排骨。
那时候我刚好是恋爱的年纪,发现了母亲这个特点,就三天两头在饭点带上女孩回家,看到我母亲在冰箱和炉灶前快乐地来来回回,我以为自己意外地尽了孝心。
不过我母亲烧的糖醋小排骨,最后还要淋一些香油。我曾经和老恩师华永根提起过,他说老苏州也有这样的套路。
隔一天遇上姜浩的时候,我说你不如开一家饭店吧,就叫老姜师傅,你本身姓姜,还有俗语说姜是老的辣。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有灵气,就在朋友间吹嘘,最后大家写文章的时候,薛亦然的题目是“老姜遇‘老姜’”。其实我本来要写的是“老姜师傅”,所以有了最初的感慨,这里也是文章的前后呼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