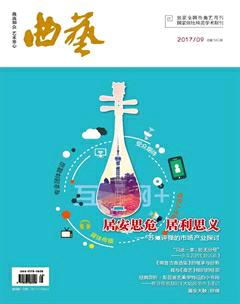“五家”
侯耀文
按照我父亲侯宝林的说法,要做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必须得具备“五家”的条件。哪“五家”呢?就是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杂家。从这个讲法可以看出,当初家父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也确实是按照这个讲法一直在督促着自己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高度去攀升。我父亲的这个说法,不仅是对他自己的要求,并且还影响了相声界的其他人。当然,能受影响的人一定得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如果人家自己根本就没有要当好演员的想法,干吗非得费好大的劲向这“五家”的目标去努力呢?那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要知道,往这“五家”的目标努力要刻苦发奋,甚至必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在这方面相声界中谁做得比较显鼻子显眼呢?我给您介绍一位——姜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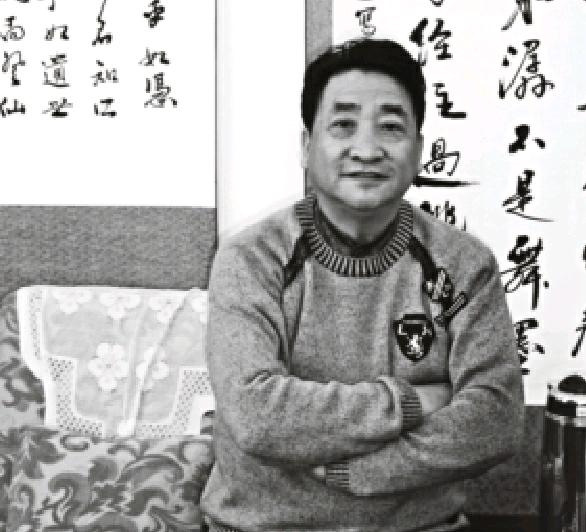
说起姜昆在“五家”这方面的追求,我必须首先声明一点,对任何人都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人无完人,更不能说他自己就是这“五家”的代表者,因为目前正是他奋力向最高艺术境界攀登的过程中,而不是最终的结论。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也只不过是这个过程,无非是想让大家明了我们在进取时的难度。
姜昆这个名字,在中国不用加更多的注释,其实根本就不用加任何注释,因为这个名字和这张脸中国人太熟了。干吗中国人呀,据姜昆自己说,有一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先生跟姜昆一起走(怎么碰上的他可没说),当布什看到很多中国人都跟姜昆打招呼的时候,他急忙指着姜昆,对其他在场的中国人说:“我也认识他。”说完以后布什先生竟然流露出特别满足的神情,而且好像心里踏实多了。就凭这件事,我看说姜昆是“外交家”和“政治家”就足够了。
姜昆爱文学,如果有机会各位可以到他家看看(每天别超过五六百人,多了接待不了),书架上所收集的古今中外名著相当丰富。这可并不是摆设,能把这些书读下来,又能有机地和相声专业结合起来,才正是一件难事,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比如说姜昆表演的相声中,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作品如《朦胧诗》《诗歌与爱情》《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等,都体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追求,而且也正是这些作品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他才有了今天这个知名度。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文学是他相声的底蕴。当然姜昆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专著还没问世(我觉得不一定非有这方面的书问世,还得签上名字再卖,太累),因为我们的专业是相声,能在相声中表现出来不就行了吗?我觉得行。
在艺术上姜昆执着的追求,恐怕外行不全知道,因为观众只要看见他“吃肉”就行,没必要非得知道他是怎么“挨打”的。记得1994年春节晚会,姜昆拿了一个作品进组,当时审查没通过,又得重新创作第二段。领导一看,还不如第一段呢。再弄吧!又设计第三段,写好之后,负责同志说:“跟今年晚会不搭调儿,你再试试写一段。”刚写好,上级的意见就回来了,“姜昆,你不写讽刺的行不行,写一个让大伙儿都高兴的。”此时的姜昆已经不像刚进组的时候那么鲜活了,已经开始躺在床上写相声了。就这样一连枪毙了六个作品。您再看姜昆,脸是绿的,眼圈儿是黑的,眼珠儿是红的,如果当时想买帽子,肯定得比原来小一号儿了。但是,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作品参加晚会,作品叫什么名字我现在都记不清了(为什么?您知道!)。反正在艺术上能有这种不屈不挠精神的人,要再不算“家”,实在是没有天理了。
我这次重点要介绍的姜昆是一位杂家。历史上有名的杂家不多,因为跟别的“家”相比,雜家有点儿档次不高,“杂而不专”,这就不算好名声。再有就是能杂即闲,就是说杂家都是没事干闲的,要不怎么叫“闲杂人等”呢(到哪儿都禁止入内)。再有,杂家这个职称,没有什么界定,也没有个尺度,究竟杂到什么地步,杂到什么程度,杂到什么规模,怎么能杂出个高低上下来,都找不着人来评定,所以一般人对“杂”不感兴趣,而没有尺度的事又是最难干的,所以还有谁愿意跟这路“家”较劲呢?
那相声为什么要求做到杂家呢?因为相声本身涉猎的方面太广了,得有点儿无不知百行通的意思。而姜昆做杂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位高人告诉他说“功夫在诗外”,就这句话算把姜昆给坑了,开始“杂”起来了。头一样,他开始收集钱币,为什么先收集钱币呢?他说当杂家没钱可干不了。于是就东跑西颠,花了不少钱,弄了几手提包的铜钱来。擦汗之余找了一位专家来帮助考证,结论是花的钱比收来的币价值高。得,这头一样就办砸了(哪位想要,可以拿走,就在床底下放着呢)。
知道错了就改,这得算有悟性。于是姜昆改项收集古董。一次,听说河南拉来几卡车的出土文物(您听这数量就瘆得慌),姜昆花了几万买了一个“东汉”的说唱俑。据他说,这东西只有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再有就是他这个了。当时我跟他打听过,还有没有,给我也来一个。他说:“我给你问问。”后来怎么也问不着了,听说卖俑的那批人进公安局了。原来这批东西是当地人新做的,把一些专家都给蒙了。您瞧,这事又算办砸了!
后来,听说姜昆又改项收集字画了。那天,我去他家,他指着墙上的一幅油画对我说:“这怎么样,够棒的吧?”我问:“多少钱买的?”他说:“一万二。”我问:“值那么多吗?”他说:“现在不行,得等着,过一二十年这位画家成了名,一万二准能卖出去,没问题。”当时我心里说,这位画师,您快点成名吧,要不然姜昆离砸了又不远了。
回到家里,我仔细一琢磨,姜昆这位杂家怎么老“砸”呀,哦——我明白了,当初我爸爸那“杂”字儿呀,兴许写错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