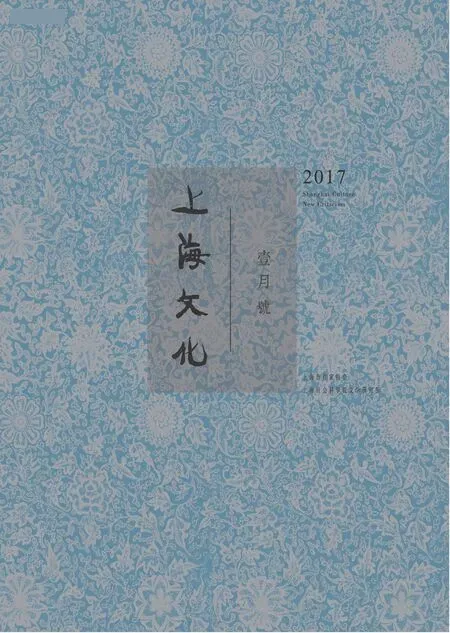炼金,追鱼,或捕风 关于文学批评
金 理
炼金,追鱼,或捕风 关于文学批评
金 理
我们今天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想象,或者说诉求(希望文学批评承担的功能),好像跟1980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在变化的情况下,与其去提取文学批评的某种本质,还不如先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存在。很多人希望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炼金术”,把我们这个时代最一流的作品、最顶尖的作家选拔出来,这当然是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不是唯一的功能呢?本雅明曾以大量精力去处理二流作家,那些在今天文学史上根本已经找不到名字的作家,恰恰是通过寄居在本雅明的批评文本当中,让我们一瞥其存在。那么本雅明的用心是什么?当然,二流作家不会因为得到一流批评家的认真对待就声名鹊起、文学史地位拔高;但或许可以说,二流作家有可能激活了文学批评的某种问题意识。
清末林译小说中品类最多的是哈葛德的作品,当年一纸风行,然而今天即便我们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上也不会出现其大名。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倒是解释过:“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小说,亦由于是。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哈葛德“并非高品”,绝非一流人物,但是其作品结构精密,恰可弥补中国古典小说夹杂骈枝的缺陷。如此说来,研究者若将问题意识聚焦为吾国文学现代转型,那么这位“文学史上消失的作家”,兴许不能被轻轻揭过。
类似的,我们通常说19世纪40年代是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的时代,可是据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提示:现在留存下来一些当时书店里的畅销书榜和最受欢迎的作家名单,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没有一个在榜单上,而榜单上实际出现的作家,今天的我们全都不认识,而当年他们的读者,可“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这些作家尽管进入不了文学史,但是如果想要理解当时人对文学的想象,其实离不开这些现在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类比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如果要理解今天的人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庄严肃穆的大学课堂、研究会场等当然不能忽略;但是也不妨将目光转向人流拥挤的飞机场、火车站,我们是不是想过,哪些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会出现在上述地点的书店内。
把这些方方面面的信息集合起来,兴许能获取我们这个时代“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这个说法得自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的启发。葛著提出极有创见的命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我们以前的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精英思想史”,叙述、罗列的是少数思想天才的成果。葛著举例,一提及宋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往往就是如下一条线索:从周敦颐到邵雍、二程、朱熹,前后加上张载、吕祖谦,左右加上陈亮、陆九渊,这条脉络似乎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思想精英的思考,往往是“突出”于历史背景之上的,是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就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的“历史的断裂”, “断裂是与常规的轨道脱节,与平均的水准背离,它常常是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可是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提供给、作用于普通人去应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也就是说,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过去思想史著作一再大书特书且加以编排谱系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一般思想状况相关(其地位确认往往出于“回溯性的追认”)。反过来,有些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或著作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过印迹。总之,“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
二流作家有可能激活了文学批评的某种问题意识
史学家沟口雄三有个很精彩的比喻:如果我们要研究鱼,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把鱼一条一条钓离水面,但也可以选择其他方法,不要把鱼钓起来,而是你自行潜入到水底,去观察鱼在水里面游弋的姿态,鱼跟鱼群构成的关系,鱼跟周围的动物、植物构成的关系…… “单独观察一条鱼而绝不可能了解的鱼群的生态或者鱼群生息的海底生物链,这才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倘使批评要去获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可能就不能眼光只盯着那条体型最大的鱼,也不妨去追踪那些样貌上还不具备太多特殊性的鱼,在那些“不具备太多特殊性的鱼”身上,可能负荷着一个时代的重量与情感结构。
在那些“不具备太多特殊性的鱼”身上,可能负荷着一个时代的重量与情感结构
提起盛唐,我们会说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是李杜的时代。但李白与杜甫这两位站在巅峰的诗人,实在不能代表盛唐时期诗歌的典型风格,倘要求取当时诗歌的典型风格,倒是必须得去关注次一等级的诗人,细读他们的创作,辨析其诗艺的展开所体现的修养、感觉与才性。恰如宇文所安所言:“我们的目标不是用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炼金术之外,文学批评应该匀出精力,去追踪那些“一般的鱼”,藉此获取一个时代“实际的文学标准”,以及“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在此之后,我们反过来才能体悟,那条体型最庞大的鱼,何以如此气势雄伟。
进而言之,文学批评的对象,在个体的鱼或鱼群之外,还应包括富有生命的鱼群生态、动态。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的“风气”:“一个艺术家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作者所处“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便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换言之,“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风万状而无形,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从四面八方吹来。同样,一个时代的文艺风气,得自于精英的制作,也少不了“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它们杂糅在一起,或轻或重,围绕在创作者周围, “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钱先生还提示,风气是会代兴的, “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作为捕风者,文学批评当能察势观风。一个时代中同时有无数股“风势”,有如日中天、莫之能御的飓风,也有起于微茫、却伏脉千里的微风,说不定微风有一天也会变成飓风。吕思勉先生曾以地质变化作比,“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今天我们身处颓靡、涣散的时代,实则波澜不惊的表面下未必不存龙蛇起陆的迹象。文学同然,我们认真对待“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也不是一味迁就,而是在平和的“风化”中细绎“山崩的所以然”,知常待变,会不会迎向又一轮灿烂的文学革新?
❶ 陈寅恪: 《论再生缘》,《寒柳堂集》 第67、 68页,三联书店2009年9月。
❷ 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第64页,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
❸ 以上参见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9~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❹ 沟口雄三: 《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 《中国的冲击》第218页,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7月。
❺ 宇文所安: 《盛唐诗》第2页,贾晋华译,三联书店2004年12月。这一点蒙孙甘露老师提醒,特此致谢。
❻ 钱锺书: 《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锺书论学文选》 (第六卷)第1、 2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
❼ 吕思勉: 《历史研究法》,转引自罗志田: 《假物得姿:如何捕捉历史之风》,《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历史学家对于 “风”的论述,还可参考王汎森: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收入氏著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2014年1月。
❽ 黄德海兄在读完本文初稿后,曾提示:“体型最大的鱼,也往往就是漏网的鱼”,那么这一部分如何影响 “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并且提供施蛰存先生 《唐诗百话》中唐文学成就高于盛唐的判断——这些建议本可丰富本文的论述,列于此处,留待日后进一步思考。亦特此向德海兄致谢。
编辑/黄德海
一个时代中同时有无数股“风势”,有如日中天、莫之能御的飓风,也有起于微茫、却伏脉千里的微风,说不定微风有一天也会变成飓风
——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