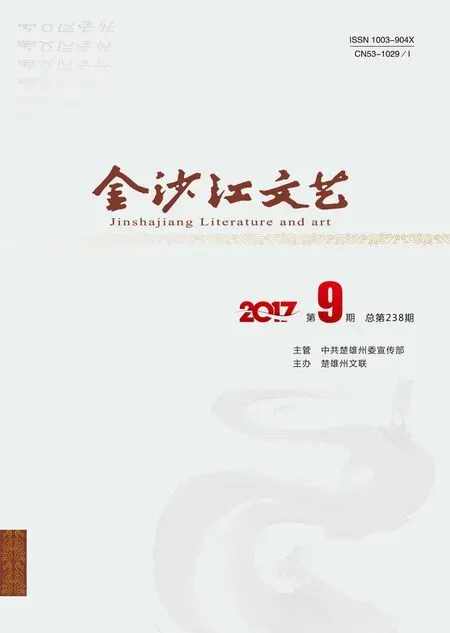苴却黉学庙四百年记
文芳聪
2016年是中国农历丙申年。这一年的冬天,修复一新的苴却黉学庙悄悄地过了自己四百周年的生日。在古代,中国人有早婚的习俗,十八九岁结婚已属晚婚,以25年为平均代际,四百年够16代人扎扎实实地走过。16代人走过的时间是多么的漫长,这时间长得让人有些发晕;但是作为永仁人,我们应该记住四百年前的那个冬天,记住那年冬天建成使用的苴却黉学庙,这是永仁教育有迹可循的起点,是永仁官办学校的开端。
一
回想遥远的过去,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被双重放逐天外。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中,当时的思想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开始了对规范人们生活新秩序的思考,造成了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像百花一样竞相绽放的崭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通过恢复周礼,开启用历史人文传统来服务时代需求的新探索,提出以“仁”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新观念,逐渐形成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黉学庙,又称孔庙、文庙,儒家思想往往通过庙学来教化、传播、普及。古地苴却远离中原,最早接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并有遗存保留到现在的就只有始建于明代的苴却黉学庙。
黉,古时对学校的称谓,也称黉序、黉校、黉门、黉宫、黉学。“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除留考城人也。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年四十,县召补史,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这是《后汉书·循吏列传》里的一段话。所谓循吏,就是 “奉公守法、注重农事、重视教育、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古代地方官吏。范晔在为循吏仇览作传时无意中把东汉时期黉学的办学特点记载了下来。据仇览后来还被报送到 “太学”深造这个历史事实来看,当时是分级办学的,黉学当属农村初级学校,所招学生为农家子弟,农忙时节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农忙结束又回到黉学庙继续学习。从中原到西南,黉学传承千余年后落脚苴却,苴却黉学庙是怎么办学的呢?1995年版的《永仁县志》对此有记载: “(黉学)招收15岁以下儿童入学,以 《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幼学琼林》《小学》《大学》《论语》等为主要教材。”
开永仁教育之先河的苴却黉学庙建成数百年来,既命途多舛而又生命力强劲,毁坏一次就有一次重修而又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彩。家住文庙街、曾任永仁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的已故教师王宗仁老先生对1952年被 “拆牌倒碑填泮池”改作粮食仓库前的苴却黉学庙原貌有过记述。苴却黉学庙背靠来凤山,面向永定河,内部结构精巧,外观庄严壮丽。布局为三进院落,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宽大,北南两厢建有两幢房屋,是旧时作为学堂供子弟读书的地方。前院有泮池,中院有大成殿,后院为崇圣祠。前院一进大门是一照壁,转过照壁就看见泮池,也称学海。泮池上有一座石拱桥,名为三沅桥。泮池周围有几排柏树和紫薇树,树身枝丫交错,相映成趣。泮池边上围有雕琢精美的石栏杆,小孩子可以在院内玩耍、嬉戏。从前院坝到中院大成殿还有二十多级台阶,台阶两边采用光滑坚硬的大石板镶嵌,小孩子可以在上面 “梭滑梯”,并不会遭到训斥。中院的大成殿是整个黉学庙最重要的建筑,殿内数十棵大柱子将大殿高高擎起,高大巍峨。大成殿为重檐歇山顶,棂星门、南庑和北庑均为单檐硬山顶,挑檐斗拱,画栋雕梁,是突出的明代建筑风格。大成殿里是供奉孔子圣贤的地方,殿内正面正中供奉的是孔子的牌位。左右两边是孔子的弟子牌位,左侧从外向内是曾子、孟子、子贡、子张等,右侧是颜回、子思、子路等。大成殿及其院心是祭孔活动的主要场所,每年祭孔大典都在这里举行,小孩子要由大人带着才可以进殿祭拜孔子。后院的崇圣祠是单檐硬山屋顶,琉璃瓦屋面,梁架结构,设格子雕花门,是黉学庙老师的住所,一般人是不可以进去的。
这样肃穆的地方,用作粮食仓库也就作罢,不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外县红卫兵来永仁搞大串联和七十年代初全县批林批孔运动中,黉学庙一再遭到破坏,里面的文物被肆意砸坏丢弃,部分建筑被任意拆建拉走,周围的土地也被蚕食和侵占,昔日规模宏大的黉学庙建筑群,只留下大成殿和南庑。又过数十年失修,使黉学庙硕果仅存的大成殿和南庑翼角残缺,椽断梁朽,脊坠墙塌,像一艘在历史长河中风雨飘摇的破船。
历史的长河太长,长得有些让人迷茫。回顾苴却,秦汉灵关道上开路先锋的喧嚣、隋唐姚巂道上商队马帮的铃声都已经从这里走远,迎面而来的是大宋王朝。宋太祖赵匡胤在平蜀将军王全斌所献的地图上沿着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这是发生在公元965年时的事情。从这以后,大宋王与大理国政治上互不信任,经贸上少有往来,从成都出发,渡过大渡河,翻越小相岭,经西昌、会理,在苴却过金沙江,前往洱海地区的这条古道冷落了。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宋史》在《大理国传》里也有 “自后不常来”的记载,明代嘉靖 《大理府志》的记载则更为决绝:“王全斌既平蜀,欲乘胜取之(大理国),以图献太祖。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兹地遂与中国绝”。元世祖忽必烈1253年1月4日破大理城后经营云南,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逐渐转移到滇池地区,从成都平原南下的那条古道在会理稍稍往东南一转,取道姜驿,过元谋坝子,翻越马头山,经武定、富民,直达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昆明。从此,“环金沙江大曲”的苴却被这条奔涌的大江阻隔,三百年时间便蛮化成大姚北界之北的 “又北界”,偏僻而荒芜。
时间又过去了三百余年,这就到了明朝万历丙辰年 (1616年)。这一年冬天,江西宁都举人出身的大姚县知县谢于教在离县城 “二百余里”的苴却建成文庙,时称姚府北界胜景,就在这一年冬天,苴却依靠黉学庙正式办起了社学。社学是旧时乡村启蒙教育,元代即有规制,明清两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社学多设于当地文庙。400年前的永仁尚未置县,苴却也不是县城,但是苴却黉学庙 “先圣牌位、门庑、池泮俱与郡邑学校同”。“先圣牌位、门庑、池泮俱与郡邑学校同”可不是胡说,这是三百四十六年前大姚知县张迎芳亲眼所见、亲笔所书。崭新的苴却黉学庙开始选任教师,于农闲时节令子弟入学,教育内容包括经史历算和各种礼仪。由此而后,山荒水远的苴却,儒家教化得以广布,圣人之道晓然边陲。
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苴却黉学庙首建告成,着实让苴却街的街坊邻里兴奋了一阵子,可惜没有文字记录,哪怕片言只语。顺治庚子年是1660年,1995版的 《永仁县志》误记为1720年。这一年是董安邦重修苴却黉学庙后的第十年,苴却黉学庙里的教书先生刘芳远请新任大姚县知县张迎芳为重修后 “大改旧观”的苴却黉学庙写篇文章,记述重建苴却黉学庙的功德,欲勒石垂久。张迎芳可是一个不畏权贵、清廉出名的人物。他是湖北应城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考中进士,十年后的1668年被任命为云南省大姚县知县。张迎芳当然知道刘芳远的意思,欣然写下了 《重修苴却社学记》。这篇碑记,史书有载,文采斐然,是苴却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难得的一篇好文章,甚至可能是永仁最早的一篇文章了。
可奇怪的是朗然屹立了三百多年的《重修苴却社学记》却在解放后不翼而飞,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不翼而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无人知晓。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关心它的去向,时间就这样静默着。
直到2012年11月15日,承建苴却黉学庙修复工程的剑川工匠史福生、史安林等在黉学庙大成殿庙正堂偏西靠后的地方偶然挖出一块石碑,上面阴文刻写的正是 《重修苴却社学记》,正好印证了这件史实。县里对这块堪称文物的石碑很重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把它原样竖立在修葺一新的苴却黉学庙大成殿前。它与在这里存在了四百年的苴却黉学庙共同见证儒家文化对苴却这块土地的浸润濡养。
二
永仁县古称苴却,先秦为古滇国属地,古老的昆明部族曾在这一代游牧。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苴却先后分属越嶲郡青蛉县、云南郡青蛉县、兴宁郡青蛉县。到了隋代,苴却为南宁州总管府辖地。自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年)开始推行科举制度到修建苴却黉学庙的明代万历丙辰年 (1616年),在这千余年时间里,未曾见到有苴却人考中举人进士的记载。这么多年可以说是苴却漫长的“天荒”年,想想千余年未曾“破天荒”也是有缘由的: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学校是文化最重要的依托,黉校不兴,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代表的举人进士从何而来。黉学庙建成后,教化苴却子弟,儒家文化遂逐渐浸润濡养这块古老的土地,富有地域特色的文治之花在这里盛开。据1995版的《永仁县志》记载:“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在苴却街建文庙,至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清廷谕令废科举,凡212年,有进士、举人、贡生近百人”。
“荒营处处埋铜鼓,野菜家家种蔓菁”,这是曾经担任过云南广南府训导的姚安人王安廷 《苴却怀古》里的诗句,是苴却一地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黉学庙建成以来,苴却一地近百名的进士、举人、贡生,经历历史的风尘,他们的生平事迹现在已经无法一一列出,但有三父子在 “荒营处处,野菜家家”的苴却确实曾经显得那么耀眼,值得一书。他们是王惟宽王嵩父子、陈铨陈干宁父子、王运开王际唐父子。
王惟宽,字子亮,号千里,幼年即入黉学,习武读经。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惟宽参加武乡试,考中庚午科第二十五名武举人,时年29岁。这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姚安军民府的缙绅为其题赠匾额达七块之多,《云南通志》载其名。王惟宽曾被误认为是姚安军民府姚州人,实为姚安军民府大姚县苴却人,七十八岁寿终,葬苴却桥头寺山。值得一提的是,王惟宽不但有武才,文采也好,曾传著有 《醉书堂诗稿》两卷,云南书院教习侯如树羡其文彩,因此在他七十大寿时率子弟前来祝寿,并送过一块题款为 “锦章寿言”的寿匾。王惟宽的婚姻也颇为传奇,他娶的是远在四川、中间隔着大凉山的嘉定州 (今乐山市)袁国政之女袁氏为妻,生儿子王暠、王嵩、王翯。王嵩也是个举人。王嵩,苴却黉学庙完成启蒙教育后,获得前往姚安府学继续学习的机会。雍正十年(1732年),王嵩参加乡试考中壬子科第三十名举人。雍正年间,王嵩接受大姚县令邀请,教读于大姚书院,正值盛年而病亡,回葬永仁县乍石村傍山,年仅四十一岁。
陈铨,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庚辰科第三十九名举人。考中举人后的次年即捐资筹建苴却桂香书院,教书育人。绝非巧合的是二十七年后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的儿子陈干宁考中丙午科第三十九名举人。时隔二十七年,陈铨陈干宁父子相继,同为第三十九名举人,苴却一地争相传颂,“人争羡之”。陈铨陈干宁父子中举之后,不愿为官,热心公益,致力于教业,史载 “苴却创建社学,捐立书院,繁荣地方文化,其父子出力最多”。史称陈铨 “品行端正,心地善良,淡于仕进”“享年甚高,尊为一乡之望”。
王运开,光绪十七年 (1891年)辛卯科举人。王际唐,王运开之子,也是光绪十七年 (1891年)辛卯科举人。王运开王际唐父子双双中举,且为同年同科举人,被称颂一时,成为苴却科举佳话。王氏家族是苴却一带的望族,王运开王际唐父子虽然同年中举,族人还是称王运开为老举人,称王际唐为小举人,以示区分,也有一点炫耀的意思。
老举人王运开,字雨初,考中举人后,曾担任过通海县教谕,任期满后回苴却讲学二十余年。他品行纯正,文风淳朴,举止风雅,能文善书,尤其是书法自成一路而很受学生欢迎。小举人王际唐志行坚卓,学识渊博,毕生主讲于苴却桂香书院、大姚日新书院、仁和义学,地方志称他“桃李盈门,誉满全邑”。
据县志记载,王际唐热心公益事业。他的一个善举是修建了羊蹄江铁索桥。那个时候,苴却境内的羊蹄江上没有桥,夏秋发大水,阻断两岸交通,往来商旅因此隔绝,影响地方经贸发展。王际唐于是首倡在羊蹄江上修桥事宜,并带头捐资,得到苴却商绅响应,连接羊蹄江两岸的铁索桥得以开工建设。不久,羊蹄江铁索桥在今天的宜就镇木马村委会黑么村民小组傍一个叫做孔雀塘上方的江面上建成通行,从此不再受洪水阻隔,商旅行人因而络绎不绝。此事很受苴却邑人称赞,时称王际唐修建羊蹄江铁索桥一事为“唐公善举”。
三
苴却黉学庙修成以后,旋即招收本地懵懂儿童入学,笔墨纸砚随之引入,文化渐成氛围。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苴却人会在笔墨纸砚的使用过程中研制出一种享誉世界的名砚——苴却砚。
在曾为苴却辖区的金沙江大峡谷南岸的悬崖峭壁中有一种石头,瓦青色,可做砚台,苴却人把它叫作砚瓦石。奇怪的是这种石头里面有厚薄均匀的带彩条带,称石标;有大小各异的眼,称石眼;有金黄色、银白色的线条镶嵌在石头里,称金线、银线,特别是有些线竟排列得像书签一般非常整齐,非常罕见,极为珍贵。当地人从金沙江南岸悬崖上采来这种石头制作墨盘、砚台,供自家子弟入学使用,因此世代相传,制砚技术日积月累而日臻完善,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销往滇川两省。这种砚台因其石质细密腻滑、莹洁滋润,而且“抚之如婴儿肌肤、扣之声音清越铿然、视之文理清秀”,特别是它研墨细腻、发墨如油而冬天历寒不冰、盛夏存墨不腐的特性,加上它特殊的石质和花纹,在云南四川两省市场上很受欢迎。这种此地仅有、别处所无的特殊砚台因采产自苴却而叫做苴却砚。
民国初年,传来要在全国各地征集物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消息,宋光枢用三方苴却砚应征参展,不久,消息传到苴却,说寸秉信为宋光枢制作的三方砚台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奖章。宋光枢何许人也?宋光枢,贵州人,曾在苴却巡检司担任过三年巡检,他在苴却为官时购买收集了一些苴却砚,获奖的三方苴却砚就是从苴却砚名家寸秉信处购得的。宋光枢把获奖消息告知制砚人,并与之共同分享获奖的喜悦,获奖消息就此在苴却传开,在苴却小城引起不小的震动。
原来,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而决定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动荡中的中国决定由农商部全权办理此事,并为此专门筹备成立了专责参赛事宜的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各省相应筹备成立巴拿马赛事会出口协会,制定章程,征集物品。参赛物品大致分为教育、工矿、农业、工艺美术等,征集范围从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甚至直到普通农民百姓,征集参展物品的时间长达数年之久。中国作为国际博览会的初次参展者,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公开露面,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一是中国参展展品总数高达10万余件,为参展各国之最;二是在那一届博览会颁发的25527个奖中,中国获奖总数在所有参展国家中排名第一。这两个第一,当时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苴却偏居一隅,所产物品获得国际大奖,“藏在深山人未识”的苴却砚自此饮誉海外。从此以后,中国的名砚中,苴却砚有了一席之地,更受文人墨客青睐。
到了当代,苴却砚名声日隆,得到方毅、范曾、黄胄等中国当代政治家、著名书画家的广泛赞誉,获得 “砚中珍品”美誉的苴却砚名声鹊起。著名书法家启功的 “中国苴却砚”题名更是让苴却砚与启功的书法相映生辉。1995年4月,乔石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出访日本、韩国时,特选苴却砚赠送日本天皇和韩国总统,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受到很高的赞誉。
获得良好声誉的苴却砚还引起了文物专家的重视,甚至考证苴却砚的前身就是在宋代文士中收到追捧的“泸石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他在文章中多次写到泸石砚,对泸石砚多有赞赏,还把泸石砚与当时的其他名砚并列。特别值得一题的是中央电视台 “艺术品投资”栏目2002年12月10日做了一期名叫 “中国苴却砚 (泸石砚)的收藏与鉴赏”的电视节目,确认苴却砚就是泸石砚。那一期电视节目的收藏鉴赏嘉宾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史树青说泸石砚在北宋时就是砚中极品,并应用 《砚笺》卷三中有“泸川石砚,黯黑受墨,视万崖、中正砦白眉”来说明宋代泸石砚在名砚中的地位非凡。“白眉”典出《三国志·马良传》。马良眉中有白毛,是马家兄弟五才俊中最有才名者,因此用 “白眉”比喻同类中的杰出代表。综合各方的论述,苴却砚就是泸石砚前身的理由有三:一是向朝廷进贡泸石砚的泸州并无产砚石的地方;二是泸石砚当时又叫泸水砚,泸州一带已是长江,不叫泸水,而流过苴却一地的金沙江古代称作泸水;三是据宋元文人记载,泸石砚质地花纹与当今苴却砚十分相近。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苴却砚不但是名砚,而且还是有来历的名砚。
随着永仁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苴却石产品也从单一的砚台向苴却石艺方向拓展,使苴却石材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现在有苴却石印章、苴却石茶盘、苴却石书桌、苴却石屏风等品目不断面世,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永仁苴却民族工艺制品厂厂长马世明甚至用自己多年研究苴却石的制石技艺研制出一套由二十一块长短不一、镂空程度不同的磬石组成的乐器——石磬,音色优美动听。
苴却黉学庙普及了地方文化,推动了苴却砚台的使用、研制、收藏;而苴却砚台的使用、研制、收藏反过来也促进了古代苴却地方文化的发展。
四
如果说石刻是历史的存根,那蕴含在里面的文化就是石刻的灵魂,而儒家文化在苴却的传播则肇始于苴却黉学庙。苴却黉学庙建成以后,选聘博雅老成之儒,教书识字,教习书法,开始培养苴却自己的文化人,文化氛围渐渐养成。此后四百余年,历代苴却文化人以石当纸、以刀为笔、以文勒石,赋予冰冷的石头以艺术的生命和历史的内涵,形成了苴却石刻。这些伫立在苴却土地上的摩崖和碑刻,展现着苴却人的生活片段,记录着苴却人的历史沧桑,最终形成独特的苴却石刻文化。它们经过历史风云的洗礼,一直存留到今天,成为记录苴却历史的重要载体。
那一方方摩崖石刻就是一处处生动的苴却景观。在地处川滇要冲的苴却古道上,从江底河、羊蹄江两岸的悬崖到金沙江边方山上的峭壁,散落的摩崖石刻闪烁着历史的光辉。至今幸存的苴却摩崖石刻有清代参将彭子祥题刻在江底河南岸铁索桥头悬崖上的 “玉龙桥”,清代大姚知县黎恂题刻在方山水头箐北岸的 “幽涧鸣泉”,民国永仁县长赵韩文、李嘉策、张渭清分别于任上题刻在方山七星桥南的 “漏天”“可以悟机” “豁我清机”,而高奣映题刻于拉列地摩崖的“容中”二字则昂然进入 《新纂云南通志》,以拓片形式存之史志。志载:“‘容中’二大字石刻,高奣映题书,高七尺广三尺”。这些优美、遒劲的汉字镌刻在一块块历经沧桑的岩石上,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见证着儒家文化对苴却的浸染与濡养。
固化历史文化的碑刻,作为历史最忠诚的见证者、记录者,它们默不作声地记录下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时刻。康熙初年高奣映写了一篇叫做 《方山说》的美文,这篇不足四百字的短文把苴却方山写得奇绝而令人神往,几本地方志都有记载,文末写有“近释一朗幕开山,题禅院名‘静德’,盖高氏其先宅,其上旧以‘静德’名,不没前人意。且碑以记之,志此山之概也”,透露出方山静德寺的一段过往。在方山静德寺里还发现了一块名为 《抚彝府方山静德寺庄田租佃公判碑》的断碑。这块断碑记录了方山静德寺曾经经历过的一件庄田官司,静德寺赢了这桩官司,刻碑勒石以记之。而判决这次官司的“抚彝府”却不见史志记载,可能是战乱时期设置于苴却而管辖四方的地方临时机构。这块断碑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很久以来,彝族就是苴却这个地方的主体民族。
还是在方山,有一块碑刻不能不提:方山赑屃碑,苴却人称方山乌龟碑,碑面上刻有 “诗文之冢”四个大家,碑下是埋藏高奣映的诗文书稿的地方,因此也有人称之为 “诗文之冢”碑。据《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记载,碑面上的“诗文之冢”四字石刻是卸任姚安土同知高奣映所书,高八尺,宽一尺八寸。民国 《姚安县志》把高奣映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思想家并列,评价甚高。高奣映在康熙十二年 (1673年)接任祖上传承下来的姚安军民府土同知,但志不在政,37岁时把土司职位交给儿子高映厚,自己常在今天的姚安结嶙山、大姚昙华山和永仁方山之间游历,著书有八十余种之多。到最后,高奣映选择方山作为他诗文书稿的埋藏之地。
墓碑石刻是古人遗留下来的珍贵资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苴却和很多地方一样,会利用墓碑的方式来记录资料,保存历史,缅怀先人,比如《进士王宪伯行述碑》就记载了康雍乾盛世时期苴却王宪伯生平和品质,以及祖孙四代的家族传承。《进士王宪伯行述碑》立碑时间是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距今二百三十五年了。如果说 《进士王宪伯行述碑》是苴却文人碑刻的代表,那武将碑刻的代表则非 《李宏开墓志铭》莫属。《李宏开墓志铭》为腾越总镇图桑额巴图鲁蒋宗汉撰。墓志记述,李宏开祖籍江南,后迁住广东,清代乾隆初年,始祖奉调随征云南,落籍腾越,今腾冲,后来移居大姚右北界。大姚右北界也称大姚又北界,即苴却。咸同年间,云南动乱,李宏开追随清末名将杨玉科部转战大半个云南,授从三品游击副将领军作战。云南平定后,李宏开离开部队,选择了山清水秀的大嘎么作为自己最后的生活之所,终老支那村。《进士王宪伯行述碑》和《李宏开墓志铭》只是苴却古墓碑中的代表。在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静卧在苴却山地上的古墓碑数以百记,它们像一个个虽逝还存的灵魂,守望着这方土地。
庙堂碑刻凸现的是苴却的 “人杰”,摩崖石刻表现的是苴却的 “地灵”,有一块为涵养水源、保护森林的碑刻则是苴却先辈倡导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这块保护水源地的护林碑刻由曹罗孙李杨高六姓人在道光七年 (1827年)合立,至今仍然在桃苴祭龙箐。在林林总总的各类碑刻中,这类碑刻并不多见,因而更显珍贵。
苴却历史悠久,四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凭借着磨制石器在这里生活繁衍,二千年前秦汉灵关道途经这里,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完成南征,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设州置县。然而,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竟找不到那个时期的一碑一刻与文献的记载来相互印证,成为遗憾,直到四百年前建成苴却黉学庙。随着苴却黉学庙的晨钟暮鼓一声声一年年悠扬地传出,文化与文明的种子也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教勃兴,斯文始盛,一通通镌刻着苴却历史的石碑,一块块题写着先贤功绩的墓志,一方方记录着文人雅士的摩崖,或端坐于庙宇寺院,或镶嵌于贤人墓壁,或刻写于名山秀水,默默地记录着苴却的历史,曾经的故事。这些苴却碑刻就是一张张苴却历史的存根,传承着文化,延续着文明,也温暖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