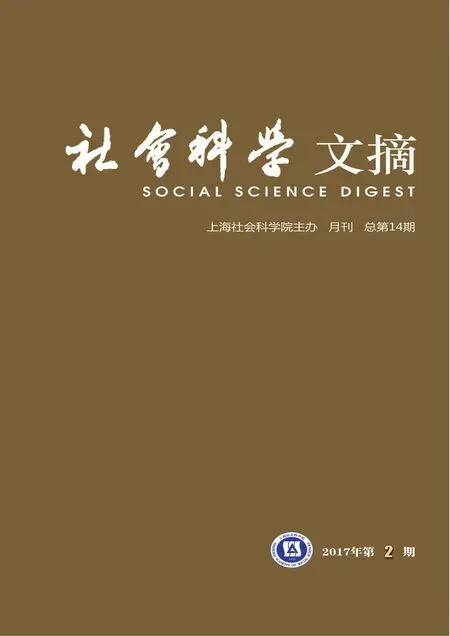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文/李春青
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文/李春青
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也可以是很简单的。就其复杂来说,我们专门用两部书的篇幅来分别探讨,也未必能够尽其义;就其简单言之,则我们可以说:文化诗学就是以文化为核心或主要研究视角的诗学,审美诗学就是以审美为核心或主要研究视角的诗学。无论哪种诗学,其研究对象都是文学现象,包括作家、文本和作品、读者、文学团体、流派以及文学思想、理论与批评实践,等等,否则便不能称之为诗学。因此这里所谓“核心”,不是指研究对象,而是指研究的视角与目的——文化诗学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目的在于揭示文学现象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审美诗学则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目的在于揭示这些文学现象所包含的审美经验及其呈现方式。正因为如此,这两种诗学也就必然地有着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与话语形态,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务,是不可能相互包容或融合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从更深层的逻辑来看,则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与文化语境而产生的两种理论形态,在思想基础、社会功能以及言说者身份等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无疑是异想天开,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简言之,如果以审美为核心,那就不可能是文化诗学;如果以文化为核心,也就不可能是审美诗学。
鉴于学界不少人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误以为把不同种类的好东西凑在一起就会成为更好的东西,故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诗学理论的差异与联系展开讨论。在下面的阐述中,我们也将对这两种诗学在中西方各自不同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轨迹予以梳理。
从哲学美学到审美诗学
审美诗学的产生是以“美学”和“文学”这两个概念获得现代意义为标志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第一次命名了这个学科,使美学成为一门与逻辑学、伦理学相并立的哲学分支。美学成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的意义在于:它使人的感性,主要是感情与感觉,作为把握美的东西的能力而受到空前关注,这是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西方认识论哲学中未曾有过的。在鲍姆加登的基础上,康德在理论上使美感或审美能力(判断力)获得普遍性并且成为一个与快感、道德感以及知性都清晰区别开来的概念,更进而揭示了其独特性及其在人的精神结构中的位置。作为康德美学的继承者,谢林美学在人类审美经验上寄托了把握或显现作为世界本体和根本动力的“绝对同一”这一神秘存在的重大企望,席勒则第一次赋予了审美以弥合人性分裂、进而改造社会的伟大价值。于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审美乌托邦被建立起来了。至于歌德、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等人,则是通过创作充满激情的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作品而对美学这个学科的独立性作出贡献的。鲍姆加登、康德和席勒等人建立起来的这门新学问是他们各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可称之为哲学美学。它致力于探讨一般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试图从根本上揭示人的审美经验的一切奥秘。在这种哲学美学之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审美诗学”——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概括那些基于康德等人的哲学美学原理而进行的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言说——诸如费歇尔父子和里普斯的移情论、谷鲁斯的内模仿说、布洛的距离说以及现象学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直至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文学批评理论,可以说都是对康德所代表的哲学美学的继承与发展。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一代一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终于把美学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审美诗学打造成一个纯美的精神世界、一座象牙之塔。在这里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绝假纯真,审美于是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自由的象征,成了现实世界的无边苦海里的诺亚方舟和这个异化的世界里人性的最后避难所。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随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人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这个美的世界。那些敏锐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了颠覆性阐释。
审美诗学与审美现代性
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再到齐格蒙特·鲍曼和吉登斯,100多年来,许多社会学家与文化理论家都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与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相伴随的现代性可以分为两大层次,一是表现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务实的”或者“功利的”的现代性,一是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超越的”或者“精神的”现代性。在这两种现代性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第一个层面的现代性,本质上是借助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而使经济生产和社会管理达到效率的最大化,这表现为一个“合理化”或者“理性化”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性理论依赖‘理性化’这一基本概念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独特性质。理性化指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技术理性的普遍化,具体说,是把计算和控制引入到一个社会的过程,并使这个社会相应地增加效率。”正是这个层面的现代性导致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的激化,也使得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产生成为必要。第二个层面的现代性,原本主要是为着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祛魅”,即清除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思想传统而产生的,故而被称为“启蒙现代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随着中世纪的梦魇渐渐被人们忘却,这种启蒙现代性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批判与反思了。如果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可以算是代表了启蒙现代性原初功能的完成,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说是启蒙现代性后一种功能的典型体现者。应该说,批判和规范其赖以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恰恰就是文化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的主要任务。
至于审美现代性则承担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作为整个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审美现代性需要对封建主义价值观进行否定与清算,这充分体现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直至批判现实主义的欧洲文学艺术之中;另一方面,审美现代性还作为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存在。这主要体现在康德以来的美学理论以及现代主义或“先锋派”的文学艺术之中。这就意味着,审美现代性肩负着双重超越的任务:既要超越封建等级观念与神学蒙昧主义的旧框框,又要超越工具理性、科层制度带来的新限制。如果说康德美学旨在弥补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的不足,席勒美学的主旨在于调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还都没有借助审美现代性来质疑和否定启蒙现代性的意图;那么到了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乃至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那面从笛卡尔到斯宾若莎、莱布尼茨、黑格尔都一直高擎着的理性主义大旗就成了反思与批判的对象。
文化诗学与后现代性
正如“审美诗学”是现代性在文艺研究领域的话语表征一样,文化诗学也是后现代性在这个领域中的现身。又正如“审美诗学”不是某种具体批评理论的专指,而是包含着所有以“审美”或“文本”“修辞”本身为中心的批评理论与方法一样;我们这里说的“文化诗学”也是广义的,不是特指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指一种研究路向。它包含着但不限于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而是可以涵盖所有基于对审美诗学的批判性反思而从外部,即社会文化、历史状况角度,审视文学艺术与审美现象的研究路向。说文化诗学与后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性,正是因为它是作为对审美诗学的反思而出现的,因此它是整个现代性反思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就是属于后现代性范畴的话语形态。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当它们面对文学发言时,它们是文化诗学;詹姆逊与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的或政治批评,当然还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都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向的文化诗学的代表性理论与方法。
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根本性差异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出:
首先,审美诗学追问“是什么”“怎么样”,而文化诗学追问“为什么”。文化诗学不满足于审美诗学把视野封闭在文本内部的做法,而是要通过文学文本介入到对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的阐释之中,所以文化诗学也可以称之为“文学文化学”。
其次,审美诗学旨在发现或建构意义,文化诗学旨在揭示对象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联。正如文化现代性的主导倾向是建立种种“宏大叙事”或云“元理论”一样,审美诗学也旨在建构一个个“审美乌托邦”。审美诗学常常把文学艺术或审美与“自由”“人的解放”“人类精神家园”“人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超越”“诗意的栖居”等现代性的元理论范畴相联系,赋予其一种伟大的意义与价值。文化诗学则不参与对这些元理论范畴的寻觅与建构,而是把它们当作可以追问、反思和质疑问题来看待。
再次,审美诗学是“照着说”,文化诗学是“接着说”。审美诗学是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东西及其表现方式的鉴赏判断,文化诗学则是关于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东西及其表现方式的反思性批判。
在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之间
如果说审美诗学是把文学观念、文本形式和审美趣味作为“所指”来加以把握,那么文化诗学就是把它们当作“能指”来展开分析。审美诗学所止步之处,恰恰是文化诗学开始之处。这就意味着,对于审美诗学,文化诗学可以采取反思、颠覆与吸收、借用两种看上去迥然不同的策略。
就反思与颠覆的一面来说,自康德、席勒以降,审美诗学建构起来的种种神话需要文化诗学重新检视。在文化诗学的视域中,那种超越历史和语境的、纯而又纯的审美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
就吸收和借用的一面来说,则可以说,来自审美诗学的文本分析方法为文化诗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例如结构主义方法就是文化诗学比较容易借用的一种文本分析方法。我们知道,结构主义并不关心一个文本传达了怎样的意义,而是关心它是用怎样的方式、依照怎样的规则来传达意义的。而且结构主义所关心的还不仅仅是个别的文本特性,而是试图揭示某类文本所共有的传达意义的方式与规则。普洛普的“叙事功能”、托多罗夫的“叙事句法”、热奈特的“元语言”以及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都是关于这种方式与规则的概括。文化诗学完全可以通过对文本构成的结构主义分析为进一步的历史化、语境化研究提供便利。换言之,借助于审美诗学文本分析的方法与技巧,文化诗学可以采取一种“循环阅读”的批评方法:首先分析文本结构等形式特征,概括出某些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因素,然后将这些文本因素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考察其生成的原因、过程以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蕴或意识形态性,而后回到文本世界,对其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诸文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定位与命名,并进而揭示整个文本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意义。
中国语境中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问题
在中国,作为现代学术的审美诗学出现于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因此,相对于延续了上千年的“文以载道”传统,审美诗学是具有某种启蒙意义与批判精神的,无论是王国维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借鉴,还是刘师培的中国式的“纯文学”主张,莫不如此。稍后,诸如周作人的“为艺术而艺术”说、宗白华的“艺术意境”说、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批评、以朱光潜和李健吾为代表的“京派批评”,等等,都是中国语境中的审美诗学,属于审美现代性范畴。20世纪80年代初期,“审美”成为一代长期饱受思想禁锢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乌托邦。让文学回归自身,不再充当政治的或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此时“审美诗学”的基本诉求。从今日文化诗学反思的立场上来看,80年代初的审美诗学正体现着知识分子寻求独立性、主体性的强烈愿望,其表面上追求纯而又纯的审美,是对康德美学的继承,但在骨子里却充满了政治性,表征着一代知识分子对话语权的争取与捍卫。此期的审美诗学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革命和激进色彩。
中国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可以说正是产生于对80年代建立起来的审美诗学的不满,这一点与西方文化诗学的产生原因相近。在“方法热”“主体性”“向内转”“文艺心理学”这些80年代审美诗学关键词相继喧嚣一时之后,文化热、寻根热出现了。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文化热或文化转向乃是中国当下文化诗学产生的现实基础。海外新儒学的大量引进与现代以来学术史的重新发掘以及相伴随的对古代经典的重视成为这一“文化热”的主要表现。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界开始形成普遍的实质性影响,中国的文化诗学从中汲取了反思、质疑与批判的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与“文化热”中形成的文化整体性关联的视野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研究路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文史哲不分的存在样态为中国文化诗学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因此中国文化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论观念的研究之中。
我们的审美诗学和文化诗学与西方学界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80年代的中国学界是审美诗学的天下,甚至当人们提到“美学”“审美”“文学”这类词语时都带有某种神圣感。而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以“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审美诗学早已式微,各种文化理论对审美诗学的“解构”已大体完成。而90年代中期以来,正当我们援引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来建构中国式的文化诗学的时候,在西方却已经开始了“理论之后”与“美学回归”的讨论。对于这种“错位”现象不能仅仅从学术影响的“时间差”角度的来解释。后现代主义学说在80年代中期已经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在当时却没有形成普遍性影响,这主要并非译介与传播的问题,根本上乃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
总之,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演变之后,在汲取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这种阐释路径以穷尽性地占有第一手研究资料为基础,以反思、质疑和重新检视一切旧有成说为手段,以梳理并呈现研究对象生成过程的复杂关联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蕴为目的。中国的文化诗学既不刻意追求边缘性的、非主流的、零零碎碎的材料,也不刻意回避对主体——无论是个体主体还是集体主体——的研究,更不刻意凸显“断裂”与“片段”,甚至不讳言“本质”与“规律”这些为后现代主义所忌讳的概念。它不预设立场与原则,不标榜解构与建构,而是在学术史的流变中提出问题,根据所能掌握的材料与重建起来的文化语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使人们对所阐释的对象产生新的理解,获得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