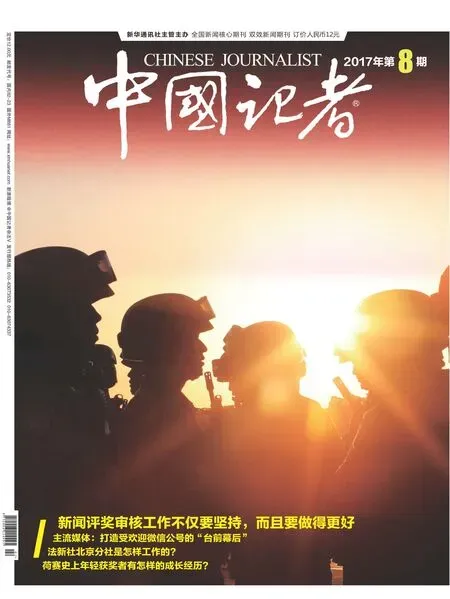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与防治策略探析
——以近年来的几起典型网络谣言为例
□ 文/宗益祥 马雅妮
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与防治策略探析
——以近年来的几起典型网络谣言为例
□ 文/宗益祥 马雅妮
本文结合近年典型案例,从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两大层面剖析网络谣言的传播心理动因。文章指出:恐慌心理、趋利心理和宣泄心理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三大个体心理动因,而理性缺失、从众心理和群体极化为代表的群体心理也与网络谣言传播存在密切联系;加强立法、信息公开和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是防治网络谣言传播的主要策略。
网络谣言 传播心理 防治策略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各类新媒体的蓬勃兴起,个体自由表达渠道不断拓展的同时,网络谣言也随之蔓延滋长。所谓网络谣言是指,“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1]本文试图从传播心理角度对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展开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关防治策略。
一、网络谣言与个体心理
(一)恐慌心理
2011年3月11日,日本突发9.0级大地震,随之引发的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紧接着国内一则有关“含碘盐防辐射”的谣言甚嚣尘上——这则谣言起初只是通过电话和短信进行小群体传播,但随后传播阵地逐渐转移到了微博上,正是新媒体的介入使得这则谣言在短短一天时间内便迅速传遍全国,接着四处弥漫的恐慌心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盐”狂潮。从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角度来看,日本核泄漏事故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认知能力范围,而在信息不确定或者不对称的紧急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自己非常有限的知识储备果断判断现实环境,因此诸如“含碘盐防辐射”这类似是而非的“安全信息”很可能成为恐慌状况下的应急之策。实际上,谣言止于科学,“其一,碘只能防止碘-131带来的危害,而放射性核物质远非只有一种碘-131;其二,即使防止碘-131的危害也需要大剂量的碘,而这恰恰又会导致对人体的其他危害,比如,引发甲亢或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2]但为何“含碘盐防辐射”这样的谣言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燎原之势?毫无疑问,新媒体的介入使得信息可以更便捷、更迅速和更广泛地进行传播,但是该案例中的个体恐慌心理才是谣言传播的根本动因。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强度(R)=重要性(I)×含糊性(A)”。[3]参照该公式,面对日本核泄漏这一重大事故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每个人都可能会心生惶恐,而当现有信息又无法及时解答人们内心的困惑之时,个体便会抓住一些含糊不明的谣言来消除不确定性,特别是当事人会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避害心理,因此谣言传播就自然形成了。可以说,个体的恐慌心理是网络谣言传播最常见的一大心理动因。
(二)趋利心理
在新媒体时代,谣言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源于一些以利益为导向的传播者有意为之。从2017年2月开始,微信朋友圈出现了大量有关“塑料紫菜”的揭露视频,拍摄者一边把紫菜泡开,一边告诉大家这不是紫菜而是塑料,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紫菜是塑料制品,视频中还有人烧焦了手里的紫菜。此视频一经传出就有相关权威部门对此进行了辟谣,但是这则网络谣言仍在短时间内对超市、经销商和种植户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后经调查,“塑料紫菜”谣言视频的制作者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谣言对一些紫菜经销商进行敲诈勒索进而牟利;同理上文提及的日本核辐射事故所导致的“抢盐”风波最初也是由一些食盐商希望利用造谣传播并从中牟利。上述案例不胜枚举,此外,类似“含氟牙膏致癌”“皮革奶粉”等网络谣言传播的背后都不乏商业推手的恶意炒作与不正当竞争,而谣言传播的根源还是一些人的趋利心理在作祟。
(三)宣泄心理
2016年春节前夕,一位自称是上海女孩的网友发帖称自己第一次去了江西农村的男友家过年,但是因一顿“难以忍受”的年夜饭便连夜赶回了上海。由于当下城乡差异和地域歧视等话题越来越牵动人们的敏感神经,因此这条网帖在短时间内便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江西网信办公开辟谣:发帖者并非上海人,而是江苏省某女网民,她因春节前与丈夫吵架,不愿去丈夫老家过年而独守家中并心生怨愤,于是便发帖宣泄一下个人情绪,而发帖内容纯属虚构。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快速发展和剧烈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复杂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使得民众很容易产生愤懑、怨恨和不满等负面情绪,的确需要寻找一种合宜的宣泄渠道。随着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的广泛普及,加之网络传播所具备的匿名性特点,人们自然选择网络作为宣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而传播谣言也成为一种释放不满情绪的“破坏形式”。
二、网络谣言与群体心理
(一)理性缺失
法国学者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曾指出:“个人一旦加入到群体,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地降低,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人”。[4]在勒庞看来,群体容易导致非理性行为,因为群体情绪容易相互感染和相互暗示,并且往往越是夸张的和煽情性的语言越容易影响群体,而那些理性之声却容易被打入冷宫。例如“山西地震”“江苏响水爆炸”“尸油煮粉”等网络谣言的“刷屏”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集体理性缺失所致。迫于环境压力以及群体之间恐慌情绪的相互感染与暗示,群体中的个体很容易丧失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进而很可能不自觉就陷入了谣言传播的强大动力机制当中。此外,正如卡普费雷所言:“传播谣言是一种容易突破社会各种禁忌的安全渠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享受一种被禁止的快乐”。[5]网络传播的较大匿名性极易导致网民的狂欢现象,而谣言则是这场狂欢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
(二)从众心理
德国学者诺依曼曾提出过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公民的自由表达并不必然形成“观念的自由市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在“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下,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6]其实,这种从众心理在网络谣言传播中也普遍存在,例如“艾滋病扎针”“滴血食物传播病毒”“小龙虾是一种处理过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来不吃”等谣言,它们看起来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是仍可以一度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而很多人传播这些谣言的动机并非因其对所见信息坚信不疑,而是其在网络信息洪流中的辨识能力实在有限,面对距离一些“似是而非”但又广泛传播的信息时,由于缺乏直接经验和相关知识,很多人便很可能屈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选择——一方面,他们更容易相信包括家人、朋友和同事等人在内的多数人的意见不大会错,另一方面,个体免去了承受沦为边缘人和少数人的外在压力。
(三)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群体的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显现。这一理论看似与上文提到的从众心理有所重合,但与之不同的是,“群体极化”理论强调的是人们在接触信息之前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某种偏见和倾向性的。在网络空间中,网民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同时也希望得到他人的赞同,故更愿意去接触一些与他们的既有倾向相符的言论,而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某个观点时,就会在论坛中形成一个讨论圈,在这样的网络小群体中,由于群体内成员的共同爱好、共同态度或者是共同情感,他们往往极易导致一种群体内部的普遍认同现象,这就容易使得原先比较平和的观点滑向极端,而网络谣言有时也由此滋生蔓延。正如美国学者桑斯坦所言:“那些已经接受了虚假谣言的人不会轻易放弃相信谣言,特别是当人们对这种信仰有着强烈的情感依赖时,谣言就更加不容易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要驱逐人们头脑中的固有想法,简直是困难之极。即使是把事实真相呈现在人们面前,他们也很难相信”。[7]
三、网络谣言与防治对策
(一)加强立法,依法管网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状况的法制意识就是要让民众明确造谣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将谣言扼杀在动心起念之间。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对网络造谣案件的定性问题给予了重要解释,并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和恐怖信息罪、寻衅滋事罪、损害商业信誉罪等《刑法》罪名予以处罚;2014年,国家又进一步出台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简称“微信十条”),其中明确要求即时通讯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确保信息真实性,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风尚。实际上,近年来的一系列网络立法已经在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和营造网络良好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就目前网络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来看,我国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依然显得比较滞后,加之我国目前仍缺乏有效针对网络谣言的处罚条例,致使一些网络造谣者仍有空可钻。因此,从根本上防治网络谣言的当务之急就是严格立法和依法管网,这要求有关部门与时俱进地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通过刚性法律进行网络谣言防治。
(二)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
英国危机管理学家里杰斯特曾提出处理公共危机的3T原则——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并且强调:在危机沟通处理上,相关机构必须做到快速说明,及时并且源源不断地发布信息。[8]根据近几年的网络谣言传播规律来看,当突发事件尤其是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人们总会利用现有信息对周遭环境进行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当官方信息匮乏之时,网络谣言便容易成为人们融解不安意识和萌生错误观念的温床。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尽可能利用黄金时间段积极公开和持续发布详细而精准的真实信息。此外,治理网络谣言,各级政府首先应当摒弃“报喜不报忧”的错误意识,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缩小网络谣言的滋生空间;其次,官方媒体应利用自身优势及时抢占舆论高地,积极发布真实动态。尽管自媒体影响巨大,但是官方媒体的丰富资源与强大公信力是自媒体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还需发挥重要的“把关人”作用,利用其强大而专业的采编队伍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据此努力从传播源头上遏制网络谣言的产生。
(三)提高媒介素养:用理性思维粉碎网络谣言
用理性思维粉碎网络谣言是公众应该具备的一项重要媒介素养。在面对诸如“绿豆汤治高血压”“生吃茄子降血脂”“紫菜是塑料袋制成的”等常识类谣言之时,公众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现有或查阅知识对其进行经验分析和逻辑推理,从而作出真伪判断;面对恐慌型谣言,公众要做到头脑冷静和理性思考,从而避免因恐慌不安导致不加思索地信谣和传谣。具体来说,媒体可以引导公众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谣言进行辨别:首先,注意消息源是否可靠,是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次,注意消息的用语风格,一般诸如医学类、科学类的信息文章用语会比较严谨和严肃,而一些披着科学外衣的网络谣言往往喜欢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情感修辞;最后,要注意是否是老帖,很多网络谣言都是新瓶装旧酒,隔一段时间就会以新形式再度作乱。总之,从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对网络谣言进行剖析也只是一种简明的分析方式,而网络谣言传播具备非常复杂的心理动因,并且它往往切中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情感共鸣和心理预期,因此防治网络谣言仅仅依靠法律性和制度性的硬手段也是不够的,最终还需要提高民众直面网络谣言时应当具备的理性辨析能力。
【注释】
[1]巢乃鹏,黄娴.网路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6)
[2]周晓虹.风险社会中的谣言、流言与恐慌[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 [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永元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20
[4] [法]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8
[5] [法]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8
[6] 郭小安.当代中国网络谣言的社会心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1
[7] [美]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9
[8] Michael Regester,Judy Larkin, Risk Issues and Crisis Managemen, Kogan Page Publishers, 2002:36
(作者分别是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本文是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本土传播心理学本体理论建设”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M013)
编 辑 文璐 wenlu@xinhu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