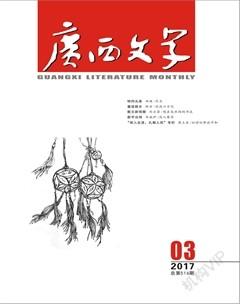隐在发丝间的河流
一
那女人身材火辣却顶着满头银丝,我假装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她的肌肤吹弹可破,我以为遇到了“天山童姥”。后来又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女人,才知道这是当下最流行的发色,名称很有趣,叫作“奶奶灰”。染这种款式的大多是自信、有个性的年轻人,要的就是巨大的反差效果。那天,站在窗口往下看,无意中发现路人发丝的颜色是如此丰富,我看着那些红的、黄的、黑的、白的……头发,它们忽然开始凝聚、缩小,变成发色卡上纽扣般镶嵌的一小团一小团的发丝,美容美发学校里的彩灯花筒忽然在眼前旋转起来,我似乎还看到了女校长那张肥胖的脸。
在那张脸的凝视下,我度过了两个月。说完这个时间,我又觉得那段时间里计时老人在打盹,让它远比两个月要漫长得多。在此之前,我每天最关注报纸和广播里的招聘热线,样子有点像等待捕鱼的饿猫。直到在嘈杂的街头,一个小小的公用电话亭里,跟女校长通了电话,才给饿猫般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女校长身高一米五,体重超出了两百斤,像个方形的肉墩。她留着板寸,头发密实,黑油油地反着光,文过的眉毛、眼线和唇线强化了五官的轮廓,看起来面露凶相。面试那天,我学生一样站在那里,不知如何安放手脚。她并不看我的简历,简单询问后,就安排我坐在她对面的座位上,然后放了一张招生广告,简单交代一下便走了。我手忙脚乱地接待咨询,在别人的追问里,一遍遍抱歉地解释:我是新来的。下班之后,我胆怯地问她,这算是录取了吗?女校长对着墙上一面大镜子一层层刷着粉底,说,不然呢?
下班时,天已经大黑。我骑着车子回住處,路灯与路灯之间正在勾勒欢快的音符,让我心情大好。我特地去市场买了两块钱的瓜子庆祝,因为馒头和咸菜根本不能表达当时喜悦的心情。
每周,我都要撰写一则招生广告,印到报纸上比火柴盒还小,变成音频发在广播里还不足半分钟。有了这些鱼饵,电话便会不断响起,时不时有人来敲办公室的门。他们大多是农村青年,刚来时,藏在父母身后,羞涩地拎着铺盖。跟我说话时,口音在普通话和家乡话之间跳跃。可是,没几天工夫,他们便脱胎换骨,头发被剪或者被烫染,拥有了看似叛逆、夸张的色彩和发式,原来的服装、鞋子顿时别扭起来。课余时间,他们去服装市场淘换廉价的衣饰,从两元店里寻找耳钉和项链。我之所以那么快地辨认出他们衣物的货色,是因为,我也是那条廉价购物街上的常客。
女校长在某个下午点评我的长发,“那么黑,那么长!”她拐着弯的腔调使这句话充满了贬义。年纪轻轻就保留一头自然生长的黑色长发,在她看来真是一种罪过。那个下午,我被拉到美发教室的讲台上,背对学生坐着,女校长一边用长梳在我后脑勺划分着区域,一边讲解头部的结构。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些部位的存在。我想到了转动的地球仪,正在被划分出陆地、山川、河谷。接着分出一个个国家、省市和乡镇,而巨大的河流涌动在我的发丝里。我第一次想到人们为什么把头发形容成黑色的瀑布。女校长抽几个学生上来,让他们尝试用各号剪子修剪。河流被剪断,变成小溪,它把内里的尖叫通过头皮传给我。面对一双双持剪刀的手,发丝的气息逐渐微弱。学生们平时用惯了塑料头模,大约忘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梳头和修剪的力道太大,把我弄疼了。但我不好意思喊疼。我假装发丝间的河流本就是死水,任他们摆弄,等到最后女校长动手时,剪子忽然心情大好,用力啃咬着头发。我想反抗,可反抗的声音一直没有发出。那种耻辱感是在多年后一点点发酵出来的。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恨不得拥有穿梭光阴之术,把那天的自己从椅子上拉起来,让发丝间的河水倒流。
台下已然是一片赞叹声,带头的是美发教师,这个一走三扭、金发齐腰的人,刚开始我真搞不清他的性别,直到看见他进了男厕。我被他们的目光沐浴,以为自己要美成天仙了,内心那点反抗的火苗瞬间被熄灭。去厕所的时候,我从门上镶的玻璃里看见一个短发的陌生人,她跟我动作如此一致,才认出那就是自己。内心的反抗在那一瞬间又回来,可我的双腿还是把自己带回了那间教室,老老实实坐回讲台上。
平时,女校长一看到食堂做饭的小许便直起脖子喊,瞧你那头发!小许的两只手便飞快地抬到胸前,准备随时护头,一边嘿嘿笑着说,那是他老妈的手艺。这天,小许正在窗外看热闹,女校长灵机一动,叫他进来。小许迟疑着,直到女校长说明让他调染发剂,并不是给他剪头发,他才大着步子走进来。小许调色的时候有点像搅鸡蛋,手腕来回用力搅动着。他在我头上一层一层地涂抹染色剂。我后来问他,是不是把我的头发当煎饼了。他只是嘿嘿笑。女校长这么做,是想说明学校有多么厉害,连做饭的师傅耳濡目染都能学几手。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问过我是否愿意剪成短发,是否愿意染色。我当时多么懦弱,一再想他们是否从我工资里扣染发费,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一個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障的人,是没有资格保护自己的头发的吧。我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情绪不过是为了保住一份工作。这样的真相,让我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就觉得嗓子眼里充满了沙粒。
我知道,小许跟我都是道具。我跟那些睁着大眼睛的塑料头模没有太大区别。后来,我明白,我甚至比不上道具,我是猴子,我模仿了他们需要的那个我。
下课时,我跟拿着剪刀的女校长保持了极为一致的表情。随后,回到办公室,她把我推到她常照的那块镜子前,赞扬了我的五官,当然重点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新发型,才能衬托出这样的五官。下班后,我骑车走在暮色里,感觉所有的风都吹向我,没有长发的遮挡,我感觉被人扒了一层皮一样。我知道隐在发丝间的河断流了,它现在变成干涸的红色山谷,像被焚烧过一般。我在心里一遍遍祈祷不要被熟人看到,在出租屋里,我故意不看镜子,好像镜子里住着鬼。
二
进美容美发学校之前,我并不知道头发和面部竟然能折腾出那么多名堂,当时流行的花生烫、陶瓷烫、玉米烫,还有什么冷烫、热烫,文眉、文唇、美容修理等项目,这些新鲜的词汇泡泡一样从我嘴里吐出来,我对其并不了解。我的工作美其名曰“校长助理”,其实也就是编编广告,接待一下学生和家长咨询。在女校长的引领下,我才知道这一切有多么简单、多么灵活,它们都可以在舌尖上延伸,连学费也不例外。用女校长的话来说,一只羊是放,两只羊也是赶,只要能把羊赶到自家圈里来,让它吃什么料,还不由自己吗?
我承认自己不是赶羊的好手,看到一个老伯拎着铺盖卷进了大门,颤抖着手从贴身的衣服里摸出几百块钱时,就不由自主想起我父亲。他身后的孩子面容羞涩,在挑选专业时犹豫不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一定得留下来,比起其他的进城方式,交钱学手艺是最为容易的一种。招生简章上说了,毕业后,会给学生安排实习,如果在那些店里表现好的话,就有机会留下来。如果有人听了这些,还犹豫不决是否要留下来的话,就为他们减免学费,从减一百开始,一直减到五百,他们总会动心的。总之,要设法缠住他们。而此后,大到头模、吹风机,小到发卡、皮筋都要让“羊”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羊毛。再者,学了美容的,也可以学习美发,学完美容美发,还可以学学摄影。全都学了的通常是些农妇,她们要回到乡村搞婚礼一条龙服务。在学校的展示区,老学长回村之后的开业典礼上就有女校长的身影。这是女校长比较得意的部分。更为得意的是她跟一些明星的合影,真假难辨。但总能让学生和家长们产生对未来的幻想。
偶尔也有毕业后的学生回来。他们的头发五颜六色,头顶上刻着些文字,或者向日葵、足球的图案。他们的性别常常跟美发教师一样,不易分辨。
在美容美发学校,太容易看到一个人外形上的变迁。这变迁是钥匙,试图开启他们通往城市的第一扇门。晚上没有课,新来的学生总是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不久之后,他们便转遍各个夜市、商场。眼睛里的羞涩渐渐退却,会对路人的衣着、发型进行点评。变化最小的是那对来自农村的中年姐妹,她们始终没有买头模,为彼此做模特时,一个人的头发烫焦了,另一个头發剪得太短了。两个人在教室里哈哈笑了好久。她俩倒很乐观,说,校长也是板寸!她们是学校里的另一种存在。
中年姐妹一下课就带个马扎跑出门。回来后,得意地说,找到头模了,还是活的!后来才知道,她们去了附近的汽车站,她俩拉着一个拎了大包小包的男人说了些什么,便让那男人坐在旁边的马扎上,开始理发。后来,人越聚越多,排起队。中年姐妹也不像往常在学校那样木讷,她们讲起自己的故乡,讲起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如果拥有理发、美容的手艺,她们就能把男人留在身边。低下头的男人不再说话,他微微笑着,脸上显出温情,似乎也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
学校也会接待一些特殊的客人。在一个单独的美容间里,墙被刷成粉红色,黯淡的灯光里氤氲着一股香气。靠里的角落摆放着一盏香熏灯,紫色的烟雾和水汽不住往外冒。女校长不时带她的闺蜜来,她们躺在美容床上,大聲闲聊,任女学生在脸上护理、描画。有时,美容床上会躺一两个男士。最常来的是一位姓李的处长,听说他就职于劳动部门,专门负责监管美容美发学校。女校长会让美容教师亲自为他服务。如果还有别人来,她便会挑班里美容手法较好的学生。当然了,容貌绝对是最好的。这时,中年姐妹就会在门口乐,一个大男人,美什么容?她们咬着耳朵叽叽嘎嘎地笑起来。
几年之后,我在另一个场合遇到李处长,他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完全不像在美容院时那般和蔼可亲。我只好假装不认识他。
三
有段时间,小许迷上摄影。一有空闲,他就借了摄影班的相机,带我出去拍照。那是早春,植物们还未苏醒,湖面不断吹来寒风。我整日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我那个季节唯一能穿出门的衣服。小许一脸感激地说,也就你愿意给我当模特。后边的话,他没说。学生们进校门不久便纷纷坠入爱河,爱情的期限大多也就在一个学期,自然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中年姐妹有几次缠着他拍照,他却委婉拒绝了。后来,一拿相机就躲着她们走。学校附近除了那片湖之外,还有一些厂子,在大门外,笨重的油桶码成一堵墙。我在它们面前,显得很纤细。小许却在一旁兴奋地说,那就是时尚。我以为那件大衣让我看来像个女巫,可等我拿到照片的时候,看到透不进光的厚墙下站立的自己,就觉得自己更像个无辜的小昆虫,红脑袋黑身子的那种。
在学校,我耳朵里奔跑得最多的词汇便是时尚,当然,还有另一个词——土气。城市是时尚的,农村是土气的;化妆是时尚的,不化妆是土气的;青年学生们是时尚的,中年姐妹是土气的;教师们是时尚的,我是土气的……为了显得时尚,有人一天只啃一个馒头,也有人连馒头都戒掉,在水龙头那里,不住往喉咙里灌水。有人隔三岔五给父母打电话,制造各种要钱的理由。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就业者。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只能说自己多么幸运。我把幸运夸大,就跟他们把生活的口子夸大一样。
有几天,女校长在办公室里计算着给初恋情人置办哪些礼品,要让他怎样办一个体面的婚礼。这时候,她是温顺的。两头猪,二十斤豆角,三十斤黄瓜……她一边写一边念叨着。她忽然抬起头问我,你想当美容教师吗?我还没有回话,她就把几本美容书摆至我面前。对于美容,我一无所知。可女校长说,那太简单了,照着书念就行了。后来,她还说了许多话,大意是:只要她愿意,谁都可以成为美容教师,跟知识、能力关系不太大。为此,她允许我一有时间就学习。
我拿着本子推开美容教室的门时,像个贼,所有人都以为我要宣布什么事情,美容教师忽闪着两片假睫毛看着我。我尴尬地一笑,从众人的目光里游过去,游到最后一排,坐定。满心忐忑地想着美容教师问我时该如何回答,我如果说,坐在这里仅是因为对美容的好奇,她会信吗?可一节课过去了,她根本没有理我。
每当女校长带着她的闺蜜在办公室里用近乎吵架的分贝大谈美容技巧和昂贵首饰的时候,我心里总翻腾着另一个声音:女人美容似乎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学会安静,比如,修炼内心。这话有点口号化,但遇到她们之后,我才发现这是真理。可我是没有资格表达观点的。她们聚集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只能待在一角,给这个倒水,给那个拿打火机,并且努力忍住随时而来的咳嗽。她们都在附近的城中村长大,几年前因为拆迁一夜暴富。她们有女校长那种文过的浓眉和眼线,常常满嘴脏话、浑身酒气。有时,故意在我面前说荤话,看我的反应。我不管做出什么样的表情都能引起阵阵狂笑。她们喜欢看一只猴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慌张,那种想模仿人却总是出丑的模样,这让她们痛快。我为什么没有转身就走,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是我许多年后才自问的。答案也很现成:比起没有钱交房租、没有钱生活的窘迫,这算得了什么?
有时,她们故意起哄,让女校长叫几个小帅哥过来坐,女校长嘴上虽然说,别祸害他们,人家还是孩子,但也时不时地让她们如愿。学生们巴不得与女校长和她的朋友亲近,期望结业后能有个好去处。
在这里,每门技艺的课程只有三个月,循环授课。结业之后的学生一部分去女校长朋友的店里实习。几个月之后,有的开了店,有的去了别处。总之,实习的人员极少留下来。不把他们开掉又有什么办法?新结业的学生该去哪里呢?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人们的脸在朦胧里开始变形,它们把我挤到门外。
四
那个午夜。城市里的喧闹被抽离,树木、建筑稳踩自己的影子,像伺机捕食的怪兽,让人恐惧。我的头发倒立着,为惊恐的心站岗。自行车轮飞快地转动着。就在十几分钟前,我接到美发教师的电话,他说,小雪喝多了,还关掉了手机,让我去看看。
小雪是美容教师的名字,但我之前从未这样叫过她。背地里,我叫她美容教师,见面时,我叫她路老师。
从一条繁华的街道进去,我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她的住处。我没想到光鲜靓丽的她会住在那样一个地方。给我开门的时候,她披头散发,假睫毛飞在颧骨上。那间屋子小而温馨,像一个装芭比娃娃的粉红盒子。进门前我先把鞋脱了。她拿着纸巾擦了擦脸,坐在床上发呆。
茶几上的啤酒瓶东倒西歪。我数了数,有六个。
初春的夜晚依旧很冷,她把被子的一角递给我,我们盖着同一条被子,在床两侧歪着。
小雪是学校的元老,刚建校时她就来了,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守。那年,女校长的情人在上海一个管件厂工作,弄伤了胳膊,她连夜跑去,学校就扔给小雪一个人。女校长的丈夫不像现在这般纵容她,三天两头来闹,朝她要人。那时,手机还未普及,所有的事儿都由小雪一个人顶着,每隔一段时间,女校长都会打来电话,让小雪汇款。她一个人又是老师,又是校长,又是会计,又是出纳,当然,还是保安。担心放钱的抽屉被撬,担心招不来学生,担心在校的学生不服管教……一个多月里除了办公室,她没出过校门。女校长从外地回来,要奖励她一千块钱,可她不要,她只要自己的那一部分,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
女校长想把小雪打造成她需要的那种人,跟有业务关系的人暧昧,在小房间里为他们服务,在酒场上与他们频频举杯。因为她听话,才成为女校长的亲信。她几乎认识女校长家所有的亲戚。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小雪跟女校长的侄子恋爱了。她没想到,女校长会第一个跳出来,把她忠诚于自己的行为当作她致命的污点。女校长教导侄子,找媳妇的重点在于:纯洁。说到这里,我终于明白女校长为何要我来接替美容教师的工作。
小雪说着人情如何虚假,世态如何炎凉,在这个以美化外形为主题的行当里隐藏着那么多见不得光的勾当。这时,仅有一墙之隔的街巷里响起油条摊搬挪东西的声音。我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看着她,没有浓妆的她看上去亲切了许多。我眼前出现了画皮的女妖,她们一层层穿上新皮,一遍遍描画,她们都有绝佳的美容素养,还有尖利的指甲……我被惊醒的时候,发现小雪的長指甲正抵在我胳膊上。
她伸着懒腰说,天亮了。
小许说过,某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跟女校长聊天,忽然停电了,他们就继续坐在那里说话。女校长描述着小雪诸多不堪。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笑得很神秘,眼角却流露出兴奋。他要求我保密,他不知道,同样的话,女校长早对我讲过。也是在那时,我明白,当一个人对你说要保密的时候,他的小喇叭就已经开播了。我看着小许描述在黑暗里与女校长说话时的一脸荣耀,不再吱声。
女校长出去吃喝玩乐时,不再带小雪,而是带上我。在饭桌上,她轻轻捅我的后背,示意我去敬酒,或者把肥厚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你当我是你姐吗?你要认我这个姐,就把这杯喝了!那些天,我总是醉着酒回家,当我顶着一头那么短的红色碎发走回出租屋时,邻居奶奶总会用看不良青年的眼神看我,她问,怎么了?我答,没事!但感觉舌头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女校长的情人我见过多次,那是个高大帅气的男人,跟女校长站在一起极不相配。他的眼睛总在发光,好像在给每一个看他的女人发射某种信号。他们常在美容间幽会,女校长示意我从外边锁上门。有次,她瘦小的老公送来一份排骨,他盯着我问,校长在哪里?我的心狂跳不止,但嘴上还是说,不知道。我想起,在许多个他打来的电话里,我都充当了欺骗他的角色。即使他碰上那个男人又能如何?我见过他宣誓主权的场面。当他们面对面走来时,他看也不看情敌一眼,把便当盒塞到女校长手里,说,老婆,早点回来。他以为当着情人的面叫她“老婆”就能把他击败,却不知道他转身离去的样子总是引来女校长的一阵嘲讽。他们在美容间待够了就会打来电话让我把门打开。我打开门,赶紧躲到办公室。等她回来,我交出钥匙,才发现因为刚才攥得太紧,手掌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好像那把钥匙在我掌心印出了一道门。那男人像来的时候一样,从后院时常锁着的一扇小门出去了。
在来学习的人群里,也有这样一部分人,她们学习美容美发就是为了保鲜自己的婚姻,要把自己调制成丈夫最喜欢的那种色调。这样的人,往往等不到结业就走了,成为女校长那些友人店里的常客。她们和女校长一起把我对婚姻的想象涂抹成无望的灰色。
女校长让我给美容班的新人指导。小雪挥着手说,来吧来吧,贡献一下肩膀。我就坐在椅子上,任她把我肩膀上的穴位指给学生们看。她不知道我正在成为她的复制品,并将替代她的存在。我为自己站在那里真正的理由心存愧疚。
在一个下午,我从美容教室回来,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女校长闺蜜的胳膊缠绕在美发教师的脖子上,急忙退身出来,但还是被她闺蜜看到了,她叫我进去。那女人让我找纸笔,又让我写下一些字,什么“上”“下”“手”之类。我红着脸看校长,以为她能给我佑护,可她却说,让你写就写!那女人手撑着脑袋,不住吐着烟圈。我写字的手在颤抖。她隔着桌子对女校长说,我看看你招的都是啥人。然后,她举着那张纸,从里边猜测我的身世和过往。我明知道那是一种羞辱,心里百般抗拒,却还是应答了她的每一句问话。中途,电话铃响了,我竟然微笑着接待了一个学生咨询。
几天后,女校长让我去美容教室,那里停放着一张床,她要我躺上去。我闭上眼睛,意识到要面对的并非化妆品,而是一排细针和一管颜料时,猛地一下弹起来。我拒绝他们为我文眼线时才终于明白,想要像小雪一样,长久地留在这个与“美”有关的场地,就必须把那些“丑”一点点吸附进身体里。我对学校里的楼道充满了恐惧。我时常盯着那个长发的模具,头发变弯、变短,颜色不断转换。到学生们毕业时,它们中的大部分被遗弃在垃圾桶里,犹如尸首。我想不明白我和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领到第二个月的工资,我便提出了辞职。女校长非常气愤,她认为我辜负了她的栽培,为此,还要回了部分工资,并且像看贼一样看着我收拾东西。走出办公室,路过美发教室,我看到学生们正举着调色盤不住搅动,调制着他们需要的颜色,而头模们都静候着。小雪正把一块清洁棉举过肩膀。饭香味在楼道里飘散,小许忽然拿着铁勺追出来,向我道别。连他自己也无法想象,半年后他会以美发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
出门后,我看到一棵刚吐絮的杨树,树冠上挂满了白的、黑的塑料垃圾。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摸着自己细碎的红色短发,路边店铺的音乐河流一样淌过耳朵。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就泪如泉涌。
作者简介:刘云芳,20世纪80年代生于山西临汾,现居河北唐山。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诗刊》《散文》《文艺报》《作品》《散文百家》《福建文学》《中国诗歌》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