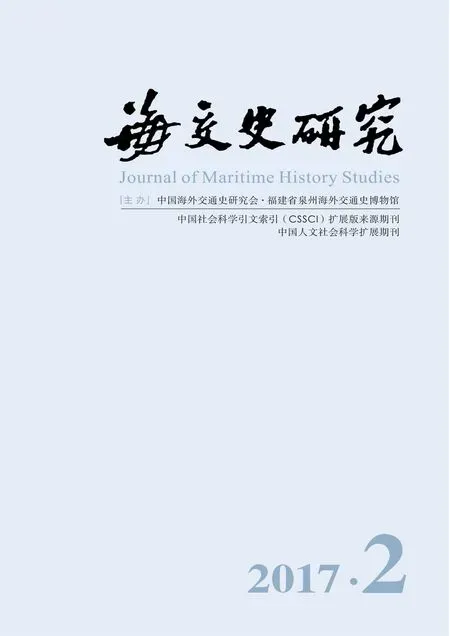泉州海神通远王源流与信仰流变新探*
谢应祥 王元林
泉州海神通远王源流与信仰流变新探*
谢应祥 王元林
泉州海神通远王史载多有抵牾。宋代灵岳祠神为崇应公、通远王,蔡襄与其封号无关。北宋末年通远王由山神向海神转变。延福寺与昭惠庙互惠互利,放弃血食祭祀成为两者结合的体现。明代九日山通远王信仰衰落,随着时空变化,其从神陈益在安海、黄志在青阳的地位隆升,甚至超过了主神。
通远王 神职 延福寺 从神
泉州港作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使与其相关的海神通远王信仰备受学界瞩目。通远王初封“崇应公”,南宋绍兴年间已是“其灵之著,为泉第一”*(宋)李邴:《水陆堂记》,见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7-578页。。灵岳祠即是其庙,后封昭惠,南宋时成为泉州官方举行祈风典礼的场所。有关通远王信仰的著述多集中于九日山市舶祈风石刻的研究,对通远王的源流缺乏关注。*方豪在详实考证九日山祈风石刻的基础上,结合宋代泉、广、琼三地以及回族祈风活动,认为祈风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且其与市舶司、泉州官方和海外交通都有着重要联系,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1201-1246页。吴文良主要考证了九日山祈风石刻中涉及的官员及相关祈风活动,认为宋代通远王信仰兴盛于市舶祈风之时,而衰落主要是政权交替和新海神——天妃的崛起使然,见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先生增订的《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06-631页。吴鸿丽则阐释了作为海神的通远王与对外海上贸易的神缘关系,见吴鸿丽:《通远王崇拜:宋元时期泉州的神缘与商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以往研究多采用明清方志记载追述与附会宋代的情况,忽视通远王信仰在宋以后的演变。本文试图从通远王信仰形成过程入手,考察其神职的演变与延福寺的关系,探求明代从神陈益、黄志地位隆升,还望方家指正。
一、张冠李戴:飞阳庙非灵岳祠、显应王非通远王
现存《宋会要辑稿》是有宋一代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虽然由于清代徐松辑佚时出现错杂混乱的情况,但并不影响该书的价值。遗憾的是,以往的通远王信仰研究鲜见使用《宋会要辑稿》中的相关记载。书中“宋会要广福王祠”条云:
广福王祠。在泉州府南安县,旧号灵岳显应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封崇应公。徽宗政和四年二月赐庙额“昭应”(笔者按:应为“昭惠”)。宣和三年九月封通远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六月封通远善利王。孝宗乾道四年正月加封通远善利广福王。*(清)徐松辑,刘琳校点:《宋会要辑稿》礼20之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58页。
神宗熙宁八年(1075)赐封崇应公前,通远王“旧号灵岳显应王”。该旧号对于考察宋廷敕封之通远王在九日山有着重要意义。泉州郡守蔡襄曾于“嘉祐三年(1058)七月……是岁春夏不雨,祈飞阳庙。明年旱,诣灵岳祠……”*(宋)蔡襄:《端明集》卷8,《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6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27页。。可见,“灵岳”并非正式赐号“崇应公”前的旧号,而是该神祠原有的庙额。宋廷一般赐给祠神的封号需遵循公、侯、王的赐号规则,朝廷正式赐封公爵之前不会出现王爵的封号。因此,该“显应王”并非通远王的封号。
实际上,“旧号灵岳显应王”应是张冠李戴,混淆了飞阳庙的显应王与灵岳祠。《宋会要辑稿》云:“(飞阳)庙在福建路泉州。真宗天禧二年五月,泉州言:‘当州有飞阳神庙。按《图经》,庙在南安县西一里。初置在晋江之南,太康五年,夜有雷电起于庙,迟明视之,其庙已移于江北之阳,故谓之飞阳庙。梁朝追封昭德王庙,乞赐封崇。’诏特封显应王。”*《宋会要辑稿》礼21之21,第1086页。可见,飞阳庙的封号由来已久,但天禧二年(1018)之后不再封赐。*(明)何乔远:《闽书》卷8,《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这与熙宁八年(1075)才首获官方赐封“崇应公”的灵岳祠神形成时间上的鲜明对比。
显应王在五代梁到北宋真宗时已是晋江著名祠神,其庙恰巧就在九日山下。因宋代南安县治在今丰州镇,而九日山“左则南安属邑”,*(宋)曾会:《重修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寺碑》,见《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中),第574-576页。即紧邻县治丰州镇的西边,而飞阳庙“按图经,庙在南安县西一里”,故两庙相近。今原址仍重建飞阳庙,紧邻九日山。*黄柏龄:《九日山志》卷3,福建:晋江地区文化局文管会, 1982年,第152页。宋人常出现官员同时或先后在二庙祈雨的事例。除前文已述蔡襄外,还有北宋熙宁三年(1070)的知州刘袭礼“因祈雨显应、灵岳二庙”,*(宋)程荀:《九日山祈雨石刻》(笔者按:原石刻无题,应为郑书作者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中),第577页。元祐元年(1086)至绍圣元年(1094)任泉州教授的郑侠也曾先后分别向崇应公和显应王祈雨。*(宋)郑侠:《西塘集》卷5,《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58-559页。因此,后世混淆了庙址相近、又常被官员先后致祭的九日山通远王和显应王。而蔡襄祈雨之“山神”应为何处山神?是明清方志记载普遍认为灵岳祠神的缘起地——永春乐山?*明清史料、方志多言通远王“盖乐山神也”,(明)黄仲昭修纂:(弘治)《八闽通志》卷59,《祠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9页,当是明清时人们的认识,并非宋时灵岳祠神。宋代永春县确有乐山*(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44页。,但鲜见有祈雨记载。*笔者仅找到时任知县的黄瑀于绍兴年间明确在永春县乐山祷雨,参见(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45,台北:鼎文书局出版,1971年,第172页。而九日山则是宋代文人骚客雅集之地,蔡襄、刘袭礼、郑侠等人当是在九日山分别向灵岳祠和飞阳庙祈雨。所以,蔡襄祈雨之山神当为九日山神而非乐山神。《宋会要》所赐封之广福王祠明确“在泉州府南安县”即是例证。故宋廷敕封通远王的诸多封号应是颁给九日山之崇应公,即日后的通远王。
有关宋代通远王的封赐,有必要加以整理明晰,现以《宋会要》相关记载为纲、辅以其它史料来勾勒出通远王受朝廷正式赐封的时间、庙额、封号和主要灵迹(参见宋代泉州通远王封赐与相关史载一览表)。其中,明显的误解是明清方志中多称蔡襄与通远王的封号有关。弘治《八闽通志》曰:“嘉定中,岁大旱,郡守蔡襄祷祠下,甘雨如注,襄以状闻,封善利王。”*《八闽通志》卷59,《祠庙》,第539页。类似的是万历《泉州府志》云:“宋嘉定中大旱,郡守蔡襄祷雨有应,以状闻,封善利王,寻加广福。”*(明)阳思谦等修纂:(万历)《泉州府志》卷2,《山川》,影印明刊本,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23页。诸如此类臆测蔡襄与通远王的封号有关的记载不在少数。史实上,蔡襄与通远王官方赐封并无关系,因为蔡襄卒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宋史》卷79,《列传·蔡襄》,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00页。而通远王赐封崇应公是八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另外,《宋会要》记载南宋朝廷赐号“善利”是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宋会要辑稿》礼20之134,第1058页。与蔡襄去世已相差近百年,蔡襄请封之事不可信。实际上,这种揣测也非空穴来风,应是源于蔡襄在嘉祐四年(1058)万安桥(即洛阳桥)建成前后曾在桥东北立有昭惠庙一事有关。“宋皇祐五年,蔡忠惠公作桥时,即创是庙,以奉兹桥香火。”*(明)王以道:《重建昭惠庙记》,见《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中),第730-731页。万安桥建成当年,蔡襄因泉州大旱曾以知州身份向灵岳祠里的山神崇应公祈雨,并将祭文保留在自己文集中。*(宋)蔡襄:《端明集》卷8,第427页。因此,后人出于抬高崇应公地位的目的,便多以此来臆测通远王的某些封号来源于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蔡襄。
随着北宋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元祐二年(1087)泉州正式设市舶管理机构,崇应公在宣和三年(1121)得以进封王爵,获得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封号“通远”。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更加注重市舶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作为海上贸易重镇的泉州地位日益凸显。海神通远王随之加封王爵“善利”“广福”,在九日山上的昭惠庙和延福寺举行祈风典礼也应运而生。

宋代泉州通远王封赐与相关史载一览表
注:《宋会要辑稿》以及其它宋代史料中未见“显济”,明代陈道远《重建昭惠庙叙》提及通远王有“显济”封号,当有附会之嫌。
二、转变融适:宋代通远王神职变化以及与佛寺关系
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郡守蔡襄因泉州大旱向灵岳祠里的山神崇应公祈雨。*(宋)蔡襄:《端明集》卷8,第427页。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通远王的最早记载,说明通远王信仰作为当地著名的祈雨灵验之山神形象在仁宗嘉祐年间以前已颇具影响。至北宋末年通远王的神职开始转变,出现了海神特征的灵迹。“以至海舟番舶,益用严恪。公尝往来于烈风怒涛间,穆穆瘁容于云表,舟或有临于艰阻者,公易危而安之,风息涛平,舟人赖之以灵者十常八九。”*(宋)王国珍:《昭惠庙记》,见《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第16页。虽然庙记语言难免夸饰,但泉郡海上船员应当普遍接受了他的海神形象,通远王由此新增了保护海船安全的海神灵迹。
通远王信仰在北宋末年传播到晋江安海*安海即今晋江县安海镇,元明时期称“安平”,在两宋及清代至今多称“安海”。,并建有行祠,王国珍和林献可均为此昭惠庙作记。安海是宋代泉州城西南的重要海上贸易兴盛的缩影,因为得到通远王的庇护,而“市虽滨于溟渤,而未尝有汛滥海涌之恐者,以(崇应)公之庙端居于右。”*(宋)王国珍:《昭惠庙记》,第16页。宣和二年(1120)作于庙之西廊的《昭惠庙献马文》曰:“……而公无不通也,无不在也,未尝有违所愿,此海滨之民,所以获建行宫焉。”*(宋)林献可:《昭惠庙献马文》,见《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第17页。作为泉州海外贸易重镇的安海,正需要通远王这样的本地海神护佑。
南宋时期通远王信仰虽仍有“农之水旱,人之疾病”*(宋)李邴:《水陆堂记》,第577页。方面的灵迹,但继续向海神方面的拓展成为主流。而绍兴年间通远王信仰与延福寺的融适值得关注。
宋代延福寺“其刹之盛,为闽第一”*同上。,名列宋代泉州乃至福建最兴盛的佛寺之列。昭惠庙于延福寺东侧建庙的原因正如王国珍所言,宋初寺院新建大殿时曾倚赖通远王顺水送木的神力。*(宋)王国珍:《昭惠庙记》,第16页。所以,当灵迹创造者们灵活地借助这则久远故事而在延福寺之侧建立灵岳祠,则是对数百年前的恩德应有的回报。这是通远王信仰流变的关键灵迹之一,为信众和僧人认可祠神庙宇与佛寺相伴而生的格局编造更合理的解释。
血食祭祀是宋代不少民间祠神与佛教的戒律之间不可忽视的冲突,这种矛盾也体现在通远王与延福寺之间。南宋绍兴年间,昭惠庙一度仍是“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戕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已而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狼藉。”*(宋)李邴:《水陆堂记》,第577-578页。这种情况与佛教云门宗所尊崇的静修和忌杀生的主张格格不入。延福寺里的慧邃禅师通过卜卦方式进行人神对话,质问通远王:“吾教以杀牲为大戒。神依佛而守焉,犹人之于家于乡者,而弗从其教,可乎?”*(宋)李邴:《水陆堂记》,第578页。在象征性的得到“神其许我矣”的卦象后,慧邃禅师向信众传达了这一结果,并顺利在祭祀通远王时推行花果水陆会。接受佛教因素的改良是宋代通远王信仰另一个关键转变,通过与佛教的相互调适,从而和谐相处,共享这一区域的信众。而慧邃禅师引导信众放弃通远王庙的杀牲祭祀方式,能否理解为让通远王祭祀活动接受佛教的仪式?*徐晓望:《宋代福建史新编》,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420页。从他在文末列举智者大师、元奎禅师降服山神的案例来看,说明他的想法并不只是仪式那么简单,应是试图仿效他们以佛法统摄、降服民间祠神通远王。*(宋)李邴:《水陆堂记》,第578页。但显然,地位日盛的通远王并未被其收服,二者关系更多还是合作与相互补益。因为延福寺也受益于昭惠庙不断出现的灵迹与官方祭祀所带来的信众和声誉,这正“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同上。的道理。宋代祈风文献中,常将昭惠庙与延福寺并列(见表1),便表明二者相得益彰的和谐关系。
南宋在昭惠庙和延福寺举行的官方祈风典礼,表明通远王信仰在泉州海外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意义。孝宗隆兴元年(1163)任职泉州市舶提举的林之奇所撰《祈风舶司祭文》,虽然没有言明在何处祈风,但表明泉州官方的祈风仪式已经出现。*(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9,《祈风文》,北京:国家图书馆,2013年,第122页。而九日山现已发现的首方祈风石刻出现在淳熙元年(1174),此后在昭惠庙前的祈风仪式已是“修岁祀”、“遵令典”的官方定制。*关于九日山祈风石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见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先生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南宋末年,知州真德秀的祈风文中不仅谈到通远王帮助官军剿灭海寇的灵迹,还表明自己来此祈风“是以国有典祀”。*(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4,《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9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96-498页。可见,通远王的神迹神职愈加丰富,地位亦愈加重要的同时,官方力量逐渐渗透。然而,在通远王信仰与官方的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反映普通民众诉求的灵迹却少见于南宋史籍。
三、主次颠倒:明清通远王从神陈益、黄志地位隆升
陪祀从神,是神灵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其地位低于主神。陈道远在明成化六年(1452)所作《重建昭惠庙叙》为迄今所见通远王出现陪祀从神的最早记载,但仅记有从神陈益。*(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见《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第79-80页。另据成书于弘治二年(1489)的《八闽通志》记载,当时的通远王已陪祀有两个从神。“(昭惠)庙之从神曰陈益,累封仁福王;曰黄志,累封辅国忠惠侯。”*《八闽通志》卷59,《祠庙》,第539页。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晋江的安平镇(即宋代的安海)祭祀着通远王和他的从神陈益,而青阳镇(今晋江市青阳街道)则同时还祭祀另一从神黄志。南宋灭亡后,通远王信仰失去官方的支持,加之元政府大力扶植的新海神——天妃的崛起,这是元明时期通远王信仰衰落的主要原因。因此,作为通远王信仰体系延续至明代所产生的具有典型性和地方特色的案例,他们在这两地的变化轨迹值得关注。实际上,通远王信仰与时俱变,两从神的出现恰是后世附会形成。
传说陈益陪祀通远王始于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经过明中期的文献修饰过后,他的身世演变成“其先东海太守陈蕃之后。五代间为官徙于泉者,是为神之曾祖”。*(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第79页。因“熙宁间,有西夏警,诏求敢勇”时,表现出色,而被郡守授予宋代鲜见的“廵辖官”之职,后随郡守祈风时“睹(昭惠)庙之灵,誓舍身为佐”。*(明)何乔远:《闽书》卷8,《方域志》,第197页。这些附会无疑都在粉饰陈益,为安平祭祀的从神陈益提供更显赫的身世。
明成化年间,从神陈益在安平已经受到高于主神通远王的礼遇。“乡人以之为父母”,“且从祀之显尤懋”*(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第79-80页。。陈道远《庙叙》仅在开头提到通远王在宋代的显赫灵迹,更多的篇幅都在介绍仁福王陈益。如此铺垫,有理由怀疑这是当时安平信众出于自身需要而改变了叙事的侧重,似乎在他们眼里陈益比通远王更亲切,因为安海的昭惠庙及“慈济宫四畔皆陈家人居”*(清)佚名:《安海志》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33辑,上海:上海书店,2013年,第525页。。此疑为亦神亦祖,为陈姓祖先崇拜进入官方祀典找到合理的外衣。
这一变化趋势在嘉靖年间更加明显。南宋以来,海外贸易兴盛的安平“自古海贼何止百千至……自后至明朝正德二年丁卯(1507)十月十三,广贼远袭,剽掠甚惨。五年庚午(1510)十月廿四,广贼又至,皆山寇也。”*(清)佚名:《安海志》卷3,第525页。这是闽粤海寇、山贼肆掠安平的记载,明代的安平在嘉靖年间曾屡受倭寇突袭,受害颇深。史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四百余,从郡境长坑头登岸,由龟湖突至安平市,杀掠数日乃去。”*(清)周学曾等纂修:(道光)《晋江县志》卷66,《烈女志》,第3659页。陈益相传在宋代熙宁年间的西夏战乱时,曾发挥“寇侵以熄”的灵迹,*(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第79页。因此安平更需要像陈益这样能护佑一方安宁的祠神。另外,陈益还是“贾行遍郡国”*(明)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儒人寿序”条,福建文史研究馆编:《福建丛书》第一辑之五,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726页。的安平商人,“商行则顶以香火”*(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第80页。的商业保护神。安平居交通要冲,国内和海外贸易均很发达,“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师、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明)何乔远撰,陈节、张家壮点校:《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70页。。明代通远王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仍是宋代官方祈风的海神,鲜见有新的重要灵迹出现,而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的主要走私港口之一,*王日根:《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以明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这也与通远王的官方海神形象背道而驰。
嘉靖三十六年(1557),时任晋江县令的卢仲佃和士绅为安平筑防倭寇之城墙时,“因为乏石,乃拆斯桥(安平东桥)之石以筑城”*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2,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48页。,试图拆毁安平桥及桥上之昭惠等庙补之。而始作俑者是倚仗本族有官宦势力的“蔡宦之兄请产废折”,甚至请来“晋江卢公督折”,恰巧当时“东塔兜居民失一男一女,连索三日不得”,昭惠庙旁东宫里的仁福王(非通远王)在民众的祈求下,显灵帮助缉凶,因此通远王和从神都得以继续被奉祀在安平桥头。*(清)佚名:《安海志》卷3,第524-525页。事实上,与其把这件事看作灵迹,这更像久居近旁的陈氏等族民众为保护昭惠庙所做的努力。相比通远王,明代依然能发挥一定灵应的从神陈益在安平更受欢迎,“是以仁福王得至今奉祀,皆显之力也”*(清)佚名:《安海志》卷3,第525页。。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安海的昭惠庙已直接易名为“仁福王宫”,*(清)柯琮璜纂修:《重修安平志》不分卷,《中国地方志集成·乡土志专辑》第33辑,第623页。从神陈益已成鸠占鹊巢之实。
无独有偶,距安平不远的晋江县青阳镇也建有通远王和从神黄(一作“王”)志的祠庙,这里的通远王及其从神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石鼓原为神庙,蔡王二家先世所建,奉福佑真君……庙之西边,仁福王……右一庙,左边奉顺正大王,俗呼本官,相传姓黄名志,本潮州人,宋孝宗丙午年九月初五日诞降,为蔡宝谟门客,掌簿籍、有道术。宁宗嘉定庚辰正月初四日化于庙……辛巳,显化助国。明永乐间,命内监三宝大人征琉球,战舰几危,永宁卒(笔者按:“永宁卒”疑指明代闽海重镇永宁卫的士兵)配神香火,显应纵火烧夷。凯奏上,神灵敕封慈济显应威烈明王顺正大王……”*(明)李伯元纂修:《青阳志》卷1,晋江图书馆藏手抄本,第33页。由此可知,黄志生活在南宋中后期,生前是蔡家门客。但其宋代的灵迹似无史料可以佐证,应是后世附会。明代,他的灵迹因与郑和出海有关,而被朝廷敕号“顺正”。但郑和征战琉球之事纯属虚构,显然是当地乡民编造的故事。当时这类传说应该比较普遍,因而在崇祯年间的《闽书》中出现相似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泉州的港口多作为政府使者往来琉球国的起止点,似乎暗合了该时代特征。由《青阳志》的这段记载可知,当地的大族蔡、王两家合力建起了最早的石鼓庙,进而不断纳入新的神祇;嘉靖年间经过当地士绅庄方塘的改造后,该庙成为主祀青阳先贤的乡约所;其间,青阳当地民众为黄志塑造并祭祀其父母神像;他还被纳入到蔡氏的家族传说中加以渲染,这些都说明了他在青阳取得了主次颠倒的地位。*(明)李伯元纂修:《青阳志》卷1,第36页。
石鼓庙的通远王以浓厚道教色彩的福佑真君、也叫福佑帝君的形象出现。庙中的福佑帝君在青阳乡间“俗呼翁爹”*同上。,而这一时期的通远王“又呼翁爹也”*《闽书》卷12,《方域志》,第284页。。明弘治以前,南安县就已有“乐山上有福佑真君祠,乡人岁以鼓乐赛祷故名”的传说。*《八闽通志》卷7,《地理》,第179页。明万历年以前永春县传说乐山上“宋有西蜀隐者居此,危坐不垂二十年,令江公望,扣梧作歌招之”。*《泉州府志》卷2,《山川》,第23页。史实上,所谓南安有“西蜀隐者”的故事,早在编撰《八闽通志》时已被发现该故事和江公望治南安一样,是源于宋代江西的南安军(治今江西省大余县),并非泉州的南安县。*《八闽通志》卷86,《拾遗》,第1420-1421页。从后世由此继续编造出相关灵迹可知,这例舶来的故事并不妨碍当地民众附会更多灵迹在通远王身上。明末以前这类传说进一步演化成“郡志‘宋有蜀圣僧,号员普,来永春乐山趺坐二十年……’绍圣二年(1095)蜕化,邑人塑像,乐山祀之,敕封福佑帝君”的传说。*(明)李伯元纂修:《青阳志》卷1,第36页。明代通远王的另一新身份——福佑帝君或真君的传说,就是这样被构建起来的。加之前述从神黄志生前“有道术”的传说,也表明了道教因素在明代已经参与到通远王形象的重塑当中。因此演变成清代传说中来自四川的福佑帝君,即俗家姓李名元溥、颇具道教色彩的通远王形象。*(民国)苏镜潭修纂:(民国)《南安县志》卷2,民国铅印本,第16页。
通过考察明代泉州安平和青阳的两个典型案例,通远王与其从神的关系演变可以发现以下特点:一方面,明代海上走私贸易一度兴盛的安海较之惠安、永春等地更能承继海神通远王信仰的内涵,成为海神通远王信仰的新中心。另一方面,安海在祭祀通远王四百余年后的明成化年间,通远王受欢迎程度已逊于从神陈益;由于从神黄志被纳入到当地蔡氏的家族传说中而更受青阳信众的青睐。因此,明代重新建构起的通远王信仰体系是从神地位高于主神的新格局,而通远王似乎又只是被陈益、黄志神化的建构者借用的有名无实的主神。但无论通远王还是他的从神,都没有出现直接与当地社会重大事件相关的关键灵迹,官方背景的缺失,促使这些庙宇多为民间祭祀。明代安海和青阳在奉祀通远王和从神时都紧邻医药神保生大帝吴夲的慈济庙,其影响力明显高于当时的通远王和从神,因此仅有的几例医疾治病的新灵迹应是从该神借鉴而来。
余 论
宋亡后,南安九日山的通远王信仰衰落,明代方志中通远王庙散见于晋江、永春或惠安诸县。除晋江外,泉州惠安的万安桥(即洛阳桥)上亦有昭惠庙*(明)莫尚简修纂:(嘉靖)《惠安县志》卷10,《丛祠》,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242页。,永春乐山广福王庙(即昭惠庙)和州治西,亦有传说建于宋大观年间(1107—1110)的昭惠庙*(明)林希元修纂:(正德)《永春县志》,卷9,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第38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917页。。晋江安海之昭惠庙分别于永乐年间两次翻修,成化六年(1470)重建。*(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第80页。而另一要地洛阳桥之昭惠庙则在嘉靖二十七(1548)、道光六年(1826)、咸丰九年(1859)三次重建。*(明)王以道:《重建昭惠庙记》,第730-731页;(清)张选青:《重修昭惠庙记》,第772-773;(清)庄志谦:《重修昭惠庙记》,第776-777页;《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中)。但已远非陈道远所说北宋政和年间朝廷赐封崇应公后,“泉之村落多立行庙”时数量之多的盛况。*(明)陈道远:《重修昭惠庙叙》,第79页。
从宋元明时期通远王信仰分布地区来看,主要分布在泉州沿海,与泉州经济、交通地理有关。在泉州海上贸易兴盛的背景下,九日山崇应公逐渐演变成海神,形成以依托州城和南安县治丰州的九日山为中心,向泉州的晋江、永春、惠安等县辐射拓展之势。青阳至安海是泉漳间的交通干道,万安桥又是泉州途经惠安前往兴化和福州的必经之路。因此,宋代海神通远王信仰分布特征是以九日山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辐射,集中于泉州港及其腹地的交通干道上。明代九日山昭惠庙废毁后,较之海上贸易不及晋江、惠安、内陆的永春乐山和晋江青阳等地,作为海神的通远王信仰在晋江安海的影响更为深入,似有在此形成新的信仰中心之势。
总之,宋代朝廷赐封之通远王正是官方祈风典礼所在地南安九日山,而非永春乐山。借助《宋会要》等史料得以厘清通远王相关封赐的时间,进而纠正名臣蔡襄请封通远王之封号“善利”这一流传近千年的误解。北宋末年通远王海神神职的出现和南宋初年昭惠庙成为官方祈风典礼所在地,都是当时泉州海外贸易兴盛的结果。九日山的延福寺与昭惠庙相伴而生的格局,以及寺里的高僧引导民众放弃血食祭祀通远王,对其信仰的流变大有助益。宋代是通远王信仰形成和蜕变为海神的重要时期,元代海神通远王信仰衰落后,其信仰中心由南安九日山转移到了晋江安平,而明代则奠定现今通远王信仰新中心和新信仰体系。同时,地方社会的嬗变导致了明代的从神陈益在安平、黄志在青阳的地位都高于主神通远王,从神的建构也更加切合当地民众信仰的需求,也是其信仰流变的主要体现。
作者谢应祥: 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广州: 510632)
王元林: 广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ongyuan King, a sea deity in Quan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Lingyue Temple honored Chongying Gong and Tongyuan King,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ferred title of Cai Xiang. Since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ngyuan King had been regarded as a sea deity instead of a mountain god. Following this integration, Yanfu Temple and Zhaohui Temple gave up offering sacrifices. At Jiuri Hill, the worship of Tongyuan King declined in the Ming Dynasty. Over time the subsidiary gods, Chen Yi in Anhai and Huang Zhi in Qingyang eventually became more important than Tongyuan King.
Tongyuan King; Deities’Functions; Yanfu Temple; Subsidiary God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7至14世纪东南沿海多元宗教、信仰教化与海疆经略研究”(项目编号:15BZS009)阶段性成果。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