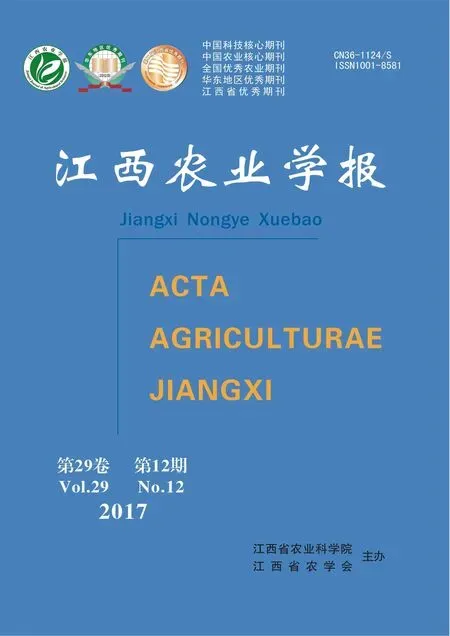有机食品消费的价值认同与地点的重新连接
肖 慧,刘风豹
(1.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有机食品消费的价值认同与地点的重新连接
肖 慧1,刘风豹2
(1.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以普朗克有机田园为例,探讨了有机食品消费活动,即有机食品消费价值认同和空间表征下对有机田园的认同建构,以及生产地和消费地重新连接的地理空间意义。研究发现,有机食品的物质、情感文化和道德消费价值,与生产空间表征共同构成空间认同的基础。有机食品消费促进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重新连接,有助于将食品消费作为关系重新连接的新载体,重新建立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促使城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在物质、文化与情感维度上的重新连接。
城乡连接;认同;有机食品;消费
0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品不仅仅是补充身体能量的物质,也是生活方式的表达[1]。食品是构建个体、组织和地方认同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工业化社会以来,快餐食品引发的肥胖率上升,食品安全及卫生问题频繁,消费者对食品失去了感知价值[2]和信任,陷入了“食品恐慌(food scare)”[3]。食品原本是人与自然连接的纽带,但是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食品系统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缺陷[4-5]。食品和地方原本以最原始的方式交缠在地理想象和我们生活的中心[6]。传统的食品往往与地方相连[7],与地方的文化和历史相关[8]。食品体现了人们对地方的情感倾向[9]。然而全球化的食品生产与消费体系,不仅断开了食品与地方的联系[10],使得食品趋向于“无地方化”[6],而且切断了消费者和地方的联系。这一断裂的状况带来社会性的反思与反击,促使人们重新眷顾地方食物与有机食品。其中,1980年代以来欧美率先掀起的有机食品热潮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将食品重新嵌入当地的社会背景下,思考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有机食品是指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的,并通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产品[5]。Buck等[11](1997)研究发现有机食品从田园到餐桌的消费过程,推动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重新连接。Holloway等(2007)强调了有机食品消费中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和生产地建立了亲密连接[2]。Fonte[13](2008)则认为食品在地化生产重新建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人际关系生产”的连接。有机食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和安全食品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生产和消费地理隔离和文化疏远[14]。它强调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认同,从时间和空间上缩短了生产和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日益重视,有机食品生产与消费应运而生。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有机食品消费国,而且增长快速。2014年我国有机食品市场规模为274.1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倍多。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城市化带来城乡距离扩大,居民的“乡愁”加剧,有机食品生产和消费带来城市和乡村的重新连接,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当下的有机食品消费正转变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不仅在于这是一种相对安全和高昂的食物消费,而且在于其主张消费者去接触和了解生产者和生产地,让消费者重获食物及食物生产的感知价值与信任。然而,国内相关研究还较为缺乏。有机食品消费与生产对居民生活、乡村发展、城乡联系带来的影响缺乏评判。为弥补这一缺失,本研究从有机食品消费的多重空间实践以及体现的价值认同入手,探讨有机食品消费带来怎样的地理重构,及其对弥合日益分离的城乡社会、空间联系的意义。
1 案例概述、数据获取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南京市普朗克有机食品公司及其消费者为研究对象。普朗克公司是江苏省有机蔬菜生产与销售产量最大的企业,于2001年开始专门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研发与销售,现已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产业链模式(图1)。目前,普朗克公司有3个有机农场,在南京拥有19家连锁专卖店、8个超市专柜和一家有机体验馆(图2)。有机农场采取的模式是“公司+农场+产业化工人”的生产组织模式。在3个农场中,本研究选择位于南京溧水区永阳镇王家店的普朗克有机田园为主要考察对象。销售端是连接消费者和生产端的关键环节,普朗克公司采取会员制模式,销售员对消费者熟悉和了解度高。因此,调查首先从南京市5家具有代表性的专卖店开始,通过与销售员和消费者的初步访谈,了解消费者的基本状况及其对有机食品消费的基本认知、行为与感受。之后,多次单独前往有机田园及附近村庄调查获取有机田园的基本资料,并跟随消费者参加普朗克公司组织的有机田园体验游,采取非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了解消费者的实践与感受,以及经营者、生产者、村民的态度与行为。受访者共40人,访谈时间长10~30 min不等。本研究的实地考察、访谈完成于2015年12月~2017年4月期间。
现代食品生产和消费的脱离,以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需求的增加,普朗克有机田园通过对空间表征的建构来建立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并促进消费价值的提升。同时,有机食品消费价值输入有机田园,也是对空间表征的认同建构。有机食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带动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一体化,不同行动者的加入也改变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空间意义。

图1 普朗克公司有机食品产销组织模式

图2 普朗克公司有机食品销售点在南京的分布
2 有机田园的空间实践、消费价值实现与认同建构
消费是现代社会个体表达和建立认同的媒介[15]。随着空间中消费转为空间的消费,空间的特征、意义与价值成为人们通过消费建构认同的重要维度[16]。在“消费同仁”的联合行为与互动中,空间认同成为个体认同的一种表达[17]。本研究力求证明有机食品消费认同不仅是一个存在于价值与观念维度的抽象过程,而且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实践。有机田园,是这一实践的重要载体,也是实践产物。有机食品生产管理者、劳作人员、消费者共同参与这一实践,有机食品消费的多维度价值实现是实践的核心。主要包括:(1)物质价值,指有机食品的天然[18-19]、健康、安全[3,20]和好口味等;(2)情感价值,指有机食品消费蕴含的对家庭成员健康的关心[21]、个人与集体记忆[22]、享乐主义和刺激[19]等;(3)道德价值,指有机食品消费所体现的“仁”和“普世主义”的象征意义[2,19,23]。
2.1物质消费价值实现与认同
有机食品消费的物质价值核心是健康与安全[24],健康和安全的价值追求,反映出整个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人自身对健康和安全的认同与需求[25]。有机田园通过塑造自身为“以人为本、与自然为善”的有机食品生产空间,来强化消费者的认同。主要体现在选址、土壤改良、执行标准的生产环境与过程空间等具体实践中,以及如何通过精心设计向消费者展示上述实践与意图。
健康的生产环境是有机食品物质消费价值创造的基础。普朗克有机田园选址远离南京市区,当地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良好,周边没有污染类工业企业,且园区初始水质、土壤、空气等环境要素较好。另外,土壤无污染、有肥力是有机食品生产的保障。普朗克田园特别将改良的方法和过程展现给消费者。让消费者获悉这里的土壤是经过自然抛荒,土地轮转至少3年,从而降低土壤中的农药残留和污染。藉此,让消费者认可这里生产的有机食品应当具有的物质消费价值。生产管理者强调不仅要严格执行生产环境的标准,如规划和平整平均地块、设置隔离缓冲带(栅栏和种植隔离带),同时还要严格控制一些动态性影响因素,如禁止劳作人员吸烟或涂抹化妆品,采用可分解的新型包装材料和手工加工、专车物流配送,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化学类合成物质、运用生态农业技术、原始人力种植和物理除虫(黄板和沼气灯)等。环境指标的高标准能够凸显有机食品在安全和健康方面的物质消费价值。通过定期带领消费者到有机田园参观体验,让消费者接触到食品生产的源头,了解各个环节,也就是掌握有机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信息和知识。消费者对安全健康的价值认同不再局限于贴在有机食品上的标签,不再停留在城市的消费端,而是建立在生产端的身体接触和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有机食品消费者通过亲身实践,通过对有机田园空间生产环境、生产方式的认同而进一步确认了对有机食品物质消费价值的认同。
2.2情感消费价值实现与认同
情感消费价值的核心主要涉及消费者的关爱、归属感、释放、记忆等方面。价值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感官与物质世界的接触,产生于发自内心的感觉、心情和状态[9]。城市消费者与有机田园接触的过程中,实现多种情感体验,表达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反思[2,24]。新鲜有机食品的现场制作,往往象征着归属感和爱的功能[8],带给人们感官上的触动,以及轻松感和幸福感[19]。普朗克公司定期组织消费者到有机田园参观体验,使得有机田园除了基本的生产功能外,还成为城市消费者暂时逃离城市、释放压力的场所。
有机田园的体验实现了唤起情感与记忆的功能。在运用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同时,保留当地传统耕作方式,使用传统生产工具,向消费者传递一种回归自然、顺应自然的价值取向,唤起有关乡村和历史的记忆。在普朗克有机田园体验时,消费者表达了他们重获童年记忆和对家乡与家人的思念[21]。
有机食品消费蕴含身份认同的建构,亲近有机田园使有机食品消费者通过消费有意义的食品寻求社会地位的认同[26]。有机食品消费者借助有机食品不仅将自己与普通食品消费者区别开来,而且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积极的形象和身份,进而在同类群体中获取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在一同游览有机田园的全程中,同类消费者之间获得充分的交流时间、空间和话题。他们交流有机食品消费的知识、经验与感觉,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记忆、参与、情绪和情感等[27]。借此,人们从分散独立的个体变成有着强烈认同的小群体,并进一步推动社会联系的建立。
食品消费能够促进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田园文化的认同、对新生活方式的表达,从而获得自我情感和认识的提升。有机田园通过知识标牌、宣传片播放硬件以及会议圆桌这些符号建构了一个知识型与交流性的文化空间,实现了有机食品情感文化价值的建构,弥补了消费者有机食品知识的空白。同时,在消费实践过程中,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消费者体验反馈,完整和丰富了消费者的情感体验,提升了对有机食品的文化情感认识。
有机田园中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从深层次体现了有机食品精神和文化的融入,从情感和文化上追求与消费者价值的共鸣,建构对有机田园的认同。尽管消费者开始注重有机食品消费情感价值的认同,但是仍然缺乏深层次的融入和诉求,在城市的范围和深度不够。
2.3道德消费价值实现与认同
道德消费价值超越了消费者基本的物质价值诉求。但是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国际国内有关环境保护观念、运动的扩展,如倡导“道德消费主义”(ethical consumerism)[28],有机食品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道德选择,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关注,对动物威胁的关注以及对人类生命威胁的关注[29]。
普朗克有机田园在有机食品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透过显像的空间环境促进消费者道德消费价值的认同。普朗克有机田园重新关注并改良土壤,视土地为生命物质和生产的根本。同时,普朗克有机田园也顺应生物生长规律,保护益生生物的自由生长,促进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保护动植物的福利。
普朗克的本地生产与消费的食品链模式,减少有机食品的“食物里程(food miles)”,减少运输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普朗克在食品消费中推动即时性的“农夫市集”,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新鲜有机食品,表达对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尊重,体现了对双方的信任,从食品消费促进社会公平。
经营者重视有机田园的土壤环境,在生产过程中保护动植物福利,将有机田园塑造成充满道德价值的空间,消费者的有机食品消费实践满足了道德消费价值的需求。对所有人和自然福利的理解、欣赏、忍受和保护,普世主义和仁慈的超越价值对有机食品消费者来说更重要[19],它不仅包括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还有更深远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德消费价值的需求,消费者重新与土壤、生物等建立联系,与当地重新连接,最终认同有机田园空间。
3 生产地与消费地的重新连接
有机食品消费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连接,消费者与生产地的连接,以及生产者与地方的重新连接,具体体现在社会关系、空间的串联与交叠以及人地关系3个方面。
3.1社会关系多元化
有机食品和有机田园的出现和兴起,在生产者(被雇佣农民)、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复杂交互的关系。(1)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建立。现代食品产销系统中,食品生产链的复杂,城市消费者与食品生产者之间的地理距离逐渐增加,相互认知不断淡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疏远甚至断裂。有机食品突出了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直接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传达了面对面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是客观的商品交易,还是一个连接。消费者开始接近他们食物的起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从陌生到熟悉,有机田园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重新建立联系的重要载体[30]。(2)生产者和经营者直接互动。有机食品经营者承包乡村土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移,部分成为生产者。生产者和经营者角色分工明确,经营者直接向生产者传授有机食品的知识和种植理念,与生产者建立了直接的互动关系。(3)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的亲密化。传统食品消费模式,消费空间的模糊化,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关系疏远。有机食品透明化的生产和产业链的缩短,消费者直接给经营者反馈消费需求,刺激经营者调整生产和经营方式。同时,消费者和经营者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增强了交易的灵活性和人性化,进一步强化了彼此的信任。(4)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去陌生化。常规食品消费下,城市消费者之间缺乏接触和交流的切入,个体与个体之间相对隔离和陌生。而有机食品消费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模式,形成了以分享和交流为特征的消费行为模式,拓展并延伸了消费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消费者参与体验有机田园,相互交流并分享对有机食品的感知和理解;同时,城市消费空间的明确界限和独特性,消费者之间的同质消费行为推动他们建立新的联系,打破城市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并基于有机食品形成了新的朋友圈,建立有机食品消费之外的延伸关系。因此,在消费者的内部建立起以有机食品消费为依托形成的小群体社会关系网。
对比传统食品,有机食品消费模式下,农民的角色和职业发生变化,成为有机田园中的职业化农民,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角色分离,职责更加明确。不同主体的加入,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多样。传统食品消费中农民、中间商和消费者之间只是单一化的关系。有机田园模式下,食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地呈现双向的流动关系,不仅体现于社会关系,还体现于双向的信息、人才、市场等。生产地和消费地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加强了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连接,进而推动城市和乡村的重新连接。
3.2空间的串联与交叠
常规食品生产消费模式下,生产地仅仅作为食品的生产空间,消费地也仅是食品消费的空间,在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地和消费地距离遥远,功能也相互独立。有机食品实行本地生产和本地消费,缩短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空间距离,同时,普朗克有机田园实行生产和消费一体化,避免第三方的介入,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关系不再被层层的中间节点所隔断,重新建立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直接联系。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的缺失,有机食品消费体验需求增长。有机田园体验主要有公司组织和消费者自发体验2种。普朗克有机田园开放化和透明化的生产,改善了当地乡村生产地的基础设施,并融入当地景观特色,优化生产地的景观,将生产地塑造为以有机食品为载体的消费空间。消费者体验到的有机田园不仅仅是有机食品的生产空间,同时也是消费空间。消费者在有机田园的即时采摘和消费,生产地兼具生产和消费的职能,既是生产地也是消费地。因此,有机食品消费推动了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重新连接,消费者在生产地的消费实践,有机田园不仅是有机食品的生产空间,同时也充当了消费者的食品消费空间。
3.3人地关系的变化
常规食品生产消费模式导致人地关系的疏远。有机食品消费改变了传统食品消费的人地关系,这里的“人”包含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地”则是生产地和消费地。(1)消费者加强和消费地的联系。现代生活节奏的快速化,消费空间的广泛化,消费空间仅仅是消费者消费物质的场所,缺乏对消费空间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消费者和消费地之间的关系不断削弱,而有机食品个性化的消费,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空间食品文化,塑造了更利于交流的平台空间。有机食品消费空间的明确化,消费者在城市消费地不仅能够直接获取所需要的物质,同时能够与经营者进行文化交流,消费地成为消费者有机食品知识和信息的获取空间,推动了消费者和消费地紧密化联系的建立。(2)生产者和生产地关系的变化。有机田园入驻前,农村集体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普朗克田园的建立,部分农民职业身份发生转变,从自由生产者变为受雇于有机田园的生产者。同时,有机食品的劳作方式和环境要素标准,生产者加强了与土地的联系,重新建立与土地直接而又紧密的联系,在经济方面与生产地建立了紧密的联系。(3)经营者和生产地关系的亲密化。有机田园的经营者负责田园土地承包和市场信息传递等,同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及时掌握生产地的各个要素信息,长驻有机田园,加强对生产地的关注。(4)消费者和生产地重新建立连接。常规食品消费下,城市消费者缺乏食品知识,仅仅通过标签得知食品的生产地,对生产地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生产地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有机食品消费体验下消费者关注有机食品的知识和内在文化价值,同时追溯至有机食品生产地,了解生产地的环境和生产过程,重新建立了与生产地的连接。城市消费端的消费者不仅实现与消费地的连接,同时在食品追溯的消费模式下,重新建立与生产地的密切联系。
总体上,有机食品消费下人地关系又呈现2个不同的趋势。(1)消费者和生产地联系的不断加强,有机食品生产地区别于一般的食品生产空间,在于它将本空间的代表性文化以一定的方式展示给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和生产地产生跨空间的人地互动。(2)在有机食品的公司组织和土地流转情况下,虽然在经济上加强了与生产地的联系,但是生产者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对生产地在情感上趋于疏离。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食品是一个特别好的镜头,可以通过它来观察人对于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与空间的态度。本研究以有机食品和有机田园的出现和兴起为背景,探究有机食品消费对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关系变化,得出以下结论。
(1)对有机田园的认同。从有机食品消费价值切入,并结合有机田园的空间表征,透过消费者的消费实践,建构消费者对有机田园的认同。物质消费价值,主要体现于选址、土壤改良、执行标准的生产环境与过程空间;情感文化消费,消费者的互动休闲,从生产者的叙述以及自我的感官上体现;道德消费价值,表现于有机田园的生态循环系统和生态保护方式。生产者主动的空间建构,有机食品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追求得以实现,建立了对生产空间的信任,产生了有机田园的空间认同。
(2)生产地和消费地重新连接下地理空间意义的改变,体现于社会关系、空间功能和人地关系。有机食品消费下的社会关系更加多元化和具体化,重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旧”关系、发展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新”关系;有机食品消费新模式的发展,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重叠,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关系重新紧密化;有机食品消费的人地关系由疏远到重新确立,以及更加具体化的联系。
4.2讨论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当代食品文化包含人与地方之间的深刻联系,有机食品文化为食品生产空间塑造提供了新的契机,成为地理空间意义变化的载体,也成为地理学者研究的关注点。地理空间意义的转变对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有机食品消费下地点的重新连接与认同建构,对目前有机食品和有机田园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加强消费价值的空间表征、有机食品文化特性的提升等。国内外的有机食品发展背景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外有机食品的兴起源于对环境问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担忧,消费者更加关注动物福利和社会发展,也即情感消费价值和道德消费价值更凸显,并且通过消费有机食品实现自己消费价值的追求。并且国内的有机食品发展模式异于国外,发展市场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国内外消费者在消费价值认知上差异较大。通过比较国内外的发展模式,对比消费价值认同的差异值得研究。同时,有机食品作为一种新型食品消费模式,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动特征,生产地和消费地重新连接的动力机制,以及如何解决有机食品地方生产和城市消费的相对空间,有机食品消费引发的城市和农村重新互动和连接等都成为新的研究关注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1] Tovey H. Food, environmentalism and rural sociology: on the organic farming movement in ireland[J]. Sociologia Ruralis, 1997, 37(1): 21-37.
[2] Honkanen P, Verplanken B, Olsen S O. Ethical values and motives driving organic food choice[J].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06, 5(5): 420-430.
[3] Torjusen H, Sangstad L, Jensen K O, et al. European consumers’ conceptions of organic food:A review of available research[M]. Osl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sumer Research, 2004: 12-15.
[4] Sarah E Lloyd. Sustainable rural system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commun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09, 7(4): 323-324.
[5] Morgan K, Murdoch J. Organic vs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knowledge, power and innovation in the food chain[J]. Geoforum, 2000, 31(2): 159-173.
[6] Feagan Robert. The place of food: mapping out the‘local’ in local food system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1): 23-42.
[7] Rebecca Sims. Food, place and authenticity: local food and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experience[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9, 17(3): 287-301.
[8] Kane, G O. A moveable feast: contemporary relational food cultures emerging from local food networks[J]. Appetite, 2016(105): 218-231.
[9] Tellström R, Gustafsson I B, Mossberg L. Consuming heritage: the use of local food culture in branding[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06, 2(2): 130-143.
[10] Harris E M. Eat local? Constructions of place in alternative food politics[J]. Geography Compass, 2010, 4(4): 355-369.
[11] Buck D, Getz C, Julie G. From farm to table: the organic vegetable commodity chain of northern California[J]. Sociologia Ruralis, 1997, 37(1): 3-20.
[12] Morris C, Kirwan J. Food commodities, geographical knowledges and the reconnec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case of naturally embedded food products[J]. Geoforum, 2010, 41(1): 131-143.
[13] Fonte M. Knowledge, food and place. A Way of producing, a Way of knowing[J]. Sociologia Ruralis, 2008, 48(3): 200-222.
[14] Clarkea N, Clokeb P, Barnettc C, et al. The spaces and ethics of organic food [J]. Rural Studies, 2008, 24(3): 219-230.
[15] 林俊帆,林耿.意义、权力与再物质化食物消费地理新进展[J].人文地理,2014(6):40-46.
[16] 陈丽晖.消费空间研究关注点的转变及其意义:兼论西方消费地理研究动态[J].世界地理研究,2010,19(1):86-93.
[17] 张敏,熊帼.基于日常生活的消费空间生产:一个消费空间的文化研究框架[J].人文地理,2013(2):38-44.
[18] 郑毅敏.有机食品的社会属性及其销售渠道建构原则研究[J].江苏商论,2009(3):42-44.
[19] Joris A, Wim V, Koen M. Personal determinants of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a review[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08, 111(10): 1140-1167.
[20] Stewart L, Kristen L, Geoffrey L, et al. Eating green: motivations behind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in Australia[J]. Sociologia Ruralis, 2002, 42(1): 23-40.
[21] Mohamad S S, Rusdi S D, Hashim N H.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onsumers:preliminary results[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130(130): 509-514.
[22] Makatouni A. What motivates consumers to buy organic food in the UK? Result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02, 104(3): 345-352.
[23] Holloway L, Kneafsey M. Reading the space of the farmers’ market: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from the UK[J]. Sociologia Ruralis, 2000, 40(3): 285-299.
[24] Jarosz L. Understanding agri-food networks as social relations[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0, 17(3): 279-283.
[25] Miele M. Consumption culture: the case of fo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2006, 166(1): 47-53.
[26] Holloway L. Virtual vegetables and adopted sheep: ethical relation, authenticity and Internet-mediated foo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J]. Area, 2002, 34(1): 70-81.
[27] Stiles K, Özlem A, Bell M. The ghosts of taste: food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1, 28(2): 225-236.
[28] Harper G C, Makatouni A. Consumer perception of 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nd farm animal welfare[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02, 104(3): 287-299.
[29] Nina M, Louise H. The role of health consciousness, food safety concern and ethical identity on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towards organic foo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08, 32(2): 163-170.
[30] 谢晓如,封丹,朱竑.对文化微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研究: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J].地理学报,2014,69(2):184-198.
(责任编辑:管珊红)
ValueRecognitionofOrganicFoodConsumptionandItsReconnectiontoLocation
XIAO Hui1, LIU Feng-bao2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Taking Planck Organic Countryside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activities of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namely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the approv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c countryside under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spatial significance of reconnecting the production place to the consumption pla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terial, emotional culture and moral consumption value of organic food, together with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production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spatial recognition.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promoted the reconne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place and consumption place, which was conducive to rebuilding the consumer’s confidence in food, and prompting the reconnections between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and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in the material, cultur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Urban and rural connection; Recognition;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K901
A
1001-8581(2017)12-0137-06
2017-07-18
肖慧(1991—),女,江苏靖江人,硕士,研究方向:城乡区域研究。